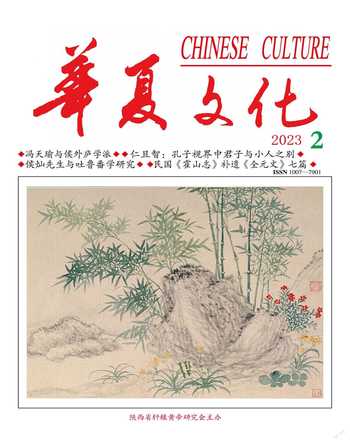《庄子》中髑髅意象
2023-07-25吴晓阳
吴晓阳
髑髅,作为人死之后所遗留的尸骨,一直被当作死亡的象征。按《说文解字》:“髑,髑髅,顶也。从骨蜀声。”髑髅应指死人的头骨。髑髅这一意象在先秦典籍中只出现在《庄子》以及《列子·天瑞》中。在《庄子》中出现了两次,均在《至乐》中。而《列子》中的内容与《庄子》中第二段大致相似。自《庄子》以降,髑髅所衍生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著名的有汉代张衡的《髑髅赋》、魏曹植的《髑髅说》、元代的道情《庄子叹骷髅》、明代王应麟杂剧《逍遥游》、清末梨园京剧《敲骨求金》以及鲁迅先生收录在《故事新编》中的《起死》一文。其中,鲁迅的《起死》相较于其余作品形式特殊、内容深邃,借用古代的故事并加入现代的元素,对《庄子》中的故事情节做了巧妙的改编,用现代主义荒诞的手法讽刺和批判了庄子以及道教思想的弊端和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起死》虽脱胎于《庄子·至乐》,但二者的主旨却大相径庭。前者是用戏剧化的手法表达对文人“唯无是非观”的批判,而后者的重心则是探讨生死问题,让人看淡生死,安时顺化。
一、鲁迅《起死》一文的内容和创作目的
《起死》被收录在鲁迅创作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该书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为基本内容,结合新的创作形式,融入现代社会和生活的元素,对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改编,借以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取舍和对国民性改造的努力。其中不乏有对勤劳、智慧、勇敢、正义等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优良品质的歌颂,如《补天》、《铸剑》、《理水》等;也有对避世、消极、虚伪、圆滑等导致中国人劣根性的糟粕的批判。对于后者,《出关》和《起死》是其中的典型。《出关》讽刺了道家和道教的始祖老子避世、“无为而无不为”的消极思想,而《起死》则展开了对道教尊奉为南华真人的庄子的批判。
鲁迅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5页)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消退之后,社会上封建复古的浪潮嚣张一时,国民党政府对外采取投降政策,对内实行残酷压迫,大搞白色恐怖,发动文化“围剿”。当时的文艺界极为混乱,逃避现实的作品不断出现:有专门描写三角恋爱的小说,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诗,还有的专门向青年推荐《老子》和《庄子》。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刻,他们企图用老子、庄子的清静无为、无是无非的思想来麻痹群众,混淆是非曲直。这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创作了《出关》和《起死》,对道家和道教思想中的糟粕展开了批判,激发人民的抗争意识,从精神上改造国民。
鲁迅对《庄子》中的情节做了改造:庄子在前往楚国的路上碰到一个髑髅,庄子用道教的起死方术请司命大天尊将其复活。髑髅是死于五百年前纣王时期的汉子,名叫杨必恭。汉子复活之后不相信庄子会起死回生的巫术,不仅不知感激,反而认为庄子偷了他的衣服和财物。庄子对汉子讲了一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大道理,无奈纠缠不过,就请司命大天尊将其性命收回,但这次法术不再灵验。汉子大骂庄子为“贼骨头”“强盗军师”,并要扒庄子的衣服。庄子别无他法,拿出警笛唤来巡士。巡士听说过“漆园吏庄周”的大名,知道自己的局长喜欢庄子的《齐物论》,因此执法中偏向庄子,庄子穿戴整齐安然离去。小说在赤身裸体的汉子与巡士的争吵与纠缠中戏剧性结尾。
庄子复活髑髅时与鬼魂的对话很有趣味,“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呀,奴才也就是主人公。我是达性命之源的,可不受你们小鬼的运动。”(《起死》)这样一种泯灭生死差异、阶级差异,无是非、无彼此对待的观点失去了其本来的面貌,完全沦落为上层统治者压榨和欺骗百姓的工具。百姓的生死都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而御用文人可以编出诸多高尚的哲理来为百姓是死是活提供理论依据。庄子在此借楚王的圣旨复活了髑髅,后面又想用同样的方法让汉子死去。普通人的生死俨然变成了上层阶级玩弄的工具。不仅如此,庄子复活髑髅所念的咒语是《千字文》的头四句和《百家姓》的头四句,再加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起死》)。这样的咒语即使是刚入学的孩童也会念。鲁迅在此深刻揭露了道教法术的欺骗性本质,同时也隐含对所谓儒家经典的至上性的消解。此外,鲁迅也辛辣地讽刺了庄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种泯灭是非彼此差异的“齐物论”思想的内在矛盾和欺骗性。汉子赤身露体向衣冠整齐的庄子要衣服遮盖时,遭到庄子拒绝,并对他大讲:“衣服是可有可无的……”(《起死》)。但当汉子扭住他不放,他就摸出警笛吹响唤来巡士驱赶汉子。庄子出场的形象是“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道冠、布袍”(《起死》),言谈举止看似庄重严肃,实则世故圆滑、自私虚伪。当他的学说和人格的虚伪全盘暴露时,便恼羞成怒,摸出警笛,唤来巡士进行镇压,露出其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的本相。
文中汉子的执拗朴实,庄子的虚伪圆滑,巡士的见风使舵无不栩栩如生,深刻地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道家思想的局限性、道教方术的欺骗性。在当时的中国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教育和引導作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笔下的庄子并不是真实的庄子形象,鲁迅笔下的庄子哲学也过于片面,有失偏颇。
二、《庄子·至乐》中的骷髅情节与形象
骷髅意象在《庄子·至乐》中出现在两个段落和故事情节中,分别是“庄子之楚见一空髑髅”,“列子行食于道见百岁髑髅”。鲁迅对《庄子》的改编主要选取了前者。
《庄子·寓言》有云:“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寓言在《庄子》一书中所占的篇幅为十分之九。所谓寓言,就是借助一些比喻性的故事来说明意味深长的道理。此处髑髅意象的使用其目的不在于叙述一个客观事实,而在于借髑髅来探讨生死问题。因此,故事的真假无须费心考究,重要的是“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庄子”(此处加引号指寓言故事中的庄子,并非真实的庄子形象)首先质问髑髅为何失去生命:“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至乐》)“庄子”所列五者除了春秋故是自然死亡,其余均是死于非命:获刑、亡国、自尽、饿毙。同时,只见头骨而不见尸骨,也暗含髑髅生前身首异处的下场。
“庄子”说毕,就拿起髑髅当作枕头睡觉。夜半,髑髅托梦于“庄子”,并对“庄子”的质问作出了回应。“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至乐》)髑髅认为“庄子”只知死之苦痛,却不知生之劳累。髑髅意在消解生死对待以及乐生恶死的世俗之见。“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从”当通“纵”,“纵然”为从容纵逸之意。在髑髅看来,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不用被生时的君臣大义、四季的冷热冻晒所扰,可以达到从容自得与天地遨游的快乐,这种快乐即使是王侯也无法比拟。有了这种快乐,即使有司命复生其形,重返闾里,与父母亲朋见面,髑髅也不愿意。“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至乐》)
可以说,髑髅所言才是《庄子》此段所要表达的主题。《至乐》所探讨的问题就是至极的快乐。《至乐》的开篇就批判世俗所沉湎的“官能之乐”而提出“至乐无乐”。最高的快乐不在于外在感官的满足,而在于内心的恬淡、安适与解脱。而解脱的关键在于对生死的看淡。“死生亦大矣”(《庄子·德充符》),常人总想着求长生,一方面追求现世的种种感官享乐,极力满足声色口腹之欲;另一方面又刻意追求着长生不死。“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庄子·齐物论》)世俗之人从一出生就与外物打交道,一直到死亡也不知道停止,整日沉溺于物质世界的名利争夺享乐之中,却让自己的心灵得不到丝毫的宁静与舒适,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
因此,《至乐》借髑髅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对外物、对生死的超脱。此则寓言的主旨并非是好死而恶生,而是向死而生,借思考死亡来让人更好地生。这里也并非完全否定亲情友情君臣之义,而是教人们如何处理好外部世界和自己内心的平衡,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
在髑髅段之上,有“庄子妻死”一则寓言。“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庄子”的妻子去世,按照常理“庄子”自然要痛苦流涕,或者至少要流露出哀戚之情。但“庄子”却蹲坐着敲着盆子唱歌。“庄子”并非不悲伤,“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至乐》)但是“庄子”深究生死之理,人的生死不过是气聚气散的大化流行,“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人之生,是气之聚,聚而有形,形而有生。人之死,是气之散,散而为死,复归于自然。因此,从天地自然运化的角度,生死太正常不过了,根本不需要悲伤。
“列子见髑髅”一则更加证明了此点。列子在道旁遇见一个百岁髑髅,拨开蓬草指着它说:“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至乐》)这里“养”,读为“恙”,《尔雅·释诂》:“恙,忧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20年,第470页)“养”为忧愁之意。髑髅既没有死也没有生,髑髅不会因死而忧愁,而列子也不会因生而快乐。髑髅无死无生的原因就在于“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至乐》),此处的“几”,《说文解字》曰:“几者,微也。”《庄子·寓言》:“万物皆种也。”“几”正是指物种最初时代的种子,一种极微小的生物。万物都是从这个本源种子出生,死后又复归于它。髑髅也是如此,生时由“几”而生,死后又复归于“几”。因此,生命并非完全消亡,只是变换了一种形态生存。万物永恒存在,不生不灭。所以没有必要为人身躯的消亡而感到悲伤,也没有必要为身躯的存在而感到高兴。人明白了大自然的运转,也就通达了生命,看淡了死生。
三、总结
髑髅这一意象自《庄子》肇端,目的是借人死后所化的髑髅来探讨生死大事,从而获得对死亡恐惧的消解以及超越生死的解脱。人作为有死的存在必定会思考死亡问题,人的现世生活有诸多舍不得,有诸多外物的牵引,因此在面临死亡之时就难以让心灵复归于宁静与安祥。《庄子》中所讲的正是一种看淡死亡的态度。世人总好生恶死,《庄子》中就反过来讲生之劳累与苦痛,死之解脱与安乐。但这绝非教人轻视生命,“夫大塊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生死都是自然的运化,生就好好活着,不为外物所累;死就安然死去,也不必有多么悲伤。
而鲁迅《起死》所批判的正是后人对《庄子》的误解。《庄子》经过道教以及民间方术的改造,其中的齐是非、一生死的思想成为了欺骗人民、麻木人民的工具。而其中对入世的消解以及所谓的“无为”与“逍遥”也成为了部分知识分子和贵族逃避现实,只管自身享乐不管百姓死活的借口。鲁迅所着眼的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糟粕部分,究出其根源,并对其展开批判。《庄子》中的思想的确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庄子》关注的重心在于个体心灵的安顿,因此非常重视精神层面的逍遥与安适,但是并不关注现实的改造与治道的建构。对于后者,荀子、墨家、法家、黄老家、纵横家等则讨论得更加深入,秦扫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乱世所依靠的正是这些思想资源。
(作者: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