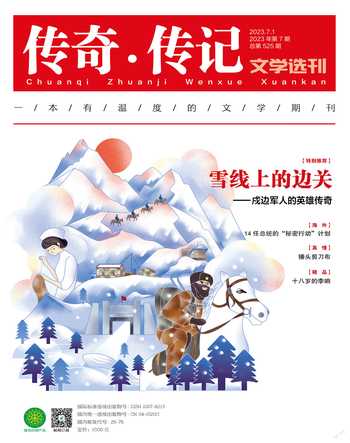治砚平生事,匠心绘大方
2023-07-18王业芬
王业芬
张硕,1966年生于安徽歙县,国家一级高级技师,中国美协敦煌创作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歙砚雕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幼深受徽派文化的熏陶,酷爱绘画,16岁师从砚雕大师方见尘。治砚40余年,张硕雕刻技法细腻深沉,挥洒自如,融工笔、写意于一炉,集诗书画于一体;砚雕作品构图磅礴大气,去繁琐求雅洁,去陈俗求清新,去浮华求浑朴,形成既含蓄沉蕴,又潇洒奔放的独有风格。
《万佛朝宗》赋传奇
对张硕和他的砚雕,歙县文联主席汪祖明有股子说不尽道不完的劲儿。尤其是谈到张硕获“山花奖”的巨型砚雕《万佛朝宗》时,汪主席的话头就像刹车失灵一般,呼啦啦直往外冲。他说:“这件作品参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时,可让我们伤透了脑筋。”
《万佛朝宗》长2.3米,宽1.8米,厚0.3米,重达6000斤,体量之大在砚雕作品中实属罕见,堪称当代歙砚雕刻之最。这样一个“巨无霸”,且圆咕隆咚的,如何才能安全运到展评现场呢?思考再三,他们还是专门给这个宝贝做了个托座,让它稳稳地端坐在上面。托座用精选大红酸枝木做成,既结实牢固,又典雅大气,与“巨无霸”的格调很搭。把这一整套珍品放到卡车上,颇费一番周折。先用大吊车把托座吊到卡车上,然后为“巨无霸”裹上厚厚的毛毡,绑上粗绳,慢慢吊到大卡车上与托座嵌合,还得专门派人全程护送,谨防运输途中出现任何损伤。一路长途奔波来到山东烟台参加初评,和来时一样首先一番吊车操作,“巨无霸”被安放到托座上之后,还需铲车来帮忙,连着托座铲起运进展厅。初评首亮相,《万佛朝宗》便艳惊四座,获得评委们的一致赞赏:“难得啊,至今没见过这么巨大且雕工这么精细的砚雕!”此后不久,《万佛朝宗》开启了在杭州的终评之旅。
有了初评的运输经验,《万佛朝宗》顺利抵达杭州,可是因为体型太大,无法运进展馆。进不了展馆,评委怎么能看到呢?这不是白来了吗?送展的一行人愁眉紧锁。汪祖明一拍大腿说:“进不去,咱就放门口,在展厅外面展览,独一份!”说着他请工作人员向评审组汇报这一特殊情况,以免漏评。尽管一切安排妥当,张硕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独一件作品放在展厅门外,万一评委忘了呢?就算没忘,孤零零一件展品跟谁比啊?评展评展,不就是各种民间艺术精品在一起比较吗!”越寻思,张硕心里越犯嘀咕,脸上渐渐愁云密布。
上午10时许,评委们信步来到展厅门外,观看这件特殊的展品。《万佛朝宗》砚面原本是浅铜色,此时在阳光的照射下透出一层淡黄的光晕,金灿夺目。评委们绕着巨砚转了一圈又一圈,不停地啧啧称赞!巨砚顶端,佛祖盘坐莲花宝座之上,面容慈祥,神情专注,双目微垂,似乎在俯观芸芸众生,禅悟世间因果。佛祖两侧往下,大小众佛一百三十余尊,烘云托日盘结于砚池四围,菩萨、罗汉、金刚等佛三五成群,形态各异,或立或卧,或昂首,或俯瞰,或打坐静修,或弘法布道……另有飞天悬舞,祥云漫卷,神兽凛然,其场景祥和、达观、丰盈,实乃佛事之洋洋大观也!此外,张硕用爨宝子书体题写的砚名和用楷体撰写的铭文,端方厚重,古朴雄浑,与砚雕主题相呼应,实乃绝妙至极!
砚面之上,纷繁的人和物,丰富庞杂的情与境,宏观场面与细微神情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精细之处,甚至每一位人物的眉眼口鼻都无一雷同。如此宏石巨制,如此精细入微,令人叹为观止。
巨砚诞生之初
多年来,张硕渴望寻得一方可心如意的大砚坯,进行一次雕刻制作的创新突破。2017年10月,婺源朱子艺苑邀请他制作一方大砚。在众多砚石中,一方巨大砚坯如磁石吸铁般牢牢锁住了张硕的目光。这方出自济源坑的鱼子石,造型自然,饱满浑厚,气势磅礴。砚面为罕见的鳝鱼黄,砚底为青色,色彩对比强烈。更难得的是,砚石纹理清晰多变、纯净均匀,肌理平整,锋棱起伏。
面对这样一方巨石,张硕心动之余,更多的是山一般的压力。第一次驾驭如此巨大的砚坯,刻什么题材、什么内容好呢?苦思冥想半个月无果。忽有一晚,辗转反侧之间,张硕思绪大开,一幅宏大的万佛朝宗的情景现于眼前。对,自己擅长佛教题材,何不以“万佛朝宗”为题进行创作!砚名一定,张硕立即投入到砚稿构思设计之中。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大量有关佛教书籍,参照宋元笔法勾画人物,先将主要人物释迦牟尼和文殊、普贤三佛像定于砚稿顶端,后循序渐进勾画众罗汉、尊者,每天埋头造像。两个月后,耗费其巨大心血的《万佛朝宗》图稿终于设计完成。
图稿设计只是第一步,接着,还要照着设计图稿在砚坯上打样。为了将设计图稿精准地对应到砚坯上,张硕几乎天天和砚坯黏在一起,有时半蹲,有时跪趴,有时俯卧,反复在砚坯上思考、描摹、刻画。每次一研究就是数小时,痴迷程度,堪比当年米芾抱石。此时恰逢秋冬交际,巨石的寒气肆意侵袭他的身体,腰腿受寒,疼痛难耐,张硕只得暂停创作,住院治疗。由于心中放不下砚坯,一周后,他匆匆出院,又开始在巨石上打样。
2018年3月,一切准备就绪,终于可以动手雕刻了!张硕带领两位爱徒张明和江翔在朱子艺苑的院子里撸起袖子干起来!师徒三人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与这方巨石“肌肤相亲”。此番雕刻不得不以“宏大工程”谓之,工作时间须以月或年计算。光阴在他们一刀、一锤、一凿的雕与刻中悄悄溜走,不知不觉已进入夏季。夏日的室外,有时烈日蒸腾,有时大雨滂沱,严重影响了雕刻进程。经商榷,他们决定将尚未完成粗坯的砚台运回歙县制作。
回到歙县后,张硕专门租下一栋房子作为工作室。幸得保定老艺术家刘岩担任艺术顾问,师弟汪海滨来做后勤服务,后来考虑到工时紧迫,张硕又邀同门师弟姜和平助力,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支紧密配合的制作团队,夜以继日地大干了11个月,终于在2019年6月5日,完成《万佛朝宗》最后一道工序。
期间,张硕请来恩师方见尘亲临指点。方大师看到如此惊人巨制,不禁为爱徒点赞。他评价这方砚台“有气宇、有气场、有气象——万千气象!确實让人眼前一亮,为之一振,确实是我们歙砚界一场幸事”。
当“山花奖”终评评委们看到《万佛朝宗》时,惊叹连连,几乎全票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视台《国家档案》摄制组,还对这样一方稀世瑰宝从选料到设计到制作全程进行详细记录,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套砚八方刻忠诚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两年前张硕就开始琢磨雕刻一组套砚献给党的百年华诞。经过再三思量,套砚最终定名为《共和国之路》。
一方小砚台要呈现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实非易事。每方砚台6个面,一套8方,共48个面。也就是说,要用48幅图案展现中国共产党100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史,选图自然成了重中之重。从石库门到瑞金到遵义到延安到北京天安门,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一桩桩重大事件、一个个重要人物,在张硕脑海里频闪、回放、锁定。经过反复酝酿,精挑细选,他最终敲定48幅雕刻图案。以第一方砚台《中共诞生》为例,砚面为“一大召开”,砚背为“党旗飘扬”,砚首为“红船领航”,砚尾为“五卅运动”,砚左侧是“五四运动”,砚右侧为“武昌起义”,6幅图案相互呼应,巧妙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因势利导,领导工农革命的生动场景与时代风貌。
在张硕艺术馆欣赏《共和国之路》时,我们无意中发现其中四方砚台边角有不同程度的缺损,遂问何故。这一问打开了艺术家的话匣子,说起那年夏季的罕见洪水,张硕依然心有余悸。
2020年夏季,套砚完成过半时,歙县遭遇5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7月7日凌晨3点多钟,张硕艺术馆的门被擂得震天响:“快撤离,快撤离,洪水来了!”张硕一骨碌爬起来,抓起手电筒直奔负一层创作室,他必须第一时间把《共和国之路》的设计底稿和雕刻成形的四方砚台抢救出来。拉开工作室电灯,水已经漫进门槛,没有袋子装,四方砚台无法带出去,怎么办?情急之下,张硕把砚台搬到桌子上。就在此时,水位呼呼往上涨,眼看已经没过小腿肚,夫人催他赶快出来,他随手抓起桌上的底稿往外冲。冲到通往地面的台阶时,他听到轰隆一声,桌子被洪水掀翻了。砚台!桌子上的砚台毁了!张硕心里一紧,像挨了狠狠一鞭子,他想返回,可是水已齐胸,完全看不见路。他退回高处,坐在水泥台阶上呆呆地望着浸泡在洪水中的工作室。直到上午10点洪水慢慢退去,他又冲进工作室,摸索着把四方砚台抱出来,每一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他的心揪成一团,仿佛能听到咔咔的碎裂声。这砚料是千里挑一挑出来的,如果损毁,很难找到纹理、色泽、宽高、长短一模一样的。他细细端详,发现只是边角有破损,如果将破损处雕刻上与整方砚台内容相吻合的图案,还是可以挽回的。
砚台可以挽回,手稿却损失了两张,也不知被大水冲往何方。砚雕的最关键环节是构图设计,有了好的设计,砚雕作品就成功了一半。套砚雕刻之前,张硕准备了1000张设计底图,每一方砚台的每一幅图案都经过反复揣摩、修改,最终从数百幅手稿中筛选出64幅作为样稿。如今,大水冲走了两幅样稿,尽管他能慢慢回忆再创作一幅,但细节上的还原还是相当困难的,毕竟设计阶段的灵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找到的。
为了积累创作素材,获得创作灵感,张硕常常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只要他提出来,夫人就立即行动。夫人吴小女是张硕背后了不起的女性。张硕毫不吝啬对夫人的夸赞:“她的砚雕手艺也特别好,当年我们在同一家砚雕厂工作,经常相互切磋技艺。”吴小女不仅是贤内助,还是张硕业务上的好帮手,《万佛朝宗》《共和国之路》等重大题材砚雕作品的打磨、上蜡等工序,她都是主要参与者。画作有“三分画七分裱”之说,砚雕亦如此,砚雕打磨分粗磨和细磨,是耗工费时的细致活儿,对专业水准要求极高。这样的细致活儿,有吴小女在,张硕很放心。
传道授业身垂范
白天雕刻,晚上书画,几乎是张硕生活中的一条铁律。他的工作、生活节奏紧凑有规律,早晚散步是每天必不可少的。我很好奇,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散步,而且每次散步时间都要一个小时以上。他说,他喜欢行走在古徽州(歙县为古徽州州府治所在地)山水田園间,尤其是走在练江两岸,水网纵横,河流交错,大脑便进入思考状态,思考这一方砚台的构图设计、人物造像,思考哪些地方需要突出,哪些地需要收隐,哪些地方平雕,哪些地方浮雕,哪些地方阳雕,哪些地方阴雕,抑或是圆雕、透雕,等等。整个散步的过程其实就是大脑创作思考的过程,也是大脑排空的过程。排空是排除其他一切与艺术创作无关的东西,此时,犹如在佛堂参禅打坐,心无杂念。思考中,若有人迎面和他打招呼,他便条件反射地应一声,却往往不记得来者是谁,有时候竟然对熟人“视而不见”。他说这种“毛病”很讨厌,会得罪人,他想改,但每次一进入思考状态就忘了前车之鉴。
说起师傅的执着钻研精神,张硕的两位徒弟都万分钦佩。徒弟张明说:“师傅对自己严格要求,每晚要么作画,要么写书法,雷打不动,让我钦佩不已。可以说砚雕界像我师傅这么有毅力的,几乎没有。”徒弟江翔说:“师傅数十年如一日,对砚雕及书画艺术的热爱和钻研,深深影响着我,使我不敢有一丝懈怠。师傅这么努力,作为徒弟,不学习我都觉得愧疚。”
张硕就是这样,以自己的钻研和敬业精神,对两位徒弟潜移默化地感染和熏陶,使他们人格渐渐成熟,技艺日趋精练。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所云:“教诲是条漫长的道路,榜样是条捷径。”张硕凡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很少批评、指责。问到师傅严不严,两位徒弟都不约而同地说:“师傅对我们如兄弟、似朋友。”其实,对徒弟的要求,张硕不可谓不严。只不过,这种严不是言辞上的犀利,也不是行动上的桎梏,而是质量上的高标准。用大徒弟张明的话说:“师傅授业时严格要求,但又极耐心。特别是我有时制砚没注意,做错了,他不怒不骂,总是想办法力挽狂澜。”
张硕很赏识两位徒弟,针对不同砚坯的制作选题,常与他们商量,博采他们的意见。他说:“年轻人头脑活,思想现代,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张硕没有看错,两位徒弟的确很出众,如今二人都已成为安徽歙砚雕刻界小有名气的青年新秀。他们的作品都曾获得歙县文学艺术奖、工艺美术类一等奖,并在安徽省以及国家相关赛事中获奖。
汪祖明说,张硕大师最难得之处是,除了自己的徒弟以外,别人来请教,他也会毫无保留,耐心讲解,甚至别人请他指点画制砚稿,只要有时间,他都欣然出手。我想,这种对艺术开明开放的心态,对年轻人关心培育的大爱与情怀,恐怕只有大师级别的人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