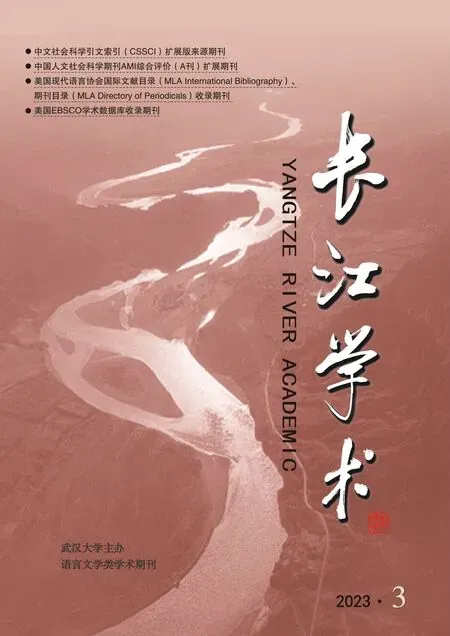维柯与赫尔德:一种奥尔巴赫式的关联
2023-07-12张辉
张辉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赫尔德:维柯的舞台布景?


作为一个以文学批评、罗曼语文学和比较文学名世的学者——一个文学研究者,在如今过于专业化乃至狭隘化的学术氛围中,奥尔巴赫的上述作为,或会显得格外逸出“专业规范”。而更出乎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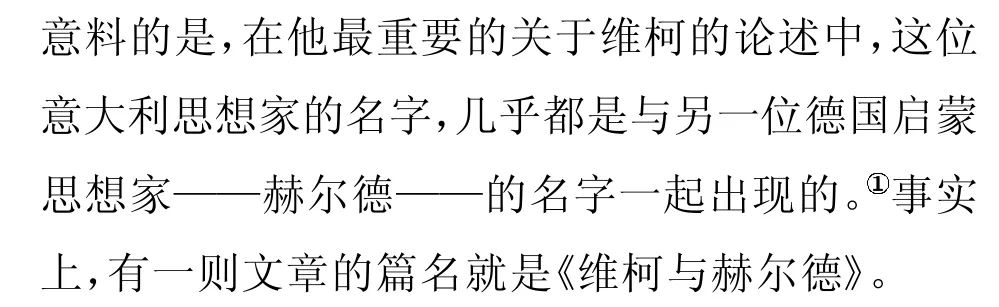
维柯逝世那年,赫尔德(1744—1803)才出生,他们不仅来自不同国别,分属两个历史时代,而且具有非常不同的政治、文化身份乃至学科背景。加之,奥尔巴赫自己也知道,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显示,赫尔德生前提及过维柯的名字,更不要说读过他的著作。(THL,p39;p47)为什么要将两个似乎并不相干的人相提并论?而且一再地并列在一起?
奥尔巴赫这样做,无疑并非率意为之。且看他自己如何表述。
奥尔巴赫将二者关联起来的最早一篇文献,是前述发表于1932 年的《维柯与赫尔德》。那实际上是他1931 年在位于科隆的德国-意大利研究所(Germany-Italian Research Institute)所作的演说。演说稿从历史问题如何日益成为现代人文学的中心入手,主要讨论维柯独树一帜的思想构成,尤其是维柯对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所做的划分。但在进入对维柯的细致讨论之前,奥尔巴赫却首先切入了对赫尔德的介绍,并指出,赫尔德乃是从现代学术意义上将历史观念加以系统化的第一人。奥尔巴赫有两个重要判断。首先,作为一个现代学术与思想事件,将历史视为一种内在而有意义的总体(an immanent and meaningful totality),而非无足轻重的一系列事件的叠加与交织,乃是基督教在精神-思想史上失去中心位置之后的事情,从此,是人的历史以及人对自己历史的理解和解释,而非神圣天意,才是意义和价值的来源。其次,这一思想事件主要发生在英国和德国、且在德国获得最大成功。不过,德国历史主义虽然是时至1760 年代才真正自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发端,并最终在黑格尔那里登峰造极的,但以历史主义的方式看待历史,“这种理解却首先获益于赫尔德的方法”(THL, p13)。在历史主义的谱系中,赫尔德举足轻重。

以一个后出的思想家作为前辈思想家的背景,这与其说是把赫尔德作为背景,不如说是让维柯这个先行者与赫尔德形成对照。究竟二者有什么不同,需要以这样“反常”的方式加以对照,后文再表。这里,我们且看看奥尔巴赫还提供了哪些将二者连接起来的理由。
我们来看第二篇。这篇发表于1949 年的《维柯与审美历史主义》,是奥尔巴赫1948 年5 月1 号在位于麻省剑桥的美国美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所发表的讲演。此文距发表《维柯与赫尔德》已有近20 年,即使距1936 年发表《维柯与语文学观念》也有10 多年。但奥尔巴赫的基本思想却并未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尽管篇名上并没有将维柯与赫尔德并提,赫尔德的名字却依旧赫然出现在这篇关于维柯的文章中,这一次是与“狂飙突进”、与歌德一起出现的。

只是这一次所讨论的问题,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general historicism),而是更进一步:审美历史主义(aesthetic historicism)。在奥尔巴赫看来,后者乃是前者的先导,这甚至格外凸显了赫尔德的重要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话题转化了,运思的逻辑却与《维柯与赫尔德》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讲述完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审美历史主义与基督教意义上审美教条主义(aesthetic dogmatism)的深刻区别之后,作为中心人物的维柯才姗姗来迟。也就是说,启蒙与基督教的对峙,依然还是引入维柯的思想史原因之所在。但这一回,由赫尔德转入维柯,在行文上显得更加突然甚至竣急,连奥尔巴赫自己也用了“令人吃惊”这个字眼。他说:
事到如今,这是思想史上最为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非常类似的诸原则(辉按:指审美历史主义的诸原则)在前浪漫派那里呈现之先的近半个世纪,就已经由一位年迈的那不勒斯学者——维柯——在他的《新科学》(该书初次亮相于1725 年)中酝酿并发表了出来。此人对50 年后培育并推进那些思想的氛围全然不知。沙夫茨伯里和卢梭的影响,十八世纪生物学的唯意志论潮流,法国和英国的感伤诗,以及莪相崇拜,德意志虔敬主义——所有这些影响、这些运动,这些营造了前-浪漫派氛围的一切,都是维柯死后发生的。”(THL, p39)
不仅如此,奥尔巴赫还特别补充说,维柯甚至不知道浪漫派的重要思想资源——莎士比亚。正因为此,他的精神底色与上面那段引文中所提到的沙夫茨伯里等人——因而也实际上与赫尔德不可同日而语。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消除上述可能困惑,1955年发表的《维柯与民族精神》,奥尔巴赫是以这句话开头的:“相似的思想和精神范式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却彼此完全独立。”(THL, p46)但与其说奥尔巴赫是在为自己将维柯与赫尔德关联起来再次指出二者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不如说他是在告诉我们,表面的相似,却是我们误读维柯的最重要原因。我们——甚至也包括奥尔巴赫自己,所看到的维柯,往往并不是维柯本身,而恰恰是赫尔德或曰现代历史主义、现代审美历史主义镜中的维柯,因而很有可能是一个歪曲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维柯。他是这么说的:
维柯的例子非同寻常。他在赫尔德之前半个世纪阐明了他关于语言、诗与历史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常常看起来与赫尔德的思想太相似,以至于因此会被误解为后者,或被误解为赞同赫尔德的浪漫派的思想,乃至黑格尔的思想。(THL, p46)



1958 年,在奥尔巴赫最后一篇关于维柯的文章《维柯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此文修改后被用于《文学语言及其受众》的前言)之中,他曾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他对维柯的论述:“这就是,我从维柯语文学观念中所学到的。”(THL, p10)那么,他从维柯那里学到了什么?他所看到的维柯,究竟与人们通过赫尔德看到的维柯有什么根本不同?
二、南方与北方之别
让我们回到《维柯与赫尔德》一文的开头。这篇篇名即已显示乃是关于维柯与赫尔德二者关系的演讲稿,是从一个关键词“历史”开始的:
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作为人文学学子,无论是研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变迁,还是研究语言、书写或艺术的历史,都是在探究历史。这一研究基于如下基本信念:我们所谓的历史,并不仅仅只是一系列的事件而已,这些事件作为人类行为和人类灾难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和没有任何联系的,它们的总和也并不只是时间过程的累积罢了。正相反,在尘世间展开的人类生活事件的丰富性,构成了一种总体性(a totality),也即一种连贯的发展或有意义的整体(a coherent development or meaningful whole),每个单一的事件以多变的方式植根于其中,并因之而得以解释。(THL, p11)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柯与赫尔德具有了某种相似性。他们既与无条件强调“上帝之计划”(God’s plan)的基督教传统,也与强调理性设计的激进启蒙主义、特别是笛卡尔主义,以自己的方式区别了开来。对他们而言,历史,不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无序叠加与交织,不是某种形而上存在或抽象理念的附庸而已;而是正相反,历史既是人的自我创造,也是人理解自身的必要条件。
但,这也仅仅是相似而已。奥尔巴赫更希望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维柯与赫尔德的不同,乃至根本不同。
在这些不同中,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尤其值得重视,即:外在生命样态、自然观、以及对民族精神的看法。生命样态的不同,原本与生俱来,似乎无须深究,但奥尔巴赫却对之赋予了象征意义,并以此体现了现代性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类型。而正因为精神类型的不同,维柯与赫尔德对自然、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分歧。相应地,对民族精神的看法,则既彰显了两人殊异的社会政治观念,也让我们进一步确认了他们在启蒙中的思想位置。如果贯通起来看,或也可以认为,上述三者代表了他们在确立个体、认识自然和人性、以及认识政治社会三个维度上的立场差异,并共同构成了他们判若云泥的两种世界观。
首先,最可见的,是二者外在生命形态的不同。奥尔巴赫甚至特别强调了他们两人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方。但这种文化地理意义上的差异,却是为了凸显两个人在个性与精神气质上迥然有别。他是这么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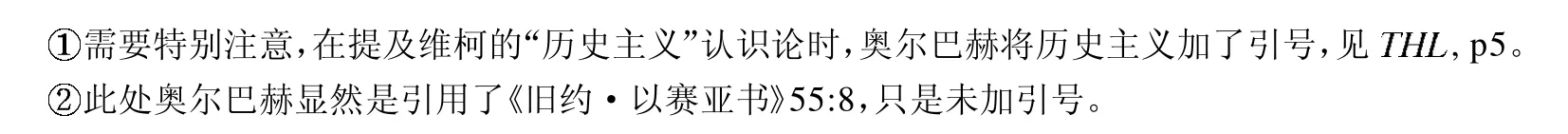
赫尔德来自北方。他是一位生机勃勃的贵族青年,且与其他贵族青年同侪为伍。无论在字面的还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他都是一位逍遥云游者——一位既在事实上也在思想和事工中经历过许多漫游的个体。但是,他却以年轻人的灼热激情浪掷了那些思想和力量。而与之相反,维柯来自南方,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教授,只有少数看重他学问的人才尊重并敬仰他。正像他的同时代人所嘲讽的那样,他“两眼圆睁,形容憔悴,手中拄着拐杖”。他一生只主要写了一本书(因为早先的著作只是为此书做准备而已),这本他以一己之固执写成的书,也仅包含一个唯一的思想。而最主要的差别乃是,维柯孑然一人而已。没有人为他开辟道路,他也无法效仿任何人的著作,更没有人回应他的问题。(THL, p15—16)
奥尔巴赫的上述对比,难免会被误解。尤其是习惯于用现代眼光观照一切事物的读者,更会认为奥尔巴赫将飒爽英姿的赫尔德与老气横秋的维柯并举,正明显是对赫尔德的赞赏和对维柯的贬抑。但细致阅读这段文字,结论却完全相反。奥尔巴赫在这里固然是在强调维柯的老迈、贫穷乃至无人理解,在另一处,奥尔巴赫甚至特别强调了维柯是一个书商的后代、一个无法实现阶层跃迁的平凡教授(THL, p15),但他却绝不是在对维柯下任何否定性的判断。毋宁说,这是一种有意味的对照。维柯的独持偏见、孤勇前行,与赫尔德的风华绝代、引领风骚,是他们体认生命存在方式的差异,更是两种精神样态的差异。对奥尔巴赫来说,后一种差异甚至尤其值得重视。因为,正是由于维柯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镜中的赫尔德,乃至镜中的“狂飙突进”。一个充满激情的启蒙者,恰恰需要有一个冷静孤绝的思想者作为对照,才能显出其可爱中透露出的幼稚,乃至浪掷青春的唐突与鲁莽。
这多少让人想起柏拉图《会饮》中的苏格拉底与阿尔西比亚德,想起莱辛晚年关于共济会的对话中的法尔克(Falk)与恩斯特(Ernst)。前者理性、审慎、具有鹰一般鸟瞰全局的视野和心性,后者则难免冲动、过于急切表达自己的意愿,因而显得很不成熟。至少,我们应该看到,奥尔巴赫通过这样的对比,期望我们不仅认识到简单以赫尔德方式理解维柯的不足为训,而且也同时认识到以维柯对观赫尔德的高度必要。因此,这既是一种现代性萌芽期两种精神存在的冲突,也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照亮。

而进一步理解上述这些,就需要看到维柯与赫尔德的第二个不同:自然观的不同,以及由此派生的人性观的不同。
在奥尔巴赫看来,尽管与赫尔德、与浪漫派类似,维柯毫无疑问也主张将史前作为现代的对照性“他者”,但是他却并不认为,那个原始的、史前的自然如卢梭或赫尔德们所设想的那样,乃是田园诗式的,平静、美好而远离冲突的。正相反,与赫尔德们的观点彻底相反,维柯的自然是野蛮的、可怕的、充满争斗的,因而也是每个普通的个人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虽然奥尔巴赫本人并没有完全追随维柯的步伐亦步亦趋,但是意识到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的区别,特别是意识到残酷自然与诗性想象、诗性智慧并生这一维柯意义上世界的本来面目,却不能不让奥尔巴赫更多地关注维柯、关注维柯的原始自然,从而更多地站在维柯一边,而非赫尔德一边。

因为,与赫尔德们对自然的审美历史主义认识相比,维柯对自然和人性的揭示虽然是危险的,甚至是可怕的,但却是深刻而伟大的。他更为勇敢地揭示了自然和人性的真实,而且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启蒙时代的到来,恰恰意味着自然之死,意味着人失去了与世界的诗性联系,而想象也渐渐消解为概念性的抽象。在写于1936 年的《维柯与语文学的观念》一文的结尾,奥尔巴赫这样写道:
值得记住的是,维柯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认为,共通人性与教育或进步性的启蒙相关。相反,共通的人性即历史之整体,既伟大,也恐怖。他不仅在总体性中见出历史的各各不同,他也视自己为一个可以理解历史的人类之一员。但是维柯并没有将自己作为人类的样本,他并未试图在他人中看到自己,而是在自己中看到了他人。他在历史中发现了自己,以及我们共通本性所显现给他的被埋葬的自然力。这是维柯意义上的人性,(这里所说的人性),比这个词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更为深刻,也更为危险。或许,正是因为此原因,恰恰是维柯发现了我们的共通人性,并将之牢牢把握。(THL, p35)
仔细阅读这段文字,我们或许不难体会到奥尔巴赫对维柯“同情的理解”。而更使我们感到吃惊的也许是,这段文字虽然是在正面讨论维柯,但压在纸背的却有着对赫尔德们、对启蒙思想者们的暗讽,至少也构成了一种遥远的互文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几乎直白地否定了通过教育和启蒙认识共通人性的可能性;而且也体现在,通过维柯以另一种方式提醒他的来自北方的德意志思想者,接受来自南方的维柯的忠告,坦白承认自然、历史和人性的双重性:伟大与恐怖并存。这既是奥尔巴赫对维柯与赫尔德思想差异的又一次高度概括,也在更深的意义上,侧面传达了他对启蒙之乐观主义基调的质疑乃至批判。这也正是奥尔巴赫要刻意将维柯与赫尔德相提并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说到共通人性,说到“在自己中看到他人”,而非“在他人中看到自己”,我们就可以来接着讨论在如何认识民族精神方面,维柯与赫尔德究竟有什么不同了。这是第三方面的不同。
“民族精神”(Volksgeist),几乎是德国浪漫派的“专利发明”,一提到此,人们也几乎会同时提到赫尔德的名字。但奥尔巴赫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维柯甚至早于赫尔德半个世纪就提出了“历史主义”的主张,因而也极容易被认定为同时也是一个为民族精神甚至民族主义张本的人,可事实却远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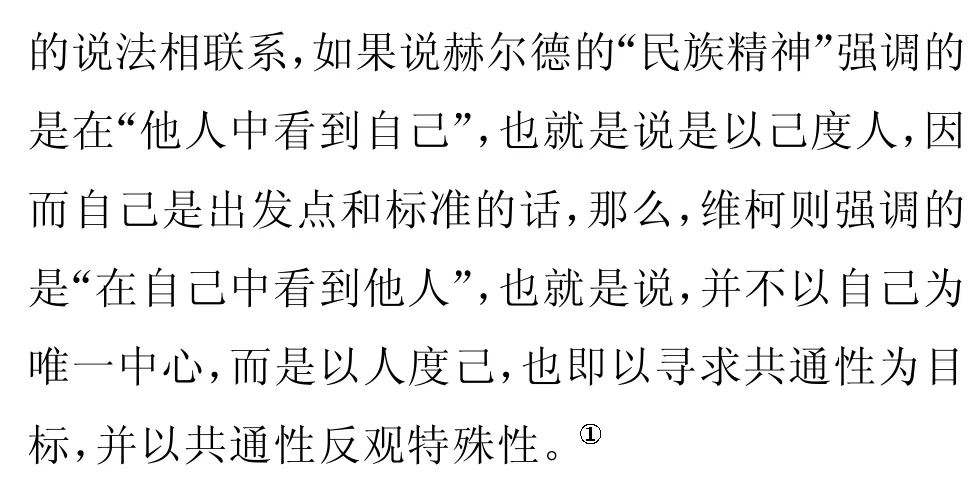
对此,奥尔巴赫在《维柯与民族精神》一文中说得更直接。他说:
维柯的历史并非目的论的,他甚至并不承认历史状况的理想模式。他对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并无很深的同情。无疑,他的心属于原始的诗与英雄的时代。
维柯并不看重单个民族的价值,因而也并不关注民族精神——至少并不以浪漫派的方式予以关注。(THL, p52)
很显然,在奥尔巴赫看来,维柯正是以诗与英雄的时代,与高级文化、也与启蒙精神相对照的。维柯介意的,不是意大利民族、法兰西民族或德意志民族等任何一个单个民族,毋宁说他更关注的是他心目中那个超越民族的、永恒循环的三个时代,而尤其关注的则是人的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和问题,人的时代所失去的诗性、活力和想象力。用奥尔巴赫的话来说就是,维柯“所聚焦的是普遍而非特殊”。(THL,p55)
在大约发表于1955 年的《作为现代人文学源泉的民族精神观念》一文开头,奥尔巴赫再次从诗作为第一语言的角度讨论了民族精神问题。在文中他意味深长地指出,认为诗乃是“人类的母语”(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human race)这一观念具有双重意涵。第一重意涵凸显的是普遍的人(universally human),第二重意涵凸显的则是“单个民族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an individual nation)。(THL,p56)不难看出,前者指向维柯意义上的诗,一切人类制度来源于诗;后者则指向赫尔德或德国浪漫派意义上的诗,民族精神之诗。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南方之诗,后者是北方之诗。
事实上,在同样写于1955 年的《维柯与民族精神》一文的结尾处,奥尔巴赫已经不仅对维柯与赫尔德在民族精神问题上的巨大差异做了区分,也对二者的根本不同做了如下概括——他甚至突兀地以提问方式,再次让我们注意赫尔德为什么对先驱者维柯毫不关心这个也许一直让他自己萦绕于怀的问题:
维柯最大限度地以理性的方式接近他的主题。他更属意于自己能够写作一部历史的几何学(a geometry of history),让直觉或同情心突入其中乃是违背他的心愿的。对他来说,历史是被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所构造的。他无意给历史理想的目标。他所寻找的是历史的永恒法则。而在另一方面,赫尔德则有意识地为直觉背书并追求感觉意义上的同情之情。对赫尔德而言,发展的诸结构既是生物学的又是情感性的;而教育的理想在在皆是。他的目标是单个民族,以及从人类宗教框架中显现的民族的个体性(national individuation)。对维柯意义上民族的或单个人的个体性均无关紧要的永恒的柏拉图之国(eternal Platonic state),赫尔德或浪漫派会说些什么?幸好,赫尔德与他的支持者们对维柯并不关心。(THL, p55)
三、语文学与哲学的内在紧张
我们当然无法确切知道,赫尔德对维柯几乎毫不属意的全部原因。但是,上文中的大量材料显然已经给出了奥尔巴赫将赫尔德与维柯关联起来的充分理由。对他而言,当然首先是帮助我们看到赫尔德与维柯的诸多不同:生命状态上青春与老到的不同,精神类型上情感型与理智型的不同,知识背景上古典语文学、罗马法与民歌与抒情诗的不同,以及对人性与自然的看法上理想、乐天与客观却偏于野性之不同,社会政治视野中强调个体与单个民族与强调永恒的柏拉图之国的不同。等等。
但仅仅看到不同,却远远不够。奥尔巴赫之所以对赫尔德居然不了解维柯无法释怀,乃是因为,在他看来,赫尔德所说出的观点有很多维柯其实已经说过,只是给出了不同解释、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而正因为此,维柯提供了与赫尔德形成鲜明对照的反思和批判启蒙的不同路径。如果赫尔德或德国浪漫派在狂飙突进中意识到维柯的存在,他们至少可以审慎一些,乃至更深沉一些,看到另一种面对现代性的可能性。

不过,反过来看,伯林的存在却更加彰显了奥尔巴赫的独特性。比较而言,如果说伯林所格外关注的是赫尔德与维柯的同,即他们同为启蒙批评者的思想立场,那么,奥尔巴赫尤其期望我们看到的,就是二者的异。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异既显示了现代思想内部的曲折与复杂,维柯与赫尔德之间的思想张力,也让我们在看到狂飙突进缺失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加深对维柯的认识。因为正是维柯既以他的尘世语文学肯定了人的历史性,也以他的哲学试图超越乃至扬弃这种历史性。换言之,也正是维柯以他哥白尼般的勇敢,既大胆地说出了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现代人,也同时说出了现代性和现代人的尴尬与危机。不仅是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尴尬与危机,也是赫尔德、哈曼式的尴尬与危机。在维柯这面意大利镜子之中,奥尔巴赫一方面试图让我们看到法国启蒙的问题——这是赫尔德们也已经看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更试图让我们看到德国启蒙也即赫尔德们自身的不足与问题。其用心可谓细也、深也。
细心的读者甚至不难注意到,《维柯与语文学的观念(1936)》(THL, p34)、《维柯与民族精神(1955)》(THL,p49)以及《维柯对文学批评的贡献(1958)》(THL, p10)三篇文章中各有一处几乎重复的文字。其基本内容,革命性地将圣俗之别转换为哲学与语文学之别,大旨如下:

维柯语文学观念的独异特征,可以用他自己的概念来概括。他将语文学与哲学对举。语文学的任务在于探究在每个发展阶段人们相信是真实的东西(尽管这只是他们的错误与有限知识的产物),而这继而成为其行动、制度以及表达的基础。他(维柯)称此为真确(certum/the certain; the established)。真确受历史变化的制约。而哲学,则探究不变的、绝对的真实,也即真理(verum)。如今,在维柯的著作中我们并不被允许看到从未在历史中显露的不变或绝对的真理。甚至在第三时代即人的时代,一个理性充分发展的时代,也并不包含真理。它也只是历史的一个步骤,不可避免地归于堕落并返回蛮野。柏拉图式的真理在每个时代部分实现,因为每个时代都是真理的某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非真理。只有在历史的整全中有真理,只有当人们认识全过程才可以达成。因此,哲学所寻求的真理与语文学似乎联系了起来,以探究特定的诸真确(certa),以及其连续和关联。这种关联,也即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la commune natura delle nazioni)正是维柯著作的主题——这因而可以被称为哲学的语文学,也可被称为语文学的哲学——仅只关涉这个星球上的人类。(THL,p10)
这段文字出现在《维柯对文学批评的贡献》结尾处,同时也不加修改地成为奥氏收山之作《文学语言及其受众》一书导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并非偶然。这里,奥尔巴赫当然是在对真确和真理,以及语文学和哲学做出重要区分。但细究起来,我们则可以说,这段关于维柯的文字,却事实上也从最根本的意义上、以最简练方式,再次概括呈现了维柯与赫尔德的最关键不同。


像赫尔德们那样——或也就是像伯林们那样,选择以语文学的方式站在真确一边,看起来可以拥有一个多元而自由的世界,一个强调个体、强调个人情感,乃至强调民族情感的世界,但却无疑远离了哲学、也远离了真理,在获得表面丰富性的假象中,失去世界的整全与完整。这是维柯所不取的,也应该是奥尔巴赫所不取的。
但否定赫尔德,乃至否定伯林式的选择,却绝不意味着简单回到基督教传统,以追寻绝对、追寻恒常不变的方式牺牲人、牺牲人的历史,最终牺牲绝对、牺牲恒常本身。
这或许也正是奥尔巴赫对维柯的解释,要以悖论性的“哲学的语文学”和“语文学的哲学”面目出现的原因?如果我们真的如奥尔巴赫所说要像维柯那样关心“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我们可以既是赫尔德,又是维柯吗?我们可以既在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吗?一种普遍的而非特殊的历史主义如何可能?永恒的柏拉图之国,与赫尔德意义上的民族精神如何共存?
与其说,奥尔巴赫通过解释维柯、通过将维柯与赫尔德关联起来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基督教所代表的整一性解体之后的现代性解决方案,不如说,他向我们提出了巨大的问题。而讨论维柯与赫尔德之别,当然不是唯一的提问方式。比如,我们至少还应该注意到《帕斯卡尔的政治理论》(1941)(THL,p215—235)一文中基督教冉森派思想者帕斯卡尔与人文主义者蒙田的特别关联,注意到《卢梭在历史中的位置》(1932)(THL, p246—252)一文中那个既试图背离又试图回归基督教的“两面人”卢梭。而我们也更知道,奥尔巴赫最为知名的《摹仿论》一书的核心关切乃是极端悖论性的“悲剧现实主义”:既崇高又现实;他的但丁研究所格外重视的则是个体生存(character)与命运(fate)的多重纠缠……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奥尔巴赫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也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维柯与赫尔德关系的更为宏大的背景和参照系:奥尔巴赫式的参照系。当然,那将是另外一些文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