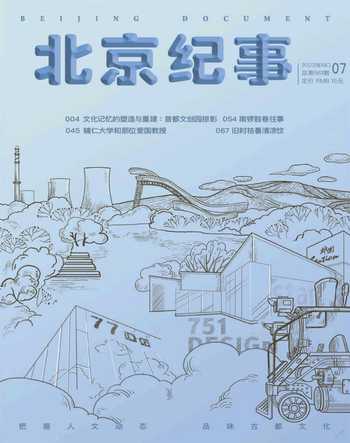挪威私人写作电影中的“虚无”问题
2023-07-11张冲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文明从脱离自然后就要面对“意义”的问题,因为人是一种需要意义而存在的物种,而原本生活在自然中的人凭本能生存则无须思考这个问题,当人类剪断了和自然连接的脐带后,要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世界之上,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危险与黑暗的世界,他需要给自己确立安身立命的基础或精神家园,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都从不同的角度回应了这个问题——而其实质都是对“虚无主义”问题的一种回应。雅思贝尔斯认为,人类体验到了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因而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虚无”力求解放和拯救,并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为自己树立更高的目标,他在自我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试图以此来同“虚无”做斗争。
本文仅就挪威新锐导演约阿希姆·提尔的四部电影《重奏》(2006)、《奥斯陆,八月未央》(2011)、《猛于炮火》(2017)、《世界上最糟糕的人》(2021)与彼特·纳斯的《他聪明谁傻瓜》(2001)来谈挪威电影如何从私人写作的角度介入“虚无”问题,在论及、面对与解决“虚无主义”这一问题时,导演们给出了怎样的社会现象呈现与建设性意见。
私人写作中“虚无”产生的根源
在上面提及的约阿希姆与彼特·纳斯的电影中都呈现了“私人写作”的特征,所谓私人写作,即是如普鲁斯特所说的“小玛德莱娜”蛋糕一样,连接着人和这个世界的最亲密的关系,“私人写作”亦可作为“小写的他者客体”指称“能够重新激发起对失落对象的被压抑的欲望”的一切事物,体会回到那个“完整、圆满和愉悦”的想象界,达成与这个世界的双向满足,带有满足感和“自由”的特征。
在约阿希姆的早期电影中这种私人写作的特征尤为明显,在《重奏》《奥斯陆,八月未央》中充满了主要人物的私人经验、私人话语、私人意识及私人无意识等。《重奏》中的伊利认为,抒情文和传记的层次不同,而安德斯想要找寻的是“绝对的语言”,一种表达所有细微事物的语言。安德斯认为,强烈的感受当然能为故事加分,但我的意思是透露受苦细节是一种八卦作风,他们巨细靡遗地描写每个悲剧,但那并非真的文学。
而在《猛于炮火》中导演又让康纳德以“零度写作”的方式再现世界及其私人体验:“我想点燃玛丽昂·维克逊头发,这是不是很疯狂,头发烧起来的气味很难闻。1999年除我外世界上还有三个名叫康纳德·瑞德的孩子出生。我用8格厕纸,有时候用12格,我好奇大家比我用得多還是少。我有14双袜子,我都穿过不止一次;我有14条内裤,20件T恤,21本书,100本漫画书,60张碟,还有121部电影存在电脑里。”这种私人化写作将康纳德的细腻心思、阴影、善良及理性真诚而动人地呈现了出来。
尼采认为身体就是权力意志本身,他的身体取代了笛卡尔式的主体。后者的内在特征正是意识、逻辑、认知和判断,这个主体与外物没有利益的纠葛及牵连,超然于外物世界,但自信能检验、测度、悟透外物。笛卡尔式的主体是全知型主体,是普遍主体,信奉逻辑、知识和理性的力量,通过它们,这个主体满怀信心地客观地抵达对象的深处。在尼采的身体这里,世界表现为一个变形之网,而在笛卡尔式的主体这里,世界表现得中规中矩,表现得纯粹、冷静、客观、中立,表现得一尘不染。
笛卡尔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讨论“存在”的意义,恰如工业社会核心价值观所约定俗成的那样,人们通过工作来呈现社会价值与存在意义,亦导致了“存在即虚无”的荒诞后果的产生。
彼特·纳斯的电影《猛于炮火》中妈妈说“媒体已经变了,公众的注意力更加分散了,噪音比以前更多了”。由于信息量激增,媒体工作越来越不好做了,必须要有更加醒目与刺激的摄影图片才能引起媒体与公众的注意,所以她一定要冒着更加危险的危险去拍摄带有刺激性与新闻性的照片。除此之外,她一直以摄影工作和忙碌填充生命的时间,并认为其充满意义并且“不该停下”工作,除了工作和被别人需要,她不明白“为什么要停下”工作,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工作”,因为她觉得“工作”是她的“职责”和意义所在,这是一种被精英世界肯定的“世界主义”思想或者共建现代文明秩序的思想。结果却导致她无法或不愿面对虚无与荒诞存在的真相,最终以“生理上的自杀”撞车出车祸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这工作让她感觉好像我还能对一些事物充满热情,无论“推石头”还是其他,都是被当代社会定义为“工作”,人存在的意义被“工作”所定义与决定,其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性,也势必导致人类重新面对存在,意即“虚无”,该如何选择,现代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被规训与所谓的文明社会中,人们对自身及身体的认知逐渐被理性所确立起来的秩序所阉割,身体在被德勒兹所说的操控系统中逐渐失去其原始的冲动、破坏力与创造力,逐渐成为温驯的“骆驼”或“羔羊”,而一味地隐忍或退居角落,自认孱弱、无力却是善良的化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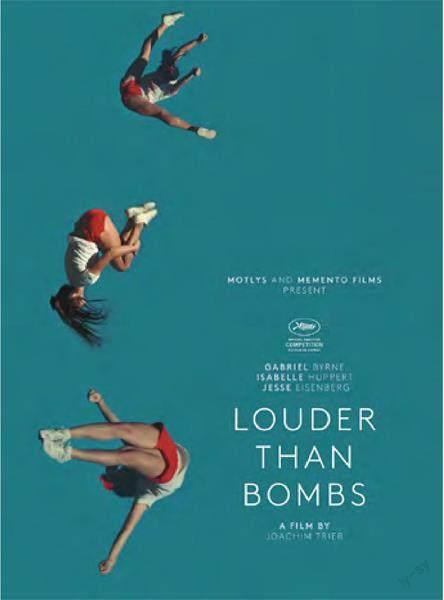
私人写作中的局外人
尼采认为,是自然,而非摩奴,将这三种类型区分开:一种偏重精神;一种偏重膂力、性情热烈;而第三种与前两者都不同,它体现的是平庸——但正是这第三种人代表大多数,而前两种是遴选出来的。彼特·纳斯的《他傻瓜谁聪明》中的杰尔比昂被同屋艾林善意地嘲笑为“大猩猩”,因为他只关心女人和食品,而杰尔比昂也的确以身体本能的方式与周遭的世界相处,他臂力过人常常搬起母亲醉酒的身体、女友、诗人友人等,除了体力,他也对象征男性力量和速度的汽车着迷,修理、保养汽车是他所喜爱的事。他与艾林不同,以单纯而原始的身体本能体验美好与幸福,这与艾林其实异曲同工——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森林里的“金发野兽”。

而似乎带有荣格所说的“一号性格”特征的艾林对于现代文明从身体上无法接受与认同,他认为拿起塑料电话听筒,并对着个塑料玩意和你看不见的人说话很不自然,这些现代文明的后果,包括超市、喧闹的酒吧和歇斯底里的诗人会使得他身体上的老敌人“头昏”和“焦虑”出现。而约阿希姆的《重奏》中情感细腻的作家菲利普面对突如其来的写作成名患上了“急性文化震撼症”,它无法再在家乡居住下去,成为游荡者,游荡在世界所谓的文明之所,“登上韦泽尔峡谷”,又去看“拉斯科壁画”,成为日本观光客的尾随者,在巴黎的地铁、机场与卢森堡花园游荡。这是菲利普在思考“生存意义”遭遇虚无时的初期症候,以身体的虚无和缺乏“信念”的游荡四处寻找意义,而最后发现意义就在自己所出生的区域,就在“爱”之上。
加缪认为,判断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意味着回答了所有的哲学问题。在时间的绵延中,一切都可以被记忆,一切亦可以如《奥斯陆,八月未央》中所说的一样,“一切都将被遗忘”,因为这是“自然法则”。可以被记忆是“无关紧要”的时间碎片,犹如《猛于炮火》中女中学生所读的类似普鲁斯特的小说:“相反,他的思绪飘向记忆深处,抵达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小事,他记起了几天前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个句子,他不理解这个句子,他想起了藏在叔叔家阁楼上的旧行李箱,想起了来自陌生人的短暂目光,此刻‘无关紧要的时间碎片,成了最后时刻,秒钟不再是秒钟。它延展成了分钟,时间已经停止。”这种文学性极强的私人无意识体验亦是这个电影的迷人之处,在这种私人的身体体验中,由于时间的绵延与“无关紧要”的事物世界因而充满意义,从而将虚无与荒诞驱逐,世界再次获得意义。
而《猛于炮火》的中妈妈认为“没有人再需要她了”而绝望,最后将身体消失在虚无之中。而小儿子康纳德与妈妈不同,他想象着母亲出车祸的瞬间,并对母亲失事前的身体体验状况进行详细的体会,他在女同学阅读极具细节性描述的普鲁斯特式的小说时,也以此种细节描述性的方法接续去描摹母亲去世前刹那间的身体及情感体验:“她当时可能在想什么,当意识到事故不可避免时,她在想什么?她想起了躺在沙滩上的感觉,睡意朦胧,感受风吹起细沙在她脸上的轻柔,她想如果多躺一会儿,身体最终会被沙子掩盖,也许她会想起很多地方,我们的房子、走廊、客厅。她甚至可能会想起他,想起她拥有的那些微小回忆,就算那些回忆她已经忘记。他(康纳德)躲起来,听她大声叫喊自己的名字,他到现在才知道,其实她早已识破,而她当时只是站在那儿,假装不曾察觉,所以她总是不走远,用眼角余光观察他。”母亲死亡的气息并没有将12岁的康纳德击垮,犹如击垮父亲和哥哥乔纳一样,康纳德以对母亲的想象延续母亲的存在,母亲在他的记忆中是绵延式存在,犹如不曾逝去那样,即使是出车祸死亡的刹那,也被他以绵延的方式无限地延长,永远在变化与存在。康纳德动物般的质朴与天真看待与接受母亲的死亡,恰如他从写作中感觉到的力量一样,他以文学和游戏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带有对权威秩序世界的颠覆的特质。而当喜欢的女孩解手时的体液流过他的脚边时,他以更加私人化的情感体验和身体经验去经历这种动物般的欢愉与狂喜。
私人写作中的爱、“信”
与虚无主义
尼采认识到苏格拉底主义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因为苏格拉底用理性对抗本能,而尼采则坚决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 “超人”仅仅是对未来的至高卓绝的人的描述的话,那么,超人的对立面则满目皆是,他们是现代人,善良人和其他虚无主义者。而《他傻瓜谁聪明》中艾林用艺术来调和日神与酒神之间的平衡,或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酒神的艺术精神使他从不敢上街到成为街头的游荡者,他又将这街头视为自然的街头,作为私人写作甚至是私密写作的诗人的街头,是诗歌艺术的力量让他走出自闭,游荡在城市与泡菜诗人之间。
艾林的信念與爱是作为诗人“E”的狂喜,当他看到报纸上说卡尔·斯文恩在市区买泡菜的故事时狂喜不已,他认为自己发表了诗歌处女作,但是却以放在泡菜盒子里给私人阅读的方式,他为自己将成为成千上万的读者的神秘诗人“E”而狂喜。艾林在这种神人合一的状态中,灵魂获得了宁静,享受着幸福,体验着奇妙无比的欢悦。他不想像其他的咆哮诗人那样在公众面前表演秀,也不想通过诗歌创作谋取暴利,尽管他也想站出来使得自己成为一种显学、名流或名人。但是艾林没有,他单纯地以贵族道德的质朴捍卫“原来的自己”——妈妈的宝宝,尽情享受宁静夜晚的街道上无名的声音以及宁静的狂喜之幸福。这是终极英雄亦是大智如愚的艾林的选择。
约阿希姆的电影《重奏》中的菲利普与凯莉最终跨越了奥斯陆东西区不同的阶层、文化与理性认知的差异,不但以“爱”为名拯救了菲利普的生命与才华,还击碎了存在的“虚无”。而《奥斯陆,八月未央》则不同,电影中安德斯因爱与信念的缺失,导致他无力面对虚无而选择走向绝路。“信”这一观念极其重要,犹如老子所说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在西方“FAITH”的哲学、神学逻辑体系里,“信”也是较为抽象与普遍的问题,在约阿希姆的《奥斯陆,八月未央》中,杂志社的负责人对男主人公安德斯说“很多人戒不掉(毒品),那个东西太异乎寻常了”,此种表述对安德斯所说的“我可以的”不信任,这种“信念”“相信”的缺失、缺席是导致安德斯毁灭的第一步。导演通过对信念力量的反思来抨击“信念缺失”的当代社会,“虚无”、荒诞及恐惧的生成,皆因人类对某种高于自我存在事物的信念缺失,或无法将其真相“信念-奇迹”辨识而堕入庸常与虚无,又被假象蒙蔽而无法自拔。最终导致加缪所说的人类面对荒诞-虚无的前两种状态:生理上的自杀与精神上的自杀。
《猛于炮火》中摄影师妈妈虽然拥有丈夫的爱、情人的爱及儿子的爱,但却因缺乏坚定的信念无法看清虚无的现实而选择绝望的处理方式。《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朱莉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糟糕状态,到不停地选择,再到对自由的理性认识,完成了从“他物内”回到“自身内”的“自由”。即通过内心与身体对阿克塞尔、埃温及父母等事物的直接认识而达到了认识了自己,并因此不再为情感、话语及糟糕的父权秩序所累,实现了她的自由。
张冲博士,武昌理工学院科研教师,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民族文化影像传承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研究员,ISFVF国际学生短片电影节审片、评委,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责任编辑等。
主讲课程有《电影文化研究》《新时期中国喜剧电影研究》《影视剧作理论与创作》《欧洲电影史(当代北欧与东欧电影)》《中国电影史》《中外喜剧电影比较》《电影批评方法论》《英美电视剧研究》《大师研究》等。
出版专著《电影文化研究》《1977年以来中国喜剧电影研究》,译著《行为表演艺术:从未来主义至当下》等。研究之余,也从事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