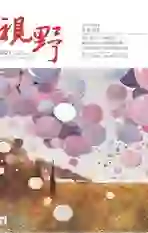大舅妈
2023-07-07新宇
新宇

大舅妈姓“和”,和珅的“和”。她是一个纯种的满族人,有着典型的“鞑虏”人的长相。如果非要我给你一个画面的话,我会告诉你:她长得极像晚清黑白照片里的隆裕太后,尤其是人中以下那部分。
父亲和母亲的家住得不远,两家人都互相认识,他们的婚姻还是三姑父和姥爷一手包办的,他们领完证连喜酒都没有摆就拎着两个大包袱进城打拼了。从一穷二白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在城里定居,经历了四五年。虽然离老家很远,但是每年的春节全家人是都要回奶奶家和姥姥家过年的,我也只有在这一年一度的聚会中才能见到我那些叫不上名字的亲戚。
在我的印象中,过年见到大舅一家的次数十个指头就数得过来,但仅有的几次见面也为我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记忆和一些别人百听不厌的“段子”。
大舅妈是“西沟”人,大舅是屯子里的人,自从大舅“嫁”给大舅妈之后,对你没看错我也没说错,大舅确实是“嫁”给了大舅妈家——结婚之后大舅有什么好东西都往“西沟”送,逢年过节也是丈母娘一家为先,过年七天乐期间几乎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一家人都在“西沟”那边过,年后回来能露一面算不错了。怎么说呢,“西沟”那边的法律上的父母比自己亲身的父母还要亲。
我对大舅的陌生感是那种在马路上迎着走过来眼神都对视上了也认不出来的,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小时候他抱着我要亲我,我像个大茧蛹一样地蠕动着挣脱了他的怀抱,逃离了他的胡茬和满身的烟酒气。
与大舅的模糊和陌生不同,在我的印象中,大舅妈却一直是一个极具漫画色彩的形象,她经常会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放在她的身上却又显得那么地理所当然。
九几年的时候,大舅妈一家跟我们家借了一笔钱,这笔钱一直到了21世纪初也没还上。爸爸妈妈都是脸皮薄的人,去要了几回,但人家很硬气地说“没有”,他们就不再追问了。但是看着人家又盖新房,又添新衣,不太像没有的样子,倒更像是“欺负老实人”。
于是在某一年的大年初三,终于忍不住的刘女士(我妈)就领着我去找大舅妈掰扯这个事情,而我的作用就相当于小学生书包拉链上的挂饰——纯粹就是个摆设,去了大舅妈那充其量能帮着吃点干果吧!
和料想中的一样,我和我妈一登门就受到了虚伪的欢迎,吉祥话说了一套又一套,半天才让我和我妈上炕,大舅妈给大表哥使了个眼色,大表哥就端上了用簸箕装的干果,好不隆重,但你仔细扒拉扒拉里面除了有干花生以外居然还有干花生。
刘女士没吃几个花生,她知道此行的目的是要钱,不能和大舅妈周旋太久,便迫不及待地开门见山:“那钱你大概什么时候还?我们也等着用钱,家里要盖房子了。”
这一句话说完屋里的空气凝结了半分钟,我妈好像触发了大舅妈的某种应急机制,待她头上的进度条加载完毕,就“噌”的一下从炕上弹了起来,用手使劲地拍着炕沿,打着四三拍的节奏,拍一个八拍就喊一句“我有钱,我有的是钱”,话音刚落就再弹回炕上,屁股刚一沾到炕席上就又跳下来了,重复着刚才那一系列动作。
我和刘女士正吃着花生,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切震惊到了,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我的大表哥就冲了进来把装花生的簸箕给端走了,我俩又是吃了一大惊。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我和刘女士都不记得最后我们是怎么回的家,钱当然也是一分没要到。说实在的即使到现在,此时此刻,写作的当下,我也真切地记得那一刻的惊诧——我的大舅妈,真的不是丰子恺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吗?
回到家,屋里一群人,姥姥姥爷询问我们结果如何,惊魂未定的刘女士将来龙去脉讲了个大概,但是关键的环节就叙述得过于苍白,她转过头来问我:“你小孩你记性好,你大舅妈怎么喊的来着?”
我正好站在地上,挪到炕沿,按照大舅妈的节奏给大家表演了一遍,惟妙惟肖,逗得全屋的人哈哈大笑。鉴于他们平日里对大舅妈这个人的了解,他们也能想象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现在想想也许我的模仿天赋就是那时候被启发的,总之我的“模仿秀”在村子里小范围地出了名,我妈还带着我巡回演出,她负责给我垫场,我负责关键性的表演炒热气氛,我们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把大舅妈那一出演了一个正月。

這一圈下来,在我和我妈的配合演出之下顺利地掌握了舆情,村里人在道上看见我大舅妈都偷笑,有的还贱兮兮跑去问“你就是有钱吗,借我点花呗”。
也不知道是不是村子里的讨论让大舅妈一家面子挂不住了,事情有了转机。一天我们正在炕上聊天呢,大舅妈突然闯入,屋里瞬间鸦雀无声。她没有想象中的歇斯底里,一反常态地安静,甩下钱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扬长而去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嘴里小声地叨咕着“我有钱,我有的是钱”,刘女士这回瞪了我一眼。
那之后,大舅妈一家在我们的世界里也没怎么再出现过,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光怪陆离的,其实也无非就是和左邻右舍吵架,但不管有理没理大舅妈都不会在面上败下阵来,她只会给对方的记忆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瞬间。后来他们一家也进城了,把那些“传奇”也带走了。
上一次听说大舅妈的光辉事迹是在姥姥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们一家风尘仆仆地来了,坐了一会又风尘仆仆地走了,给姥姥留下了一根已经不脆的炸麻花以及从浑身上下八个兜里努力翻出来的十元大钞,皱皱巴巴的和那根不脆的麻花放在一起显得十分地相得益彰。
姥姥学给我听的时候还嘲讽道:“哼,我没吃过麻花。”不过她又补充道:“这么多年来,我终于吃到你大舅妈的东西了,这半根麻花得裱起来。”
与病魔斗争了很久,姥姥走了,葬礼上的人群中哭得最凶的要数大舅了,走的时候他握着妈妈的手说:“咱们老妈走了,以后咱们得经常聚一聚。”妈妈嘴上应着,心里却也知道他只是在过嘴瘾展示自己的“孝心”和“手足之情”,就没有当面揭穿他。
再后来,我们就再没见过大舅一家了,甚至于连他们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也凝聚成了几个精彩的“瞬间”,以及模糊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