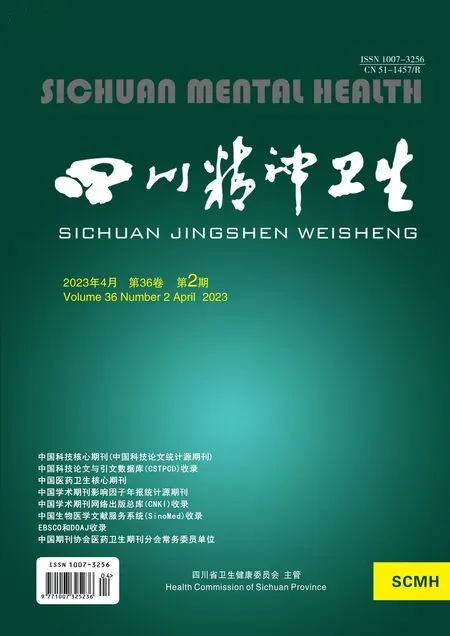心理援助热线成年与未成年自杀高危来电者特征及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比较
2023-07-03赵丽婷李春玲伍梦洁童永胜
赵丽婷,李春玲,伍梦洁,童永胜
(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WHO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北京 100096 *通信作者:童永胜,E-mail:timystong@pku.org.cn)
自杀是重要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19年全球超过70万人死于自杀[1],我国的自杀问题也依然严峻,每年约有10万人自杀死亡[1]。面对如此庞大的自杀人群,亟需有效的危机干预方式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群。因便捷、隐蔽、有效等特点,心理援助热线作为重要的危机干预方式之一,被人们广泛知晓并使用[2-4],且对高危来电干预的效果明显[2,4-6]。
既往研究表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自杀行为特征存在差异,如自杀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但自杀未遂率却相反,年轻人的自杀未遂率更高[7],且未成年人的自杀未遂率有逐年增长的趋势[8]。关于自杀危险因素的研究显示,精神障碍、物质滥用、冲动、被虐待、父母离异、欺凌等是未成年人自杀的危险因素[9],与成年人群并不相同[10]。既往心理援助热线的研究大多关注成年来电者,或者未将成年与未成年来电者进行区分探讨[2,4-6],仅个别研究关注了未成年人自杀高危来电者的特征[11]。迄今尚无研究比较心理援助热线的成年与未成年自杀高危来电者特征是否存在差异,且尚未明确哪些因素会对干预效果产生影响。故本研究对2021年1月-6月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中成年和未成年自杀高危来电者的社会心理特征以及影响干预效果的因素进行比较,以期更好地理解不同年龄阶段热线来电者产生自杀危险的原因,以及对不同年龄阶段来电者进行处理时需关注的重点。目前的热线干预实践中,尚未专门为不同年龄阶段来电者设置不同的干预模式,本研究的预期结果将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心理援助热线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入组标准:①心理援助热线自杀高危来电者;②有来电者年龄信息。排除标准:①无效来电(例如沉默、骚扰或通话时间不足10 min等);②非心理问题来电(咨询信息来电);③重复来电。若同一名来电者多次被评估为自杀高危来电,则选取自杀风险评估得分最高的一次纳入分析;若风险评估得分相同,则选择来电时间最早的一次。自杀高危来电的判断:接线员使用自编自杀危险综合评估量表对来电者自杀风险程度进行评估,该量表包括12个条目,总评分范围0~16分,评分越高提示自杀风险越高,≥8分被定义为自杀高危来电[2]。
2021年1月-6月,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共接听来电16 208例,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的自杀高危来电共2 229例。根据来电者年龄,将来电者分为成年组(≥18岁)和未成年组(<18岁)。热线在电话接通后自动播放语音提示,告知来电者热线的工作流程、信息处理原则及保密原则,来电者知情同意后,转接至接线员接听电话。本研究获得北京回龙观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高危来电干预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自杀高危来电干预要点[2]:接线员通过主动倾听、共情、尊重并给予来电者情感支持,建立情感联系;确认来电者安全;使用统一的评估工具评估来电者的自杀风险;非指导性、合作式的问题解决;制定安全计划及预约随访。热线接线员均须具备心理咨询或精神科学习或工作背景,并于接线前接受热线咨询基本理论与技能培训,包括高危来电的处理;考核合格后,在督导的指导下进行接电实践[12]。正式接线后,每名接线员均须接受每月2次的接电质量评估及督导,接电质控严格遵循技术要求[13]。
1.3 资料收集
1.3.1 一般资料
通过接线员询问,收集来电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
1.3.2 自杀意念
接线员评估来电者最近两周是否有自杀的想法,若有,则继续询问是否有自杀计划。根据此项作答,将来电者分为三种类别:无自杀意念、有自杀意念无计划、有自杀意念且有计划。
1.3.3 社会心理特征
接线员使用统一的评估问题收集来电者的社会心理特征[14],包括以下内容。①抑郁程度:采用抑郁症诊断筛查量表[15]评估来电者近2周的抑郁情绪严重程度,该量表总评分范围0~100分,评分越高表明抑郁情绪越严重。按照既往研究的划分方法[9],以平均分为界,将评分≥77分者视为存在严重抑郁情绪。②既往自杀未遂史:曾经(不包含来电前的2周内)是否实施过自杀行为。③严重躯体问题:现在是否患有严重躯体疾病或存在躯体残疾,并对生活产生重大影响。④物质使用问题:最近一年内是否非医疗需要且连续3个月以上使用安眠、镇痛、抗焦虑药物等或接触过毒品;最近一年内是否醉酒超过4次,并影响学习和工作。以上任一条目回答“有”且近一个月内仍存在此问题并对生活各方面产生影响,表明来电者可能存在物质滥用的问题。⑤慢性生活事件:既往任何时候有过家庭或工作方面的问题,且长期存在严重的影响并持续到最近一个月。⑥急性生活事件:最近一周内,生活方面是否发生了对自己有严重影响的事件。⑦被虐待:既往任何时候是否经历过性虐待或躯体方面的虐待。⑧害怕被攻击:最近一个月是否经常担心或害怕自己会被攻击。⑨亲友自杀史:既往亲人或朋友是否实施过自杀行为(包括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
1.3.4 主诉问题
通话结束后,接线员根据来电者的描述,判断此次来电的主诉问题,选择以下1~3类问题:①家庭成员关系问题;②家庭外人际关系问题;③工作问题;④学习问题;⑤经济困难;⑥其他负性事件;⑦情绪问题。
1.4 干预效果评估方法
分别于通话开始后10 min和通话结束前,采用统一标准评估来电者自杀意念强烈程度、痛苦程度和希望程度,三项评分范围均为0~100分[2]。以来电者接受热线干预前后自杀意念强烈程度、痛苦程度以及希望程度的变化值作为评估干预效果的指标:在自杀意念强烈程度和痛苦程度方面,干预前评分减去干预后评分的值≥20分,表明干预有效;在希望程度方面,干预后评分减去干预前评分的值≥10分,表明干预有效。
1.5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将9项社会心理特征和7项主诉问题均划分为二分变量。分类数据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比较成年与未成年自杀高危来电者的基本资料和干预效果。自杀意念强烈程度、痛苦程度和希望程度改善程度的定量数据以M(P25,P75)表示,采用秩和检验比较来电者接受电话干预前后的分数。将成年和未成年来电者分为干预后无改善组(赋值为0)和有改善组(赋值为1),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成年组与未成年组高危来电者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以来电主诉问题(因情绪问题与严重抑郁情绪关联过强,故未将情绪问题纳入模型分析)和社会心理特征为自变量,并设置这些自变量和年龄组(成年组/未成年组)交互项(用于检验干预效果与自变量的关联强度的组间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16],采用backward法筛选变量(P<0.1的变量保留在最终模型中),控制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检验水准α=0.05,双侧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基本资料及干预效果比较
在最终纳入分析的2 229例高危来电者中,未成年来电者885人(39.70%),成年来电者1 344人(60.30%)。在各项主诉问题比例上,成年组和未成年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5.604、24.585、49.679、29.661、24.706、5.293、5.481,P<0.05或0.01)。未成年组中,有自杀未遂史和害怕被攻击的比例均高于成年组(χ2=41.944、106.527,P均<0.01),成年组中有急性生活事件和躯体疾病的比例高于未成年组(χ2=14.371、16.941,P均<0.01)。未成年组报告有自杀意念且有计划的比例高于成年组(χ2=32.960,P<0.01)。
经热线干预后,所有自杀高危来电者的痛苦程度和自杀意念强烈程度均降低[90(80,99) vs.60(45,80),Z=-31.784,P<0.01;78(50,90) vs.25(0,60),Z=-31.347,P<0.01],希望程度升高[干预前vs.干预后:10(0,30) vs.25(3,50),Z=-20.758,P<0.01]。未成年组在希望程度上改善的比例高于成年组(42.74% vs.30.97%,χ2=26.042,P<0.01)。见表1。

表1 成年与未成年自杀高危来电者的主诉问题、社会心理特征及干预效果比较Table 1 Comparisons of chief complaints, socio-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vention effects between adult and juvenile callers at high risk for suicide
2.2 两组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控制人口学变量后,家庭成员关系问题是来电者痛苦程度改善的关联因素,存在家庭成员关系问题(OR=1.293)的来电者痛苦程度改善更明显。严重抑郁情绪与痛苦程度改善的关联存在组间差异(交互项P<0.01),有严重抑郁情绪的未成年组(OR=0.832)痛苦程度不易改善,但成年组痛苦程度不易改善的情况更明显(OR=0.642)。见表2、图1。

图1 成年组与未成年组自杀高危来电者干预效果与社会心理特征关联的OR值比较Figure 1 Comparisons of adjusted odd ratios of socio-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intervention effects between adult and juvenile callers with high suicidal risk

表2 成年组与未成年组高危来电者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risis intervention effects in adult and juvenile callers at high risk for suicide
干预后,希望程度是否改善与家庭外人际关系问题有关联(OR=1.393)。物质使用问题与希望程度改善的关联存在组间差异(交互项P=0.024)。有物质使用问题的成年组(OR=0.830)希望程度改善的几率低于相应的未成年组(OR=1.476)。见表2、图1。
严重抑郁情绪和学习问题是来电者自杀意念强烈程度变化的关联因素,有严重抑郁情绪的来电者自杀意念强烈程度的改善较差(OR=0.782),有学习问题的来电者经电话干预后自杀意念强烈程度改善更明显(OR=1.645)。慢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强烈程度改善的关联存在组间差异(交互项P=0.040)。有慢性生活事件的未成年组(OR=1.352)自杀意念强烈程度改善几率高于相应的成年组(OR=0.872)。见表2、图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援助热线来电者中约40%为未成年人,其中女性占比更高。既往对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使用态度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对心理热线的知晓率和使用率均较低[17]。因此,如何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尤其是男性青少年使用心理援助热线应对危机,是未来青少年危机干预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来电主诉问题上,未成年组以家庭成员关系问题为主,成年组以家庭外人际关系问题为主。既往研究也表明,与父母发生矛盾以及父母之间关系恶化是常见的诱发青少年自杀的生活事件[18-19]。此外,未成年组报告存在学习问题的比例更高,而成年组报告存在工作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比例更高,这一结果也与两组的年龄特征相符。
未成年组存在自杀意念且有计划及既往存在自杀未遂史的来电者占比均高于成年组。既往研究也表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率较高[9],有自杀未遂史是再次发生自杀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9,20]。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接听未成年个体的来电时需更加全面细致地评估其自杀风险。此外,未成年来电者报告害怕被攻击的比例也高于成年组,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即霸凌是青少年发生自伤行为的相关因素[21-22]。这也提示在干预过程中需关注未成年来电者身处的外在环境是否安全。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自杀高危来电者的自杀意念强烈程度和痛苦程度均降低,希望程度改善,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4,23]。对青少年而言,受羞耻感因素等影响,他们对寻求心理援助热线的帮助持消极态度[24],但本研究显示,经热线干预后,大部分未成年来电者的危机状态得以改善,提示心理援助热线对未成年自杀高危人群具有重要的干预作用。本研究中,存在家庭成员关系问题的来电者痛苦程度改善较好,Ohtaki等[25]研究也表明,心理援助热线有助于改善存在家庭成员关系问题的来电者的自杀意念。分析其原因,缺乏社会支持是自杀行为潜在的危险因素[26-27],心理援助热线服务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来电者提供社会支持,助其渡过危机。
在报告伴有严重抑郁情绪的自杀高危来电者中,未成年组痛苦程度的改善优于成年组。成年与未成年人在抑郁症的表现上存在差异[28],不同的症状表现往往预示着不同的干预难度。这一结果也对未来的热线干预方案提出了新的问题,即面对不同群体的自杀高危来电者,需要采用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在希望程度上,存在物质使用问题的成年来电者改善弱于未成年组。与未成年来电者相比,成年来电者物质使用问题存在的时间往往更长、程度更严重[29-30]。面对这些来电者,除进行即时的危机干预,提供合适的转介也是热线服务的重要一环。在报告存在慢性生活事件的自杀高危来电者中,未成年组自杀意念强烈程度的改善优于成年组。一般而言,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面对的生活事件可能相对简单,解决这些问题相对容易。既往研究也表明,问题解决训练能够帮助青少年应对个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31],而合作性问题解决正是热线干预中经常采用的方式之一[2],这可能也有助于促进未成年来电者危机的缓解。
本研究局限性在于:首先,在热线干预过程中,来电者人口学特征和社会心理特征等部分资料缺失,可能对研究结果存在影响。其次,通过电话交流,接线员难以对来电者的精神疾病状况进行评估,故本研究并未控制这一混杂因素,但纳入了与自杀密切相关的抑郁严重程度。最后,本研究对象为主动寻求帮助的有自杀风险的人群,将本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人群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