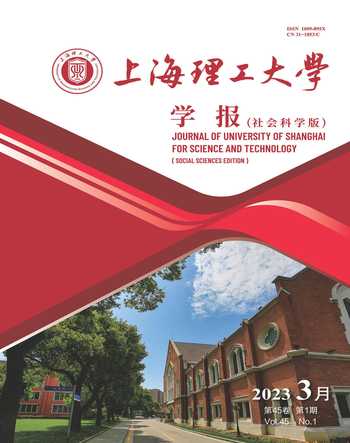克莱尔?吉根短篇小说的多重互文书写
2023-06-29易永谊罗甜甜
易永谊 罗甜甜
摘要: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存在很多人物、故事情节和主题意象的反复呈现。借助互文性理论,发现吉根的小说存在三种互文叙述模式:一是聚焦于女性的孤独和人际关系困境的自涉互文书写;二是爱尔兰乡村故事里基于宗教虔诚情感基调的历时性互文书写;三是充分调动色彩与声音等感官叙述的跨界互文书写。正是其小说运用多重互文的书写策略,吉根创造出一个具有爱尔兰乡村传统的现代生活世界,凝聚对当代女性的孤独个体与婚姻家庭双重困境的哲学性展示,并尝试得出自己独特的思考结论。
关键词:克莱尔·吉根;《南极》;《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互文性;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3)01?0045?07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3.01.008
On the Multiple Intertextual Writing of Claire Keegans Short Stories
?Taking Walking on the Blue Field and Antarctica as Examples
YI Yongyi,LUO Tiantian
( Schoolof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any repeated presentations of characters, plots and theme images in Claire Keegans work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ree intertextual narrative modes in Keegans stories: one is self-referential intertextual writing that focuses on the loneliness of women and their living dilemma of getting along with others; the second is the diachronic intertextual writing based on religious emotional Tone in Irish rural stories; the last mode is the cross-border intertextual writing that fully mobilizes the sensory narrative of color and sound. Keegan uses multiple intertextual writings to construct a modern life world with Irish rural traditions, condenses a philosophical display of contemporary womens lonely individuals and the dual dilemma of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tries to come to her own unique thinking conclusions.
Keywords :Claire Keegan;Antarctica ; Walking on the Blue Field ;intertextuality;female image
當代小说作家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出生于1968年,在爱尔兰东部威克洛(Wicklow)的一个农场长大。她从1994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尽管数量不多,但每篇小说都凭精巧的结构和细腻的情感刻画打动人心。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南极》( Antarctica, 1999)展示出其创作天赋,并获得“鲁尼爱尔兰文学奖”( The Rooney Prize for Irish literature)。2020年,葡萄牙学者丹妮拉·尼科莱蒂·法维罗( Daniela Nicoletti Fávero )讨论了小说集《南极》里的《男孩的名字》(Quare Name for a Boy)中妇女身份迷惘和社会命运的困境,指出小说展示女性如何选择更独立的方式打破女性命运的固定模式[1]。2021年,马里索尔·莫拉莱斯-拉德龙( Marisol Morales-Ladrón )针对《南极》中的性别关系和女性能动性,试图找到在经常受阻的背景下女性解放的模式[2]。
吉根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 Walk the Blue Fields, 2007)获得2008年“边山短篇小说奖”( Edge Hill Prize for Short Stories)。2012年,西班牙学者梅拉尼娅·特拉萨斯-加列戈( Melania Terrazas-Gallego)研究了现代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约翰·麦加恩(John McGahern, 1934?2006)的《女性中间》和吉根《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中《护林员的女儿》的对话叙述和女性生活[3]。2019年,伊根·史密斯( Eoghan Smith)考察了《走在蓝色田野上》的叙事风格和模式,并探讨如何与爱尔兰的短篇小说和民间故事理论、短篇小说叙事风格的发展相关联[4]。吉根最近的中篇小说《寄养》( Foster, 2010)获得2014年《爱尔兰时报》的“戴维·拜恩斯奖”(Davy Bynes Prize )。
除了研究单篇作品或作品集,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吉根小说的总体风格和文学价值。2010年,爱尔兰学者安妮·恩莱特( Anne Enright)在梳理21世纪爱尔兰短篇小说时,提出:“民间故事和短篇小说分开多年,只是在克莱尔·吉根的近作中重新聚合。”[5]2013年,比利时学者埃尔克·德霍克( Elke Dhoker)指出,吉根之所以被认为是爱尔兰最有前途的新作家之一,其中获得赞誉的标准是她与约翰·麦加恩的短篇小说比较。这种比较研究既涉及吉根大部分故事的主题:建构一个看似永恒的爱尔兰乡村,又涉及她在爱尔兰故事中经常运用的象征现实主义(symbolic realism)[6]。2014年,梅拉尼娅指出吉根对爱尔兰乡村日常生活的缺陷,以及乡村生活给人们尤其女性带来的悲剧影响,明显有着一种讽喻性理解。在她看来,吉根使用短篇小说类型专注于观看质量,而不是道德化问题,这种技巧使她的写作方式被认为是冷酷的、外在的和非情绪化的[7]。2015年,林奇和薇薇安·瓦尔瓦诺( Lynch, Valvano V )讨论克莱尔·吉根小说的反面父母形象,并批判性地审视爱尔兰语境中的儿童和儿童故事[8]。
从1999年的《南极》到2007年的《走在蓝色的田野上》,虽然这两部小说集间隔数年,但都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创作特色,即对无名女性和孤独者形象的刻画,同时这些作品也展现了其作品自涉的互文性。例如,吉根非常重视阅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她曾坦言自己是“在文学阅读和创作中成长”[9],对《圣经》传统的继承,对华兹华斯、海明威的创作思想和风格的借鉴,使得她的作品呈现与前人作品的历时互文性特征。同时,吉根在小说中酷爱用音乐和颜色来渲染作品,这不仅与她的爱尔兰民族身份相关,也更能为她揭示深层次的人的灵魂深处的孤独、感伤起到烘托作用。
迄今为止,国内有关吉根的研究论文与专题论著并不多见,主要停留于书评为主的介绍[10?12],可见中国学界对这位在西方已声名卓著的爱尔兰小说家重视不够。因此,探究吉根作品中的互文性现象,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爱尔兰乡村文学传统,也可以针对蕴含在文本内的女性主义话题探讨当代社会女性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一、“叛逆的女儿”:女性的自涉互文
正如法国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言:“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13]87《南极》与《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中存在某些人物、故事情节和意象的反复出现所形成自涉的互文性。这些文本自涉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女性形象的两个塑造途径:孤独个体的主题书写、家庭关系的主题书写。由于两部小说集前后相差数年,这两组互文又不单单只是呼应,而是构成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折射出作者在小说中对爱尔兰女性和乡村人生的思考。
(一)孤独个体的主题书写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延续《南极》中的两类人物形象: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孤独者。而这两组互文正构成吉根小说中自涉的互文性特征。吉根笔下不同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有鲜明的相似性:这些大多是孤独的无名氏。《南极》共收录15篇小说,其中《南极》《冬天的气息》《护照汤》《燃烧的棕榈》《水最深的地方》《暴風雨》《男孩子的怪名字》等7篇的主人公都是无名女性。在这7篇小说中,除了《花楸树的夜晚》叙述者明确地以女主人公的名字玛格丽特进行叙述之外,其余的6篇里:《走在蓝色的田野上》《护林员的女儿》和《妥协》中女主人公的名字都只是在不经意中出现过一次,或是在他人的谈话中,或是在练习簿上闪过,或是出现在信的落款上;《离别的礼物》《黑马》和《在水边》的女主人公是没有名字的,叙述者称呼她们为“你”“那个女人”“母亲”。
孤独者形象是吉根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人物形象群,这也构成小说中的第一组互文关系。吉根认为:“短篇小说可以很好地探索人与人之间的沉默、孤独以及爱。”[14]她笔下的孤独者大部分都是渴望爱却并不拥有爱的人物。孤独元素(相互疏离的人物关系)几乎充斥着吉根的每一篇小说,小说中的一切人物关系都给人一种若即若离、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小说中的人感到孤独,于是他们渴望外出找寻温暖、陪伴。《千万小心》中的 J. E.接受只有一面之缘的布奇的邀请,和他一起划船出游,醉醺醺的布奇无意中透露了自己杀死出轨的妻子的秘密,导致接下来的时间里 J. E.都在无尽的恐惧和孤独中度过。《护照汤》中弗兰克·科索对女儿的失踪感到自责,从这以后他的妻子很少在家,也几乎不跟他交流,两人维持冷战的状态,彼此隔绝,各自陷入孤独。《爱在高高的草丛》讲述了一段短暂的婚外情,科迪莉亚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医生,从此以后,科迪莉亚就守着这段无望的爱,独自一人等待医生有朝一日能够离婚,和自己在一起。《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中为了儿子甘愿成为他人附庸物的母亲、因为琐事失去妻子的丈夫以及长期被亲生父亲侵犯的小女孩,这些人无不是被亲人的离去或伤害变得敏感又脆弱,生活在孤独和无助之中。《护林员的女儿》中婚后的玛莎感到“婚姻生活的无趣让她觉得痛苦:铺床、拉窗帘、关窗帘,一切都那么无趣。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比单身的时候还要孤独。”[15]53这个作品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感刻画得很成功。
这些孤独的元素不仅增加了吉根小说冷淡的叙述风格,而且加强了现代社会人一个重要的精神特征?孤独困境。作者评论小说人物:“这是她曾经想要的,但是两个人很少在人生的特定时刻想要同样的东西。这恐怕是人类最艰难的一件事。”[15]38这句话点出了吉根所有爱情小说的共同特点:处在婚姻或爱情中的男女的人际关系,似乎总是貌合神离,彼此不了解也并不珍惜。这正符合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信息化时代人与人心灵碰撞的时刻越来越少,人变得越来越自我封闭,如同小说中的孤独者们那样,从不愿?或者没有机会?向自己的亲人或朋友敞开心扉。
(二)家庭关系的主题书写
吉根小说中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互文书写,主要是对家庭关系的描写,构成两部小说集第二组互文关系。她选择关注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透过父女、母女、夫妻关系,向读者展示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变化。这些爱尔兰故事以边远的家庭农场、乡村牧师、努力工作的母亲和无能的父亲为特色[16]172。故事中的女人经历了从妥协到反抗的曲折过程。《南极》是一篇关于婚外情的小说,“每次这个婚姻幸福的女人离开家时总会想,如果和另一个男人上床,感觉会怎样。”[17]1她想要寻找婚姻外的新鲜感,轻率地跟邂逅不久的男人约会。当她意识到背叛家庭带来的谴责时,她已经被这个男人捆绑在床上失去了自由。这说明吉根否定女性以出轨为解放途径的观念。《男人和女人》中,一位爱尔兰母亲和她的女儿开始意识到物化的性别角色是一种欺骗,于是她们朝着夺回权力迈出了第一步[18]。女性人物从妥协到反抗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吉根笔下的男女很少有和谐相处的时刻,往往是男性压制女性。
第一,作为压迫者的男性。吉根笔下所有不健康的女性背后都有一个强势的父亲或者丈夫。尽管她表面上回到了传统的、永恒的、通常是陈词滥调的爱尔兰乡村描写,但吉根实际上对记录变化更感兴趣?即使这是一种承认仪式和传统重要性的变化形式[17]160。在《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的首篇《离别的礼物》中,叙述者以独特的第二人称视角描写了一位少女长期遭受父亲性侵的故事。小说《离别的礼物》于2006年在秋季的《格兰塔》杂志上首次以《安全》的标题出版,这一期主题为“爱人”[8]。故事原标题“安全”指的不再是家庭,而是女孩逃离出家、远离父亲后,机场厕所紧锁的门带给她的安全感。
第二,“有毒的父母”。吉根在她精心调整的椭圆叙事和对主人公意识方面的详细揭露中,发现了“有毒的父母”造成的伤害[8]。在她笔下,家庭不再是能给人温暖和安全感的地方。例如《离别的礼物》和《弗雷斯特的女儿》都讲述了年轻女孩的故事。她们试图在家庭和爱尔兰农村当地社区的范围内,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17]161。在中篇小说《寄养》中,小女孩被亲生父母送到朋友家寄养一个夏天。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女孩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尽管被邻居告知这一切都是因为养父母失去了一个儿子,她自己只是这个逝去孩子的替代品。吉根省略了这个孩子的内心活动,读者无法知道这个孩子自始至终是如何看待养父母的,但可以知道她更想选择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因为整篇小说中,她都没有叫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一声爸爸,而在最后她却这么称呼自己的养父。这表明她想要重新选择自己的身份,想要选择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成长。
第三,反抗的女儿们。吉根小说的女儿角色都有共同点:她们都是充满渴望、聪明、富有想象力的年轻女孩,她们的抱负最初跨越了性别鸿沟。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进入青春期的少女需要学习性别规范,她们被期望学习如何在父权制社会中表现得更像个女孩[17]163-164。这也是吉根小说中一直都存在男性权威声音的主要原因,“这种对母系遗产的强调,对成为母亲和女儿的一部分的强调,是吉根大多数女儿故事的核心要素。”[17]167从《南极》到《走在蓝色的田野上》中的女性,她们不再自我封闭于家庭中,不再选择沉默、忍受,而是选择反抗和逃离,如《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开篇故事中的女儿选择离家出走。
《南极》和《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相继出版,吉根的女性主义思想也在相应发展。分析吉根的小说绕不开情爱这一主题,描写女性爱情和欲望一直是吉根小说的一大特色。吉根对女性的情欲描写也在这两部小说中呈现出整体的变化。《南极》和《走在蓝色的田野上》这两部小说集里,吉根刻画了一系列在情感和欲望上备受压抑而感到苦闷、彷徨的女性,这些女性年龄跨度从幼儿到老年,她向读者揭示这些不幸女人的遭遇的同时,也记录了这些女性不断成长、发现自我、建构自我的过程。
二、虔诚的乡村故事:叙述的历时互文
任何作品都会与其所借鉴的前文本呈现出相似性。 18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萨缪尔强调:“那些声称是原创的作品,实际上很少能够超越前人已经提供的资源,相同的想法和构思也早已被他人所论。”[19]T. S.艾略特也认为优秀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内化前辈文学家的创作经验[20]25。细读吉根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文学经典和作家的影子:《圣经》、华兹华斯、契诃夫、海明威、茨威格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吉根的小说与前文本存在历时互文性。
第一,宗教文化的影响。从文化意义上讲,吉根作品与基督教存在互文性,尤其是在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宗教神圣节期以及对宗教人物的滑稽模仿。《走在蓝色的田野上》这篇小说有浓郁的宗教气息:神父第一次见到女孩是在万灵节,最后对失去的爱情释怀是在复活节前不久。神父曾经也追问“上帝在哪里?”[15]38当他遇见一位虽然孤独却仍然热爱生活、生命的中国人时,他想上帝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上帝就是自然”。顺其自然并保持一个干净、快乐的灵魂,就是上帝为他留下的解开烦恼的方法。当他终于想通不再执着于失去的爱情时,复活节也即将到来。神父终于在精神上复归到宗教带来的平和、安详中,他又重新充满着希望。这位神父仿佛是基督的缩影,经过一场精神折磨后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脱。
小说《千万小心》的主人公 J. E.全名是耶利米·以西结·德弗罗。在《圣经》中,耶利米和以西结都是犹太族的先知,都曾有被敌方掳走的经历, J. E.的遭遇也和这两位圣经人物呼应。在《圣经》历史中,耶利米是公元前7至6世纪希伯来的一位先知,在侍奉亚述王时期被犹太人掳往巴比伦。J. E.第一眼看到布奇时,就预言“他不是个天使”,发现布奇杀妻真相也是被布奇绑架最后被关在一个有蛇的狗窝中。耶利米虽为先知,可生性懦弱,被人称为哀哭的先知,面对国家大难他经常以哭泣来表达自己的无奈和悲痛。J. E.被绑架后也是害怕到尿裤子,他说自己“不是个英雄,也不想假装英雄”,仿佛现代版的耶利米。事实上,作家吉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信奉天主教的大家庭中,《圣经》对其创作有深刻的影响。吉根把许多小说的时间都设定在宗教节日前后,比如万灵节(《走在蓝色的田野上》)、复活节(《水最深的地方》)、圣诞节(《花楸树的夜晚》《男孩子的怪名字》《男人和女人》《护林员的女儿》)等。这种互文手法在小说的现代生活中嵌入一种古老的宗教文化传统。
第二,吉根的创作观念和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有许多互文之处。首先,他们都致力于乡村题材的书写。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写道:“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21]42吉根的大部分小说故事都发生在爱尔兰的乡间,有关爱尔兰都市題材的小说少之又少,森林、田野、农房都是她的小说故事常发生的场所,农民、猎夫、乡下家庭主妇也是她许多故事中的主人公。其次,他们都推崇用简洁、朴实的语言风格讲述人生真谛。华兹华斯认为“我又采用这些人(指乡间人民)所使用的语言(实际上去掉了它的真正缺点,去掉了一切可能经常引起不快或反感的因素),因为这些人时时刻刻是与最好的外界东西相通的,而最好的语言本来就是从这些最好的外界东西得来的……因此,这样的语言从屡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来,比起一般诗人通常用来代替它的语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的。”[21]42吉根也有类似观点:“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在尝试去找到一种清新的语言,去描述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意义。”[9]两部小说集的语言也实践了她这一理念,平实质朴。最后,他们的美学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华兹华斯曾谈到他对诗歌的看法,认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21]42。他将诗人内心思考的抒发放在重要位置,开创了发掘诗人内在自我世界的现代诗风。克莱尔·吉根在谈论自己小说创作心得时,也有类似的表述,在她看来,“一部好的小说,其实是我们感情的一部分,是有关转瞬即逝的情感,是感动人心的”[9]。
第三,吉根的小说叙述风格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存在潜在的互文关系。海明威强调文学创作中的省略艺术,这种省略不是对作品内容的盲目删减,而是强调达到一种以少胜多,意在言外的境界。他的短篇小说尤其体现了他的冰山理论,在《乞力马扎罗的雪》《白象似的群山》等脍炙人口的小说中,海明威省略了本可以交代给读者的许多情节,比如《白象似的群山》从头到尾读者都不清楚谈话的男女究竟是什么关系,而作者也留下大片的空白地带等待读者用自己的经验去填充。吉根短篇小说也有着一样的特点,正如她自己所言:“短篇小说很紧凑,你必须把大多数可说可不说的话删掉,这是一种减法原则。就如聊天,似乎说得很多,其实真正说的内容很少。”[14]所以她的作品只需要寥寥几笔总能直逼人心深处。
在《离别的礼物》中,“礼物”两字始终没有出现,离家的女孩最终孤独地踏上异乡之旅;在《跳舞课》中,“破烂儿”吉姆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对吉姆产生了感情,并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对他进行性挑逗,他也如此对“我”,而接下来吉姆却上吊自杀了,作者并没有叙述原因,只将“我”发现吉姆尸体的场景以轻松、平常的语调叙述了一番,吉姆的死因读者不得而知;《冬天的气息》中,汉森带着孩子和保姆去探望好友格里尔,从两人陆陆续续的谈话中,读者才知道格里尔的妻子被一个黑人性侵了,那位黑人就锁在汉森经过的大棚里,可结尾不知是谁打开了那个棚子的大门,让这位黑人逃走。类似的情节安排在吉根的小说里俯拾皆是,读她的小说一定会让人想起海明威的叙述风格。不过,较之于海明威的作品,她的小说也有另一个“冰山理论”之外的特点?结尾总是出人意料,这又颇有欧·亨利小说的意味。
三、蓝色交响乐:感官的跨界互文
互文性既是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吉根的小说交织着色彩与音乐,能给读者带来别样的视听体验。互文性的提出为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思路。互文性打破了对文学文本性质的传统看法,从文本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向强调了某一具体文本同其外部各种因素的所有复杂性联系,使传统眼光中确定的、明晰的和封闭的文本走向广阔而复杂的开放性空间[22]116。
小说中有与绘画艺术的互文性书写。“蓝色”是吉根小说的主调,也同样是象征着爱尔兰民族的颜色。吉根小说中反复出现一种颜色?蓝色,形成一套自己的小说色彩象征体系。吉根“一直让故事笼罩在她喜爱的颜色里:蓝。飘着小雨的蓝色的天空,蓝色的火苗,蓝色的田野。蓝,那是哺育过乔伊斯、叶芝的爱尔兰的原色,是梦幻的色彩。”[12] 《姐妹》讲的是姐姐贝蒂和妹妹路易莎从童年到中年的关系变化。从童年时起,妹妹路易莎就懂得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而姐姐贝蒂长相普通,自小就生活在妹妹的光环之下。当已为人母的路易莎从英格兰返回爱尔兰农庄后,贝蒂发现她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夺走房屋的所有权。但是贝蒂一直是孤身一人,唯一拥有的就是这座父亲留给自己的农舍,而妹妹居然企图将它夺走。不同于小时候对路易莎的忍让,这一次贝蒂选择坚决反抗。终于,在一个蓝色的早晨,贝蒂看着气急败坏的妹妹路易莎一家离去。“贝蒂什么也没说。她只是站在过道里,看着外面蓝色的早晨,露出吓人的微笑。”[16]1在贝蒂眼中,早晨是蓝色的,这与她当下的心境相关。不同的色彩运用能够恰当地烘托出人物的内心情感。蓝色作为一种冷色调,正表明了此刻贝蒂的内心是低落且忧伤的,因为妹妹从小到大并不真正爱自己,只是一味地打压自己的自尊心、夺取自己的拥有物,本该血浓于水的亲情随着妹妹的变本加厉荡然无存。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讲述了一位神父参加了曾经相恋的姑娘的婚礼,并成为婚礼的主持者,在热闹的婚礼现场,只有他一个人转身走入了蓝色的、空旷的田野中。他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思绪,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整个故事都笼罩在淡淡的忧伤和宁静的氛围中:“黑梯山高高耸立,给田野投下奇怪的蓝色阴影。”[15]31此刻的神父揣着满心的伤感前往那位大家口中能够治愈人心的中国人家中,希望能够摆脱内心的忧愁。当神父重新在宗教和自然中找到了內心的安宁时,他对于同样的蓝色的田野又有了新的体会:“一头绵羊从沉睡中醒来,走过蓝色的田野。”[15]38同样是这片蓝色的田野,在这篇小说中却带有神秘气息,神父却不再沉浸在失去爱情的痛苦中,此刻的蓝色更多地传达给读者一种静谧和安详的感觉,因为神父终于体悟到“活着真是件奇怪的事”[15]38。相较于上帝、自然,人类是多么渺小的物种,人的生命总是由许多个转瞬即逝的瞬间连接成,不应偏执于其中的某个连接点,应该抓住当下,好好生活。神父想到了即将到来的复活节以及更远的未来,下决心做好一名神父。
吉根为什么偏爱在作品中植入蓝色呢?“蓝”这一色彩对于她的小说描写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在爱尔兰,蓝色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古爱尔兰国王的徽章上,国王形象就是置于一整片的蓝色背景中;女政治家康斯坦斯·马基维奇( Constance Markiewicz ,1868?1927)使用浅蓝色作为爱尔兰国民军旗帜的底色,1542年爱尔兰正式成立王国,她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国徽?天蓝色的盾面上绘有一把金色竖琴,而其中的蓝色则象征着爱尔兰人民的眼睛以及天空和大海。因此可以说,爱尔兰的民族颜色是蓝色。“不同人的色彩反应有共同性(或者一定范围内的共同性),也有差别性。形成差别性的原因,与人的个性有关,比如素质、感情、修养、兴趣、遭遇等,也和民族的、阶级的、时代的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有关。因为,感受色彩的主体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活生生的人,他的色彩感觉当然要受到他自身的主客观条件的影响。”[23]作家的创作会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他所在的民族记忆,吉根的小说创作就表现出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对于蓝色的挚爱,因此她选择蓝色等冷色调作为自己的小说叙述主要色调。歌德曾经写过《色觉学说》一书,里面就有将颜色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大类,“积极的色彩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有生命力的和努力进取的态度,消极的色彩,也可以说是被动的色彩,就‘适合表现那种不安的,温柔的和向往的情绪”[23],而蓝色就被纳入到消极的一类中。
吉根的小说总是交织着忧伤和冷淡,她力求刻画出人性的幽微深处,所以她的小说参杂了许多有关人性的黑暗面,比如殺妻、性虐待、强奸、乱伦等。消极冷色调的使用不仅反映出作者的情感倾向,更能契合吉根创作小说的主题之一:揭示人性阴暗面。文学作品中的色彩描绘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23]。小说文本的阅读依赖于读者的想象,色彩词的使用让读者在想象的过程中更能体会到作者传达的意图。小说中使用的许多冷色调词,就是读者更走近吉根的一个突破口,透过这蓝色的幕布,可以窥见不同人的孤独、沉默和爱。“blue ”在英文中有忧郁的意思,而吉根钟爱蓝色,正是因为她想透过忧郁而美丽的笔调道出人生的意义,正如她写道:“每个人都需要确信一些事情。它能帮助你发现生活的意义。”[15]135
吉根的小说除了有着绘画艺术的跨学科互文书写,同时也有音乐的互文性书写。吉根的小说时有音乐插入,这些音乐或是服务于主人公,或是服务于小说意境。《有胆量的就来吧》这一篇讲的是已婚女性罗斯琳与想要征婚的格里恩的一次邂逅。小说中为这段邂逅“插入”的歌曲有摇滚乐《世事难料》、猫王的《今夜你是否孤独?》,最后又以《世事难料》结束。这两首音乐的顺序恰巧对应着罗斯琳和格里恩婚外恋的发展:首先是两个心灵求爱的人难以预料的相遇;再经过一番了解后,两人都明白彼此的孤独,都渴望占有对方;在两人玩巨型滑梯时,格里恩的双腿紧紧夹住了罗斯琳的腰,预示着这一段婚外恋的开始;然而“世事难料”,两人以后的结局却并不可知。
四、结束语
借助互文性理论的审视,可以发现吉根笔下的文本内部之间的自涉互文性、其作品与西方经典文学的互文性以及与色彩学的互文性。透过对吉根作品内部之间的梳理,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女作家,内心对爱尔兰女性生存现状的焦灼:一方面这些女性存在于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爱尔兰,所以不得不去迎合他们;另一方面,就算她们迎合、讨好丈夫、父亲,可最终还是无法获得幸福,她们仍旧是苦闷婚姻中的受害者、男权社会里失语的无名者。寻找吉根作品和前文本之间的关联,又可以看到作者对《圣经》的借鉴,与华兹华斯文学创作思想的共鸣,以及与海明威作品异曲同工的省略艺术。一位优秀的作家必定有博采众长的本领,因为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她所写出的东西才不会轻易流于肤浅。吉根小说中笼罩着的梦幻的蓝色,既表明了她对爱尔兰民族的挚爱,更烘托出她作品中的忧郁气氛,为小说的描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吉根笔下的无名女性或孤独者一定并不仅限于爱尔兰人,在当今的世界各地都存在这样的女性,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幸福,也无法建构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让自己获得安宁。在她的作品中,能够摆脱情爱欲望的都是将灵魂寄托给宗教的人,这或许是吉根为这些苦闷中的女性提供的一条出路。而在创作层面上,通过找出吉根与先前作家作品中的互文性更可以看到其作品的历史纵深感,从《圣经》到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文学经典的不朽可以在吉根作品中再一次得到验证。互文性理论的运用不仅限于文本本身,更多时候是跨越文本范畴到达社会层面,比如吉根笔下的“蓝”就是如此。
参考文献:
[1] F?VERO D N. A female fate in “ Quare name for aboy” , by Claire Keegan[J]. ABEI Journal, 2020, 21(2): 147?153.
[2] MORALES-LADR?N M. Gender relations and femaleagency in Claire Keegans Antarctica[J]. Studia Anglica Posnaniensia, 2021,56(1):275?292.
[3] GALLEGO M T. Dialogue and womens lives in JohnMcGahern s “ amongst women” and Claire Keegan s “ The forester s daughter”[J]. ES:Revista De FilologíaInglesa, 2012(33):321?339.
[4] SMITH E. Autonomy, naturalism and folklore in ClaireKeegan s walk the blue fields[J]. Canadian Journal of Irish Studies, 2019,40(2): 192?207.
[5] ENRIGHT A. Punch and poetry: the Irish short story in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2010,72(1): 129?136.
[6] D HOKER 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begins”:present-tense narration in Claire Keegan s daughter stories[J].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 2013, 7(2): 190?204.
[7] TERRAZAS-GALLEGO M. Claire Keegan s use ofsatire[J]. Estudios Irlandeses, 2014(9):80?95.
[8] LYNCH V V.“Families can be awful places”:thetoxicparents of Claire Keegans fiction[J]. New Hiber- nia Review, 2015,19(1): 131?146.
[9] 中国作家网.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 vs 中国女作家张悦然[EB/OL].(2017-04-18)[2021-06-11]. http:// 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418/c405057?29217266.html.
[10] 张学昕.南极在哪里??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南极》[J].长城, 2013(1): 152?158.
[11] 王雪茜.花园尽处的风光?从克莱尔·吉根小说的国内流行推荐语说开去[J].鸭绿江(上半月版), 2017(11): 108?116.
[12] 赵柏田.克莱尔·吉根的梦幻蓝[J].书城, 2020(5):65?68.
[13]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M].史忠义, 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4] 时代在线网.专访克莱尔·吉根:不写出美丽的东西是一种耻辱[EB/OL].(2010-06-24)[2021-06-11]. http:// www.time-weekly.com/post/8888.
[15] 克莱尔·吉根.走在蓝色的田野上[M].马爱农 ,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16] DHOKER E. Ir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ModernShort Story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7] 克莱尔·吉根.南极[M].姚媛, 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
[18] BRZEZINSKI M. Antarctica by Claire Keegan[J]. TheAntioch Review, 2000,60(2):340?341.
[19] 张昕.约翰逊文学批评的互文性思想及其实践[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3(2):91?99.
[20]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1] 伍蠡甫,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22]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3] 刘煊. 文学理论与色彩学[J].文艺理论研究 ,1987(1):29?36.(编辑:朱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