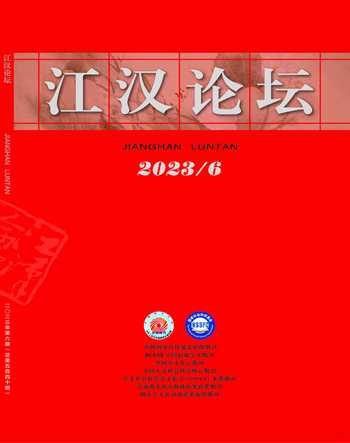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的组织建构及历史贡献
2023-06-28朱晓东吴雨函
朱晓东 吴雨函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为有效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便衣队这种独特的组织形式便应运而生。便衣队全称“武装便衣工作队”,它是游击战环境下人民战争思想和军事组织形式的创新与发展,是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的创举,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及中国革命事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在实践中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斗争活动,逐步发展为具有党政军特征的武装工作队。目前,学界对于便衣队的研究成果较少,且集中于便衣队的性质、形成与发展及历史作用等方面①。然而对于便衣队这一独特的组织形式,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本文从组织建构的角度探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的形成过程、组织特性及其历史贡献,以期进一步加强对于便衣队的研究,加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革命武装的研究,深化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
一、便衣队的组建方式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便衣队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现的便衣队,其组建方式不尽相同。林维先在谈到便衣队的形成时指出:“有的是红二十八军主力部队有意识地下放的,有的是当地农民游击小组发展起来的。”②根据现有掌握资料,便衣队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迫于形势自发的形成,二是地方党组织的发展,三是红军部队的派出。
(一)基层自发形成
便衣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是在反“围剿”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随着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攻的不断加剧,根据地革命斗争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一些地方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在边区建立起白色政权,原有苏维埃的政权机构大部分被摧毁,地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不能正常开展。许多便衣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便衣队最早出现在1933年7月间,时值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为有效反击敌人,更好地保存自己,中共红安县二程区委和仙居区委摸索和创造出了便衣队这一独特的对敌斗争形式。随后,在皖西、鄂东北、豫东南等地先后出现不同形式的便衣队组织,它们吸取在原地斗争人多目标大的教训,换上便衣、带上短枪、化整为零,广泛活动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有的地区的便衣队是由幸存的基层县区、乡村苏维埃负责人组建的。他们出没于乡村附近,隐蔽于群众家中,有条件时则就地开展武装行动。如黄安、商城等地,每乡均设有乡政府。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乡政府的负责人不能归家,就带着乡政府的印到处走,走到哪里乡政府就到哪里。“他们还带着一些枪,日子久了,印就不发生效力,他们就带着枪,称为便衣队”③。有的便衣队是部分苏维埃机构留余的干部自发组建的。如罗山地区的县区乡各级机关于1933年5月随罗山独立团进行游击活动后,区、乡干部即自发转为便衣队分散活动,与敌斗争。这样以来就自然产生了穿着便衣的武装工作队,一面掌握地方政权,一面进行武装活动。还有的便衣队是由留守干部组建的。鄂东北等老苏区一带便衣队的产生大都如此。“鄂东的老苏区那里失败后还驻有我们的机关医院等三四百人,几十里一片荒凉,没有群众,这些机关需要供给,于是组织了一个便衣队,这就是道委会的那个分队,买粮食,买东西,打些土豪,也出去做些群众工作”④。
1934年7月,鄂豫皖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白旗下群众工作较活跃,逐渐建立有组织,并有些秘密的基本便衣队。”⑤1934年2月,中央军委在《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中肯定了便衣队这一形式,“我们看见有新的希望。这个希望,是从游击队和便衣小组的行动那里来的,这里便衣小组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组织”⑥。可见,便衣队是在鄂豫皖根据地遭受敌人摧残的特定条件下,人民群众在基层干部的领导下,依据当地特殊的地理条件与敌周旋,在斗争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早期便衣队的主要组织方式,也是便衣队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
(二)地方党组织发展
由于便衣队符合根据地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地各级党委对发展便衣队组织高度重视,全力支持。1933年下半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决定广泛建立便衣队,充分发挥这一独特的对敌斗争组织形式的作用,使党的活动得以坚持下去。
1933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现在最有发展希望,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因此,省委决定用党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吸收群众来“参加便衣队工作”⑦,并委托鄂东北道委在罗山县卡房开办便衣队训练班,培养便衣队骨干力量。训练班由时任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具体负责,每期从各区、乡游击队中抽选两人,主要学习便衣队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和工作纪律等内容。学员结业后“返回原地,根据所处环境开展工作”。之后,“再回到训练班汇报总结、共同提高”;“训练班为便衣队制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行,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斗争方针和策略”⑧。
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前,专门留信指示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担负起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领导责任。当时,鄂豫皖苏区只剩下皖西和鄂东北几小块倍遭摧残又互不接壤的根据地。在此危急关头,高敬亭毅然担负起领导鄂豫皖革命斗争的重任。他根据当时大别山斗争形势的需要和自己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在重建红二十八军的同时,大力发展便衣队组织。为此,高敬亭亲自挑选人员、配备武器,亲自确定任务,亲自领导,亲自检查,并给予便衣队独立处理党政军等重大事务的权力⑨。鄂东北道委也召开会议,强调大力发展便衣队,组织地方武装和便衣队开展游击活动,牵制敌方兵力,策应红二十五军转移,建立新的立足点。经边区各级党组织总结推广,便衣队很快发展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一种普遍的游击武装方式。
(三)红军部队派出
从红军部队中派出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组建的另一种重要方式。1934年5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军长徐海东根据省委决定,从部队派出以夏云龙为队长、汪少川为指导员的一个12人的便衣队,在霍山县一带发展党员、发动群众,组建了中共霍山县六区区委,在掩护伤病员、搜集情报、牵制打击敌人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皖西北地区的第一个便衣队。团山便衣队的产生也是由于战略上的需要,1934年秋红二十五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为了在根据地留下一些革命力量继续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组织设立了这支便衣队。
为掩护在战斗中受伤的人员,红二十八军或当地游击师也先后派出便衣队。如由徐海山任队长、刘子榜任指导员的便衣队,就是在一次战役后将20多个重伤员暂时分散安排在老乡家里养伤后,临时组织的便衣队。马家河战役后留下的伤病员,就是由红二十八军留下的一支便衣队负责掩护的。王园战斗后,红二十八军又留下一支便衣队掩护伤病员,主力继续隐蔽前进⑩。
红军主力部队不仅给便衣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在转战中对于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均积极下放便衣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开辟根据地。如1934年初红二十五军在潜山、桐城、舒城边区活动一个多月,先后留下了13支便衣队和游击队。1935年2月徐成基被任命为皖西特委书记兼246团政委,统一领导皖西地区的便衣队和地方武装,至1936年春,红二十八军先后派出11支便衣队,分布在以鹞落坪、大岗岭为中心的多县交界地。1936年2月底,鄂东北独立团到应山县境活动,建立了一小块游击根据地,并留下一支十多人的便衣队。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组建的便衣队,成为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武装力量之一,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便衣队的成员结构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由于来源不同,成员结构也较为多样,既有来自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干部、工作人员,也有来自各部队的指挥员、战士,还有各地的普通群众。概而言之,党员干部成为便衣队的领导核心,红军将士为便衣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普通群众则是便衣队得以生存发展的深厚基础。
(一)党员干部
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为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鄂东北道委决定将所属的各级党组织及各苏维埃政权调整后以便衣队的形式开展活动,各级党组织、基层政权干部及工作人员转为便衣队成员。1933年4月后,光山各区乡干部陆续转为武装便衣队活动;罗山地区县区乡各级机关随罗山独立团进行游击活动,区乡干部也转为便衣队分散活动。至1934年初,鄂东北地区便衣队已发展到七个大队,成员多以县、区、乡干部为核心。皖西特委和商南县委等各级党组织也把便衣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任命一些县区主要领导干部担任便衣队长、指导员。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1935年以后,高敬亭也经常把苏维埃政府中比较年青的同志编进便衣队。各地纷纷从红二十八军、地方武装及基层政权中挑选优秀的指战员,并吸收少数当地党员组成精干的便衣队,深入村寨组织广大劳动群众,用各种方式支援红军,开展对敌斗争。
1934年6月,苏区交通员石健民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有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去参加便衣队或游击队了”⑪。此外,国民党豫鄂皖边区巡察专员袁德性在其巡察报告中也指出:“各地各有便衣队一个分队(每分队七八人),商城西河桥有一个大便衣队(人枪约五十余),金岗台有便衣队三四人,并有妇女十九人,均系党员。”⑫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区委县委工作人员多半都参加在便衣队里面,便衣队的活动为我们几月来主要的游击活动,红军而外,便衣队的组织多系过去地方武装中之负责人和战士以及区乡工作人员,成份都好。”⑬
无论是县区乡村干部自发形成的便衣队,还是由地方党组织或红军部队派出的便衣队,成员很多都是经过挑选的红军指战员和原先做过地方工作的党政干部、党员。便衣队以县区乡党和苏维埃的干部为核心,身穿便衣,和普通群众一样打扮。他们斗争坚决,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能够掌握政策,具有独立工作能力,为主力部队行军、打仗、隐蔽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加之便衣队队伍小,行动灵活、秘密,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清剿”,便衣队仍然坚持了下来,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红军战士
便衣队成员还有许多是来自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战士。为了加强地方工作,红二十八军在转战中经常抽出一定骨干力量到地方充实发展便衣队。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各部在柴家山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加强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从部队抽调骨干放到地方,建立和发展便衣队组织,以加强地方工作,建立和发展游击根据地,支援和配合部队行动。对于转战中的伤病员,红二十八军也要经常从部队中抽调干部、战士负责掩护安置他们,抽调出来的这些人员往往通过便衣队的形式开展活动。皖西便衣队的产生多半就是红二十八军或当地游击师为掩护伤员留下的人员。红二十五军西撤时留在根据地的300多名伤病员基本上都是由鄂东北道委组织人员安置的,治愈后他们大都成为鄂东北地区红军、游击队和便衣队的骨干力量。
为推动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紧密结合,商南县委于1935年7月从商南大队抽调部分骨干组成五支便衣队,分布在周围失陷的老根据地,成为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基本力量。1936年3月中旬,方永乐率部队途经黄冈县大崎山地区时,与当地地下党负责人漆先廷取得联系后,从部队抽出9名骨干组成便衣队留下进行地方工作。5月28日,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到达大崎山,为加强这一地区的工作,又从部队抽调10名骨干充实黄冈便衣队,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紧密结合,以大琦山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据王才定回忆,当时报名参加红军的赤卫军战士大部分都分到各连队,也有少数人分到便衣队。郑位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由游击队中抽些人到便衣队去了。”⑭可见各部队武装是便衣队的一大重要来源,红军将士是便衣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普通群众
以群众工作为重要支撑点的便衣队,其成员的另一重要来源即是普通群众。1933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报告中谈到便衣队的来源时明确指出:“这个运动本来是从群众中自己发生起来的革命的农民,三人五人自己成立一队,用短枪短刀矛等武装,在夜间去杀反动或袭击敌人。”⑮中央军委在关于鄂豫皖今后作战的研究中也建议:“农民自卫团是游击队和便衣队的后备军,从农民自卫团中挑选积极的农民编成便衣队。”⑯鄂豫皖省委号召“赤白区群众联合起来,工农兵团结起来……参加便衣队”⑰。在制定工作任务时强调要“号召群众发展便衣队,杀反动打民团,骚动匪军,断绝敌人交通,扩大红军来为保障春收春耕为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新区域而斗争”⑱。鄂豫皖省委多次指示下属机构重视吸收群众参加便衣队,在给皖西北道委的指示中强调:“要积极的在白旗下面发展群众的便衣队的组织,从跑反的群众中选择积极忠实的群众参加便衣队,要深入到白区内面去进行肃反和组织群众工作,从便衣队和秘密组织所领导的开仓分粮斗争中,大胆的吸收英勇斗争的群众参加便衣队。”⑲
商固边境便衣队便是一个典例。当时商固边境地区的工农武装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打击敌人,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组成一大批便衣队分赴各地活动,派到固始境内的五支便衣队,队员大都是杨山矿工等普通群众。他们熟知当地地形地貌、风土人情,战时是兵、平常是民,与当地群众能密切配合鱼水相帮,“便衣队因他的社会关系,多少可以建立秘密工作和组织与领导这些组织的公开与秘密的活动”⑳。加之利用险要地形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在极端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能够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
此外,便衣队成员中还有一支较为特殊的力量——妇女。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许多妇运干部不仅积极配合协助便衣队工作,还踊跃参与到便衣队运动中来。据信阳地委党史征集编辑委员会妇运组的调查,1933年鄂东北地区就组织了有妇女群众参加的秘密便衣队。据夏紫忠回忆,1933年她被调到罗山特委任巡视员,负责巡视当地一、二、三便衣队的工作,那时各便衣队中女同志很少,东边有张宗杏、韩松山,西边只有她一人。此外,皖西北地区的两个医疗分院在根据地形势变化后难以继续在原活动地区存在,于1935年后被迫化整为零,女医务人员基本上都编入各便衣队,隐蔽在农民家里,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给伤病员治病。总体来说,当时便衣队中虽然妇女数量有限,但亦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三、便衣队的组织特性
由党员干部、红军战士和普通群众组成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是融合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组织。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便衣队的战略和战术都取得了较大成效。便衣队鲜明的党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强烈的斗争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是便衣队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一)鲜明的党性
便衣队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新生组织,从诞生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呈现出鲜明的党性。鄂豫皖省委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便衣队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便衣队的组织建构和领导。1934年6月,鄂豫皖省委明确提出在便衣队中发展党组织,“各队伍中尤其是便衣队中,不但要有党的组织,要改进其生活”㉑。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干部,逐步在队伍中建立起布尔什维克的实际领导。
红军主力西撤后,为适应复杂严峻的斗争环境,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鄂东北道委、罗陂孝特委、光麻特委、红罗光中心县委、红安县委和皖西特委(后扩组为皖鄂特委)、黄冈中心县委、商南县委等,先后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便衣队的组织领导。鄂东北道委将所属各级党组织调整后均以便衣队的形式开展活动,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兼任便衣队领导。鄂东北道委会系当地最高领导机关,当时鄂东北地区的便衣队、交通队等一百余人均为其下属组织。1935年中期,黄安五区产生的四支便衣队分队,都是由五区区委书记领导。豫东南根据地各县区1934年春率先进行了地方党和苏维埃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各县区委干部随便衣队、游击队行动,多数县区委书记兼任便衣队、游击队指导员。据郭述申等人回忆:“皖西一带的便衣队,总归皖西特委何耀邦同志领导。豫东南一带的便衣队,归商城县委书记‘张铁匠’领导。罗山、光山、黄安一带的便衣队,归道委会领导(陈守信负责)。此外罗陂孝一带也有便衣队,情况不清。由郑位孝领导,他们活动于平汉路边,这些便衣队总的说来,归二十八军领导,二十八军高敬亭常带一些人,到便衣队去检查。”㉒由于红二十八军经常流动作战,高敬亭经常率手枪团到各地便衣队检查工作。可见,便衣队一直是在红二十八军军政委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的。
无论是迫于形势自发形成的便衣队,还是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武装派出的便衣队,逐渐演变为由各道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领导的组织。各便衣队内部基本上都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并履行相当于工委、区委甚至县委或中心县委的职责,实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队长和指导员,一般由党和苏维埃的基层干部或红军干部任便衣队长,基层党委书记任指导员,大多数便衣队的负责人还兼任当地党委的书记。这样以来,“各区工作之决定,多半是区委区苏便衣大队之联席会议解决的”㉓。在党组织领导下,各便衣队紧密协同红二十八军和各游击师、独立团、战斗营开展工作。可以说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们至今一切秘密工作群众工作侦探工作,党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这便衣队的组织当中”㉔。
(二)广泛的群众性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鄂豫皖根据地便衣队之所以能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体现了广泛的群众性。便衣队是党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为完成特定历史使命而建立的工作队。工作队作为一种具有适应性和活跃性的制度运作,它起源于苏联时期的全权代表制度,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的“全权代表”。苏联的工作队大多以工人为主,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队成员并未脱离农民。他们能够真正深入农村,了解和掌握群众的特点,动员与组织群众,同时也注重对自身进行改造。
正是这种对于农民的不同态度以及政策执行的不同方式,使便衣队在解决基层问题方面更具优势。便衣队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既能号召和领导群众,又能为群众办事,深受群众的信任,从而形成了便衣队生存的基础。正如郭述申所言:“便衣队所以能立住脚,坚持几年的斗争,主要依靠的就是群众。”㉕林维先总结道:“便衣队所以能站稳脚跟,坚持斗争,发展壮大,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比主力部队更能接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㉖
便衣队在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同时,切实关心群众疾苦,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在实际活动中,想方设法打击豪绅恶霸,严惩反动分子,为民除害;注意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困难并做好优抚工作;注意执行红军的工作纪律,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按价赔偿,吃用群众的东西给钱或归还等等。正如高敬亭所言:“广大革命群众,对敌人憎恨极深,对我红军(便衣队)非常拥护。”㉗在当时“工作好点的区域,便衣队组织群众,发展党,带群众一路分粮,帮群众一路杀反动,很有些成绩……群众工作最好之地,便衣队白天可以与群众一路耕种,匪军不能发觉,只有当地反动和民团出发才能发觉。”㉘鹞落坪的总人口不到两百人,参加便衣队的就有四五十人,再加上交通员、采购员、情报员,在不到两百人中差不多有一百余青年男女为红军服务㉙。便衣队以实际行动赢得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群众结成了情同鱼水的紧密关系,群众从内心拥护便衣队,积极协助便衣队开展工作。群众的全力支援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实基础。
许多便衣队还发展有小便衣队,据郭述申等人回忆:“便衣队一般的不发展,但也有组织小便衣队的,如皖西、太湖一带,便衣队将本地积极的农民给他拐子枪等,组织小便衣队,大便衣队一二个人带领他们(小便衣队)出去分粮等。小便衣队是不脱离生产的。”㉚到1937年初,鄂豫皖根据地共发展有不脱离生产的小便衣队16个,他们在沟通便衣队与群众的关系及协助便衣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强烈的斗争性
斗争性是便衣队的鲜明特征,便衣队从一成立就把“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便衣队因斗争而生,为斗争而存,并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便衣队积极开展对敌独立作战。1935年1月,黄安、罗山、经扶三县便衣队合力攻打了罗山县最反动的九里十八寨总寨香炉寺,全歼守敌,镇压了反动民团头子、伪联保主任陈仲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6年4月,黄安三区、四区的便衣队攻克檀树岗,烧毁碉堡,并击毙团丁20余人,接着又攻克麻城县余家河等数十座碉堡,声威大震。
便衣队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开展作战行动。1934年11月,在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的第二天,罗陂孝特委组织便衣队在罗山至汉口的公路沿线袭扰敌人,炸毁罗汉公路上的公路桥和12辆军用卡车,使敌人在罗汉公路的运输受阻,牵制了敌人两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㉛,策应了红二十五军的转移。1936年秋,河口县便衣队“在得到敌人进军老君山根据地的情报后,率先烧掉了从光山通往新集的‘经光桥’,使得敌人无法进兵”。年底,商南县委便衣队配合手枪团横扫敌人碉堡,取得重大胜利。灵山便衣队配合红军攻占敌人的磨盘寨据点,打下重兵防守的刘家河据点㉜。
除独立作战和配合红军行动外,便衣队还坚决打击所在活动地区的地主村霸。关于这一点,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便衣队成立之初就“深入到……农村中去杀反动(分子),没收他们的东西。”㉝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后,外逃的豪绅地主还乡,晚上住在碉堡里,白天经常出来欺压和胁迫群众,为非作歹,群众非常痛恨。于是,“为了保护革命干部和群众,鄂东北道委领导游击队、便衣队镇压反动首恶分子”㉞。在其他地区,便衣队开展了打碉堡、消灭“地抓哨”“七破”杀敌立功等活动。便衣队与地主村霸的斗争,既震慑了敌人,又有效保护了群众利益,为坚持长期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便衣队十分重视对敌斗争策略。对地主、富农及国民党基层政权人员,改变最初一概杀掉的“左”倾做法,实行区别对待政策,运用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减少了便衣队活动的阻力。对给敌人做事的联保主任、保甲长,注重建立统一战线,争取他们站到人民群众的一边,在便衣队的努力下,一部分联保主任、保甲长表面上为敌人效劳,实际上成了“白皮红心”的人物。在对待僧侣和僧尼方面,切实保障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改变了以前打菩萨、烧庙宇、逼僧尼还俗的做法,使一些庙宇道观成为便衣队聚散的场所。这种灵活的斗争策略,壮大了革命力量,分化和削弱了敌对势力,保证了便衣队进攻能取胜、防守有保障、给养有来源、撤退有掩护,使便衣队的工作呈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四、便衣队的历史贡献
便衣队作为鄂豫皖地区革命斗争的基本力量之一,为中国革命事业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推动党组织恢复与重建、建立与扩大游击根据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造就革命队伍骨干力量、积累游击战争宝贵经验等方面均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推动了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
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后,在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党的工作陷于瘫痪。在危急关头,根据地各便衣队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积极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组织,聚集被打散的革命力量,审慎地把在斗争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例如,黄冈便衣队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展了一百多名党员,组织了十几个党支部,建立了四个区委,成立了黄冈中心县委;皖西便衣七分队在黄梅、宿松边界一带活动时,帮助地下党发展党员,组织了三个支部,并建立了宿黄边区区委。各地便衣队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到1935年底,部分恢复了各老区党的基层组织,随后又在新开辟的根据地逐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使边区各地又有了党的坚强领导,老根据地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新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得以形成,为边区各项工作的继续开展奠定了基础,为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坚持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建立与扩大了游击根据地
便衣队充分发挥自身隐蔽分散、灵活精干,便于联系和发动群众,易在当地立足生根的特点,将活动区域发展成小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将各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例如,皖西特委和后来皖鄂边区特委领导的22支便衣队,在主力红军的配合下,不到一年时间,不仅在皖西建立了若干个小块立足点,还在鹞落坪周围纵横百余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块较大、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将舒霍潜太游击根据地逐步扩大到皖鄂边区,在十余县境形成纵横二三百里的大块游击根据地。鄂东北独立团领导的灵山便衣队在独立团、游击师和特务营的协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在平汉铁路两侧的罗山、信阳、应山三县之间的地区开辟出一大片游击根据地。各便衣队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建立起一块块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这些基地实际上成为秘密的苏维埃政权,便衣队活动的地区成了红二十八军主力部队隐蔽的立足点,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给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很大的支援。由于便衣队的经营,使得红军所到之处大都有根据地作为依托,可以声东击西,变幻莫测,给敌人有力打击。1936年6月28日《申报》刊登的《麻城民众请愿“剿匪”》一文指出:“最近‘匪’以地方绝无抵抗实力,为久踞计,择地建设苏区……现在(麻城)县境以内,‘匪’已明目张胆,四乡皆有组织,‘匪’区日见扩大,滋蔓难图……而切邻之黄冈、黄陂、礼山、黄安、商城、立煌等县,闻皆有一部分与麻城相同。”这一报道基本反映了当时根据地发展的形势。
(三)积极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
便衣队以小分队游击作战配合大部队作战,能够完成主力红军难以完成的某些任务,成为坚持鄂豫皖革命斗争的第二支重要力量。便衣队作为坚持根据地对敌斗争的重要武装力量,除了以自己活动区为内线打击反动势力外,还充分发挥自身特点,以其他游击根据地为外线,通过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作战。这些方式包括: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带路打先锋;破坏敌人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伏袭小股敌人,袭击敌人增援部队;捣毁敌人的后方,截击敌军军用物资和军事设施;配合红军消灭敌人的据点,摧毁敌人的碉堡;到敌人据点周围骚扰牵制敌人等。便衣队既担任了对敌斗争的前哨,扰乱和牵制了敌人相当大的兵力,又充分发动了群众,成为保障供给的后方,既有效地消灭了敌人、又保存了自己,成为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得力助手。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方武装在便衣队的配合下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多次进攻和“清剿”。高敬亭高度肯定了便衣队这一作用:“由于便衣队的积极活动,有时主力部队不能担负的任务,而便衣队不费什么力量就能完成了。这就增强了我们坚持大别山、桐柏山和周围平原地区斗争的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㉟郑位三专门强调:“二十八军的力量是两个拳头,一个是便衣队,一个是二十八军大游击队,这也就是当时的组织系统。”㊱
(四)造就了革命队伍的骨干力量
三年游击战争把便衣队锻炼成一支打不散、拖不跨的作战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英勇善战的军政干部。郑位三指出,新四军成立时,集合南方各部游击队,以高敬亭所部最大,也是得力于便衣队的好处。1937年9月,分散的红二十八军、各地便衣队和地方武装奉命到七里坪接受改编,部队总人数1800余人,便衣队人数竟占三分之一,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鄂豫边人民抗日军”,并在黄安县七里坪设立了招兵站,成立新兵营,积极扩大武装。1938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便衣队为随后坚持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保卫和建设边区提供了坚强的武装力量。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便衣队造就了一大批忠诚坚定的党政军骨干,这些骨干既能为群众办事,又能号召和掌握群众,成为组建新工作队的中坚力量。以便衣队为基础形成的新工作队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立下了不朽功勋。
(五)积累了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
便衣队为人民军队大力发展游击武装、深入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基本经验。便衣队依托大别山的有利地形,紧紧依靠鄂豫皖边区群众,紧密协同主力红军和各地方武装,采取正确的政策策略,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基本上恢复了老区,开辟了更大的新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创造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丰富了土地革命的实践,是人民战争思想在鄂豫皖边区的创造性发展。抗日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组建便衣队的经验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普遍应用和发展,当时活跃在敌占区的敌后武装工作队无论是组织形式、开展活动的方式方法以及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都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便衣队极为相似,这就充分证明了便衣队这一组织形式在对敌斗争中的实效性以及持续的影响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语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便衣队是根据地军民为应对艰苦的斗争环境,逐渐摸索、自发组织,得到中共中央、鄂豫皖党政军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持,进而逐步完善起来的一种对敌斗争形式。三年的游击战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有大小111支便衣队,600余人,分布在鄂豫皖边界的22个县境内,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时期和地区,组建方式不尽相同,成员结构较为多样。在各地方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便衣队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深深扎根人民群众中间,注重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实现了党性、人民性和斗争性的统一。便衣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大创举,是坚持鄂豫皖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郑位三在回忆鄂豫皖地区三年游击战时强调:“我们能在那里坚持三年游击战……最主要的是革命干部、群众根据当时的特点,创造了适合当地环境的斗争形式——便衣队,打开了局面。便衣队发动了群众,壮大了红二十八军,坚持了三年游击战。”㊲便衣队还造就了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英勇善战的军政干部,锻炼出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红军部队,为人民军队开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斗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