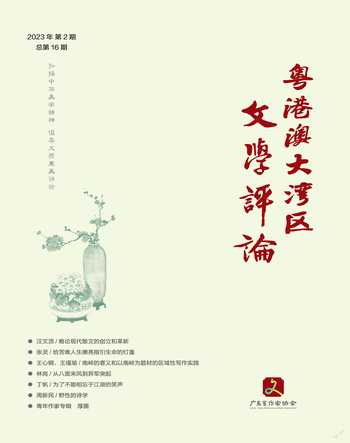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生成经验及前景
2023-06-23古远清
古远清
摘要:“世界华文文学”是指全球作家用华文创作的作品,是一个遍及世界五大洲,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中国大陆。但具体研究起来,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指中国大陆以外有着离散创伤、漂泊体验、文化差异的海外华文文学, 台港澳地区的文学也不能忽视。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突围”出来的新兴学科,从20世纪70年代末蹒跚起步,走过了从无到有、从逼仄到宽广、从单调到丰富的过程,然后在新世纪蓬勃发展起来,在日益走向成熟,其发展前景日新月异,令人乐观。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学科
40多年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在前沿批评、史料挖掘、地区和国别华文文学史的编写、学科论著的发表与出版,以及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但改变了世界华文文学在各学科的地位和影响,而且使其成为新世纪的一门显学。其中《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三本书的联袂写作与出版,便是这门学科呈葳蕤之貌的标志。尤其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的编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系“初写”“试写”,其中有几个問题必须厘清:
所谓“世界华文文学”,首先是指“世界”的,包括中国陆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是指华语或汉语写作;“文学”,是将用华文书写的考察报告、计划书这类应用文文体排斥在外。可有人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指“世界各地以华文创作的有关华人世界的作品”1,其实作品的内容不关乎华人生活和华人世界,但只要是用华文创作的作品,就是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不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也不是缺乏异域文化碰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延伸。“世界华文文学”亦不同于缺少文化归属与身份认同的“世界文学”。前者是属概念,后者是种概念。即前者范围小于后者。后者通常是指不用华文写作的文学,作者多为非华裔的外国人。当然,前者也不是无所不包的“巨无霸”式的学科,其文学语言限定在华文,作者亦多为华人。华人用外语写的作品,一般不认为是华文文学,但两者的界线也不可能区分得如楚河汉界那样清楚。模糊性、交叉性,本是文艺新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
“世界华文文学”亦不同于“海外华文文学”。前者着眼于“世界”,后者则从中国本位着眼。它“关系着经济、政治、历史、国别、种族、文化等各种共通与差异,生发出来的关于语言与生存、漂泊与离散、抵抗与认同、边缘与中心、民族性与世界性等丰富多元的话题”1。华文文学与“世界汉学”还有重叠之处,即是说,研究华文文学,不应将汉学家对华文文学的耕耘视而不见,不能将华文文学的“华文”与中华文化画等号,以免缩小华文文学的版图。必须把越南政治家胡志明、美国汉学家葛浩文、韩国华文作家许世旭等人用汉语书写的作品包括在世界华文文学之内。他们创作的华语作品虽然不是中国文学,但肯定是华文文学,再如美国当代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品唐诗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正是在“华文”与“华人”观念的纠葛中,在“华语”与“汉语”命名的尴尬中,在学科定位的困窘中,给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学术视野,在困扰中、在争议中“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脱颖而出,已经成功地建立。
众所周知,一门新学科的建立,无非是要有一支稳定的、优秀的研究队伍,著名大学开这门课,召开过多次国际研讨会,有自己的刊物,有自己的学会,有这门学科的带头人,有自己的学科著作和教材,有自己的研究年鉴,还要有这门学科的论文选。所有这些,“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完全具备。以开课而论,它不再是少数学者“闯关东”,在中国大陆已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近百所高校开这门课,有的学校还招了博士生。国际研讨会也召开了将近二十次,走出了“赶集式”的浮浅,每一届都有厚重的论文集问世。
此外,“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早在2001年就在广州建立,这对中外的文学交流和华文文学的发展繁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华文文学》杂志坚持了近四十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也出版了将近十大册,教材和著作方面有《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当代台港文学概论》《世界华文文学概论》,研究队伍方面有以刘登翰、饶芃子、黄万华为代表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刘登翰从事华文文学研究时间比饶芃子和黄万华早,他的研究覆盖面巨大,尤其是主编三种台港澳文学史为世人所瞩目。这位华文文学研究“专业户”的论著,至今还成为后学的重要学术资源;而黄万华著作多、覆盖面比刘登翰更大。他也有台湾、香港文学史及《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另还有学科理论探讨的《百年华文文学史论》。和刘登翰不同的是,他的“三史”均是私家治史。至于以扶助新人著称的饶芃子,以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独树一帜,在学会的组织工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可惜因病使其“余热”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除上述三人外,其他学者在华文文学的命名、世界华文文学空间的界定、世界华文文学历史与现状、区域性特色的诠释、海外华文文学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台港澳作家如何入史等问题做了探索。在华文文学这类著作出版方面,获得了空前丰收,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二十九本。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立有雄厚的基础,更不用说全球有众多的华文文学作品做这门学科的“垫底”。仅新移民文学就有2006年成都出版社出版的、由少君主编的海外新移民文学大系《北美经典五重奏》,2007年又推出按海外华文文学社团结集的七卷本《新移民文学社团交响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华人周刊》张辉总策划的“世界华人文库”系列丛书已出版了三辑,包括小说、散文、诗歌、随笔、作品评论等多种文类的作品集、选集共五十多本,是迄今为止规模宏大、品种多样、汇集作家最多的大型新移民文学丛书。1
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立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以广东《花城》创刊号所刊登的曾敏之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为标志,具体时间是1979年5月。但这门学科有生成前史,即1975年夏天旅美华人所开展的小规模认同新中国文艺运动。在70年代后期,从美国赴祖国大陆访问的於梨华、聂华苓、叶嘉莹等人为世界各地华文作家的汇合做过架设桥梁的工作。还有1979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前途座谈会”,以及聂华苓伉俪所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正如沈庆利所说:“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建构,是海内外学界和华人作家持续联动、互动的结果,由此也决定了该学科融纳国际性、移动性、本土性和边缘性于一体的学科特色。”2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的分期,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79年5月到1982年“首届台湾香港文学研讨会”的召开,为酝酿时期。1983年到1993年在庐山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为成长时期。从1994年到2001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建立,为壮大时期。2001年至当下,为丰收时期。
有一种成见必须打破,就是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没有走出它的幼年期,还不成熟,不值得写史,更不应该将其经典化。其实,经典化离不开“实在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从‘实在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两个维度来理解经典。‘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从关系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而同时文学经典亦是属于时代(即一定的历史坐标系中)与特定地域的。”3按照这个标准,完全可以将在北美最有实力、最有后劲,在华人世界中知名度极高的哈金这类作家其作品从“实在本体论”和“关系本体论”两个维度加以经典化。为了未盖棺先定论,今天在场的人就要有火眼金睛辨识和肯定的目光,有不做事后诸葛亮的大胆判断、作经典化的勇气。所谓时间老人的筛选,固然必要,但这不应当成为逃避经典化责任的借口。盲目经典化固然不可取,但否定经典化,不让散发出淡淡幽光的一块玉发掘出来,也不一定是正途。大家知道。“世界华文文学学科”风风雨雨已走过四十多年,它处于动态的建构之中,不能稳定后再写史。对作家不一定要去世了才能定论。至于通俗文学如以写武侠小说著称的金庸和以写言情小说成名的琼瑶,不能上文学史,更不能封为经典作家,这同样是一种偏见。通俗文学有广大的读者群,它并不因为高雅文学的竞争就被排挤了出去。严肃文学读者有限,而通俗文学可以走向民间,况且有时雅與俗也很难区别。谁也不能保证通俗文学没有雅的成分,金庸一类的优秀作品未来不会上升为高雅文学。
学术界多次呼吁撰写《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如陈辽在《我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前言中说:“20世纪‘五四以后,过了30年,我国有了现代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后30年,1979年有了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到2009年以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将会出现。”1可这种“研究史”千呼万唤不出来。撰写学科史的难度比编着华文文学创作史难度还要大,因此一直只有个别专题学科史,如《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2《台湾文学研究35年》3,以及一些“访问记”“对话录”一类的回忆录文章,缺乏更系统更完整的整体性观照。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危机在于缺乏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建立,不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科学地总结世界华文文学所走过的道路。通过世界华文文学的经验总结,去建设一个我们所珍惜所守护的华文文学世界。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生成经验
20世纪快要结束时,杨匡汉等北京学者在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这个选题很有开创性,但总结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验,除“第一世界”的中国大陆文学外,“第二世界”的台港澳文学不能缺席,甚至作为参照系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华文文学也应有一席地位。
世界华文文学经验的总结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它的第一个经验是:华文文学是一种跨区域、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的“文学共同体”4。跨区域,是指它包括海内的中国境外台港澳文学,另涵盖多描写游子思乡、文化冲突和生存压力的海外华文文学;区域主要是指北美、欧洲和澳洲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东北亚华文文学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文学。跨学科,是指跨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跨时代是指从19世纪中叶华工的口头文学或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加州天使岛木壁上留下的汉语诗歌到21世纪的华文作家长篇、短篇创作。跨文化,是指华文文学研究包括作家的母国和居住国及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书写。跨文化研究本是世界华文文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旨在研究华文文学作家创作的初衷,在两种或多种的文化冲突及交融的表现,简言之就是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线的文化。这里有文化认同问题,即作家对母国或居住国特定文化的归属和认定,它有中华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价值的特定指向性。
第二个经验是“双重传统”。这是周策纵在1988年8月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德国歌德学院联合在新加坡主办的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提出来的。任何有经典之作的国家,其文学都有继承性,都有来龙去脉,华文文学也必然有自己的传统。在中国大陆,从《诗经》开始,到屈原,到唐宋,到明清,均有“文以载道”一类的文学传统。世界华文文学自然无法与“华”脱离关系,更不能与中华文化断奶。华文文学的“华”,不仅指华文,也指华人,这是华文文学赖以生存的命脉,是无法抛弃的。但华文文学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单靠这个“根”而没有居住国的本土经验,是无法开花结果的,正如王润华所说:“因为海外华人多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地的文学传统( NativeLiteraryTradition)。”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据王润华的观察,“都已融合了‘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我们目前如果读一本新加坡的小说集或诗集,虽然是用华文创作,但字里行间的世界观、取材、甚至文字之使用,对内行的人来说,跟中国大陆的作品比较,是有差别的,因为它容纳了本土文学传统的元素。一个地区的文学建立了本土文学传统之后,这种文学便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更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文学之支流。”1也正因此,周策纵认为应该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
和“双重传统”关联的是“双重视角”,如看待美国华裔文学代表汤婷婷、谭思美的作品,不应在语言和华文、族群与华人之间打转,而应聚焦世界华文文学版图的延伸性:“华人文学的形态,先天就带有某种混合性,故世界华文文学不应固守‘华文的疆界。华人文学作品不管有无中译本,都应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研究对象。这不仅可以扩展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版图,而且可以起到对照和互为补充的作用。”2
第三个经验是“多元文化中心论”3。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拥有全球最多的作家队伍,最多的图书出版单位,最多的阅读人口,最广泛的文学市场,因而有人认为世界华文文学中心在大陆。我们不否认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的重要性,但华文文学的中心系相对而言,且不能认为只有一个中心,而应承认多元文化中心的存在。这多元文化中心,包括许多种文化区域,因文化背景差异,出现各地的独特文坛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主体论”均在动摇,世界多元文化已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以美国华文文学而论, 不仅接受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而且在空间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焦虑中担负着时代的文化命题。作家们从外地漂泊到美国后尽管各自人生经历不同,但离不开母国的历史传统,在这一基础上出现的华文文学,才能展现出各自的特色。“一方面,华人移民共同的民族属性和中华文化背景,规制了美国华文文学的族属性,使之不仅区别于美国的主流文学,也不同于美国其他少数族裔的文学,如非裔黑人文学、犹太裔文学、亚裔的其他族裔文学等;另一方面不同时代华人移民的历史际遇、文化背景、生存方式和人生经历,以及介入美国社会的方式与深度,在和西方文化的交会、冲突和融摄中,也发展出不同时期美华文学的不同形态和不同文化关注点,响应着他们对于故国母土的历史焦灼和自身生存的文化困惑。因此,美华文学文化主题的演化,既归根于移民在故国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移出动因中的时代和环境因素,同时又是移民在所居国生存状态和文化适应的反映。”4也就是说,在多维文化视域中重审中国形象的当下美国华文文学,已走出放逐文学的模式,也不再重复“留学生文学”的写法,更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学的写法,而形成与加拿大华文文学、英国华文文学相似的那种既有独立性,又有自主性的文学。有众多华文报刊和华文作家組织、有哈金等人的优秀作品的美国,尤其是北美的华文文学突破了古代中国因位居“天下”的中心位置而以代表“天下”即“天下之中央”的局限,不妨也看作是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同样,东南亚华文作家有众多人不出生在中国,在心理上和社会关系、文化风俗上,距离华人的祖先渐行渐远。没有远涉重洋的他们,对自己的母国拥抱得更紧,其爱国主义的“国”也不是专指中国。在新的土地上,其爱的主题会发生变异,对新的国家的爱也会生根发芽长大。就是少数来自中国的作家,从叶落归根转换为落地生根,也就不可能完全按照中国经验写作。如果完全模仿中国作家,“就会令马华作品失掉创新性,令马华文学失掉主体性,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1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或来自“中国台港的作家”,对异国文化的迷茫与刺痛,其在他乡行走所创作的文学,具有界域意识和认同焦虑的核心意识,这促使他们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中国的华文文学中心。如五十年代美国的“白马社”人多势众,影响不可小视,因而自称为“第三中国文学中心”。对有人认为世界华文文学“中心”只有一个是客观存在,中国文学就是“中心”这一说,也就是赖伯疆说的:“世界华文文学划分为一个中心,即中国(包括台港澳地区);两个基地,即东南亚(包括东亚的日本、朝鲜)和北美;三个发展中地区,即澳洲、欧洲和非洲。”2痖弦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得好:“海外华文文学无需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徘徊,无需堕入中心与边陲的迷思,谁写得好谁就是中心。搞得好,支流可以成为巨流,搞不好,主流也会变成细流,甚至不流。”3《新加坡作家报》也有人撰文认为各国华文文学是兄弟关系,而不是母体与子媳的关系。如果承认一个中心,就可能会出现狂妄自大与妄自菲薄两个极端。也就是说,如果有中心,也是多中心。对中国作家来说,不应以主流自居歧视别的国家的华文作家。别的国家的华文作家也不应以本土性为名完全脱离中华文学这个“根”。跨越族群、跨越语言、跨越身份的各国华文文学应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承认中国中心、东南亚中心、欧美澳中心的多元文化中心,有助于建立一个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这种多元文化中心论的出现,也使中国学者研究华文文学更谦和,更平易近人,更容易为对方所接受。杨松年如是说,华文文学“可以分成好几大块:中国大陆是一块,港、台、澳是一块,美、加是一块,欧洲是一块,东南亚又是另一块,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香港移民的增加,澳、纽华文文学又形成新的一块。”4这每一块均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中心。不过,应该说明的是,不管多少个中心,中国大陆作为华文文学的“源头”和“母体”,这个中心就是以“大”著称,任何中心均无法取代它。
为了和“多元文化中心”相呼应,90年代后,中国学者以世界华文文学为整体观照的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1994年王一川等合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5在“重写文学史”,该文库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卷,其中以“小说大师文库”的排名最具争议:原来有定评的茅盾惨被除名,而取而代之的金庸名居第四。在排名者看来,当代文学也有“文学大师”,但这“大师”不出在内地而出在香港,其取得成就的文类不是雅文学而是俗文学,这均显示了编选者研究百年中国文学中突破世界华文文学只有一种中心的局限,显示了文学的新视角。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如不把考据算在内,其理论构架、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从西方拿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的经验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域外,这经验促使了文学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本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分离出去不久的一门独立学科,对研究者的学识修养,要求并不很广很深。可自从80年代更新文学研究方法,尤其是提出“世界华文文学”的命题后,研究者仅知道大陆文学史,而不甚了解境外文学,不行了;或只知道境外文学,而对海外华文文学史知之甚少,也不行了。正是在更新文学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不少人打破专业分工限制,向中国大陆当代文学范围以外的领域进军。这在陈辽、曹惠民主编的《1898—1999百年中华文学史论》中有所表现。该书突出了“变革”的观念,统摄包括大陆、台港澳文学在内的整个百年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不像过去那样强调政治因素,或反过来强调文学因素,而是强调文学形态或运动方式对文学发展的作用;对当代文学论争中的阐述,强调了政治与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使这部跨区域文学史含有文化史的成分在内。
台港文学经验与海外华文文学经验同中有异,下面着重说“异”:
台港文学本来就是一座重镇,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地图上均占据有重要地位。它在参与建构中华文学中,作出了下列特殊的历史贡献:
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表现生活的空间。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是在不同的两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祖国大陆文学所表现的多是神州大地风貌,很少有人反映宝岛的民俗和文化生态,而台湾作家作品均留下了台湾同胞独特的面貌。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中国化及环保意识的觉醒,不同于大陆作家狭义的故乡情结的“乡愁”书写,还有“同志”书写和后现代、后殖民的书写方面,台湾文学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充实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使中国当代文学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多彩。
在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上,由于台湾开放比大陆早,接触西方文论与大陆的进程及角度不同,因而诸如比较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语言行动理论等,较早就被台湾引进。这是他们的文论建树有与大陆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20世纪中国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的文本“细读”法以及新批评的诸种方法,还有叶维廉的诗学(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远离了长久以来形成的理论思维模式,具有一种异质性,有大陆文论家所没有的理论深度。1949年以后在大陆中断的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乃至批判现实主义,在台湾也得到了延续。
在六七十年代,当大陆文学呈现一片荒芜景象时,这时台湾作家们没有被“下放”,文学团体没有被“砸烂”,他们仍然坚持创作,写出了像《将军族》(陈映真的小说)、《尹县长》(陈若曦的小说)、《乡愁》(余光中的诗)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片空白。
在表现中西文化冲突的对峙方面也有自己的特殊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如何处理西化与中化的问题。开始是西化占上风,如卡夫卡影响了台湾现代小说家,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兴的《家变》均从伊乔斯的作品中得到启示。艾略特则影响了现代诗。后来从恶性西化走向善性西化,如受现代主义影响比白先勇多的王祯和,他晚年的作品所呈现的是现代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奇异结合,其作品真正有价值的是自然主义感性所捕捉的东西。1
台湾部分作家用闽南话、客家话的方言特质丰富了大陆文学国语的内涵,让“白话文学”的道路变得更加宽广。
香港文学的经验与台湾文学不完全相同。
香港自1950年5月罗湖边境关闭从此与内地断裂后,作家们在外来者统治下从事创作,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生态造成与内地不同的特色,这特色表现在香港文学在时代的大动荡中历尽艰辛。这是一个寻找香港文化身份的过程,也是“南来”与“本土”作家从对峙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尽管没有出现更多大师级的作家和经典之作,但仍积累了自己的“香港经验”:自由身份。在东西方阵营冷战时期,港英当局的自由港政策,使香港文学不受或较少受政治干预,以至成为全球华人写作高度自由的地区。回归后特区政府也不制定应写什么不写什么的文艺政策,作家们均以个体为单位进行艺术创造。正是凭借香港作家的努力及其积累的香港经验,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使中国文学不致贫乏而真正成为多元共生、百花齐放的苗圃。
此外,还有边缘地位。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政治上看,香港均属非中心地位,这便使香港成了陆、港、澳、台文学交流的纽带。那里人才来去自由,雅俗作品百花盛开,不论是现代主义“蝙蝠”或后殖民“蝴蝶”,都能在这里共存共荣。当然,边緣地位不等于香港文学是边缘文学,更不是边角料文学。在六七十年代,内地众多作家停止了写作,可香港作家还在努力耕耘,出版了许多作品,它和台湾文学一起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空白。
再是本土立场。所谓“本土立场”,就是不论在“纵的继承”还是“横的移植”中,保持香港本土的文化特色,恪守本土的文化身份——这不是拒绝普遍性或背向全球化,而是因为越有本土特色的文学,越能引起岛外的重视,越容易走向世界。本土立场也不等于局限于写香港的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也可以写香港以外的事物。但不管是写外国还是写中国内地,处理题材时仍具有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本土视角,融入港人感受识见,他们用“香港造”的本土作品去形成自己的写作中心。
华文文学生成的经验,还应包括澳门的文学经验。澳门以华文文学为主,但也有别的地区没有的“土生文学”,即加入了中国澳门籍的土生葡人用葡萄牙语写的文学作品,这又是一个另类中心。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远景
探讨世界华文文学远景,有点像用后视镜来看前路的危险,但也不妨一试。
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不出其三:第一是将意义扩大,有更多的学校开设这门课;二是华文文学学科会脱离创作的依赖,而走向更独立的道路,以致自成一派;三是研究方法不再停留在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格局中,而从多学科互渗的交叉研究和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评价台港澳文学的成就和发展趋向。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所面对的是华文作家与学者、读者,只有通过调查,才能知道这门学科的走向。剩下的华文文学学科所面对的有如一片茫茫大海。我们必须去设想:未来的学者的研究范畴、方法如何超越前人。别的不说,仅开课而论,至少未来各高等学校开设华文文学课,越来越多的学者会具有“世界”意识、“世界”情怀,会倾向使用“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这便恢复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纯正性,并以主流形式出现在高校和论坛。即使有少部分学者在使用“华语语系文学”或“汉语新文学”等概念,但不太可能再去使用老名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不过,当概念过度整齐划一后,学科也就容易走向死板化。过度的规范本来是对学科发展的一种束缚,华文文学概念的驳杂与丰富,正是学科的一大胜利。
如同华文文学创作离不开海外漂泊、家园怀念和双向认同的模式一样,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有自己“离散”一类的话语体系和经验。尽管“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在名称和研究对象方面仍存在着诸多争议,但这争议至少说明这是一门有潜力、有生机、有众多学术生长点、大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可以持续发展的学科。
在研究题材的选择上,实行“拿来主义”,通过实践检验完成自主创新的命题,也就是说不再原地踏步。像北美华文文学研究,不再局限在于梨华、聂华苓、哈金等明星作家身上,会增加新出现的文学新人。港台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在继续研究白先勇、陈映真、刘以鬯、董桥等人的同时,把新生代作家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在文学史写作上,台湾不会再让大陆独占鳌头,会迎头赶上。以往期望本地作者写出自己的台湾新诗史,却千呼万唤不出来,如今在北京学者古继堂著作的刺激下,台湾已出现张双英、郑慧如、孟樊和杨宗翰等人写的台湾新诗史,以后可能还会出现,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台湾小说史、台湾散文史。至于香港本土学者写的香港文学史,以前一直缺席。在有了陈国球主编的两套《香港文学大系》后,这种空白也有可能填上。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不属“重写文学史”而属“初写”,但受“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陈思和等这些倡导“重写”者不仅要改良《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性质,而且还要改变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文艺观:把华文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以思想伦理为出发点的狭隘的研究思路中解放出来,对原来在华文文学史上缺席的作家重新补上和审视。这种审视,就是对过去夸大文学中的政治因素、人为地把华文文学区分为主流、支流乃至逆流公式的质疑,对那种以左右对峙唯一选择文学主潮论的质疑。华文文学研究者所追求的是一种在艺术标准下自由争鸣的风气,以改变过去的大一统学风,对过去出现的许多有争议的现象重审,在新的美学标准下涌现众多新的评价。
有了世界华文文学,就不会再按研究中国新文学的话语模式来研究华文文学。因为左翼史话语不全适合海外华文文学。这不仅解放了研究对象,而且有助于填平台港澳与大陆文学分隔的鸿沟。华文文学这种无定型的学科命名,使研究者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華文文学史做出崭新的解释。此外,它设定的作为大背景的世界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关系构图,有利于研究者寻找华文文学的源头和认识它与世界文学尤其是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同步性,确认华文文学发展成就绝不比世界其他语系的文学逊色,这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华文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三位一体,又有利于提高华文文学的研究水准。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华文文学拥有了更多的理论资源,为寻求新的学术生长点激活学科,研究者无不在做跨界也就是跨地域的延伸,其研究范畴在日益扩大,旧的研究模式由此进一步瓦解。所谓旧的研究模式,就是运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去套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这种模式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人物与环境的描写、语言的艺术性等方面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且评价作品时激动、兴奋远多于冷静的思考、论证。今后将不会再局限于以社会学、政治学为根基的传统批评路径。在面对新思维挑战的时候,会使用精神分析、叙事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文化人类学的批评方法,努力站在客观立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本是发展中的学科,也是有一定“风险性”的学科,它的不确定性与移动性和一些作家作品的前卫性,不是建立一门新学科的障碍而应视为获得生机的重要因素,也是区别于兄弟学科的一个重要地方。因此,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应具有更浓烈的学科意识,应允许不同途径去研究它,具体来说在中国高校是研究课题化与个人化同时并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均设有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部分,但台港澳文学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难中标,这类课题的立项已明显呈下降趋势。即使有,也是研究左派作家这类符合主旋律的题目。由于申报台港澳文学研究立项很难,一些不愿被边缘化而坚守阵地的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研究时,以自由选题和由个人兴趣出发为主。鉴于在大陆出版这方面的著作相当不易,审批时间又长,因而有个别学者到境外发展。那里出版速度快,且不会大量删改著者的文章。不过,繁体字书校对远比不上大陆严格,且这类书在大陆高校不算成果,因而这种民间化的写作出版带有“自娱”性质,其中以退休学者为主。陈平原曾说当前高校老师分两种:一种是“无课题有科研”,另一种是“无科研有课题”1。所谓“无科研有课题”,是指某些教师拿到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有数额巨大的资助后,以“包工头”自居,他的研究生便成了“打工仔”。这些人主要是为拿课题费和升职而“研究”,所以说是“有课题无科研”,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个人化与民间化,却属“无课题有科研”这种状况。
作为一门新学科来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是不可回避的,比如《世界华文文学通史》《世界华文文学编年史》《世界华文文学大系》《世界华文文学大辞典》等工具书籍的编纂。待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