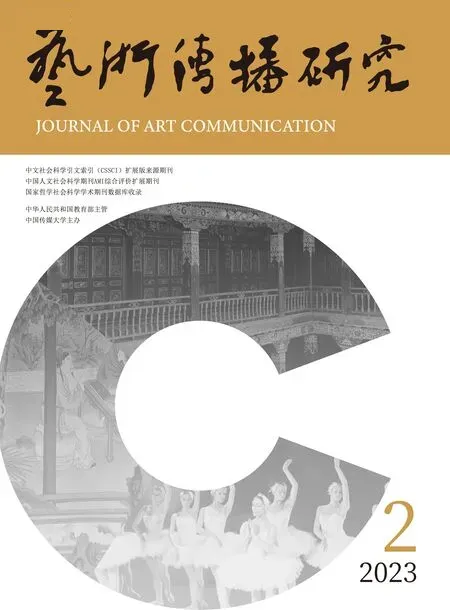早期中国现代性视野下的濮舜卿生平创作再考察
2023-06-21张彩虹
■ 张彩虹
濮舜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影,主要以其在戏剧界和电影界的创作实践为胜。201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女性电影先驱者研究工程”(The Women Film Pioneers Project,WFPP),濮舜卿以编剧身份入选。(1)参见https://wfpp.columbia.edu/pioneer/pu-shunqing/。有关她的生平资料和研究论文,大抵反映了国内外电影学界对这位中国电影的女性先驱的研究现状。不过,这些成果数量不多,且鲜见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展开的对其生平、创作演进轨迹的整体观照。(2)国内现有关于濮舜卿的研究为数不多,有代表性的是舒平的《第一个电影女编剧:濮舜卿》(《电影新作》1994年第5期)、左怀建的《女性视角与夏娃形象的改写——读濮舜卿剧作〈人间的乐园〉》(《名作欣赏》2008年第23期)、许航的《女性社会先锋的影像表达——濮舜卿电影剧作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等等。纵观濮舜卿1949年之前的生平与创作,不难发现其与早期中国现代性的“复合”与“多元”状态的“同频共振”。如果说“现代性一词是一个内涵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3)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那么早期中国现代性更是一个寓意丰富并正在不断衍生发展的复杂课题。有别于西方现代性在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构成的自反性张力,早期中国现代性以启蒙现代性为主调,以反帝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和民族独立为旨归,呈现出“复合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混沌”状态。(4)早期中国现代性的“复合”性与“多元”性研究,参见张振波、金太军:《复合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范式及其政治秩序图景》,《文史哲》2020年第3期;冯平、汪行福、王金林、孙向晨、徐洪兴、邓安庆:《“复杂现代性”框架下的核心价值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汪行福:《复杂现代性与思想再解放》,《学术界》2015年第10期;汪行福:《复杂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秩序重构》,《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方朝晖:《多元现代性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等等。其总体状态表现为:“在共时性结构上始终存在着前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多元对抗。在历时性结构上,现代文学思潮之嬗变也似乎呈现为非线性的‘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语)。但这种对抗与流动却是非逻辑的混杂,没有一种要素能够根深叶茂,取得真正的优势。”(5)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解读》,《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加强对文化运动的领导,引发革命文艺、普罗文艺热潮,直接推动了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崛起。与此同时,抵抗日本侵略、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也使“革命”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成为30至40年代中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在此背景下,濮舜卿的思想及创作与早期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相对应——从“教育启蒙”“戏剧、电影启蒙”到“法政启蒙”的“娜拉三态”观照了有关现代性的思辨在不同阶段的主题转化,呈现出“混沌”状态的镜像式存在。
一、始于现代教育的启蒙现代性之路

1924年,《妇女杂志》第10卷第3号刊发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女革命家向警予的《中等以上女学生的读书问题》一文,呼吁为拓展女子职业发展,应开办女子高等教育。而濮舜卿在1923年即已考入东南大学的预科,1927年3月毕业于该校的政治经济系。该校和1919年创办的燕京大学同是国内最早实现男女同招的大学,其教员队伍中既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主任王伯秋,也有词曲学大家吴梅等国学大师,可谓学风开放、兼容并蓄。(10)东南大学编印《国立东南大学一览》,1923年,第75-78页。在这样的校园氛围里,濮舜卿虽主修政法专业,却对诗词、戏剧情有独钟,是吴梅主持的该校学生社团——“潜社”的主要成员之一。(11)王季思:《忆潜社》,载王为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潜社”成立于1924年春,寄寓吴梅“希望远离政治漩涡,潜心学习之意”(12)徐燕婷:《吴梅词学教育新范式与潜社女词人的词学活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然而,就濮舜卿而言,以法政护航、以艺术熏陶性灵并开启民智才是兴趣所在。在校园戏剧活动中,她和教育专修科的侯曜相识、相恋,一起创办了东南剧社,联袂出演了侯曜的剧本《山河泪》(1925),成为继留日女作家白薇、北平女子高等师范附小教员吴瑞燕之后又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并登台表演的知识女性。侯曜对由教育转向戏剧的初衷的剖白,也代表了她的心声:“我……喜欢研究戏剧,以为戏剧教育民众,感化民众的力量比任何事业来得大。”(13)侯曜:《悲欢离合的生活》,《和平之神特刊》,1926年。早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亟待以启蒙理性革除封建积弊,唤起大众的个体解放意识,推动民族国家走向新生。这是激发濮舜卿以诗词、戏剧为媒介,拓展启蒙现代性对现实的影响力的外在动因。
濮舜卿的现代教育和戏剧启蒙之路,也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进入中国后引发的“出走的娜拉”社会寓言的时代镜像。该剧于1907年进入中国,剧中追求人格独立的新女性“娜拉”的形象对早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8年《新青年》杂志出版的“易卜生专号”,引出了胡适、田汉、丁西林、欧阳予倩、郭沫若等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性作家一系列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倡导恋爱自由的剧作。然而,囿于性别差异,男性作家对封建伦理压制下的女性痛苦很难有切近的“具身”体验,所以难免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或“救赎”姿态。因此,“尽管胡、陆、田、丁等男性作家重构了易卜生的戏剧模式,倡导女性解放,但他们关于性别和女性身份的观点却受到一种自我参照的立场限制,即男性和女性都作为公民肩负着国家改革的共同责任。这种往往以男性为导向的‘改革妇女’的话语并没有充分考虑妇女自身的作用,以回应她们的社会和历史使命”(14)Li Guo,“Rethinking Theatrical Images of the New Woman in China’s Republican Era”,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no.2(2013).。1926年《妇女杂志》第11卷第6号上刊发的宋淑贞的文章《期望女文学家的崛起》表示,“文学是以情感为主的,而女子心思幽静,富于感情,自然与文学最为相宜”;与男子读书多为博取功名不同,“女子是多数赋性纯洁,不易沾染社会的恶习,发露其天赋之灵思美感,研究文学,比较很易成功”。(15)宋淑贞:《期望女文学家的崛起》,《妇女杂志(上海)》1926年第12卷第6期。当然,女性写作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现代教育的普及。有统计称,截至1930年,全国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为1653016人,其中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有90386人,受过大学和专修学校等高等教育的只有3283人,占同期男性的10.81%,而出国留学者更是格外稀少,截至1931年仅为227人,不到留学总人数的1/8。(16)啸云:《现阶段女子教育的问题检讨》,《妇女生活》1936年第2卷第5期。即便是有幸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其走向独立自主之路依然困难重重。不过,濮舜卿在性格志趣上的爽朗潇洒,决定了她的戏剧、电影创作不会拘泥于同时代女作家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犹豫、彷徨、感伤的自叙色彩,而是更富有积极乐观的理想主义倾向。1927年,她在《妇女杂志》上发表《易卜生与史德林堡之妇女观》一文,指出《玩偶之家》敲响了“妇女解放的警钟”,相较于“莎翁的妇女是能支配一切,造福一切的幸运之神”,易卜生对妇女的“同情的态度和鼓励的态度”才是最可取的。(17)濮舜卿:《易卜生与史德林堡之妇女观》,《妇女杂志(上海)》1927年第13卷第9期。因此,濮舜卿的戏剧创作也多着眼于以“智慧”(知识)开启女性心智,鼓舞女性自强、自立的反抗精神,她也由此自觉践行了以现代教育唤起民族意识更新的启蒙之路。
二、影、戏双栖:启蒙现代性的媒介先行者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18)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载金元浦编《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有别于西方现代性在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自反结构,源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中国现代性主要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将小说、戏剧的改良视为在社会上推广和普及启蒙现代性的一种媒介工具。濮舜卿的戏剧和电影生涯集中在1924—1929年。相对于具有传统优势的戏剧,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对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媒介的接纳程度并不高,电影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不被传统文化界认可和接纳。对此,从美国学习戏剧归来并于1925年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标准化电影剧本《申屠氏》的洪深感慨道:“我有两个观念,第一,我以为做影戏,是正当职业,在电影界劳心劳力混口饭吃,也同人力车夫。跑了一身大汗,赚两角小洋车钱一般,不是什么可耻的事。第二,凡是道德人格的名誉,乃是个人的事,与职业没有多大关系的,……不过不幸社会对于电影界,格外的苛求,格外的注意罢了。”(19)洪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8页。同一时期,美国电影界倒是已经出现大量写作电影脚本的“脚本女孩”(script girls)。她们多为白人中产家庭主妇,还不乏曾为杂志撰稿的女作者。她们在公开投稿或写作比赛中胜出,为默片撰写几行、一段或一页的情节大纲,赚取稿酬以提升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身份与地位。(20)See William K.Everson,American Silent Film(New York:DaCapo Press,1998),p.32;and Tom Stempel,Framework:A History of Screenwriting in American Film(New York:Continuum,1988),pp.10-14.这种类似兼职的工作深受女性喜爱,因为它既不妨碍女性承担家庭义务,又能“追求更多创造性体验”(21)Martin F.Norden,“Women in the Early Film Industry”,Wide Angle 6,no.3(1984):64.See Anne Morey,Hollywood Outsiders:The Adaptation of the Film Industry,1913-1934(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48-49.,并且较容易获得,毕竟“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个新行业,所以大门向女性敞开”(22)Cari Beauchamp,“Frances Marion:‘Writing on the Sand With the Wind Blowing’,”Creative Screenwriting 1,no.3(Fall,1994):56.。美国最早的有记录可考的电影女编剧是卡莱姆制作公司的演员兼作家吉恩·冈蒂耶(Gene Gauntier),她从1907年就开始写“粗糙的”剧本——“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短篇故事、当前戏剧中的一个场景、报纸上的一个标题”(23)Gene Gauntier,“Blazing the Trail,” Woman’s Home Companion LV,10 (Oct,1928):183.。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约50%的好莱坞电影剧本是由女编剧撰写的。(24)Wendy Holliday,“Hollywood’s Modern Women:Screenwriting,Work Culture,and Feminism,1910-1940”(PhD.diss.,New York University,1995),p.100,114,140(note 49),144(note 82).然而,同样因为性别歧视,大部分女编剧都只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她们的作品,电影文学的概念也是迟至40年代才在好莱坞确立。(25)邵牧君:《电影、文学和电影文学》,《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相较而言,中国电影文学的地位确立要更晚一些,像1935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就收录有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却未包含电影剧本。因此,对濮舜卿来说,与大洋彼岸的女性先驱者一样,投身电影业着实需要一番对抗流俗、跨越媒介、挑战自我的见识与勇气。
1924年,濮舜卿随侯曜加入由留美学生梅雪俦等人创办的长城画片公司,该公司前期出品的多为侯曜编导的“移风易俗、针砭社会”的社会问题剧。1925年,该公司拍摄了根据濮舜卿剧本改编的同名电影《爱神的玩偶》,并在《申报》上连续刊登推广消息,称这部影片“为东南大学女学生濮舜卿所编,剧旨高尚,剧情曲折,对于现在的婚姻问题多所讨论”(26)《游艺消息》,《申报》1925年9月28日第14版;《长城新片〈爱神的玩偶〉告成》,《申报》1925年10月19日第3版;《游艺消息》,《申报》1925年10月22日第20版。。该片的主人公是小学教员明国英和“醒华大学”学生罗人俊,两人的自由恋爱被封建家庭阻挠,所以热切向往着“到新社会去找新生活”。濮舜卿在该片的“本事”中写道:“他们是有志的青年,终归是不肯做爱神的玩偶的。”(27)濮舜卿:《爱神的玩偶》,载郑培为、刘桂清编选《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这份对冲破封建家庭阻力的自信,充满了青年人特有的天真与浪漫。与同期的好莱坞女编剧热衷描写女主人公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性与掌控力,以及对刺激的冒险生活的向往等审美现代性表达不同,濮舜卿以启蒙主义为出发点,着力于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当然,《爱神的玩偶》在写作格式上与《申屠氏》相比也显稚拙,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写作的剧本,其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对电影文学的性别突破上。
除了编剧创作,濮舜卿还勇于尝试表演工作,她在侯曜执导的电影《弃妇》中饰演了追求妇女解放的侍女采兰。1926年,长城公司因经营不善,转向当时流行的古装片路线。因旨趣相悖,婚后的濮舜卿和丈夫侯曜转入新成立的民新影片公司,她也成为该公司主创人员中唯一的女性。濮舜卿全程参与了侯曜导演的反对封建压迫、提倡恋爱自由的《西厢记》,还与侯曜联合导演了《木兰从军》,(28)《剧场消息》,《申报》1927年6月6日第2版。跟随摄制队在沙漠中经受了“席地而卧”“腹饥如鼓”的恶劣条件,顺利完成了“黑山”外景戏的拍摄任务。(29)濮舜卿:《在沙漠过年之民新摄影队》,《电影月报》1928年第1期。濮舜卿的电影小说也被改编为反战题材影片《战地情天》,于1928年拍竣。(30)濮舜卿:《战地情天》,《电影月报》1928年第5期。濮舜卿在民新影片公司身兼数职,既担任编剧部主任,(31)《剧场消息·民新影片公司摄制蔡公时影片》,《申报》1928年6月30日第6版。又担任导演、剪辑、制片工作,当时的同业女性中无出其右者。1927年,上海电影界成立摄片助饷会,下设执行、导演、编剧等7个分委员会,濮舜卿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成员。(32)《上海电影界摄片助饷会成立大会》,《申报》1927年7月7日第15版。20世纪20年代,即使是好莱坞的女编剧们,也必须在社会空间和私人生活之间保持脆弱平衡:一方面,她们笔下的女性人物越来越具有现代感和掌控欲;另一方面,她们自己却要在媒介中刻意打造具有“女人味”的、“没有女性主义的野心”的、“在写作的同时安于做一个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形象。与此同时,她们还不得不忍受性别歧视导致的同工不同酬。(33)Aline Carter,“The Muse of the Reel,”Motion Picture Magazine XXI,no.2(March,1921):62,105.因此,可以料想,身处当时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社会的濮舜卿,也必须付出更多的勇气和努力,才能在早期中国电影业参与多种职业身份的实践,并获得上海电影界对她能力和地位的肯定。
随着阅历的增加,濮舜卿对社会事务的关注不断加深,创作选材也随之在女性解放、婚姻自主类的议题之上加入了更为宽泛的社会时政问题。早在1926年,她创作的剧本《芙蓉泪》就已获得“中华国民拒毒会”电影剧本征文比赛的甲项奖。(34)《拒毒会电影征求昨日揭晓》,《申报》1926年7月18日第15版。1927年,她的文章《她的新生命》获得该年“全国女青年协会编剧部”举办的评奖征文活动第二名。(35)《女青年协会悬奖征文揭晓》,《申报》1927年9月7日第15版。同时,她还保持着戏剧创作的热情。1927年,在独幕话剧《黎明》中,她以象征主义手法讲述了一个反对社会压迫的寓言故事:生活于平静乡村的夫妇在城市中遭遇了“金钱”“道德”和“舆论”等一众恶魔的诱惑。这些恶魔象征着城市生活中的各种欲望,而剧中的妻子在“智慧”女神的鼓励下,产生了强大的反抗力量。1931年,该剧在天津公演,濮舜卿亲自出演了“智慧”女神一角。(36)参见《天津商报画刊》1931年第3卷第8期。1928年,濮舜卿又以“济南惨案”为原型撰写了激发民众抗日爱国热情的电影剧本《蔡公时》。(37)《剧场消息·民新影片公司摄制蔡公时影片》,《申报》1928年6月30日第6版。遗憾的是,上述戏剧和电影剧本大都没有获得巡回演出或投拍的机会,这主要与彼时商业电影公司追拍粗制滥造、逃避现实的古装片和武侠神怪片,商业戏剧界也比较浮躁有关。濮舜卿把戏剧、电影当作启蒙现代性的媒介利器,唤起民众关注日益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初衷由此也并未充分实现。
1933年,濮舜卿的剧本集《人间的乐园》作为“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第七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收录了她的四幕剧本《人间的乐园》(年份不详)、三幕剧本《爱神的玩偶》(1925)和独幕剧《黎明》。1935年,《人间的乐园》又被收入洪深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中,是该卷18个剧本中唯一的女性作品。1936年,该剧再度被收入由俊生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仿古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现代女作家戏剧选》。一系列的收录,说明濮舜卿以剧作家的身份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界的认可。《人间的乐园》作为濮舜卿的戏剧代表作,继续以象征主义手法聚焦女性解放的主题。“智慧”女神激励“亚当”和“夏娃”把“天国”的美丽花园建设到人间:“你们是人,要去做人所应做的事,过人所应过的生活,何必定要讬(托)庇神力呢?”(38)濮舜卿:《人间的乐园》,洪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她称赞夏娃为“最有胆气的女子”“将要被推为女权运动的始祖”,(39)同上书,第286页。并敬告女性说:“你们不要怕自己能力薄弱,只要有决心,有毅力,什么伟大的事业,都可以成就!”她同时也不忘勉励男子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和女子合作”(40)濮舜卿:《人间的乐园》,洪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对控制人类思想的“上帝”,“智慧”说:“若是你们不信有上帝,上帝就会消灭的。”(41)同上书,第294页。关于濮舜卿以象征主义手法行理想主义之实的戏剧风格,洪深批评说,“可以代表那时期的学生剧——就是学生们写了在学校里演的戏剧”,其特点“就是说教的意味太重,而事实太近于空想了”(42)同上书,第70页。。确实,因为“实地的观察和生活的经验”(43)同上书,第11页。的不足,濮舜卿的剧本多采用《圣经》元素,童话、寓言的痕迹明显,内容略显清浅稚拙,而这也是“五四”之后一批女性剧作家作品的共性,这些作品在西方现代戏剧流派的影响下,“尚未深化为对其深层的戏剧审美意识的共鸣”,更多是一种“探索、模仿、尝试”。(44)陈方:《中国早期女作家戏剧创作论》,《戏剧艺术》1994年第3期。然而瑕不掩瑜,濮舜卿1925—1929年间的戏剧、电影创作,在戏剧和电影文学领域确立和推进了女性话语权,在全球电影先驱者群体中为东方女性实现了“显影”,为处于“五四”启蒙现代性中的媒介革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法政”启蒙:对“革命”现代性的探索及其局限
1930年之后,濮舜卿逐渐淡出电影圈,开始执业律师生涯。这一由艺术启蒙到法政启蒙的路径转换,可以看作中国现代性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转向的一种反映。彼时,中国社会的内外危机日益加深,各种保守、复古思潮沉渣泛起,继续革命则成为左翼思潮的旗帜,“成为一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普遍意识,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45)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5页。值得指出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媒介中高频出现的“革命”,其内涵同样存在着“多元”指向。夏中义认为,现代中国革命观起源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具有“三维二元”特征:“三维”指“革命”一词既是对中国语境的古义翻新,又是借助日文中介,对英文单词revolution的对应性意译;“二元”则指“革命”在上古汉语中就有维新改良的“尧舜革命”和暴力颠覆的“汤武革命”的双重意涵。只不过近代以来,受法国大革命影响,中国语境中“革命”的二元指向渐渐朝向革旧鼎新的一元面向发展。(夏中义:《“革命”探源启示录——评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在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同时他也认为“战线应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46)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萌芽月刊》1930年第1卷第4期。“左联”的成立拉开了激进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序幕。与此同时,提倡以渐进方式推动制度改良的右翼“革命”理念也在滋生。濮舜卿显然更倾向于后者。早在1928年,她就在《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一文中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表达了欣喜之情,并误将民族国家振兴的希望寄托其中。(47)濮舜卿:《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电影月报》1928年第8期。1929年,以罗明佑、黎民伟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创办联华影业公司,发起“复兴国片、改造国片”运动,力图以“联华新片”打破商业电影粗制滥造、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濮舜卿和侯曜也参与创办了“联华”在北平的“电影人才养成所”,并拍摄了《故宫新怨》一片。然而,在动荡的时局和混乱的思潮中,以戏剧和电影为媒介贯彻启蒙理性的现代性追求,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挫折。基于上述背景,濮舜卿选择回归法政专业,谋求以法政启蒙和制度改良继续推动妇女解放与社会进步。
1931年,濮舜卿加入天津律师公会,开始在平津两地执业。(48)《律师公会改选结果》,《益世报》1931年9月21日第6版。回顾20世纪初叶,中国女性的法律从业自然也有一个曲折的历程。1912年,上海女子法政学堂成立,然而同年北洋政府却仿照日本公布实施了《律师暂行章程》,不允许女性从事律师职业。1920年,宋美龄在南京创办女子法政讲习所。(49)铜雀:《宋美龄创办女子法政讲习所》,《福尔摩斯》1929年5月14日。同年,上海出现了第一位女律师——美国人海伦·麦考利夫人(Helen Leary)。1926年,出身广东政商世家、留学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的郑毓秀女士,以法国律师牌照在上海的租界区挂牌执业。1927年7月23日,《律师章程》修订版终于发布,女性获得了和男子同等的法律执业资格,然而女律师依然凤毛麟角。1939年,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名录中共有1204人,其中女律师53人,仅占4.4%。至1948年,女律师缓慢增加至70人,在1178人的总数中占6%。(50)陈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女律师很容易引发社会关注,比如1927年,天一公司就推出了由胡蝶主演、以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为蓝本大幅改编的电影《女律师》。同时,真实的女律师也很容易成为与电影女明星一样的话题人物,被各种娱乐小报作为谈资。
濮舜卿的执业足迹遍及津沪之间,“平津一带一人而已,委办案件妇女为多,是法律家也是文学家”(51)心冷:《女律师濮舜卿访问记》,《大公报(天津)》1932年4月30日第7版。。此时的她惊觉道:“以前理想,觉得现代中国的妇女,多半处在黑暗悲惨的境地。谁知执行律务以后,承办不少痛苦妇女受人欺压虐待的案件,才知以前的理想,只是百分之一的比例,以后愿以法律的能力保障女权……”(52)同上。她代理的陈旭芙诉宁夏军阀马鸿逵解除婚约案,在《大公报(天津)》连续五天刊载启事。(53)《律师濮舜卿女士代表陈旭芙女士声明否认婚约并与家庭脱离关系》,《大公报(天津)》1932年2月17-21日第1版。1933—1934年,她又在天津《益世报》上以18期连载的《妇女应有的法律常识》,进行系列普法宣传。1934年,她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由天津迁往上海,次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54)《最近迁沪执业之女律师濮舜卿女士在其津办公室留影》,《天津商报画刊》1934年第11卷第29期。随后,她在《申报》副刊《妇女园地》设专栏答复读者的法律问题,并担任进步女性杂志《妇女生活》的法律顾问。《妇女生活》杂志创办于1935年7月,其主编沈兹九后来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本杂志多刊发鼓励妇女解放并积极参与抗战救国的文章。例如,其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报人金仲华的文章《给现阶段的中国妇女》,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停滞状态,上层社会妇女满足于“班克赫斯脱”(55)埃米琳·班克赫斯脱(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又译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英国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她出生于曼彻斯特具有激进主义传统的中产家庭,与律师出身的丈夫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 Pankhurst,1838—1898)同为社会主义者。1903年,她建立了“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主张以暴力手段推动男女政治平权,该组织的口号是“给我们死,或者让我们获得所要求的”。但一战爆发后,她开始与政府合作,号召女性广泛参与生产劳动,弥补因男性参战而导致的劳工不足。1918年,英国议会通过《全民代表法案》,规定年满30岁的女性拥有投票权。1928年,在她去世前一个月,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年龄下降到21岁,与男子相同。式的、脱离现实的政治点缀作用,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妇女运动才是最最值得注意的”(56)金仲华:《给现阶段的中国妇女》,《妇女生活》1935年创刊号。。该刊第2期登载的《法律与我们》一文,更谈到杂志聘用法律顾问的初衷,在于唤起女性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并指出:“人与人之间真正得到了平等的国家,自然他们制造出来的法律,才是真正平等的。”(57)《法律与我们》,《妇女生活》1935年第1卷第2期。
濮舜卿在当执业律师的同时,还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比如积极参与由李璜组织的地下活动,从天津的租界购买弹药,秘密运抵东北抗日前线。李璜回忆道:“……幸得一个广东同志侯东明(即侯曜),他的国语说得很好,而他是电影导演,常往来平津,摄取镜头,无人不知他是戏剧界中人,他的太太濮舜卿也是同志,同他一道活动。我与他夫妇商量运输的事,难得他俩对这危险工作,一口承认(即答应)……”(58)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页。由此可见,濮舜卿有着一般知识女性所不能及的才略和胆识。然而,时局弄人,这对世人眼中志同道合、家庭美满的贤伉俪却因动荡时局而分离。(59)有关侯曜与濮舜卿幸福家庭生活的报道,见《侯曜先生与濮舜卿女士伉俪合影》,《天津商报画刊》1931年第2卷第38期;《在他爸爸导演下之姿态(名导演家侯曜君之爱女)》,《天津商报画刊》1931年第3卷第44期;慕维通:《侯曜妻,濮舜卿业律师:夫唱妇随,艺术家生活羡煞天下人》,《开麦拉》1932年第84期。1933年,华北局势日益紧张,侯曜不得不南下香港避难。1938年左右,侯曜与身兼入室弟子和秘书的编剧、导演尹海灵结成伴侣,直至1942年被日军杀害于新加坡。(60)罗卡:《侯曜:传奇的审视和重构》,载香港电影资料馆编《香港早期电影游踪第二册·电影先驱侯曜》,香港电影资料馆2014年版,第21-39页。这段情况在抗战胜利后被发表在上海《东南风》杂志的《女律师濮舜卿》一文中,此文还将侯的遭遇描述为他抛弃故乡妻室的“报应”。(61)友孙:《女律师濮舜卿》,《东南风》1946年第4期。文章认为濮舜卿与侯曜在东南大学相识时,侯曜在广东老家已有妻室。1924年,侯曜加入长城公司编剧(导)《弃妇》乃是因为“侯濮相爱以后,侯曜便把乡间的妻子遗弃了”。1933年,两人因“家庭细故”仳离,侯曜只身南下,与尹海灵结成伴侣,“又表演其弃妇事实,将濮舜卿遗弃于天津”。迷信固不足取,人物可待全面评价。
家国离乱下的个人生活变故,使濮舜卿以法律意识唤起女性群体自我保护能力的意愿更为迫切。1935年,她在《女青年月刊》上发表《妇女与法律知识》一文,指出在“两性”和“金钱”问题上,法律可以“保护个人的生存,比较积极而有力量”,还指出当时坊间热议的电影明星阮玲玉“殉讼”悲剧就是阮玲玉缺少法律知识造成的。(62)濮舜卿:《妇女与法律知识》,《女青年月刊》1935年第14卷第6期。
抗战胜利后,国家面临着从战争泥淖中重建的契机,濮舜卿开始为男女平权谋求法律和制度保障而奔走呼号,并参选南京市参议员。(63)李忠峰:《濮舜卿:一位南京市参议员竞选人,谁知她是一位女话剧作家》,《妇女月刊》1946年第5卷第2期。同时,她还主编了《上海妇女》杂志,一如既往地关注妇女问题。1947年,她针对日本侵略导致的家庭离散、女性惨遭离弃的社会问题,尖锐地指出妇女以法律为武器保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并认为“五四运动之后,易卜生《娜拉》(即《玩偶之家》)一剧介绍到中国来之后,不但骚动了整个的文坛,也震荡了中国法律界的心灵”(64)濮舜卿:《战后离婚问题的面面观》,《妇女文化》1947年第2卷第3期。。她的观点呼应了昆仑影业公司同年拍摄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批判现实主义主题,然而“出走的娜拉”的社会问题,经过30多年的时光流逝,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一年,濮舜卿以妇女组织候选人身份参选南京市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止步于“妇女团体”候补人选。(65)《南京国代选举选票结果公布》,《申报》1947年12月3日第2版。民国时期,女性参政不免被人讥讽为政治点缀品;战后国民党政权的深度腐朽与信用崩塌,更使偏向理想主义的濮舜卿很难实现抱负。这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前提下,寄希望于以法律启蒙推动社会制度局部改良的右翼的“革命”现代性道路是走不通的。
濮舜卿在20世纪10—40年代的“娜拉三态”,对应着齐美尔关于现代社会中“人是天生的越境者”的论断,充分体现了“五四”知识女性的内在生命力对超越固化时空限制、不断突破边界束缚的渴望,以及探索民族国家现代化之路的各种努力与尝试。本文对濮舜卿的再考察,涉及她以现代教育启蒙激发女性关于独立自强的初步认知,以戏剧和电影等媒介启蒙大众并改造社会风尚,以理想主义的法政启蒙改良社会制度的经历,力图还原她相对完整的个体精神谱系以及她与早期中国现代性的那种“复合”与“多元”的“混沌”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希望通过对这位先锋女性的个体生命的解读,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回顾和反思早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有关现代性的思辨、论争及其文化症候,以钩沉历史去烛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