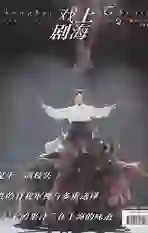猿之出路与人类困境 评《一只猿的报告》
2023-06-10京锐
京锐


《一只猿的报告》由郗望导演、李腾飞主演,从内容设定、形式到剧场呈现效果都实现了与观众的直接交流,并成功投下了情感与思考的双重涟漪,让剧场间积极的双向交流绽放一种独特的魅力。
《一只猿的报告》改编自卡夫卡中篇小说《致某科学院的报告》(1917),讲述一只名为“红彼得”的猿在科学院内向院内成员报告自己如何通过学习人的行为举止、待人处世而摆脱束缚、融入人类社会的历程。相比于其他独角戏,它似乎更加简单,甚至有些朴素:舞台上仅有由李腾飞扮演的红彼得、一张圆凳以及一束灯光,台下的每一位观众便是他要报告的对象。可以说,《一只猿的报告》不仅远离了热门的多媒体手段,甚至缺乏所有我们熟知的戏剧要素,仅有短短的60分钟、没有对话、没有情节、没有“人类”角色,甚至没有第二个角色。但也因此,这部独角戏凸显了戏剧最为无可替代的本质特征——活人具有无限可能、能予人无限想象的身体,它是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少有的、接近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以及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之理想的作品,通过演员李腾飞极具魅力的肢体表现,给观众充分想象快感的同时建构起一种鲜明的戏剧节奏,因而摆脱了独角戏以及“淡情节”戏剧常有的寡淡和沉闷的观感。更重要的是,它给观众带来一次直接而强烈的精神冲击,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极为清醒的思辨空间:通过人类扮演猿,并由舞台上的“猿”反观舞台下的“我”(人),它的困境与我们的困境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每一个走出剧场的人都无法置之度外。
此剧的成功昭示着,当下观众渴望的那种情感与理性综合的触动或许无需视听的奇观化、情节编排的奇巧化,但必须是来自台口传递出的某种“回声”,这种“回声”源于两个层面:于个人层面理解与平等对话,于社会层面真实揭露和批判。就具体叙事而言,又体现为前半部分红彼得逃出被关押的笼子前的内心斗争,后半部分红彼得逐步同化融入人类社会后的内心异化,两部分同时又是交织着的。
一、选择:“自由”或“出路”?
红彼得复杂的心路历程是推进叙事发展的全部动力。在全剧中,这一心路历程又起于当红彼得被关进笼子后该如何“选择”,它没有选择设法逃出追求“自由”或是认命被驯服,而是认清并选择“人化”为自己的出路。“出路”与“自由”成为全剧隐喻极为丰富的关系之一,其内核表达直接关乎于舞台上如何将这种内心冲突外化。剧场中,内心外化往往借助具象的其他角色、道具或其他声画效果。例如《狗儿爷涅槃》中地主灵魂的直接“现身”揭示狗儿爷为土地而疯癫;《琼斯皇》中密匝的鼓点节拍则好似将琼斯皇剧烈恐慌的心脏直接呈于舞台。然而,《一只猿的报告》中,内心选择的外化除了依靠角色自身的面部、肢体语言,便只有外部灯光。舞台中心几条竖向灯光打在黑色背景上,映出类似牢笼格栅的模样,红彼得刹那间由台前侃侃而谈的发言人蜷缩回那团灯光范围内,双手抱身颤抖着。随着他躯体有节奏的颤动,灯光在其脸上呈现或明或暗的光影。无需用复杂的景片转换昭示海上之船是如何颠簸,船舱角落又是如何阴暗,一切已尽在观众脑海中,红彼得在不得已的恐慌中却仍保持着镇静并立马做出决定:“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出路,左边或右边,随便什么方向都成。”毫不犹豫地舍弃乃至不屑于被束缚时理应向往的“自由”,执着选择那个仿佛是自由替代品的“出路”,全剧为我们撕开自由的虚假向往,揭露出一个“出路为王”的现代社会。
作为“已人化的动物”对着台下科学院成员做报告时,演员通常离观众区很近,几乎要贴近第一排的观众,以一种近乎骄傲的语气复述过往;但作为“猿”复现过往艰苦历程时,则往往向后退至舞台的底部,离观众较远,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动物的世界而非人的世界。通过改变与观众间的距离穿梭于过去和现在的兩种身份间、两种生存环境间是巧妙的,它直观地显示出红彼得的两种视角,而这两种交织的视角使得红彼得似乎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人类社会之荒诞。具体到剧中情节,作为被关押在船舱底部的猿,它没有失去选择的自由,但追求自由却大概率意味着寻死:或被人类抓住、或被其他动物欺凌、或逃出船舱掉入海中葬身海底。“假如我真的是前面提及的自由的信徒,那么我的出路就是遵循这些人阴郁目光的暗示而投身浩瀚的海洋。”可见,作为“猿”时它首先拒绝的就是做自由的信徒,拒绝愚蠢地扑向自由的火焰而毁灭。同时,成为“人”后又直指人类的自由不过是个虚名,相比于红彼得曾亲历的、动物世界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规则成法众多的人类社会里“自由”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幻想。
红彼得不仅因兼具两种视角而讽刺现代社会对“自由”的追求,更巧妙解释了它之所以能够走“人化”之路是因为人有时无法完全放弃自己的本性去追求出路,因而沉湎于自由的幻想,但红彼得正因超脱了人的这一局限,故而能够不顾一切地奔向那条出路终获成功。红彼得甚至坦承无人许诺加入人类就可以让它摆脱它四周的栅栏,但这或许能为它带来更多的选择,这种行动的勇气与果决无疑是对沉于精神困局而耽于行动却热切歌颂自由的人类至深的讽刺。
通过舞台上演员李腾飞的肢体表现,不同身份视角间切换得是如此自然,观众在不自觉间颠覆了认知:“猿成为人”的选择是多么荒诞却又合理,“自由”的歌颂是多么泛滥却又虚妄。
二、同化与异化: “人”或“非人”?
选择“成为人”后,全剧进入了红彼得心路历程更为重要的阶段:“如何成为人”以及“成为人后怎样”。继引导观众对于“自由”和“出路”的关系进行思考后,这两部分又启发观众思辨“人”本身,即“人”与“非人”之分。“人”有两层含义,生物层面,应符合人类的生理特征,精神层面应有“人性”,否则就是被异化了的人。不仅是上一部分所说的、生物层面的两个物种/身份和视角之间的转换,李腾飞所扮演的红彼得也在精神层面灵活地游走于二者中间,彰显了他作为活人极富能动性、具备丰富表达层次的身体。红彼得“非猿非人”的精彩演绎映射着逐渐被规训褪去本真人性的众人。
“人”与“非人”之分首先便是生物层面。演员李腾飞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前期大量地模仿了猿猴的一举一动,在排练期间又花费大量时间观摩动物园中的猿猴是如何对外界做出反应、外界游客又是如何“参观”猿猴的。于是他成功塑造了这样的一个红彼得,粗看和人无二异,但却又在举手投足间保留了猿猴原始的、无法消除的痕迹,比如,走路时驼着背,双手下垂稍稍弯曲几近触及地面,步伐是外八字的;在叙述的间隙时不时发出猿猴那尖细响亮的叫声;同时,当红彼得向观众走近,我们便能发现那扭曲着的人的五官,眼睛始终是瞪大几乎外凸着、嘴始终是向下撇的、鼻孔微微朝天,这些组合起来又构成了和猿猴极相似的动态神情,在直观形象上人与猿似乎已经模糊了界限。进一步的,这种区分进入了更深的层面。演员通过抽象出几个当下社会颇具代表力的现代人行为,从而活灵活现地表明其被人类社会规则的同化过程。这里演员加入了与观众的互动,一边自白学会了握手甚至亲吻,抓干净身上的虱子等等“社交礼仪”,一边走向观众席和观众握手、仔细检查观众的头发等等。这种在他人注视下与演员亲密互动所带来的不适与尴尬,使得观众多对演员的互动表现出犹疑甚至略有抗拒的态度。这一互动不仅有效调动了剧场的空气,更巧妙地点明观众(人)仍无法迅速将“人化的动物”当作人类社会中的一员而接纳,加深了“人”与“非人”的中间处境。
而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学习喝酒”一场。原著中红彼得在学习喝烧酒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对烧酒剧烈气味的反感而屡屡不能成功适应。而在舞台呈现时,导演将原文本中的“烧酒”本土化成了“白酒”,这是一次极巧妙的本土置换,二者共同具有强烈刺鼻的气味,更重要的是,白酒在中国文化中构成了酒桌文化的重要部分,酒桌上的人喝白酒后会近乎程式般地从喉腔发出“哈”的一声,而觥筹交错的酒桌则成了很多重要事务的场合,乃至成为工作社交的重地。这里,演员不仅强化了延长那一声“哈”的长叹,还加入了演员改编自彼得·汉德克《自我控诉》的一段台词:“我学会了喝酒/我学会了喝酒之后会头疼/我学会了敬酒/我学会了敬酒时要把酒杯放低/我学会了喝酒之前要先敬酒/我学会了劝别人喝酒。”这段话可谓概括了酒桌文化及其背后的人情社会法则。演员语调逐渐上升、語气逐渐加强,最后近乎咆哮着吼完了这段台词。这一场给人以极强的震慑力:比起原著中单纯的努力克服烧酒的气味,舞台所做的改编显然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含义,它抓住了我国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切面,也就凸显了成为“人”最为艰巨的困难是知悉并融入充斥着不成文规矩的人类社会,融入精神层面的社会集体意识。
那么,“成为人后怎样”?红彼得经历了从融入的同化到异化的过程,感受到了那种回归猿(重获本真人性)之不可能。一方面,它为自己已具备“欧洲人具有的一般文化水平”而骄傲,不仅与人交往自如,甚至还拥有了自己的经纪人;另一方面却饱受与原始的猿猴种族已有隔膜的痛苦:比如它说“即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回去,在重新穿越它时也非得掉一层皮不可”,比如它既需要母猩猩来满足生理需求,却看不惯母猩猩那“兽”的目光。
《一只猿的报告》正因揭示了精神层面的异化的“人”,而显现出它的深刻内涵。精神层面的“非人”常常是不可见的,过去封建礼教的极端压迫造就“非人”,现代金钱名利的吞噬亦能造就“非人”。 对真正意义上“人”的张扬是话剧应有的价值评判,却也是当今许多舞台作品含糊其辞或遗忘而不自知的。正如卡夫卡所在的德语文学世界中有一种猴的象征,意为上帝警醒世人的标志,就舞台演剧而言,与人外貌类似的猿,便恰巧成为了最好的“警醒意象”。此剧主角虽非“人”,却借助了生理层面上的“非人”(动物)来给予人类以警醒,要人类时刻观照“人性”的缺失与在场。
这一设定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了曹禺创作于80余年前的《北京人》。它讲述一个封建的没落士大夫家族中的三代人无力冲破家族与命运,最终家族四分五裂,各自也都走向毁灭。剧中唯一的正面形象、也是未出现的象征便是“北京人”即北京猿人,它虽非人类但具有“人”应有的人性,没有封建礼教的约束,单纯、勇敢、富有强烈的生命力。曹禺在谈到写作动机时曾说:“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到一条路子来。”而《一只猿的报告》的导演也谈到自己此剧意图展示“被压抑的生命与社会规则对人的规训”,历史在相隔大半个世纪的两端产生了震耳的回响。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主题在舞台上也依靠简单的灯光完成了精彩的具象呈现。红彼得在叙述至自己如何最终完成了融入人类社会的目标时,剧场的灯光从舞台左侧打出,呈现出从左至右渐次放大的放射性金黄色光区,演员从左上场,猿猴般的走路姿势不断直立起来,变成近乎站立行走的人,行走过程中仿佛迎向“无限光明的前途”。因与婴儿逐渐学会行走成人、学会为人处事进入社会过于类似,这一过程令观众感受到了一种熟悉与陌生的交织。人的“成长”和猿“成长”为人何其类似,在学习和模仿中接受社会规则,融入社会。但在这个过程中,正如猿失去了动物以身体去感知这个世界的天性一样,人也失去了婴儿时期的单纯以及对社会的直接感知,在熟稔这个社会的运转规则时,受挫了、妥协了、阉割了,终同化为了一个“人”。换言之,规则塑造了我们,也压抑了我们生命的本性,让我们从某种程度开始走向“非人”,“同化”本身即与“异化”紧密相连。
但《一只猿的报告》中的现代性困境显然与《北京人》不同了。曹禺在《北京人》结尾借“北京人”的意象给全剧灰暗的基调添上一抹亮色:“天要亮了”,这给观众提供了一条“出路”。然而,《一只猿的报告》中,导演只是设下了“自由或出路”“人或非人”的两重问,它暗示着“非人”化已是我们当下无可逃脱的困境。他并不寄希望、也不可能给观众提供一个“出路”,因为现代人困境已触及到了我们作为人难以超越的某些本质。当过去曹禺式的“出路”无法给予我们希望,这种自觉的自反性,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时代虽有一个时代的困境,但“像人一样地活着”的呐喊,意识到并开始思索如何面对这种异化,是此剧的时代精神与超越时代的精神。
全剧尾声处,红彼得脱下身上的西服、西裤,嘶吼着结束了全剧。也许,这是成为人的猿自觉地认识到被压抑、被规训的个体再无回头之路,而只能通过脱下人社会交往必须要穿着的服装,卸下捆绑其的沉重枷锁,获得一瞬间的短暂释放,也让全剧在最后互换了“人性”的光芒。
“出路/自由”“人/非人”这两重关系,是《一只猿的报告》通过间离的形式所具备的深刻哲理内核。《一只猿的报告》之所以能够获得当今剧坛难得一见的极佳口碑,正在于剧场内的每一个瞬间里,我们虽不曾真正对话,但却有某种直接交流的存在。活生生的人之间那种被理解、被包容、被表达的审美体验,是戏剧存在的价值,也是其永远无法被别的艺术形式所代替的根本所在。当今剧坛呼唤更多如此能够描摹人类当下困境、思考人类本质、呐喊要人去成为“真正的人”的舞台演剧作品。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