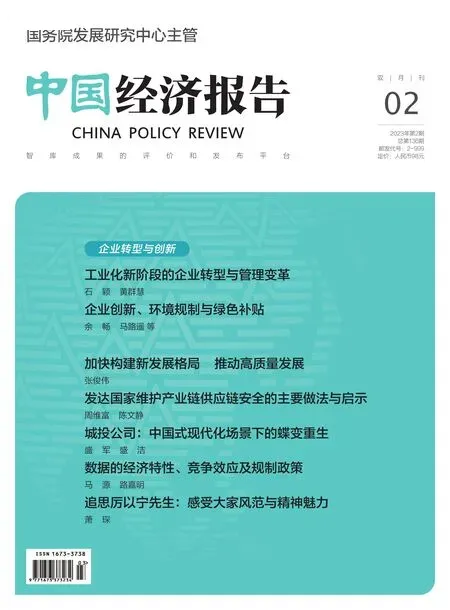感受大家风范与精神魅力
——追思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
2023-06-06◎萧琛
◎ 萧 琛

永远缅怀厉以宁老师(1930-2023)
壬寅惊蛰,厉以宁老师走了。连月来,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刷屏,悼念诗文如漫天雪花为先生送行。作为长期沐浴师恩的弟子,作为老师几十年的帮手之一,也作为他几十年的近邻,笔者深知如此传奇的人生是何等不易,也深感北大的精神魅力与笔者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吐不快,怅然命笔。信马由缰,去思可矣?
几十年如一日,最先吃螃蟹的勇士与智者
厉老师是国内最早让西方经济学系统走进大学本科生课堂的教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始,他的《西方经济学概论》就在北大开讲。风清气新,反响强烈,听者云集。外系同学也纷至沓来,教室几度被换成大的。热门讲座甚至被排到了校长办公楼上面的剧场,而那是昔日燕京大学可容纳全校师生的地方。一席难求,求知若渴者竟需要席地挤坐在舞台上。
北大虽相对自由,但那以前西方经济学的课程,通常在研究生层次,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之类。刚过去不久的“文革”,令人心有余悸。
厉老师的《概论》课程系统述评西方经济学原理,以思想逻辑推论与几何统计图表为主,以数学推导为辅。教材出版时数学推导部分是由数学教授秦宛顺编写的。谋篇布局上,老师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大板块上,依次选定并植入了相应成果。这对于已修过政治经济学与三卷《资本论》的高年级本科生,显然便于产生共鸣。由于没有教材,当时又几乎没有录音笔之类,课堂笔记便益显重要。于是,上课记得又快又工整的,考试前就成了香饽饽。我们世界经济专业的一位女生,就曾被大家戏赞:厉老师的每一句话、甚至休止符,她都不会落下。
结合国情并因材施教,对行将走向大千世界的莘莘学子们来说,显然意义迥远。长期植根于民族土壤,厉老师对于短缺经济的困难与计划体制的弊端,可谓了如指掌切肤深刻。“反右”斗争时,厉老师曾被定为“内控人员”,在系资料室工作了很多年。这期间,他参与写作和编撰了多达40期的学术内参《国外经济学评论》。几十年如一日之后,终于时来运转。
一天等于二十年, “流沙无意却成洲”
概论课之后还有众多后续,西方财政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还有流派专题等等。胡代光、范家骧、杜度等名师也纷纷进场。硕士研究生阶段厉老师还为我们开讲了《国外经济学经济史比较研究》,当时我们年级各专业硕士生总计只有20余人。一学期20讲记录下来,基本上就是一部新著书稿。
思想火花很多。历史学派的“布登布洛克动力”,福利经济学的“契约曲线”,凡伯伦的“炫耀性消费”,加尔布雷斯的“公司治理专家结构”,罗斯托的“起飞”学说,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等,都曾是宿舍里热议的话题。多年后回头看,这些同学,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出口成章的背后,是老师丰厚的学养与长期的积累。没有惊人的记忆力、表达力与转换力,不可能那般娓娓道来游刃有余。厉老师的讲稿,往往是昔日读书笔记或新著文稿。通常一门新课成熟后,他就会转向更新的领域。厉老师曾回忆:经济系的老师,陈岱孙、赵迺抟、陈振汉、罗志如等,都热心地教会了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不过他现在所开的课,基本上还是来自毕业后的不断学习。
在北大经济系学习七年后,笔者曾赴美国马里兰大学修过那里的经济学,知道留学生深夜攻读之累与反复作业之苦。那些不厌其烦的函数凹凸性论证,很难不令人产生审美疲劳。回母校北大任教后,笔者曾不止一次下意识地温习厉老师当年的笔记,油然而生的往往是莫名庆幸与豁然开朗。
厉老师给我们的思想火花很多。历史学派的“布登布洛克动力”,福利经济学的“契约曲线”,凡伯伦的“炫耀性消费”,加尔布雷斯的“公司治理专家结构”,罗斯托的“起飞”学说,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等,都曾是宿舍里热议的话题
有教无类、不拘一格,“此生甘愿作人梯”
回母校后我投给北大学报的第一篇稿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周期理论的成熟、扬弃与回归》。该文涉及几十位经济学大家,时间跨度超半个世纪;一万多字的篇幅,想写出周期思想演进的“长波”。该稿毫无声息地被审查了近一年之久。
我并非经济思想史本行,更不是他们的嫡传弟子。但有教无类是大师们的传统。从他们后来的眼神中,我能感到他们对学生的认可。让翻译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可算能令人聊以自慰?在该书中译本发行仪式上,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也欣然光临。当时他正着手重译凯恩斯的《通论》。早年北大徐毓枬教授的译本属半文半白,著作权也已到期。而徐版《通论》的中译本绪论,长达30多页,就出自厉老师之手。
二十世纪末北大成立了五个学部,厉老师是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任,我被任命为学术秘书。起初以为是压担子,后来十几年中我才知道这是给机会。学部下属14个院系或中心,在职称晋升与学术仲裁等方面举足轻重。不过厉老师渠道畅达、举重若轻,很少用到我。得益于此,我在校内外学术交流上一直“左右逢源”。例如,加入WTO前夕,我曾随中国教授代表团赴日内瓦,考察了WTO、UN、ILO、WIPO、UNCTAD、ITU、世界经济论坛等一系列重要机构。
十二年前学部一分为二,独立出了经济管理学部。业已八十高龄的厉老师老当益壮,出任了北大学报编委会主任。主管副校长跟我谈话说,厉老师年事已高又身居国事要职,他提名让你担任他的代理。私下里厉老师对我说,“你就放手做吧。只要不出事,我不会找你。”年逾古稀之后,笔者愈发体味到前辈这样安排的良苦用心。
“改革先锋”经世济民,“村有溪流必有桥”
厉老师的社会主义经济教科书,论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都是他关注国内经济的大作。后一本还被译成英文流传海内外。他也曾应邀访问过16个国家,飞行了60多万公里。散文集《山景总须纵横看》《出访影集》,都是这些亲历的结晶。
认真想,早期的《体制·目标·人》,应该是他直面改革开放的进军号。制度设计俨然已成了新的目标。《面对改革之路》,则是厉老师的论文小辑,是国家发改委组稿的论丛之一。受激励,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曾斗胆备了一本《面向开放之光》投稿。主编委婉地说,可惜你太迟了,全套书的出版工作都已结束。
悻悻然后,我接到了他们的新书《中国经济专家新思想年集》的稿约。我提供的稿件是《新世纪经济学教学科研应推出新模式》。2006年我终于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世界经济转型与中国:潮流、风暴、入世和入市》。榜样力量重要,该文集的序言写在那里。这本书送给厉老师后,他笑了。
作为“改革先锋”,厉老师曾主持起草《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非公经济36条”等。林权改革、土地确权和扶贫等也是他的贡献。“国家毕节扶贫”二期项目主持人是厉老师,一期是科学家钱伟长。厉老师曾让我去那里做知识扶贫的报告。脚踏实地之后,看到了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校内,厉老师关于深圳速度、股份制、土地确权等讲座,每次都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赞叹深圳罗湖区高楼建设速度超过香港,原因是“奖金不封顶,大楼就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就不封顶”。市场经济重物质刺激,而计划经济靠“向……献礼”。在讨论深圳“810股疯”时,他观察到在挥汗如雨的大热天,排队长龙,人们不分男女,前后紧紧相搂。
在北京召开的“八国经济转轨研讨会”,国际赞助者曾让我替他们特邀厉老师光临。厉老师的演讲高屋建瓴、机智幽默,赢得满堂喝彩。他走后,各国专家在席间仍纷赞“Too wise”!
不忘初心、勇于开拓,“野无人迹非无路”
近年“共同富裕”走到前台,厉老师《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的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本书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1999年这本书出版后曾引发讨论。所提的“第三种调节”显然石破天惊。在“政策市”属性消失前,在霸王条款难以绝迹前,在累进税和弃籍税开征前,新兴经济体的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显然难以体现一国应有的道德要求。在这种国情下,扬善惩恶、鼓励赞助,无疑是有效的次优选择。对于推进“民营新政”、呵护非公企业、促进市场真实主体的成长与壮大,显然富有深意。
如何从“先富”走向“共富”,是极其敏感且充满两难的议题。这不仅需要理论突破,而且需要切实权衡。经验表明“杀富通常都不能济贫”。计划时代“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调控怪圈,新世纪决不应重演。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摆脱贫困与走出短缺方面,中国速度俨然已成了世界之最。中共二十大和今年“两会”以来,科技、金融、机构等重大改革,都闪现着新的希望。
中国改革的下半场已经开启。 “中间品”正被消减,“最终品”正被添加。不妨以捕鱼经济为例。渔船渔网是中间品,买鱼吃鱼是最终品。渔船渔网越多,捕鱼效率越高,需要买鱼的钱和吃鱼的人就越多。由此,从根本上解决“需求收缩”“预期转弱”和“供给冲击”的新一轮改革大幕已经徐徐拉开。
我们对厉老师最好的怀念,就是不懈地传承、发扬与光大他勇于探索、经世济民的精神。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门前,矗立着一块深褐色的巨石,上有厉老师笔力雄浑的金色题词:“敢当”。
创建光华、一波三折,“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才”
七十周岁时,历届弟子及各界人士为厉老师庆生。当天厉老师填了一首《破阵子》送给大家。那时光华管理学院已初具规模。走廊里知识经济满满,到处是教员们的大部头著述。会场时尚前沿、空间宜人充足。出于习惯,我常带研究生去他们的机房上课。同学们无不眼前一亮,开玩笑说这是“跟老师出国”。
可我知道,在北大要创建这样一所新院,需要多大魄力与多少艰辛。筹建工作一波三折,一言难尽。起初我们国际经济系是随他们一同从经院分离出去的。学校批准后,厉老师曾爬五楼到我家门口,叮嘱我与他麾下抓紧时间拟定新的教学培养计划。那时,他虽然早已不再是面带菜色,但因疾步登高而起伏喘息的样子,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建院38年以来,光华管理学院发展迅速,已成了世界知名的商学院。“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因学术、而思想,因思想、而光华”的精神气质,使得她已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可又有谁知道,中国台湾地区光华基金的那笔千万美元的办学资助,曾经辗转过几多大学并让他们全都噤若寒蝉。
厉老师学术言辞犀利,有时眼光不无咄咄逼人。但实际上他却谦和周到很有原则。光华管理学院的题字是厉老师的亲笔。“学”字上面少了一点,为何?共勉各位“多学一点”。经院需要他来给老师讲讲,他一定“召之即来”。而我们78级本科毕业生30年聚会时,我曾代表大家邀请厉老师被拒。也许是看我失望,他补了一句,77级同学大聚会时我也是如此。的确,他太忙了!

2006年5月2日,厉老师夫妇与作者家人在京畿稻香湖畔的留影
一介布衣、诗意人生,“笑声惊散细鱼群”
厉老师开会出差常常一走多日。师母何玉春在中关园时就曾不时地帮他取邮件。厉老师得空时则常陪她采买。在一本新书的后记中,厉老师曾谢及夫人,说她是搞发配电的,也算是资源配置。他们相爱相知,始终相濡以沫,有过13年的两地分居。“笑声惊散细鱼群”,是厉老师《浣溪沙》中的最后一句。1957年,两位年轻人曾在圆明园溪水边嬉戏。
新世纪,几百名北大教授搬进了蓝旗营教师小区。厉老师的新居可谓鸟枪换炮。印象深的是他家的画作,空间感好、功力非凡。一问才知那是何师母亲哥的作品。她哥是北京舞美大家,擅水粉油画。他们还送了我一本她哥的画册。她哥去世时,何师母一说起就眼圈发红。
搬进新居后不久,他们从超市归来碰上我们。也许是看我们拎得多,他问怎么还不买辆车;再后来又问怎么还不买套房。几年后我们交了卷,他饶有兴致地为我们“暖房”郊游。“五一”长假,日丽风暖,柳绿水蓝。我们吃着乌江鱼,喝着老师提来的红酒,听他讲人间的烟火。厉老师会做菜,何老师喜摄影。奈何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住行升格了,但老师家仍不宽敞,尽管已大了一倍。卧室床下堆满了书,个别床还支高了不少。电视柜周围也挤满了珍贵的纪念品。随便问个花瓶,那也是出自某某王子,满载着海外的祝愿。尽管多年邻里常见,但他的变化仍不难察觉。演讲时他精神矍铄眼里有光,而在席间或家中他则已显疲态,偶尔甚至还会握筷不稳。
九十大寿后厉老师住进了医院。生命最后阶段他曾老想着回家。但毕竟九十有二,听和说都已困难,医院怎敢放行呢。可有谁知晓,厉老师的心里究竟还记挂着多少案牍上的事与人……
厉老师走了。他留下了思想、花朵与美好的回忆;但也带走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