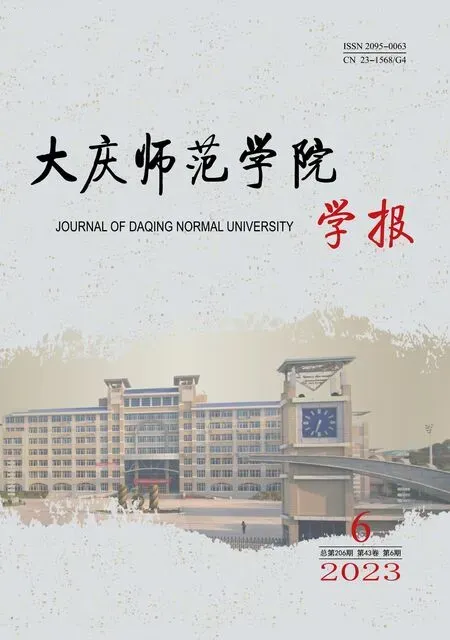从去殖民化到民族构建:伊拉克亚述族群治理问题
2023-06-05张娟娟薛巧红
张娟娟,薛巧红
(1.兰州大学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2.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现代亚述人(Assyrians)(1)伊拉克亚述人自认为是古代亚述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阿拉米人的后裔,但刘易斯认为这些观点缺乏历史依据。参见Jonathan Eric Lewis, “Iraqi Assyrians: Barometer of Pluralism,” Middle Eastern Quarterly, Vol. 10, No.3, 2003, p.50.主要信仰基督教聂斯托里派(Nestorians)、迦勒底派(Chaldeans)、叙利亚天主教(Syriac Catholic Church)和雅各布派(Jacobites),其民众主要分布于今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北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的交界地带,属于典型的跨界少数族群。(2)现代亚述人属于“跨界族群”(transboundary ethnic group)。在政治人类学范畴中,“跨界族群”与“跨境族群”(cross-border ethnic group)涵义不同。前者指传统祖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割而居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后者指跨国境而居,地理上可能并不连成一片的同一民族。参见曹兴:《论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39页;葛公尚:《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1页。其中,伊拉克是中东亚述族群人口数最多的国家。1921年伊拉克建国之际,亚述族群占全国总人口的5%以上。随后,伊拉克亚述族群历经三次大规模移民浪潮(20世纪20年代、70—80年代和21世纪初)后,其人数已不足全国人口的3%。(3)参见G.T. Kurian, The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 Civilization,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1, p.1.伊拉克战争期间,愈15万基督徒离开伊拉克。(4)参见A. O’Mahony, “The Chaldean Catholic Church: The Politic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Modern Iraq,” Hey J XLV, Vol.45,No.4, 2004, p.445.根据“亚述人欧洲联盟”(Assyrian Confederation of Europe)2017年报告显示,当下全球约有350万亚述人,(5)参见R. Hanna and M. Barber, “Erasing Assyrians: How the KRG Abuses Human Rights, Undermines Democracy, and Conquers Minority Homelands,” Assyrian Confederation of Europe, September 25, 2017, p.9.生活在伊拉克境内者不足20万,(6)参见“Struggling to Breathe: The Systematic Repression of Assyrians,” Assyrian Confederation of Europe, April 1, 2019, p.2.不到该国总人口的1%。尽管亚述族群在人口数量上属于“微型”族裔,却是伊拉克最主要的基督教群体,其治理问题也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伊拉克对亚述人的治理政策深受英国殖民历史的影响,即亚述族群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当局合作而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历史遗毒”。(7)参见王伟:《殖民主义的历史遗毒:当代族群冲突的根源探析》,《探索》2018年第5期,第91页。伊拉克历届政府尝试以不同的民族政策和政治手段整合,复兴党甚至推出民族同化措施与军事手段予以规训,却催生出更为复杂的族群治理问题。新世纪以来,学界愈加关注中东少数族群治理,伊拉克亚述族群治理也进入民族构建的讨论议题。现有研究多以族群为叙事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故而,笔者尝试跳出族群视角,从伊拉克去殖民化和民族构建两个历史阶段来阐释伊拉克亚述族群治理的内在困境与民族国家重建的前景。
一、伊拉克亚述族群治理的历史阶段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治理主要基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目标。相对于阿拉伯人而言,伊拉克亚述族群是政治、宗教和文化意义上的少数群体。因此,加强亚述族群的历史文化认同和国家政治认同是伊拉克民族构建的主要任务之一。
(一)委任统治与去殖民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哈卡里山区的亚述人加入协约国阵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约5万名亚述难民逃往美索不达米亚,接受英国的政治庇护。稍后,又因为摩苏尔问题,土耳其亚述人大量流入伊拉克北部。1921—1922年,约有1.5万名来自哈卡里山区的亚述人选择定居摩苏尔和库尔德斯坦地区。(8)参见S. Zubaida, “Contested Nations: Iraq and the Assyrian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6, No.3, 2000, p.366.1925年,摩苏尔被划入伊拉克版图,英国获得未来25年对摩苏尔地区的控制权,并承诺同国际联盟一道解决伊拉克北部亚述人的集体安置问题。上述举措短期内有利于稳定该区域亚述人的政治秩序,也加强了其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合作关系。
彼时,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体,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不仅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还要承受殖民统治带来的公民身份分裂。(9)参见N. Al-Tikriti, “Was There an Iraq Before There Was an Iraq?”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i Studies, Vol. 3, No.2, 2009, p.133.1920年,英国通过《圣雷莫协议》,确立了其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地位。亚述人积极加入英国组建的“雇佣军”(1915—1932年),参与镇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次年,伊拉克王国建立,其国内政治精英被迫接受英国的殖民安排,放任深受殖民当局青睐的亚述人游离于伊拉克国家政治和社会管控之外。这导致亚述人对伊拉克国家的政治认同意识和民族归属感极其薄弱,并拒绝加入伊拉克国籍,也排斥与巴格达当局直接接触。整个20年代,伊拉克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频频爆发,摆脱异族统治和殖民压迫的情绪高涨。英国当局被迫于1930年签订《英伊同盟协定》。1932年,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亚述雇佣军随之解散,失去政治庇护的亚述族群要求伊拉克官方承认其文化和政治自治地位。为了顺利加入国联,伊拉克政府承诺维护土著居民的生命权、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文化教育等权利。(10)参见A.H. Hourani, Minorities in the Arab World,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92.为表示诚意,费萨尔国王于1933年8月前往北方,就亚述人的定居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但政府与亚述人群在划区自治、组建亚述军团等问题谈判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随着英国的撤出,这些“抵制融入新民族国家”的亚述人很快成为伊拉克去殖民化和强化国家权威的打击对象。此时,伊拉克尚未形成“一个文化和情感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11)参见A. Cobban,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 1970, p.110.而伊拉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清除殖民“残余势力”,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巴格达政府承认不同信仰群体的相关权利是以“同为伊拉克人”为前提的,而激进的亚述领袖沙蒙依旧拒绝成为伊拉克公民,坚持前往日内瓦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1933年9月初,费萨尔国王去世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被用于推进去殖民化实践。为了减少非阿拉伯人和非穆斯林对国家建设的干扰,军方决定对否决巴格达提案和拒绝融入国家的亚述群体施以暴力,对亚述人活跃的塞米勒地区展开血腥清洗,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伊拉克民众也对政府针对亚述人的措施表示支持,西德基将军一度被视为民族英雄。1933年的亚述人危机似乎更像是伊拉克消除“威胁人民团结者”,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隐喻。随着英国委任统治势力的退出,伊拉克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及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加快,伊拉克亚述人不得不接受其伊拉克公民身份,此后的亚述人独立诉求主要由流散境外的离散民族主义者推动。
(二)共和国政府推进民族构建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内核建构的民族构建,是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伊拉克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先形成国家,尔后在国家框架下进行民族构建。(12)参见冯燚:《国家建构视域下的伊拉克国家认同困境》,《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第33页。
1.公民民族主义与民族构建的失败尝试
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是由一个国家民众的共同身份来定义,宪法保障所有公民不分种族、宗教或信仰的权利和自由。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初建,卡塞姆政府致力于解决民族问题,努力打造完整的国家公民意识和政治共同体。伊拉克中央政府推出阿拉伯—伊斯兰社会和文化价值观,意在加强公民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感。
首先,政府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文化自由和政治参与权。按“族裔—文化”分类,(13)参见H. Rae, State Identities and the Homogenization of Peo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4.将亚述人等基督教少数族群划入库尔德人的势力范围。阿拉伯语被设置为亚述社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叙利亚语的教授和使用没有强制性规定。(14)参见E.Y. Odisho, “The Ethnic,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Modern Assyrians,” Melammu Symposia 2, p. 144.其次,政府将“美索不达米亚想象”引入国家民族构建的话语体系,塑造伊拉克国民身份。“在意识形态层面满足库尔德人的要求,即他们在共同的家园中与阿拉伯人地位平等,伊拉克的历史是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共同的历史”,(15)A. Baram, Culture,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Ba’athist Iraq, 1968-198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21.倡导以阿拉伯社会的优越性和大城市的经济优势吸引边缘群体。
卡塞姆政府的民族政策最终因库尔德问题而功亏一篑,公民民族主义逐渐被复兴党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所取代。阿里夫总统拒绝公民民族主义,强化阿拉伯人的社会主导地位和民族语言文化优势,以政治手段向非穆斯林族群推广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语。1970年宪法规定“伊拉克人民由阿拉伯民族和库尔德民族组成”,强调亚述人是“难民”和“外来者”,拒绝承认其民族身份。1972年4月,巴格达通过的第251号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说叙利亚语的国民”享有有限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权利。(16)参见Iraq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Granting the Cultural Rights to the Turkman and Syriac-speaking Nationals, Information Series 58, Depository Number for National Library-Baghdad(774), Baghdad: Al-Hurriya, 1974, pp.11-12.这一政策对亚述人的传统文化、历史语言、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延展意义重大,也为调和族际关系提供了契机。然而,这一短暂的民族权利很快被宣告废除。贝克尔(Ahmed Hassan al-Bakr)政府急于应对南部什叶派,为避免两线作战,确保缓冲区少数族群保持中立,旋即收紧族群文化政策,由中央政府控制全国的宗教和文化教育,驱逐外国传教士、强迫基督教职人员改宗,取缔“叙利亚语言协会”及相关的学术活动,等等。至此,公民民族主义主导下的亚述族群治理尝试宣告失败。
2.国家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民族同化措施
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促使阿拉伯国家寻求加强国家民族主义,以服务于国家的独立发展、国族整合和国家构建。贝克尔、萨达姆政府先后推行伊拉克民族主义,向美索不达米亚辉煌的过去“寻找灵感”。利用石油美元,萨达姆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塑阿拉伯人的历史。阿拉伯人被塑造成两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的继承者,伊拉克的历史被回溯至前伊斯兰时代,乃至尼布甲尼撒时期。(17)参见F. Matar, Saddam Hussein: A Biographical and Ideological Account of His Leadership Style and Crisis Management, London: Highlight Publications, 1990, p.235.正如戴维斯的评价:“复兴党政权将历史记忆政治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前政权。”(18)E. Davis, Memories of State: Politics, Histor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Modern Iraq,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3.与此同时,亚述人等古老的非阿拉伯土著族群的历史和民族存在痕迹被日渐抹除或解构。(19)参见S.G. Donabed, Reforging A Forgotten History: Iraq and the Assy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53.
国家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化进程呈现在民族问题畛域的情景在中东既具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其一,政府施行强制手段来构建国家疆域内非阿拉伯族裔的同质化和国家认同。在北部亚述人聚集区推行城市化和阿拉伯化运动,试图将亚述族群纳入主流社会,进而切断其与祖居地的联系。其二,重点管控教会学校,打压亚述族群的文化活动和政治运动,1974年复兴党政府将包括伊斯兰学校和天主教学校在内的所有伊拉克学校收归国有。其三,改造教堂、征收土地和破坏村庄等行为导致大量亚述土著社区消失。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的亚述人不得不进入大城市谋生,讲阿拉伯语或者库尔德语,穿阿拉伯服饰,甚至改用阿拉伯名字。其四,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民族政策。1977年,政府试图切断现代聂斯托里教徒和古代亚述人之间的联系,要求亚述人注册成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1979年萨达姆上台后,对亚述人施以强制性的民族同化。1987年的人口普查中,复兴党直接将“亚述人”剔除出伊拉克国民身份登记表,仅剩“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可供选择。(20)参见R.J. Mouawad, “Syria and Iraq: Repression,”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8, No.1, p. 21.
1988年的“安法尔行动”中,复兴党以亚述人“拒绝”民族同化为由,对其推行种族灭绝行动。在这场不对等冲突中,伊拉克境内将近三分之一的亚述族群选择流亡或改称“阿拉伯基督徒”。(21)参见A. Giwargis, “Until when? The Assyrian Ethnicity Persecuted and Marginalized in Its Own Homeland,”An-Nahar Newspaper, October 1, 2002.概言之,这种由国家民族主义推动的系列措施不仅无益于族际关系的和谐,而且易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长期化。
3.战后国家重建时期亚述族群治理尝试
后萨达姆时期,新政府尝试将亚述人等基督教群体纳入民主重建进程。如2005年宪法初次使用“土著”(indigenous)一词,在第35条规定“国家应以尊重伊拉克文明和历史文化的方式促进文化机构及其活动,并支持伊拉克土著的文化取向”,“关注少数民族在特定省份寻求家园时被迫阿拉伯化或库尔德化的普遍问题,同时确保少数民族在伊拉克境内的行动和居住自由(防止强行驱逐或剥夺家园)”。这些内容主要是针对萨达姆时期的民族问题而制定的,旨在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增强少数群体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意识,但从实践效果检验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一方面,巴格达政府将亲政府的迦勒底基督徒纳入政治体制,以代替整个亚述人的集体发声,有意区分“迦勒底人”与“亚述人”。在2005年《伊拉克宪法》中所列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权利,直接将亚述人与迦勒底人并列,从政治层面割裂了迦勒底—亚述人的整体性。同时,在全国人口普查中,伊拉克的文件草案中列出的族裔群体清单中去除了“亚述人”选项,改为“阿拉伯人”,并在2016年《国民身份法》第26条强制要求父母有一方是非穆斯林的子女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另一方面,2005年《宪法》有关“保障少数民族拥有宗教和信仰自由权利”的条款并未解决亚述人等基督教群体的生存和安全问题。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亚述族群因与美国入侵者的宗教信仰相同而遭受国内民众歧视和排挤,成为有针对性的暴力活动受害者。有评论者称,解决伊拉克少数民族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重申公民身份的基本概念,而不是就族群配额进行谈判。(22)参见J. Castellino and K.A. Cavanaugh, Minority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40.单就伊拉克民族构建的现实条件来说,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力和沙里亚法的广泛施行使得伊拉克非穆斯林群体的社会权力受到诸多限制,即使伊拉克民主政府建立,亚述族群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意识也未见明显提升。
二、伊拉克亚述族群治理的内在困境
在族群治理的过程中,国家处于何种角色,国家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都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族际政治。在族裔文化多元和民族构成复杂的伊拉克,政府对亚述族群的治理凸显了其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践困境。
(一)国家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博弈
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为解决“认同危机”的有效方法。然而,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国家民族主义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族裔民族主义往往二元相悖。长期来看,伊拉克境内各民族、宗派缺乏将伊拉克视作命运共同体的统一观念,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无从谈起。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占据意识形态主流,前两种具有“排他性的思潮”(排斥非阿拉伯少数族群和非穆斯林)(23)参见黄民兴:《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析当代中东国家的社会整合》,《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10页。基本主导了伊拉克王国时期的宗教少数族群政策——以武力排斥和暴力打压为主。伊拉克实现了“去殖民化”任务后,将民族国家整合设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威权政府时期,重点强调并实践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大力发展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时,将非阿拉伯人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伊拉克国家主义者极力宣传,20世纪的伊拉克人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巴比伦人的直接后裔,并努力促进民众对新国家的自豪感和忠诚。(24)参见M. Farouk-Sluglett and P. Sluglett, Iraq since 1958: 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 New York: I. B. Tauris, 2001, p.17.复兴党政府通过文化考古活动重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辉煌,庆祝民间传统节日、民族活动以重构伊拉克民族的文化历史,却将土著亚述人视为一个种族化的、有威胁的“他者”进行驱逐或同化。
相应地,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民族构建遭遇了亚述族裔民族主义者的抵抗。尽管伊拉克建国已有百年,但亚述族裔民族主义如同潜藏在其族群意识深处的一种“自然基因序列”,它所承载的族裔情感和认同意识从未消失,而且会在特定的情境下被激发出来。亚述族裔民族主义者在本土创建政治团体和文化协会,以“亚述人全球联盟”(Assyrian Universal Alliance)和“亚述民主运动”(Assyrian Democratic Movement)为代表的政治团体在伊拉克议会中占有席位,为亚述人发声,延续亚述人文化,维护亚述人在祖籍家园和流散地的人权和生存权。同时,流散在外的亚述人以欧美为基地,创建了族裔政党组织,寻求“维护亚述人传统文化,提高离散亚述人的集体意识,重申‘国际公认的合法权利’,并组建一支防卫部队来保护亚述人民”。复兴党统治期间,萨达姆命令革命指导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打击或取缔任何谋求自治或威胁国家的政党组织,监控大城市中势力强大的组织团体,逮捕并监禁了基尔库克亚述慈善协会成员,(25)参见F. Aprim, Assyrians: From Bedr Khan to Saddam Hussein-Driving into Extinction the Last Aramaic Speakers, Bloomington: Xlibris, 2006, p.215.清洗与“民主运动”有关的亚述村庄。因此,亚述族群人口大规模流散,亚述族裔民族主义运动更加激进化,尤其海外的亚述离散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回潮,给复兴党政府制造了不小的国际舆论压力。
(二)政治整合与战争冲突导致族际矛盾激化
历史上,伊拉克亚述族群频频陷入中央政府的暴力整合,被迫卷入库尔德冲突。20世纪60年代,深陷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的亚述人分裂为“亲库派”和“亲政府派”,饱受两方面政治势力的拉扯。复兴党政府将宗教少数族群视为伊拉克北方的安全“平衡器”:一方面,政府以“承认”亚述族群的基本宗教和语言文化权利拉拢之,企图将其“驯化”为中央政府压制库尔德人的工具;另一方面,政府恢复东方教会流亡主教西蒙的公民身份,旨在以东方教会牵制“亲库派”亚述人。同时,政府向亚述—迦勒底基督徒抛出政治交易筹码,让其组建“亚述警察”,帮助政府钳制库尔德人,而拒绝合作的亚述人很快遭到打击报复。
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开始。为了消除潜在的“反叛分子”,伊拉克军方将亚述人部署到前线,战争中死伤和失踪的亚述人达4万余众。(26)参见M. Nisan,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McFarland &Company, 2002, p.191.数百名亚述人沦为战俘被扣押在伊朗长达二十年之久。(27)参见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 Justice (AJJ), “Iraq: Continuous and Silent Ethnic Cleansing; Displaced Persons in Iraqi Kurdistan and Iraqi Refugees in Iran,” January 2003.幸存者被视为“没有战斗能力的人”或“残害穆斯林”的潜在隐患,遭受阿拉伯士兵的排挤。为躲避战乱和政治迫害,两伊边境地区仅1984年就有339名亚述人逃往伊朗。(28)参见S.G. Donabed, Iraq and the Assyrian Unimagining: Illuminating Scaled Suffering and a Hierarchy of Genocide from Simele to Anfal, Ph.D. Dissert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0, p.186.1988年2月以后,萨达姆政府以亚述人拒绝注册成“阿拉伯人”或“库尔德人”为由,(29)参见“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Human Rights Watch, July 1993,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7fdfb1d0.html, 2022-08-20.对其与库尔德人一同实施无差别的“安法尔行动”(The Anfal Campaign)。该行动波及亚述人聚集的2个省份20多个地区80多个村庄,近6万亚述人遇难或被俘。据统计,1987年伊拉克基督徒人口高达140万,到90年代中期伊拉克北部有明显亚述人特征的人口则不足20万。(30)参见L.J. Yacoub, Minorités: Quelle Protection?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95, p.241.那些“饱受政治屈辱”的亚述人成为离散族裔民族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事实表明,暴力整合不但没有促进亚述人的国家认同,反而加深了少数族群的悲剧性历史记忆和受害者心态,进而消解了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意识,不利于族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与民族融合的推进。
(三)亚述人的次国家认同消解国家认同
亚述人处在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两大主体民族的缓冲带和油气资源富集区,此区域长期的政治对垒和资源争夺塑造了亚述族群多元化的认同结构。其中,亚述族群对库尔德政治组织的次国家认同意识渐趋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亚述人的国家认同。
长期以来,库尔德政治组织为争取自治地位而推出庇护政策和政治承诺,拉拢亚述人及周边族群。1991年,库尔德斯坦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成为半独立地区。库尔德议会随即承认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允许基督教教育和叙利亚语合法使用。2005年《伊拉克宪法》第140条允许有争议地区实行投票公决,以决定此类区域是加入库尔德斯坦还是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在库区议会占有席位的迦勒底人相信加入库尔德斯坦“比分散在伊拉克政府和库区政府之间更好”。(31)“Christians of Iraq, Christians of Iraqi Kurdistan Demand Autonomy and Annexation of the Nineveh Plain to the Region,” Tahawolat, January 22, 2010.2009年《库尔德斯坦宪法》的第35条明确规定,保障阿拉伯人、迦勒底—亚述人、叙利亚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以及亚美尼亚人等族裔的文化和政治权利,并允许少数族群在其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享有自治权。
与此相对应,库区通过宽松的语言文化政策争取亚述族群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库区2005年《宪法》第1章第4条规定,除阿拉伯语和库尔德语两种官方语言外,允许以亚述语和古叙利亚语为母语的基督教少数群体有自由使用语言和教育子女的权利,公立学校亦可使用古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教学,私立学校也可以选择其他语言教学。2014年,库尔德地区继伊拉克《官方语言法案》之后颁布《库尔德地区官方语言法》,规定除了库尔德语和阿拉伯语之外,古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也是其民族聚居地的官方语言。(32)参见马慧琳:《现代伊拉克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民族关系的视角》,《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20年第1期,第27页。亚述族群显然更倾向于各方面条件相对优渥的库区,他们还在多个领域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展开合作,进一步培养新一代亚述人对“库尔德斯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此外,库区还在伊拉克战乱和恐怖主义盛行时期给予少数族群一定的庇护,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央政府的职能。2016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IS)占领亚述人集中的摩苏尔地区。库尔德人及时为亚述人提供庇护,安置难民。相对于安全形势复杂的阿拉伯地区,库区能够为亚述人提供必要的安全庇护场所和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亚述人倾向于选择到库区生活和工作。2017年9月25日,库尔德地区发起独立公投,对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国家统一构成挑战,其中也有伊拉克亚述人为代表的基督教少数族群的政治助力。
(四)安全问题和人口流散性加大治理难度
后萨达姆时代,威权政府轰然倒塌,宗派战争、种族暴力和恐怖主义肆虐,民族构建和基督教族群治理问题陷入困局。一方面,新政府缺乏整合社会的实力,安全部队亦缺乏有效维持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强大武装力量,无法高效保障亚述人等非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安全。因战乱中的社会秩序混乱,当基督徒不遵守某些伊斯兰着装规范或宗教行为规则,很容易遭到恶意攻击或暴力针对,亚述人等少数群体被迫沦为什叶派和逊尼派政治权力争夺的边缘参与者或宗派暴力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亚述基督徒因宗教身份易成为极端分子实施肉体消灭的目标。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后,“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大肆扩张。极端分子以“不尊重伊斯兰教”为由攻击亚述人,如抢占其住宅,随意绑架并勒索财产,攻击教会,骚扰妇女,等等。2014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捣毁并盗卖摩苏尔博物馆的历史文物,肆意驱逐和屠杀亚述人,强迫其缴纳“人头税”并改宗伊斯兰教。这些暴力行径,迫使尼尼微和摩苏尔等地的亚述人大量逃离祖居地。那些逃往大城市或境外的亚述人无疑面临就业、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棘手的问题。
此外,战乱导致大范围的人口流散。据统计,2003年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直接后果导致约100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战后约有200万人口流亡国外。(33)参见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mergency Needs Assessments,” IOM bi-weekly report, March 15, 2008, p.1.联合国难民署2005年10月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0月到2005年3月,仅前往叙利亚避难的70万伊拉克难民中就有36%是基督徒。2006年5月3日,联合国发布报告(IPS/GIN)称:“如果不及时觉醒,伊拉克亚述人就会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庞大的流散者群体加大了伊拉克民族整合的难度,也为少数族群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虽然2008年伊拉克政府制定了一项有关难民流离失所问题的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 to Address Displacement),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的行动。(34)参见R. Cohen, “Iraq’s Displaced: Where to Turn?”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4, Issue 2, 2008, p.328.
三、伊拉克对亚述族群治理的现状评析
多民族国家通常围绕核心民族进行建构,而少数族群治理是多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共同体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国家政治碎片化的现实困境要求伊拉克政府重视民族建构,将少数族群纳入国家重建进程,巩固国家政治和民族共同体。
(一)从威权到民主:族群治理条件与环境变化
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重建是两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但都对族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反萨达姆派高举的“宗教”群像,标志着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一个国家的族群分化程度较高,其民主转型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也更大。(35)参见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第5页。伊拉克国内长期形成的民族矛盾、部落隔阂和教派冲突在战后出现了集体性的爆发。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伊拉克民主政权在强化族群政治动员和政治竞争时,同样容易激发族群冲突。2005年《伊拉克宪法》中为亚述人等基督教少数族群设置了议会席位,保障“少数族群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自由权利”,但在实践中言行不一,朝令夕改,严重挫伤了亚述族群参与战后民主重建的积极性。2006年伊拉克陷入社会动荡与族际冲突,亚述人等宗教少数派成为政治极端者暴力迫害的目标。2009年1月的省级议会中相关少数群体权利的条款引起一场针对基督徒的社区暴力运动。2009年美国撤军后,亚述族群因被视为“美国与西方的代理人”而被暴力针对,40名基督徒遇害,12000多人流离失所。(36)参见Mumtaz Latani, “Still Targeted: Continued Prosecution of Iraq ’s Minorities,”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June 10, 2010, p. 5.2010年3月议会选举前夕,另一波针对亚述基督徒的暴力活动频繁发生。
可见,从威权统治到民主政治,伊拉克对少数族群的治理并未收到积极的效果。根源在于,对于伊拉克国家而言,无论文化纽带,还是血缘关系,都不能有效地凝聚亚述人等古老族裔群体,还需重点保障其政治权利和族群利益来激发其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从而赢得族群成员对国家的长期性忠诚。一方面,政府要承认亚述族群保持和加强其自身习俗、文化传统以及按照自身需要和愿望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保证亚述族群的社会和文化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务必完善伊拉克的民主制度,将亚述人等基督教少数群体纳入现代国家的政治轨道,以避免其进一步边缘化。
(二)离散民族主义与亚述人问题的国际化影响
“民族主义的历史力量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形态,但民族主义所内含的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仍然与国家政治构成某种紧张关系。”(37)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对于散居在外的亚述人来说,民族同化的威胁和离散化的状态促使他们重新审视族群身份,其政治诉求中往往凝结着对族群悲惨记忆的叙述、对族群未来的担忧以及对族群生存现状的努力挣扎。因此,离散民族主义者在思想上往往比本土族裔民族主义者更为激进。他们致力于族群后代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力尽所能延续族群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尽管亚述族群以阿拉伯语、库尔德语或英语作为工作和生活语言,但叙利亚语是其内部情感和宗教交流的主要语言媒介。每年8月7日是亚述人的“烈士日”,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都建有大屠杀纪念碑。这些纪念符号和历史标记加强了亚述人的集体记忆,维系并延续着亚述人的族群认同感和使命感。在亚述族裔民族主义与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的数次暴力对抗中,都伴随着大量人口死亡和流散,这些流散者和政治难民的创伤性历史记忆在不断叠加,为亚述离散民族主义积蓄了充足的情绪能量。(38)参见梁茂春:《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第66页。1983年,贝特纳哈宁民主党(Bet Nahrain Democratic Party)发表《亚述民族宣言》(Assyrian National Manifesto),要求将“亚述自治州确定在摩苏尔省或杜胡克省”。(39)参见S. Dadesho, “The Assyrian National Ques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 A Historical Injustice Redressed,” Bet Nahrain, 1997, p.275.20世纪90年代,散居美国的亚述人继续坚持自治主张,要求创建一个以杜胡克与摩苏尔省为中心,并与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划界而治的自治区。
今天的亚述离散民族主义运动内容十分庞杂,跨越不同的教派、地域环境和社会政治背景。尽管亚述人在伊拉克及其所流散国家均属于绝对少数,但他们的政治民主运动活跃,积极扩大海外族裔民族主义力量,四处游说并寻求大国援助,对巴格达政府施以政治压力或舆论讨伐。离散民族主义者长期关注伊拉克亚述人的命运,也曾尝试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亚述人组织起来,力求与本土民族主义者实现政治联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跨界族群及其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出现了跨国、跨地区联合的趋势。阿拉伯变局以来,中东少数族群的本土民族主义和海外离散民族主义实现了网络联合,政治运动呈现出新的态势。亚述人、亚美尼亚人等群体很早就通过互联网平台介入、影响区域政治,尤以流散在外者为主,他们通过互联网实现了个体间的互联互通:创建网站、整理档案、举办学术论坛,密切关注故土同胞的生存状况,积极教授和传播民族语言,将伊拉克政府的族群政策和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曝露在国际舆论中。亚述族群问题国际化、焦点事件透明化,不仅加大了伊拉克政府对少数族群的治理难度,也为伊拉克国家的民族构建理路附着了国际舆论监督,迫使其政府在制定民族政策时更加审慎。
四、结语
从伊拉克王国到共和国,从威权政府到民主政治,伊拉克亚述族群的治理始终问题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归纳原因,首先在于其国家政权性质的特殊性。伊拉克是以阿拉伯民族为主导的伊斯兰国家,缺乏现代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也缺乏妥善的民族治理政策。起初的治理思路主要借鉴了伊斯兰帝国时期的“米勒特制度”,即承认宗教少数族群的部分权利,又不承认其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而是代之以宗教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伊拉克中央政府既要强调民族整合、民族构建,又不愿从根本上承认少数族群获得平等的政治文化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少数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意识淡漠。其次,民族凝聚力长期欠缺,也是现代中东国家处理少数族群问题时遭遇的普遍现象。因而,培育少数族群的共有观念和国家认同意识对国家稳定和民族国家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层面的共有文化观念,单靠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约束,族群冲突在所难免。因此,国家层面需要建立具有共同性的“文化”作为各族共享和一致认同的向导,促使各族群在价值观念上认同彼此。显然,亚述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同一性还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同时,正值民主重建和民族国家构建关键阶段的伊拉克,国家与亚述族群之间的关系将继续处于互动、试错、纠错、调适与适应的过程中。再次,亚述人对库尔德自治政府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与传统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这一类次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严重威胁到了国家认同的形成,但并不能说明族群认同、次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彼此相互矛盾。因为在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结构上,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与次国家认同三者是可以协调共生的。“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40)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因此,要客观对待不同层次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方能制定更为切实可行的族群治理政策。
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跨境、跨界人口流动频繁,多民族国家势必要面临各类离散民族主义者的考验。伊拉克亚述离散族裔民族主义在互联网的加持下,虽然可以有效监督伊拉克政府的宗教少数族群政策和治理实践,推动其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但也容易导致国家政府频繁遭受国际人道主义谴责和巨大舆论压力。由此引发的外来势力干涉和族群问题国际化,也将是伊拉克政府未来民族构建和族群治理过程中较难规避的风险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