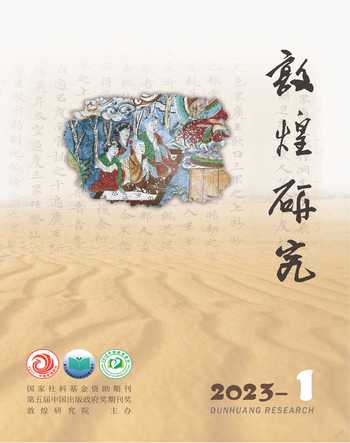莫高窟第428窟影塑千佛相关问题考述
2023-05-30陈培丽宁强
陈培丽 宁强



内容摘要:千佛在敦煌早期石窟的各类题材所占壁面比例中居于首位,是敦煌早期石窟艺术中十分兴盛的题材。莫高窟第428窟四壁上层保存了敦煌石窟中最多的影塑千佛,有1485身,它们按照一定的排列组合方式精心制作而成。该影塑千佛与西壁五塔图中央大塔上层的白衣佛构成三世三千佛,其在第428窟中的造作与北朝时期僧尼坐禅观像和僧俗信众礼拜供养三世三千佛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莫高窟第428窟;影塑千佛;三世三千佛;禅观与礼拜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1-0056-09
A Study on the Clay-Molded Thousand Buddhas in Mogao Cave 428
CHEN Peili1 NING Qiang2
(1.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Gansu;
2.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The Thousand-Buddha motif was a very popular theme in Buddhist art that appears more than almost any other theme in early Dunhuang caves in terms of wall surface used to paint murals and house statuary. There are 1, 485 molded small Buddhas stuck to the upper part of the four walls of Mogao cave 428, the largest amount used to express the Thousand Buddhas motif in any of the Dunhuang caves, all of which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specific patterns of combination. Together with the illustration of Buddha in a white cassock on the upper level of the large central pagoda in a painting of the Vajrasana Pagoda on the west wall of the cave, this set of artworks combine to form the Three Thousand Buddhas in the Three Ages. The appearance of this theme in Mogao cave 428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tivities of both monastic and secular practitioners paying attribute to the Three Thousand Buddhas in the Three Ages, and to the meditation and image-worshiping practices of Zen monk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Keywords:Mogao cave 428; clay-molded statues of the Thousand-Buddhas; Three Thousand Buddhas in the Three Ages; meditation and worship
一 引 言
影塑是用泥制模具(泥范)将泥、细砂和麦秸等混合物翻制成塑像后,将塑像的背面粘贴于墙壁上,并在其表面敷彩,装饰成高浮雕的彩塑工艺。用影塑制作的佛教艺术题材有佛、菩萨、供养菩萨、千佛、飞天、化生和莲花等,圆塑身上的璎珞、珠串、花饰等也多使用影塑[1]。千佛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竺法护译《贤劫经》中:“佛告喜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千佛名号。” [2]可见千佛最初指的是贤劫千佛,之后扩展成三世三千佛,即过去庄严劫千佛、现在贤劫千佛和未来星宿劫千佛。另外,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乃至十方诸佛、化佛、分身佛等也一般被歸为千佛,并且在制作千佛图像时也不一定完全按照佛经中的千佛数量进行制作,因此人们一般将数量多的佛视作千佛{1}。用影塑制作的千佛图像即是影塑千佛。
第428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三层,为敦煌北朝时期最大的一个中心塔柱窟,学界一致认为其由北周时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义主持修建。窟形为中心塔柱式,前部为人字披顶,后部为平顶。主室后方的中心柱四面均开一龛,龛内外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四壁分三层,上层为影塑千佛;中层为佛传、本生、因缘故事画及佛说法图等;下层为供养人画像。本文主要围绕四壁上层的影塑千佛展开研究。
沙武田认为,第428窟影塑千佛的出现是由于敦煌画工感到绘制千佛非常麻烦,因此创造出省时省力的影塑千佛来代替,为以后大量出现的模制佛像提供了先例[3]。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其一,影塑千佛早在北凉时期修建的张掖金塔寺东、西窟中就已经出现,但是未得到大量推广,莫高窟也只有为数不多的4个早期洞窟中有影塑千佛,它们分别是西魏第288窟、北周第428窟及隋代第302和第303窟,其他地区的影塑千佛仅见于麦积山北周第31、4窟。这说明在几乎窟窟有千佛的敦煌和河西北朝石窟中,影塑千佛并不受欢迎。其二,根据宁强、胡同庆对莫高窟第254窟千佛图像的研究可知,绘制千佛的制作程序大致可以分为七步:第一步确定位置坐标,第二步确定比例关系,第三步描绘轮廓,第四步晕染分明暗,第五步上色,第六步绘定稿线,第七步提神点睛[4]。西千佛洞西魏第9 窟是展示绘制千佛程序的实例,该窟前壁上方的五排千佛以红、蓝、黑、绿四种颜色为一组横向循环排列,其中最下排的千佛没有绘完,仅留有确定位置坐标和比例关系的起稿线,绘完的四排千佛上下排又有平行分界线和定型线,完全印证了宁强、胡同庆对于绘制千佛步骤的看法(图1){2}。相似的例子还见于西千佛洞第12窟。据笔者访查,影塑千佛③的制作程序大致可以分为八步:第一步确定位置坐标,第二步确定比例关系,第三步制作模具,第四步翻制塑像,第五步将塑像背面粘贴于墙壁上,第六步上色,第七步绘定稿线,第八步提神点睛。即是说,将绘制千佛描绘轮廓和晕染分明暗的步骤换成了制作模具、翻制塑像和粘贴塑像的步骤,当然其中还包括和泥和翻制方式等更多粗细结合的工作,实际上更为繁杂。其三,莫高窟早期洞窟中的影塑千佛大多位于中心塔柱窟的中心柱上方,如第288窟的影塑千佛位于中心柱四面龛上方,第302窟和第303窟的影塑千佛位于须弥山状中心柱的七级倒塔上,而绘制千佛则大多充斥四壁,造成“光光相接”的艺术效果,如第272、259、254、257、251、263、260、435、431、249、288、286、247、461、438、430、290、442、296、297、299、248、301窟等[1]161。由上可知,影塑千佛要比绘制千佛的制作工序更复杂,以致敦煌画工较少使用。
第428窟的千佛全部位于四壁上层且全部采用影塑方式制作,凸显千佛在该窟中的重要性。目前未见对该影塑千佛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仅有少量相关文章简要提及,如张大千《敦煌石室记》(苏莹辉点校后改名为《漠高窟记》)将莫高窟早期洞窟中的千佛图像一律定名为贤劫千佛,但却对第428窟(张大千编号为213窟)四壁上层的影塑千佛单称为千佛[5];《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将莫高窟早期洞窟中的千佛一律定名为千佛,其中第428窟条后注曰:“此窟四壁上部原各影塑千佛”[6];施萍婷认为第428窟四壁上层的影塑千佛5排,代表三世十方诸佛[7]。显然前人对第428窟的影塑千佛并无统一认识。鉴于此,本文在考察该影塑千佛布局与构成情况的基础上,初步分析其性质和功能。
二 布 局
莫高窟第428窟是敦煌石窟中影塑千佛最多的一个洞窟,有1485身①。这些影塑千佛按照一定的排列组合方式精心制作而成。四壁上层的影塑千佛均分五排制作,高度一致,约1.5m,所有小佛像占据的矩形平面宽度、高度亦一致,宽约0.18m,高约0.3 m{1},由于南、北壁较宽,有13.5m,东、西壁较窄,有10.8m,因此南、北壁较东、西壁的小佛像数量要多一些,具体为:南壁415身、北壁425身、西壁335身、东壁310身。
目前,四壁靠下排的小佛像脱落严重,变色严重,靠上排的小佛像保存较为良好,东壁和南、北壁东侧的小佛像脱落严重,变色严重,西壁和南、北壁西侧的小佛像保存较为良好。考虑到五代宋以后前室曾大面积坍塌,大量光线自东壁甬道口进入主室,推测脱落的小佛像是由于光线影响了其与壁面的黏合度所致。小佛像脱落后的壁面仍保留了泥地外形轮廓,与现存小佛像一样逐个排布,根据现存小佛像的分布规律可推知脱落小佛像的身色和形态。
三 构 成
莫高窟第428窟四壁的影塑千佛均以土红色涂地,并以相互垂直的经纬直线构成面积相等的矩形平面,所有小佛像被平均分布于这些矩形平面中。小佛像的宽度与矩形平面一致,约0.18m,不过高度稍低于后者,约0.25m,因此形成了佛与佛左右之间排列紧密而上下之间留有空隙的状况(图2)。
所有小佛像的左(或右)上侧均有用于书写佛名号的榜题框,由于矩形平面的纵向线(即起稿时绘制的经线)没有残存痕迹,且上下两排小佛像的榜题框互相之间没有完全对齐,因此粗看无法分清每一方榜题框与其左右两侧小佛像的从属关系,只有将目光移到各壁面的起始位置方可知每一方榜题框从属于其右下方的小佛像。榜题框为白色长条状,宽约0. 03m,高约为小佛像背光顶部至矩形平面上方横向线(即起稿时绘制的纬线)的距离,约0.07m—0.1m。遗憾的是,所有榜题框中的内容都已经无法辨识。
所有小佛像的形态一致,均作正面相,面部圆润,有的五官漫漶,有的五官尚存;头顶的肉髻扁平,与中心柱四面龛内主尊的肉髻相类,体现出北周佛像的艺术风范;身披通肩圆领袈裟,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莲座位于矩形平面下方横向线以下的位置,既可作为上排佛像的坐具,又可作为下排佛像的华盖,节省了专门绘制华盖的工序;每身小佛像身后都有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背光,头光和背光不仅凸显了它们的神圣性,也对它们起着衬托作用。
头光、背光、袈裟和莲座都是第428窟影塑千佛的基本组成元素,它们以白、蓝、黑、红四种颜色组合成四种不同的小佛像:第一种小佛像为红袈裟、黑头光、蓝莲座和蓝背光;第二种小佛像为蓝袈裟、黑莲座、白头光和红背光;第三种小佛像为黑袈裟、蓝莲座、红头光和白背光;第四种小佛像为白袈裟、黑莲座、蓝头光和红黑相间背光(表1)。四种小佛像作为一组横向循环排列,上层与下层则按错一位的方式循环排列,整体形成一种“∕”式的光带效果,依次连接组成千佛组画(图3)。
四 性 质
目前学界对莫高窟千佛图像的研究大多是围绕榜题中有千佛名号的千佛图像进行的,如第254、100、98、246窟等,通过将它们的佛名号与相关千佛名经进行比对就可以确定这些千佛图像的性质。但是,莫高窟中更多无法识别佛名号的千佛图像不能采用这一方法,这些无法识别佛名号的千佛图像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榜题,但是榜题中的佛名号由于年代久远而隐没,另一种是在绘制千佛图像的初期就没有榜题,当然也就没有书写佛名号。根据梁晓鹏的研究,有榜题的千佛图像主要表现的是《千佛名经》或其他佛经中的千佛内容,千佛为图像的主体,而无榜题的千佛图像只是作为某个经变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多个经变的共享部分,主体是其他佛经,如《法华经》《观无量寿经》等,千佛图像只起供养对象和行为见证的作用[8]。第428窟的影塑千佛有榜题,可以肯定其表现的是《千佛名经》或其他佛经中的千佛內容,但是由于榜题中的佛名号无存,因此只能借助相关《千佛名经》和千佛图像来考察其性质。
根据前人对莫高窟现有题名的千佛图像研究可知,莫高窟充斥四壁和窟顶的千佛图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三世三千佛,如北魏第254窟四壁的千佛图像,佛名号出自阙译人名今附梁录的《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和《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4]25-28。另一种是贤劫千佛,如晚唐第9窟中心柱南北侧平顶千佛图像和绘于盛唐第121窟甬道平顶的五代千佛图像,它们依据《密迹金刚力士经》和《大悲经·礼拜品》绘制而成,表现了贤劫千佛宿世因位受记和今世果位兴世的主题,属于贤劫千佛变相图[9];五代第98窟窟顶千佛图像,佛名号出自敦煌本《佛说贤劫千佛名经》(该经底稿与S.6485《佛说贤劫千佛名经》类同)[10];五代第100窟窟顶千佛图像,佛名号出自北大藏D079号《贤劫千佛名经》(卷上)[11]。西魏第246窟四壁的千佛图像为西夏时期所绘,该千佛图像的佛名号出自S.4601《贤劫千佛名经》(卷上)和北848《贤劫千佛名经》(卷下)相似的敦煌分卷本《佛说贤劫千佛名经》 [12]。其他窟内有榜题的千佛图像不出这两种千佛之外,因此第428窟影塑千佛应是三世三千佛或贤劫千佛之一种。
目前所见的《贤劫千佛名经》主要有大藏经收录的《贤劫千佛名经》和藏经洞出土的写卷《贤劫千佛名经》,大藏经收录的《贤劫千佛名经》有“阙译”和“开元”两种译本,“阙译本”中共有1006个佛名号,“开元本”中共有1000个佛名号;藏经洞出土的写卷《贤劫千佛名经》大多残缺,从保存较完好的《贤劫千佛名经》看{1},没有超过1000个佛名号的。莫高窟中目前所知为贤劫千佛的千佛图像也没有超过1000身的,如第98窟的千佛图像有703身,第100窟的千佛图像有197身,第246窟的千佛图像有918身,等等。第428窟影塑千佛的数量要多于《贤劫千佛名经》中收录的千佛名号数和莫高窟中表现为贤劫千佛的千佛图像身数,因此其不可能是贤劫千佛,只可能是三世三千佛。
莫高窟北朝洞窟中目前可以确定为三世三千佛的千佛图像在北魏第254窟。该窟为中心塔柱窟,窟内的千佛图像按照一定的规律分布于四壁,共有1235身,每一身都有榜题,榜题中可辨识的千佛名号有783个,不过仅出现了过去庄严劫千佛名号和未来星宿劫千佛名号,由于有的榜题漫漶,宁强、胡同庆对其中有无现在贤劫千佛名号持保留态度[4]25。贺世哲则认为该窟很可能是以塑绘联壁的方式表现了三世三千佛,即四壁的千佛图像为过去、未来劫千佛,而中心柱四面的释迦、弥勒塑像和四壁的佛传(《降魔》)、本生(《萨埵太子本生》和《尸毗王本生》)、因缘(《难陀出家因缘》)故事画为现在贤劫千佛[13]。从宁强、胡同庆抄录的第254窟千佛榜题校录及位置示意图看[4]39-44,该窟千佛图像中的佛名号虽然有缺失,但并不是大面积缺失,缺失者均位于可识别的过去庄严劫千佛名号和未来星宿劫千佛名号中间,这意味着该窟的千佛图像在绘制初期就没有绘现在贤劫千佛,那么现在贤劫千佛是否真如贺世哲所说,是以中心柱和四壁的释迦、弥勒、佛传及本生图来代替呢,笔者不这样认为。
莫高窟第254窟西壁中央绘一铺白衣佛,恰好位于过去庄严劫千佛和未来星宿劫千佛的中间(图4)。据《法苑珠林·法服篇》记载,在释迦牟尼初成佛道时,河神转交给他一件迦叶佛遗传下来的“安陀会”(又称白?五条衣),当释迦牟尼穿上它时,大地震动,“安陀会”四角放光,寻光而来的十方梵王告诉他,此衣为拘留孙佛衣,拘留孙佛涅槃后辗转相付而来,在释迦涅槃后应将此法衣付嘱娑竭龙王,“令依此法衣造八万领,仍造塔供养,镇后遗法……此衣贤劫中最初而造”[14]。可见“安陀会”是贤劫千佛相继法付嘱的信物,衣为白色,联系莫高窟第254窟中心柱龛内的释迦像和四壁的佛传、本生、因缘故事画,可知此白衣佛应是处于贤劫中的释迦牟尼佛,其与四壁的过去、未来諸佛共同构成三世三千佛。莫高窟北朝第263、435、431、288窟西壁中央的白衣佛周围亦围绕有千佛图像,四壁绘有释迦说法图及佛传图,这些窟内的白衣佛表示的亦应是处于贤劫中的释迦牟尼佛,它们分别与同窟四壁的千佛图像组成三世三千佛{1}。
最早提到三世三千佛的汉译佛经是刘宋畺良耶舍译《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经文指出,三世三千佛是因闻五十三佛名后辗转相教而成,它们与五十三佛有着一定的师承关系。不过,经文却并没有将三世三千佛的名号完整记录,而是仅提到其首尾六个佛名号:
其千人者花光佛为首,下至毗舍浮佛,于庄严劫得成为佛,过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孙佛为首,下至楼至如来,于贤劫中次第成佛。后千佛者,日光如来为首,下至须弥相,于星宿劫中当得成佛。[15]
在南北朝及以前的汉译佛经中,目前所知完整记录三世三千佛名号的是“开元拾遗附梁录”(开元本)和“阙译人名今附梁录”(阙译本)的三千佛名经,即《大正藏》收录的《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和《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宁强、胡同庆将第254窟千佛榜题中的佛名号与上述两种版本的三千佛名经进行比对后,认为该窟千佛图像的榜题内容来自于“阙译本”所依据的译本和初始本[4]28。至于第428窟影塑千佛的榜题内容来自于哪一种三千佛名经,由于榜题内容无存,目前实难判定。
“开元本”和“阙译本”三千佛名经中所载的千佛名号(包括重复出现的佛名号)各有3000个左右,第428窟1485身影塑千佛不可能将它们全部表现出来,其很可能与第254窟一样仅表现了过去、未来二劫千佛。不过,与第254窟不同的是,第428窟并没有在西壁中央绘白衣佛,而是将白衣佛移至了西壁五塔图中央大塔的上层,并在白衣佛两侧配置了二菩萨(图5),结合五塔图中央大塔中层的右腋诞生图,可知此白衣佛表示的是处于贤劫中的释迦牟尼佛,其位于佛塔中起“镇后遗法”的作用,与四壁上层的影塑千佛共同构成三世三千佛。
五 功 能
第428窟为中心塔柱窟,中心柱将主室分为前后两个空间,前部为人字披和南、北壁前部及东壁构成的殿堂式空间,后部为中心柱与南、北壁后部及西壁构成的甬道式空间,这种空间结构决定了该窟兼具供出家僧尼入塔观像和供僧俗信众礼拜的两种功能,而窟内的塑像和壁画则是这两种功能施行的对象。
僧尼入塔观像是为了坐禅观像,而僧尼坐禅观像时也需要观想千佛,值得注意的是,佛经中很少提到观千佛,而是观三世诸佛或观十方佛。作为三世三千佛的第428窟影塑千佛属于三世佛的组合形式之一{1},其应是禅僧坐禅观像的对象。相关佛经中有不少禅僧坐禅观像需要观三世诸佛的记载,据《禅秘要法经》卷下云:“佛告阿难:‘我灭度后,若有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若有欲学三世佛法,断生死种,度烦恼河,竭生死海,免爱种子,断诸使流,厌五欲乐,乐涅槃者,学是观。”[16]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2 《世间净眼品》记载:“若念一切三世佛,广能观察佛境界。诸佛国土成败事,以佛神力皆悉见。”同经卷51 《入法界品云》:“入于现前定,普见三世佛。离垢清净眼,分别诸佛海。”[17]梁曼陀罗仙译《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云:“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18]
俗世男女雕、绘佛像,毋庸置疑是为了现世或来生利益,佛教典籍中有《佛说作佛形像经》《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等专门宣传作佛形像功德的佛经,经文详述了通过“作佛形像”可以获得的种种利益,如“作佛形像报,作大名闻王,金轮飞行帝,典主四天下”“作佛形像报,临终识宿命,见佛在其前,不觉死时苦”[19],等等。通过雕、绘三世三千佛所获得的善业功德与《佛说作佛形像经》一脉相通,《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就提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三世三劫诸佛世尊名号,欢喜信乐,持、讽、读、诵,而不诽谤,或能书写为他人说,或“能画作立佛形像”,或能供养香华伎乐,叹佛功德至心作礼者,胜用十方诸佛国土满中珍宝纯摩尼珠,积至梵天,百千劫中布施者”[20]。“能画作立佛形像”指的即是雕、绘三世三千佛的形象,另外,“能书写为他人说”指的是书写三世三千佛的名号,而“读诵”“供养”和“赞叹”则与僧俗信众礼拜三世三千佛有关。
莫高窟第428窟供养人画像中既有身披袈裟的出家比丘,也有身穿寬袍大袖的俗家男女,因此,该窟中的影塑千佛应是为僧俗二众服务,它一方面为满足僧人坐禅观像得观三世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俗家男女通过雕绘、书写、礼拜三世三千佛,祈求现世消灾免难、来世得生佛国刹土的愿望。由此也可进一步理解,第428窟千佛采用影塑制作而非绘制,在于影塑制作难度更大、时间更长以及费用更多,以此所体现的功德更深。
参考文献:
[1]季羡林. 敦煌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9.
[2]竺法护,译. 贤劫经[M]//大正藏:第14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45.
[3]沙武田. 敦煌画稿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271.
[4]宁强,胡同庆. 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千佛画研究[J]. 敦煌研究,1986(4):35.
[5]张大千. 漠高窟记[M]. 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432.
[6]敦煌文物研究所.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58.
[7]施萍婷,贺世哲. 近承中原、远接西域:莫高窟第四二八窟研究[M]//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二八窟.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19.
[8]梁晓鹏. 敦煌莫高窟千佛图像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44.
[9]梁尉英. 敦煌石窟贤劫千佛变相[C]//敦煌研究院. 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石窟考古卷.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35.
[10]刘永增,陈菊霞. 莫高窟第98窟是一忏法道场[J]. 敦煌研究,2012(6):29-40.
[11]米德昉. 敦煌莫高窟第100窟研究[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212-222.
[12]陈菊霞. 莫高窟第246窟研究[J]. 敦煌研究,2019(3):1-16.
[13]贺世哲. 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122.
[14]释道世. 法苑珠林[M]. 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1116.
[15]畺良耶舍,译. 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M]//大正藏:第20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664.
[16]鸠摩罗什,译. 禅秘要法经[M]//大正藏:第15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267.
[17]佛陀跋陀罗,译. 大方广佛华严经[M]//大正藏:第9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401-723.
[18]曼陀罗仙,译.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M]//大正藏:第8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731.
[19]阙译人名. 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M]//大正藏:第16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789.
[20]阙译人名.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M]//大正藏:第14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