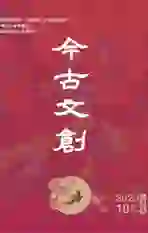《发条橙》主人公的神经症形象分析
2023-05-30赖妍君
赖妍君
【摘要】 《发条橙》(1962)是英国作家伯吉斯的代表性作品。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主人公亚历克斯的神经症人物形象入手,重点运用卡伦·霍尼和弗洛姆的神经症人格等理论,揭示青年主人公激烈反叛的成长历程,这在《发条橙》研究中是新尝试,为小说文本提供新的解读空间。《发条橙》是20世纪中期西方现代小说的现象级作品,分析其主人公的神经症形象的塑造,既是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也能为当下个体自由和健康发展提供启示,以人文关怀的视角观照当代文化的建构。
【关键词】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神经症人格;青年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0-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0.006
《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是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17-1993)1962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塑造了青年主人公亚历克斯的神经症人格形象,他是一个对所在社会的现实和秩序极度不满又无所是从的青年人。这尤其体现在神经症人格的主人公与环境发生冲突的源头、冲突表现和解决冲突的过程中,通过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青年个体发展的影响,能贴近小说中身处异化社会的现代人图景。
一、亚历克斯神经症人格的体现
伯吉斯在《发条橙》中塑造了一个具有神经症特点的人物典型亚历克斯,展示当代社会中人的异化。自弗洛伊德开始,神经症是针对患者对异常有自知能力、代指几种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在所有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结构上的心理障碍,这种探讨是神经症的广义概念。
亚历克斯的精神障碍表现很隐晦,尽管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和同伴的暴力行径不被政府和社会允许,但他认为这是社会需求和个体欲望发生了冲突,他的作恶行为是自我选择应该被肯定。然而在少年帮派作恶生活的大篇幅描写中,亚历克斯不时表达出一种“不耐烦”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他不断推进暴力游戏、寻求新刺激的借口或动因,又并没有因暴力活动得到纾解。事实上,这种烦躁的情绪来自他内心强烈的疲惫感和焦虑①。虽然他也在暴力中得到消遣,但相比其他帮派青年,他对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有超乎寻常的要求;尽管他处于疲乏状态以至于出现生理不适的症状,仍用不间断的快感刺激,掩盖身体和精神的疲惫;用尽情地暴力狂欢,来压抑对自身角色的厌烦。而这种沉溺于放纵几乎是超出他意识外,不可控制的下意识行为,因此亚历克斯的形象具有神经症人格的特征。
二、亚历克斯神经症人格的形成
亚历克斯的神经症根源正在于个体所处的环境和文化。卡伦·霍尼提出神经症是冲突导致的焦虑与无法消除焦虑的矛盾导致的,焦虑根源于来自社会文化固有的矛盾和人际关系的失调。
(一)家庭的创伤
《发条橙》的亚历克斯是因为父母在成长过程中承受了严重的家庭创伤的青年主人公,他长期处于恐惧与防御的心理状态,又试图解决自己的困境带来的心理困扰,刺激其神经症人格的形成。神经症是基本焦虑与基本敌视汇流交织而成,他们都可以追溯到神经症患者童年的家庭关系中,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儿童真正的爱与关心,就会造成基本敌意与基本焦虑。
亚历克斯的父母处于一种异常的精神状态下,亚历克斯的父母每次出场总是“忧郁地”“哇哇哇大哭”。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出“比单纯的保护更深层次的”,是要“灌输给孩子爱生命的态度,使孩子感到活着是美好的” ②。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父母“必须是个愉快的人” ③是培养孩子热爱生命和积极生活态度的基础,父母对生活的态度会传递给孩子。然而,父母如果总是处于紧张苦闷的情绪和极度忧郁精神状态,必然在点滴生活小事中感染孩子,同时也无法担当父母的责任。
总是 “嘟嘟囔囔”的父母想必不能给孩子家庭的安宁和成长的安全感,因此在这样亲子关系下,亚历克斯对父母态度敷衍,缺少真正的敬重之情。小说第一部第五章,父亲对儿子“上夜班”有所猜疑,甚至察觉到他的越轨行为,借梦境小心劝诫儿子;但是,精神的冷漠麻木已经渗透到亲情关系中,亞历克斯用金钱搪塞,竟让父亲选择掩耳盗铃。在亚历克斯受难后,父母不仅不关心儿子反而把他赶出家门。亲情不能为成长提供庇佑,孤独和无助不断累积,就会结晶成一种焦虑的人格态度,它是培养神经症的肥沃土壤。
(二)权威的压迫
权威的压迫,是亚历克斯神经症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现代人在巨大的机器社会中蝇营狗苟,失去自我感,产生极大的生存焦虑。这也引发人们对权力极致的渴望,促使小说中人们背叛感情、欺凌弱小,通过暴力游戏追求权力,展示出异化社会中现代人的心理障碍。
在《发条橙》中,权威往往不是直接出现的,它的象征意义被具象化为父母、学校、警察等。在弗洛姆看来,他们就是公开权威的典例,是实在具象的权力形式,在小说文本中他们成为权力的化身,是压制人性的、不公正的代表。小说《发条橙》中的公开权威无处不在。法律规定“人人都要上班”,亚历克斯的父母终日疲惫的工作;德尔托得家访关心“我”,是因为一旦改造失败,教养跟踪顾问就会得到一颗“大黑星”。为了把“所有的监狱腾空给政治犯”④,亚历克斯在哄骗中当了“矫正疗法”的试验品;迫于政治压力,当局又治好了“我的格里佛”。人们的行动、生活和命运都彻底掌控在权威之下。孤独不安激发人们对力量和权威的更大焦虑,人们希望能成为优越于他人的、管理社会的“官僚”。但是,人们对自我价值感到自卑,意味着人不再感受到对自己的力量和丰富品质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存状态、希望和理想投射到外在力量上。
权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无名权威”,它出现的方式更加隐秘。在弗洛姆看来,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结构和个人发展有更多流动的可能性,所以相比过去固定的社会符号,“群体认同感”更是现代人身份认同的关键。因此,现代人往往有一种“求同”的倾向,它不仅意味着自己与他人亲密关系的联结,还要求人作为一个集体志趣和行为趋向一致。这一过程中隐秘的“无名权威”就在无形中生成;由此,社交是“无名权威”发挥作用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人要真正成长为独立个体,才会也必然会确认自我身份,探索历程就是回答“我是谁”的主体性问题的过程。小说第一章既展现了亚历克斯某一天的夜生活,也是“我”对帮派作恶活动的概览。这些看似“叛逆”的行为,似乎是反主流的,也似乎是他们自我堕落的结果,然而这些夜夜狂欢的青年,并没有所谓的犯罪动机,“下面玩什么花样呢,嗯?”就是他们行动的号角。
“‘一致性是无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这样描述,它促使个体抹杀掉自我的独立个性,用他人的认同去定义自己的存在,因此,不问是非对错“而应当问自己是否顺应了潮流”,“做别人都做的事”⑤,从而失去了自我独立判断的能力。显而易见,亚历克斯们的犯罪是违背小说世界的法律规定,也不容与我们现实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这些行为看似危险又叛逆。但是,求同模式下生成的“新道德”,并不一定能与人文主义传统的道德良心相适应,也不一定会与极权主义相适应。亚历克斯是小团体里“拿主意”的人,但是他自以为是自己所做的决定——小说开头入狱前的亚历克斯成日聚众狂歡,第二十一章痊愈后的他还是和弟兄们混迹奶吧的老样子,这些实质上都在强化团体对个体身份的确证,消解自我的独立性,使得他在沉闷压抑的大环境的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当了另一个“集体”的一员。然而,牺牲独立性所获得的身份认同感终究是虚妄的,在第七章亚历克斯对这样的生活终于感到莫名的厌倦。
三、青年亚历克斯主体性建构的过程
《发条橙》展示出权威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对人的生存方式造成影响和压迫。弗洛姆提出的“公开权威”和“无名权威”两种权威的表现形式都有所体现。而个体也有减轻权威压迫的诉求,因此权威的压力也刺激他们进行主体性建构,重新找回自我意识的过程也是个体成长的过程。
当时的社会文化潮流影响了亚历克斯主体性建构过程的呈现。《发条橙》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既有50年代“垮掉的一代”用自我放纵堕落的方式寻求精神自由的基因,在聚众狂欢里宣泄感情;也有在60年代刚萌生的“嬉皮士”运动崇尚暴力的踪迹,暴力被视作争取生存空间的方式。
《发条橙》的第一部就显示出一群底层叛逆青年在无望中的暴力探索。然而狂热的暴力难以维持个人的理性,亚历克斯们聚众斗殴、诱奸强暴、谋财害命……绝对的自由意志带来个体的极端膨胀,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被他们踩在脚下,他们的行为也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因此,他们为暴力而暴力,暴力行为成了他们本能释放的夜间游戏。就像现实世界的嬉皮士们企图用暴力实现个体的自由,但使用暴力的过程也是他们被动地甚至主动地放弃价值判断的过程,虚无的正义不能为他们的暴行提供合理性,因此这样的探索注定是失败的。伯吉斯通过构建《发条橙》中暴力横行的未来时空,表达出作者对暴力扩张的警惕和警示。
青年是从儿童进入成人世界的过渡阶段,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把“青年文化”视为一种抗拒成人的约束、服从和期望的生活方式。⑥因此,20世纪中期的西方小说中,以亚历克斯为代表的青年主人公往往以自身的行为表达对异化现实尖锐的讽刺,探索个体发展的可能性。个体要摆脱依附实现独立,首先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必须在诚实直面内心的前提下,才能探索真正找到存在的意义。因此,真实是主体性建构的第一步。小说第四章,亚历克斯直言他的不良行为是“关乎自我的”合理存在,尽管为政府等“非自我”不容。所以,亚历克斯的暴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自我真实的认识和遵循。
在暴力探索的明线外,“家”的概念在文本反复出现,家庭创伤促使亚历克斯在潜意识中近乎偏执的寻家之旅,是贯穿主人公成长历程的线索。“家家家,我所需要的是家” ⑦,亚历克斯经历非人折磨被放出国家监狱后,“回家”的渴望异常强烈。强烈的孤独和焦虑造成人的精神困境,消灭困境的强烈欲望又使焦虑加剧,形成神经症人格的恶性循环。现实给了他迎头一棒,父母担心儿子会打破安宁的生活,拒绝他回家。其实,早在亚历克斯锒铛入狱前,他的家庭关系已经有了裂痕。
原生家庭的失败,迫使亚历克斯要在成长中找到“家”。被赶出家门后,他和殴打过的老头们、曾经的哥们儿、仇敌等人重逢,遭到他们的报复和羞辱。这一段经历实际上是对小说第一部的亚历克斯作恶经历的回溯和呼应。他们曾以“弟兄”之名结盟成一个帮派,能玩乐做伴,还能纠集起来和其他帮派对抗,似乎形成了类似于家庭、能共同抵抗风险的新的社会单元。然而,“弟兄”只是小集体内部尖锐权力斗争关系的遮羞布,脆弱的联结最终因背叛彻底分崩离析。“我找到的果然是‘家。”⑧后来,亚历克斯游荡到作家的处所并且得到了体贴和善的照料。作家与主人公亚历克斯之间存在复杂的象征关系。首先,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我”向读者“弟兄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文本中,小说《发条橙》的作家手稿署名“F.亚历山大”(亚历克斯是简称)。其次,“我”逼迫作家观看妻子遭受轮奸和毒打,而“我”在接受行为主义疗法时也遭遇类似的处境。作家亚历山大就像未来的亚历克斯,亚历克斯把此时的作家看作“哥们儿”和“母亲”⑨,在这个名为“家”的地方短暂获得了家庭温暖。然而作家利用主人公的后遗症,把他困在公寓里用音乐诱导亚历克斯自杀。至此,亚历克斯对家的追寻通通失败了。
亚历克斯在不自觉地寻找“家”的过程中不断游荡、反复受挫,痊愈后他又回到了帮派生活在寻欢作乐中游荡,直到萌生了对理想家庭的具体想象。当亚历克斯决定“长大”后,此时他不再呼朋引伴,相反,亚历克斯把这一独立思考后的新目的地称作“独自一人的去处”。由此可见,个体独立是主体性架构的根基。直面自我,勇于实践;从寻找一个“家”,填补内心的空虚,到主动建设一个“家”,实现自我价值;这是他自我觉醒的成长过程,也是他解决家庭问题、找到真正情感归宿的过程。
四、结语
《发条橙》的青年主人公亚历克斯因异化的西方现代社会和苦闷压抑的社会文化,导致无法调节的焦虑,造成深痛的创伤。通过分析人物形象将文本世界与现实社会相联系,亚历克斯的神经症人格展示出人的异化,是对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他与所在环境发生巨大冲突,在不断地碰撞后开始接近真实的自我,展示出青年的发展与蜕变。分析以亚历克斯为代表的神经症人物形象,有助于理解当代文化潮流中的非理性因子,也能为当下个体自由和健康发展提供启示,以人文关怀的视角观照当代文化的建构。
注释:
①Stinson, John J."Condemning the neutrals in oppressively dull worlds:look back in anger,a clockwork orange,and Equus."Notes 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38,no.5,2008.
②③(美)艾里希·弗洛姆著,刘福堂译:《爱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页。
④安东尼·伯吉斯著,王之光译:《发条橙》,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⑤(美)艾里希·弗洛姆著,孙恺祥译:《健全的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26页。
⑥(加)迈克尔·布雷克著,岳西宽等译:《越轨青年文化比较》,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13页。
⑦⑧安东尼·伯吉斯著,王之光译:《发条橙》,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⑨安东尼·伯吉斯著,王之光译:《发条橙》,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参考文献:
[1]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M].王之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2](美)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美)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4](美)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M].陈收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5]蒋天平.疯癫:文化的反叛和文化的拯救—— 20世纪中期美国小说中的青年形象[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5):8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