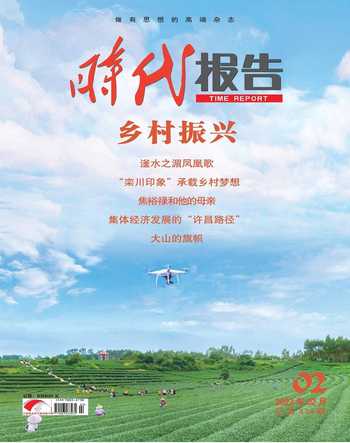从西王楼漫谈明代王氏家族兴衰变迁
2023-05-30丁进兴
丁进兴
2018年4月,在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最关键节点,我分包的扶贫点从北部山区的浅井镇二郎庙调整到城西火龙镇的西王楼。二郎庙因为地理位置靠近杏山及犊水河,村中还有二郎庙,因此,在扶贫间隙,得以登临杏山,下村入户,寻访远古时期和合二仙下棋的石台、志书中记载的汉代神仙刘根隐居之所;站在花果岗上,瞭望犊水源头地貌;亲临二郎庙柏树下,想象二郎神担山的气魄和雄姿。
刚才罗列的这些文化信息,听听就感觉很有味道。到了西王楼时候,远远就看到建于21世纪初期的大唐龙岗发电厂的高大煙囱,以及高大烟囱下村民居住的紧凑而又密集的两层砖混结构的楼房。好在村部在村子最东边,与几家小加工厂、养殖场相邻,显得几分清净。对于喜欢历史文化和寻古访幽的我来说,调整到这么一个一点特色都没有的村子,当时心中有几分失落。由于土地被征收,村民大多在电厂务工,西王楼已经看不到农耕时代的特征,在后工业时代各种利益矛盾交织中平稳地前行。
一、西王楼王氏来源
出于职业的敏感习惯,我翻阅了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的《禹州地名志》,查找到这个村子唯一的文化信息:清代称王七楼。2021年10月,精准扶贫进入后评估时期,即将拉开乡村振兴的序幕,我需要从以前的工作模式中调整思路,开始关注这个村子的历史文化,顺着这个脉络寻访我要找的东西。村干部说,村子原来叫王七楼,是因为一个姓王的进士考了第七名,在村中建有楼房,村子南边古时有个义学,称南学,现在村部的位置原是一个寺庙。
能够捕捉到这些信息确实幸运,我问村里有姓王的没有,村干部思忖了一下说:“有,但是没有几户。倒是两个80多岁的老年人都姓王。”村支书吴国印和我同行,先是到村部东南角一个养殖场,里边养的有羊、鸵鸟,原先还有蛇,听说放生了。王懿德老人正在杂草中清理沫子,他带我们坐在一个简易的办公室里。他说,王七是个进士,考了第七名,城西禁沟有他立的碑,王进士在村子东头盖了楼房。后来一个比他名气大来头也大的南方进士来访,王七的楼只盖了主楼,客厅还没有建起来,来人扮作弹花婆,顺路看了看就走了。后来他们两个见面,王七对那个进士说,你根本没有来过我家。那位进士笑了笑,回答说,你只是不知道,我早来过了。
王懿德老人知道的就这么多,我们到村子最西头电厂一号路王保山家。他家开个小批发部,儿子几年前在外地工厂打工身体损伤,坐在门前晒太阳。王保山说,王进士叫王七,家在村东,建有楼房,再往东今天大队部位置就是寺庙。王进士墓在一号路西边,过去叫石门沟,占地三亩,阴森恐怖。古代有人伐墓,发现是座空墓。建电厂时候,有人挖开墓穴再次进入,什么也没有找到。王保山说,很多人都怀疑王进士在山西当官压根就没有回来过。
询问两位老人是不是王进士后人,二人异口同声说不是。王懿德说自己是从东边太和迁来的,王保山说他家祖上是从南边方岗迁来的。他们既没有家谱,也没有遗传基因,只是凭借祖坟不在西王楼,就判定自己不是王进士的后裔。其实,王进士的后人在明末闯王之乱中纷纷逃离附近村庄,据可信资料分布在方岗东炉、西炉,槐荫街、梁北等地,只是反复迁徙,今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出发地。
二、从史料中寻找王进士
因为近几年编纂第二版地名志的缘故,我要对现代村落增补很多文化信息,在现在词条中,写进了高铁、高速、国道、省道、乡村公路、产业特征、经济来源等近40年变迁发生的巨变,但是,因为第一次地名普查中,各地都把自己家族的来历定义成来自山西洪洞,似乎谁不是洪洞人都感觉没有找到祖根一样,那么,历史文化厚重的中原,尤其是禹州脚下的大地上,明季李自成战乱之后难道是赤地百里,空无一人?很多地方比如无梁、浅井、苌庄等地,出现了从密县迁来,但我认为更多人口是战乱之后回迁,比如明代禹州大家族马文升、刘湛、董世彦家族在战乱中出逃外迁,清代回返的现象,从他们家族人员的个人简历中即可窥见一斑。因此,这次编纂志书,我更多是往前追,从村子的历史脉络中发现古代遗漏的文化信息,为荒芜的地方历史文化增添有价值的内容。
因为这个原因,在禁沟、谷水河、汪楼等地方发现了明代显赫的王氏家族。王纳诲,1521—1606年,字养直,寿八十六,妻郭氏。其祖王善1403年永乐元年癸未科举人,抚幼弟成武弁。任麟游县教谕,升平阳府通判。也就是说,王善在明初就以科举身份在官场出现,那么在第六世王纳诲、王纳忠则家族开始兴起,第七世出现了一门两进士王述古、王则古。在县志中对王纳诲的介绍,是以子述古贵,先后封崇德县令、封刑部主事、赠山西右布政。生七子:习古、宪古、师古、酌古、述古、期古、遂古。在这七子中,最为显赫的王述古排行老五。而县志中记载王纳忠,是这样写的:贡生,有义气。任山西阳城县教谕。以子则古贵,累封礼部郎中。禹州明代一门两进士、三进士比比皆是,比如马天官家族、连格家族、董世彦家族、李乘云家族、魏尚纯家族、刘调羹家族等,那么,因为王姓是个大姓氏,村名中带有王字的多达几十处,又没有家谱传承,确实很难印证。重新查阅进士王述古、王则古的家世,明确记载王姓始祖王善1403年永乐元年癸未科举人,至六世王纳诲、王纳忠时显赫,纳诲生子七,第五子述古1564—1617年,字信甫,号中嵩。1588年万历十六年戊子科举人,1589年万历十七年连登己丑科焦竑榜进士,官至布政司从二品右布政,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卒;纳忠生子一,则古字继则,号具茨,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举人,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周延儒榜进士。官至山西冀北道三品参议、大同知府。
仅仅看到这些信息,不能明确判断其家庭所在地的位置。那么,让我们继续在相关资料记载中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清顺治《禹州志》卷之九·陵墓志:封布政使王怀义墓郡西五里,子封君纳诲祔。民国《禹县志》卷十三·陵墓志:封布政使王纳诲墓 县西镇峰里一甲禁沟西,吕坤撰墓表。
清顺治《禹州志》卷之九·布政王述古墓:郡西板桥。民国《禹县志》卷十三·布政王述古墓,县西义让里四甲汪楼西北。
清顺治《禹州志》卷之九·王则古墓:赠员外王纳忠墓谷水河。子参议则古祔。民国《禹县志》卷十三:参政王则古墓县西镇峰里三甲谷水河。墓在父赠员外纳忠之次。
从王纳诲、王纳忠及其后辈王述古、王则古的墓葬位置看,都在城西禁沟、谷水河、西王庄、西王楼一带。古代墓葬位置非常讲究,尤其是名门望族,更加看重风水堪舆学,往往选择山水俱佳的地方购置茔地,期盼子孙后代兴旺昌隆。那么,西王楼出现的王七的名字引起我的极大兴趣。老百姓口中所谈的王七,直接指向是位进士,他们不知道弟兄几人,只能从科考排第七来定义这个名字。再看王述古,在弟兄中排行第五,王则古则弟兄一人,而志书中记载王则古,则直接称王述古弟,二人同为进士出身,在其同辈分弟兄排名中,只有王则古有排行第七的可能,因此,这个王七,就是古代乡间对王则古的直接称谓。
三、槐荫街王氏家族来历
由于有这些新的发现,我无意间把这几天下乡寻找王七楼历史的情况发到了一个与史志相关的微信群,很快引起王金生的关注。他说,他在南方工作,父辈住在槐荫街,出了一门三将军。对于槐荫街一门三将军的事,大概禹州很多文化人都会知道。但是,我问怎么证明槐荫街王氏就是明代王进士后人?
王金生提供了他们槐荫街王氏的家族传承谱系,而且王伯骧民国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自传:祖居河南省禹县城内西南隅王官街,后改为三官庙街,盖于明朝末年即居于此。王伯骅自传誊录:祖居河南禹县槐荫街(原名王官街)。王伯骅信:所生八子皆以孝廉入仕,父子九人俱受爵禄,乡人名其居里曰王官街。
1626年生的禹州白沙人李经世,其传记有“天性凝重,先达王则古重之”。据州志、县志记载,王则古最后在大同任参议(三品),在他同科进士、大同巡府张宗衡的资料中出现过,而且是在参议任上“仕归”的。在李经世传中王则古的出现不知何年,有可能是“仕归”之后。
从李经世的个人简历中可以看出,他出生于1626年,卒于1698年,明末清初禹州白沙人,字孟常。父果琦,其叔果珍无子,以经世为子。经世性庄重,甚得名人王则古器重。州人任应辰抢劫白沙,果珍事先闻风远避,州守得知此情,疑果珍通贼,囚于狱中。经世怀冤难平,申诉辩白,终得平雪。清朝建立后,李经世位禹州生员,重修白沙书院,竭力助人向学,多赖成就。后经世患病,拒绝就医,遂作《逍遥歌》二章,并自整衣冠,就枕而逝,年72岁。著有《一得录》《录乐录》各一卷。那么如果李经世得到过王则古的夸赞,也定是在王则古致仕之后,这时候的王进士应该在所办南学中对李经世格外照顾。王则古去世年代不详,而其后的李经世已经入清朝任职,但他助人向学,重修白沙书院,此等恩德一定是传自王进士博学好古、助人为乐的风尚。另据无梁龙虎山下村民介绍,白沙李氏古时曾经到周定王附近李氏祖坟上坟,而此支李氏是明初随周定王棺椁一起从开封封藩之地前来守墓的,共有李氏、白氏、王氏等,此后这几个姓氏相继外迁。
查阅张宗衡简历,山东临清人,上任大同巡抚是崇祯四年(1631)戊午,离职是崇祯七年(1634)九月,结局是革职戍边。查阅王则古简历,明代禹州人,字继则。王述古弟。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四十一年(1613)登进士。授任雄县知县,兴办学校,后调任宝坻县知县。任职中,则古刚毅果断,因不会同流合污,被降为江西藩司幕。终因才能声望素著,起用为济南府推官,升大理评事。调兵部主事时,魏忠贤迫害东林党,因则古与其成员友好,受株连削职。魏忠贤败,起用为礼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升任大同知府。由于才干练达移任冀北道参议。因与镇守总监意见不合,辞官归里。那么,从张宗衡与王则古共事时间可以看出,在张宗衡1634年从大同知府革职之后,王则古调任冀北道参议,很快就辞职归里。那么村中所传的南学,是否就是他的最终归宿。村民所说的比他官职大的同科进士来访的人,是不是这个张宗衡?
今天的槐荫街位于老城区西南部,原名王官街。北起四角堂街南口,南至赵坑街火神庙,全长245米,宽5米。相传,该街原为宋家门,至元代,街中古槐荫翳蔽日,枝叶茂盛,人们常聚古槐树下乘凉,故称槐荫街。民国年间,住在街中的王氏一家出了三位将军,王伯镶,六十八军中将代军长。自厦门赴台后任“国防部”中将高参、银行顾问、教会大学中文教授;王伯骏,医学外科教授,抗战时期曾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少将私人医师等,定居南昌百岁正寝;王伯骅,陆军少将師长。人称“一门三将”。因战乱频发,世道混乱,各街道争建栅门以自卫。王家也在街口建起一道栅门上书“槐荫街”,故得名槐荫街。此街道在清代至民国也是重要药市,驻有福泰药棚、义丰长药棚等。此街至今保持着原始风貌。
在王金生提供的大伯王伯骧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自满清入泮,祖训潜研经史,不事满清功名。王家祖训一定始自王则古,他自1635年致仕之后,发生了李自成攻陷禹州三日屠城事件,接着满清入关,统治中原,他倡议后人精研经史,不慕功名,他的后人在清代至十四世王守义悬壶行医济世,朝典承继,一直到民国年间才出了一门三将军,实在是可喜可贺。1929年,直奉大战,蒋介石督军住在禹州倒座关帝庙,1937年版民国《禹县志》在1929年9月的“大事纪”中记道:“蒋总司令督师莅禹”。解放后1989年出版的《禹州市志》“大事记”保留了这一记载,只是口气有所变化,时间记述得更具体了。称“1929年10月8日,蒋介石督师来禹县”。这段经历在禹州籍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先生的文章中有所记载:2018年3月12日,禹州著名“国军一门三将军”之中将王伯骧的儿子王台生先生,从英国回禹省亲时也谈及“蒋来禹”的情况。他说:“(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军)整编为以蒋为统一的中央军,蒋在初次与家父王伯骧见面吃饭时,蒋与家父说,‘禹县有全国唯一的倒座关帝庙,我很喜欢,我巡视过那,还特地在那住了三晚上。”
后来,王金生先生在给我提供的补录资料中谈到:文史资料很具影响力。军委陈宇将军见《汉源文史资料》载王伯骅文章如获至宝,写就长篇报告文学《梦落月城》,其中大篇幅涉及王伯骅。王先生告诉陈将军,《禹州文史资料》有这方面内容,等他注意查阅禹州文史资料后准备再版。
王金生说,我明代始祖王善,开创家族科举入仕,先祖王述古、王则古相继登进士,故乡“世科”牌坊标彰家族世代登科。王述古曾任保定知府,王则古曾任保定的雄县知县,开创家族保定渊源。晚清,祖父王度彰赴保定莲池书院求学,又执教名校直隶高师。全面抗战,父辈王伯骧、王伯駧、王伯骅随26路军驰援卢沟桥,是长驱直入华北的第一支中国军队,在保定涿州与日军第一次大会战。抗战胜利,父亲王伯骏随孙连仲将军北平受降,于保定创办河北省立医院,发展为今天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英国台生弟嘱我撰联他书写敬赠河大附院,联曰:
进士二先人各宰府县,莲池先人执教直隶高师,明清先人重保定;
将校三父辈首战涿州,学者父辈创建省立医院,两岸父辈续前缘。
王金生先生把我文章中谈到的内容发给居住在郑州年已86岁的禹籍人士、河南省出版社退休编辑刘文平,刘先生看到我文章中谈槐荫街原名宋家门,他来信介绍现已无存的宋家门,实属禹州宝贵资料。其信如下:
前面你已发过,我忽略了。我也是从母亲述说中知道的。从我的记忆里,宋家确实是高门大户:一对石狮子把门,青石铺成几个台阶,两边有青石夹护。走马门楼上的匾额上有“明经首宋”四个大字。因年深日久,题头和落款依稀难辨。宋家大院盖得很威风:进了大门坐北朝南是装饰相当豪华的二门。进了二门,临街房是出前檐,有柱子,明三暗五的大房子。南北两厢房各六间。北厢房从西往东第三间是个三层老式炮楼,看家护院。东向是上房两层楼。同样是条石夹护着五层台阶。看来是一个大院儿,我看到的就是院中间一道墙,隔成两个院子,西院走原二门;东院从楼南角又开了门走胡同出去。记得我曾说过我外祖父就住后第四进院。金生,我的印象中的宋家大院就这样。
人上年纪了总有怀念桑梓、叶落归根之感。但愿这篇文章只是抛砖引玉,引出更多人关注,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