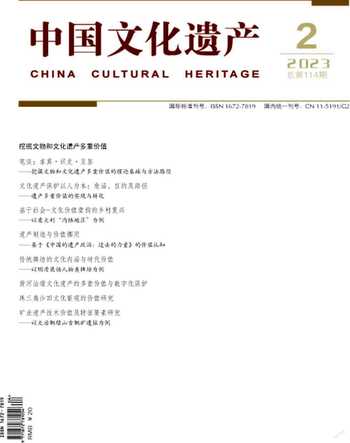遗产制造与价值挪用
2023-05-30潘煜
潘煜
关键词:遗产政治;遗产价值;遗产制造;价值挪用
2020年,由朱煜杰(Yujie Zhu)与克里斯蒂娜·玛格斯(Christina Maags)合著的《中国的遗产政治:过去的力量》(Heritage Politics in China:The Power of the Past)①出版,它整合了二位作者近年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基于此展开更为深度、本质的探讨。概言之,本书首先厘清了遗产话语的诞生、规范、批判变革的历程,提出“遗产已成为现代化工具”的论点,进而阐述使遗产得以“工具化”的两个关键概念,即“遗产制造(heritage-making)”与“价值挪用(valueappropriation)”,并借助城市遗产、活态遗产、民族遗产三类实例予以具体分析。
“遗产制造”和“价值挪用”是理解本书的核心所在。“ 遗产制造” 是一个主体意图驱使的有意识的过程, 作者将这一复杂过程分解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sation)、认证(Authentication)、认可(Recognition)、博物馆化( M u s e u m i f i c a t i o n ) 、商业化(Commercialisation)五个阶段,阐明了事关主体、对话以及利益分配的当代中国遗产事业的形成及有序运行背后的逻辑,为理解国家主导下多主体参与的遗产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笔者认为,这一过程构建了对话的空间:自上而下的官方话语与自下而上的本土声音在此相遇、碰撞,历经争论、协调,最终达到和谐。在此过程中,遗产本体价值被有意识地挑选、强调或模糊,随实践被赋予新的内容,这便是串联起“遗产制造”五个阶段的“价值挪用”:前三阶段是评定中对遗产本体价值的诠释、承认与选择,后两阶段是具体实践时不同主体对遗产价值的感知、赋予与占用,最终生成基于遗产本体价值的实践价值。
本文首先围绕作者梳理的中国遗产利用的演变历程,解析遗产被逐步解放的实质,进而探讨遗产再利用的机遇及其得以完成的关键,即“遗产制造”与“价值挪用”。注重情感叙事、着眼社区参与的“遗产制造”挑战着西方主导的自指式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对遗产边界与实践体系的建构[1],因此本文也意在探寻它在中国特色的遗产利用中的体现。最后,笔者将目光转向“价值挪用”操作不当导致的后果,即实践价值与本体价值的冲突以及实践主体间话语权与机会的不对等所引发的困境。
一、认识当代遗产:被解放的“工具”
遗产自诞生至今,逐步从统治者独占的、服务于单一政治意图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逐渐回归文化本意。但遗产的回归自我并不意味着工具性的丧失,它依旧能与当今政治话语衔接贴合。
(一)被解放的遗产:遗产回归自我
封建帝国时期,遗产只是统治权力的象征,遗产实践从本质上是一种“帝国精英的文化参与与社会控制活动”[2]。随着西方关于遗产保护、利用的思想传入,遗产成为国家统一民心的工具;与此同时遗产实践主体也逐步下移,遗产不再是统治者的“私藏”,而成为彰显民族身份的“公共物品”。中国具有当代特点的遗产利用始于改革开放,政府一方面追求国际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应对城市化、移民、西方流行文化等不稳定因素[3]带来的冲击,同时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的任务也提上议程。
纵观此历程,笔者认为最显著的变化是国家对遗产态度的转变。封建历史时期,前朝遗物对本朝而言是“他者之物”,通常会通过销毁或占有[4]来显示本朝正统。此态度与现代国家完全不同:更迭的封建政权将“非我族类”视为敌对,尤其敌视前朝及本朝他族政权,往往会越过前朝去往更久远的历史时代甚至神话传说中寻求统治合法性;现代国家则强调几千年历史中存在的遗产,即任何朝代、任何民族政权的遗留,都应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遗产而非他者之物,以证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不曾间断的线性统治。
遗产的实践主体则经历了从以统治阶级、知识群体为主,到国家规划、专家指导下,当地社区乃至社会公众多方参与的历变。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与遗产直接相关的人群的情感表达、与遗产交融的生活与信仰,以及由遗产塑造的认同、归属与信念,使遗产在寻求身份合法性时都更加具备跨越时空的情感指向与叙事优势。因此“从当地人手中夺走的”逐步专业化与官僚化[5]的遗产制造发展至今,是专业化与行政化架构下的对话的、情感的回归。
此外,遗产评定也从权威强制认同逐步转向规范的法制化程序。遗产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事业,与之配套的法律、机构以及名录也相应产生。伴随着改革开放,遗产已不再仅是中国的“家事”,而是逐步走出国门,寻求国际的对话与认可,通过将国际话语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逐步探索出适用于中国语境的遗产实践,同时也丰富了世界遗产话语体系。
上述三项转变彰显了中国的遗产认同向规范化迈进,遗产利用逐渐从单一的政治意图中解放出来,逐步回归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然而,表面回归本意的遗产实际更具工具性与可操作性:随着国家由稳定转向稳定发展,遗产不再是单纯具有纪念性、审美性的物或形式,基于国家的需要,它需要“活起来”,即产生于当下的遗产不仅可以追忆过去,还需要它不断与社会发展相贴合并指向未来。
(二)遗产的当代之用:机遇与方向
本书作者多次强调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批判遗产思潮,即“去中心化”和“去边缘化”。笔者认为,这两个概念②具有相通的指向:去中心化是对权威话语体系的批判,去边缘化则是改变政府单一主导下忽视公众需求与本地参与的现状。与此同时,非遗作为个体“治理”更柔和的方式[6],使個体具备了利用遗产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对中国而言,有大量的遗产资源作为基础,加之市场经济的繁荣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全国范围内出现遗产热潮成为必然。综合来看,国内外环境共同决定了遗产利用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不可缺失的一环。
当代中国的遗产利用依旧与官方政治话语衔接,国家发展遗产事业的意图与国家政策紧密贴合,即要求深度挖掘遗产的教育、经济、社会等价值,以求达到人与自然、社会内部以及国际社会三方面的和谐;同时当今的遗产发展理念也与国家的奋斗目标相贴合,比如在遗产地脱贫地区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业工坊促进社区脱贫[7],这实际上是国家依托个体对遗产价值的充分探索,以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目的。遗产承载了国家的政治意图,遗产术语“成为了一种权力机制”[8],它不再是简单的“是什么”,而是“被诠释成为什么”,是“一种源自记忆的官方叙述”[9]。
作者提出的“遗产制造”与“价值挪用”两个核心概念,清晰地阐明了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与以社区居民为代表的个体对遗产价值巧妙的转化与占用过程。
二、作为过程的遗产:遗产制造与价值挪用
(一)遗产制造是一个过程
遗产并不是结果而是过程③。作者将遗产制造的过程分为制度化、认证、认可、博物馆化、商业化五阶段。制度化阶段对遗产的定性有着重要意义,决定着再利用中“谁有执行文化实践的权力以及谁将从后续的转型中获益”[10],此阶段为遗产得到官方合法“认证”奠定了基础。在“认证”阶段,国家以及专业声音往往更具有决定性,但同时专业化与制度化也导致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被忽视[11]。“认证”使遗产取得国际承认的合法身份,而“认可”则侧重于构建公众对遗产的承认。笔者认为,相较于遗产领域的专家,占社会大多数的非专业公众对于遗产的认可是因于官方的“认证”结果,这便是官方权威话语的体现。
遗产的“博物馆化”充斥着规范与重构,原本的遗产空间被重新规划,新增游客中心、商店等服务设施,道路得到整修,交通更为便捷。私人空间成为公共展示场所,官方承认的遗产继承人在其中展演着“被遗产化的”日常生活。而在最后一阶段,作者谈到了旅游业发展对“已冻结的(frozen in time)”遗产进行的商业化改造,作为公共利益的遗产地逐步变为可以用价格来衡量的消费场所。在此阶段,除政府与投资商外,本地居民也参与其中,将他们的生活转变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曾经真实的仪式成为了一种‘舞台表演,一种文化‘商品”[12]。
遗产正式被认定前作为一种资源被利用,制度化、认定与认可的阶段使其完成了从资源到遗产的转变,此过程实际上荡除了过去私人独占的、服务于以往社会的情感与利益网络。而随后两个阶段则使遗产又重归资源,与多元主体的意图相衔接。
资源到遗产的阶段去除了附着于旧社会的价值,而遗产到资源的阶段又赋予其新的社会价值,回归文化意味着“去(过去)利用”与“再(当今)利用”,其实质是实践主体价值取向随着社会演进的变化。遗产制造彰显了遗产价值从私有到公共再到“私有”的转变,而完成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价值挪用”。
(二)遗产制造的核心:“价值挪用”
詹姆斯在《文化挪用与艺术》中谈到“挪用(appropriation)”被定义为“据为己有或者供自己使用” , 并将文化“ 被挪用(being appropriated)”分为三种类型:物品挪用(object appropriation)、内容挪用(content appropriation)④、题材挪用(subjectappropriation)。“价值挪用”与詹姆斯讨论的“文化挪用”并非同一概念,但二者有相通之处⑤。詹姆斯提出文化挪用是有意识的过程,同样,“价值挪用”也是承载主体意图的行为。相较于“文化”,挪用“价值”不仅是外部群体对目标物、形式或风格⑥的作用,它还包括内部群体的自我操作。总结本书作者对于“价值挪用”的阐释,笔者认为,它表现为对遗产本体价值的当代再利用,实质在于具体语境中行政(可协调的)管控下不同实践主体对遗产价值的自由调整与占用。
国家的“挪用”意图贯穿遗产制造始终。遗产在寻求官方承认时试图呈现的是遗产本身的真实性、完整性乃至叙事性价值,这些由业内专家判定,当然权力与知识的对话也会充斥其中。获得“合法身份”后,遗产的呈现则受到权威的挑选、强调与噤声[13],经过“价值挪用”,遗产价值超越了单纯的艺术性、纪念性等本体价值,生成了有具体指向的实践价值,满足了国家促进稳定、社会和谐以及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价值挪用”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国家上层。遗产不仅是一种实体的“物”,它还包含地方与本地个体无形的“共生关系”,是情感、信仰甚至日常生活。朱煜杰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遗产話语存在“情感缺失”⑦,因此中国语境下的遗产制造需要情感的回归。“遗产制造”后两个阶段显示了中国的遗产制造并没有与个体脱节,它关注公众需求,允许公众辩论。个体的“挪用”直观体现在遗产地社区群体对遗产价值的“己用”:通过发展遗产旅游,遗产地社区居民凭借遗产孕育出新型商业化意识[14],在利用遗产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还促进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国家现代化进程。
基于此,笔者认为除国家政治意图驱使外,“价值挪用”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原因还在于无形的情感也承载了遗产价值,但占主导的实践主体(政府、专家)与本地人存在着宗教信仰、生活经验方面的差异,因而需要当地个体作为遗产的“发声人”参与到遗产制造中。“价值挪用”表现为对权威话语、情感缺失的批判,是国家与权威、社区与官方之间主动的、非对立的适应与协商。这二者又与批判遗产思潮中去中心化、去边缘化的概念紧密贴合,是遗产利用在中国的独特呈现。
三、不和谐的“挪用”:价值冲突与主体缺位
“价值挪用”基于遗产本体价值融入了制造者赋予的实践价值,是对遗产价值的充分挖掘与有意利用。但此过程若操作不当,便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笔者将其总结为两部分:一是有意识的挪用行为可能会导致实践价值与本体价值的冲突,突出表现为商业模式下遗产真实性与真实感的混杂;二是多主体参与下的话语权与机会分配不均,即部分主体可能会“被动缺位”,使得“挪用”无法完成。
(一)模糊的边界:舞台、购物中心与遗产地
旅游商业化对遗产真实性的冲击首先体现在经济至上导致的商品市场的“同质化”生产中:当遗产被认定后,诞生于此环境的物品也作为“遗产代表”进入市场。在旅游市场的诱导下,依赖工业批量化生产带来的生产效率,大批“同质化”的机器产物以及“拥有传统风格”的现代物品被卖到游客手中,已然与约瑟夫·康奈特(Joseph Cornet)提出的“为了传统的目的、由传统艺术家制作、符合传统的形式(for a traditional purpose;by atraditional artist;conforms to traditional forms)的物件才可以被认为是具备‘真实性”[15]的论点相悖。当然游客或许并不怀疑它是否“真正真实”,“因为它们与真实事物的相似性给了这些游客一种真实的感觉”[16],游客实际得到的是具有真实感的体验。
冲击其次体现在迎合观众体验的遗产改造:阿尔津·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制造传统会随着商业和审美要求或者更大规模的、远处的顾客诱因而改变⑧。为使游客更好地参与“纳西族婚礼”的体验项目,承包商与当地人简化了传统婚礼繁琐的过程,为游客们“定制”了适合他们的纳西族婚礼,这其中甚至有汉族的表演人员[17]。对游客来说,他们进入的并不是真正的“后区域”[18],而仅仅是预先准备好的“没有出口的”舞台式旅游空间[19]。商业化模式引导下⑨丧失文化内核、徒留形式外壳的表演式遗产使游客止步于“观众”,只能近距离观赏“舞台”上由“导演”与“演员”精心编排的新奇的但并不完全真实的“戏码”。
(二)难以完成的“挪用”:边缘化与机会缺失
即便价值挪用是对情感缺失的回应,但当今机械的商业化模式使得并非所有实践主体都能参与这一过程:作为遗产地一部分的本地居民存在着“缺位”的风险,最直观表现为遗产空间士绅化(gentrification)导致遗产内部活态载体的流失。玛格斯认为遗产制造的过程伴随着特权精英和中产阶级的涌入⑩,本书中西安城墙附近原居住地居民被迫外迁的实例显示了遗产商业化背景下环境记忆与文化记忆的流失。遗产地内部居民逐渐被边缘化的同时,商业化吸引着资本的涌入,逐渐形成以遗产为中心的“文化商业圈”。哈里森提出对遗产的复合式利用“越来越忽视了遗产的情感特性”,他认为遗产“并不简单地是‘物的集合”,而是“社会性的‘工作”[20],遗产环境中“人”的日常行为构成了遗产的一部分。“遗产应该是连续性的活态空间”[21],而西安古城墙遗产地表面的商业繁荣实际上掩盖了原社区居民不断流失的现象,使得西安古城逐渐缺失了应有的与土生土长的人的交织,只剩下商业化编织的华美外衣。在大量的拆迁与重建中疏于保留与之相关的人文环境,大量仿古商业街、酒吧、商店林立,遗产地俨然已成为“伪历史氛围”下的现代商业中心。
与遗产认证的性质相同,在遗产地需要有官方承认的遗产继承人来承担遗产(主要针对非遗)继承的任务。继承人一经选出,他们就代表着官方与权威、正当与真实,但与此同时,社区的其他个体则面临失去对遗产的“合法”使用权的风险。这将意味着他们在遗产商业化中获益减少,甚至失去财路。此外,笔者还认为,未被选择的个体在一定意义上也被剥夺了遗产的继承权利,官方在赋予某些社会群体特权的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群无法参与到遗产的“利用”之中[22],他们没能获得将“生活”变成“工作”的特权,因此离开遗产地进入城市或是被迫参与虚假生产成为他们的选择,这必将导致他们的遗产继承性质发生异变。
四、总结:过去的力量——挪用、多元与持续
《中国的遗产政治:过去的力量》一书通过扎实的理论与详实的事例探讨了中国的遗产政治,分析了国家对遗产引领规划、深度利用的做法。從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遗产评定程序的不断完备,国家在确保遗产事业按照正轨运行的前提下,对其也逐渐采取宽容的态度,在对话与商讨中形成多层次的价值集合。之于批判遗产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毕竟多元声音和多种意图被承认。但多主体参与的遗产制造势必会生成新的问题:真实性与真实感的模糊;迎合大众审美与商业经济的同质化改造;冲击、同化、融合下的“变质”……对此类乱象,政府不应坐视不管、放任自流,当地个体也应加强自身的传承意识,而不是将遗产完全视为满足自身所需的一项“工具”或“商品”。
所有遗产都是制造出来的?,约翰·滕布里奇和格雷戈里·阿斯沃思(John Tunbridge and GregoryAshworth)认为“遗产制造”是多种利益冲突下由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23],本书为理解中国“遗产制造”过程中以国家为主导的多元主体间对话、冲突、协商及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深度剖析了中国遗产背后的政治意图及实践主体巧妙的“价值挪用”行为。遗产作为历史时空中精神与存在的集合,包含着可以为之“多用”的无限潜力,正如本书作者所论证的一样:它是一种来自过去的力量,同时也是于当下乃至未来促进个体与国家持续发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