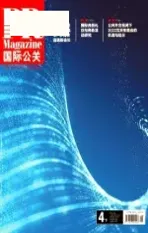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层数智治理路径
2023-05-30曾凯南

摘要:“枫桥经验”是在党的领导下缔造的一套源自基层践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策略,是坚定依靠群众的治世上策。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构建我国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效能的路上,能够主动接轨“互联网+”智慧城市科技线路,在辖区综合治理进程中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革新力。因此,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研究视域,介绍由枫桥镇到全国各地的本土版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与群众的力量,在乡村和社区土壤中探索出专群结合与群防群治相结合的新路子,实现乡村、社区善治和谐的多元格局。
关键词:新时代“枫桥经验”;“互联网+”;基层治理;专群结合;群防群治
作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基层治理方案,“枫桥经验” 历经时代淘洗与先贤践履仍历久弥新、与时俱进,持续在维护社会稳定、守护基层治安、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枫桥经验” 大致走过三个阶段:从最初的阶级斗争改造四类分子,到维护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模式,再到如今以预防化解群众纠纷为主的基层自治经验。[1]可以说,“枫桥经验” 已成为一种鲜明的由党建统领、专群结合与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和能够灵活运用现代数据科技手段以实现横纵成网、星罗棋布的网格化治理图景。
一、走向数智时代的“枫桥经验”
20世纪60年代,我国农村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于诸暨的“枫桥经验” 作为改造“四类分子” 的成功典范而被各地广泛借鉴。该经验有别于关押、打杀的“武斗” 手段,通过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说理“文斗” 实现了对“四类分子” 的摘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社教运动中,枫桥区坚持运用说理斗争的方式来化解对立矛盾,有效改造了“四类分子”,创造性地提出了矛盾就地解决,改造新人的基层经验。
顽固分子陈荫林被称为“橡皮碉堡”,在“土改” 之后思想消极落后,拒绝参加劳动,20多次的批判斗争都未能将其说服。而枫桥区西畴大队采用了“文斗” 的方式,坚持走群众路线,摆事实、讲道理,最后终于攻破了这座“橡皮碉堡”,使陈荫林交代了事实,不再顽固抵抗。[2]此后,类似的成功实践案例在枫桥区公社大队中不断涌现,就这样,“枫桥经验” 经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批示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手段的重要样板。基于此,枫桥区圹头大队治保委员会设置了“枫桥经验” 普及六标准,坚持以教育改造、说理斗争为途径来改造“四类分子”[3]。
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 由化解阶级矛盾的斗争手段转为“维护社会治安” 的社会管理途径。因社会矛盾转变与社会飞速发展,作为封闭时代产生的“枫桥经验” 被认为是已经不再适应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时经验,有些人甚至认为“枫桥经验” 是特定时期的对敌斗争经验。但实践证明,1980—1989年的10年间,枫桥全区的平均发案率和捕人率远低于浙江省当时的平均发案率和捕人率。例如,檀溪公社制定了《治安公约》,着力于农村治保会建设,在农村治保会下设置四个小组,即“一会四组”,分别是监督改造小组、帮教小组、安全检查小组和调解小组,坚持依靠群众和走群防群治的基层治理道路。在1990年“枫桥经验” 的调研报告中,枫桥区各类纠纷和治安案件中由乡、村两级调处解决的占92.4%,643人实现了就地教育改造,其中部分成为各类专业户,专注于从根源上解决犯罪问题,守护一方平安。[4]可见,“枫桥经验” 在治安防控和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依然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
两个世纪的更迭,“枫桥经验” 已成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为基层管理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和实际解决措施,强化了基层管理基础,使基层成为推广和革新“枫桥经验” 的重要载体,也使基层各项治理工作成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神经元”。
在新时代,“枫桥经验” 需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和谐治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为群众服务的职能,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 技术,动态掌握民情社情,提供社会治理“一张网” 的枫桥特色样本与“三治” 融合的源头治理范本,绘就了“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的群治画卷,[5]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提供了数字化、法治化、系统化的力量支撑。
二、“枫桥式村镇”群防群治数智治理模式
新时代,“枫桥经验”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细化自主治理、法治基层、德治维安相结合的乡村建设治理体系,创建平安乡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深化基层法治创设,提升县域德治水平,最终实现大数据时代乡村“三治” 结合的法治发展模式。
为打造“乡村善治” 治理格局,枫桥镇创建了“三有三公三和” 的基层善治样板,擘画了社会共同体多元共治的村居治理蓝图。其一,自治固本形成“三有” 局面:制定村规民约、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充分发挥乡贤组织作用、培育发展志愿者队伍、规范提升全科网格、全面推行“村干部言行负面清单”;其二,以法治为纲形成“三公” 局面:深化“一格一警一律师制度”、开展“三整治” 活动、建设村级综治中心、建立法治文化公园、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其三,德治润心形成“三和” 局面:以评立德、以教树德、以榜育德、以讲养德。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健全以诉源治理、系统治理为目标的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和、化解机制。2019年3月,“枫桥经验” 首次载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社会治理将基层视作着眼点,推广促进社会和谐的“枫桥经验”,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和、化解机制已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明文主旨。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矛盾化解在基层达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的和谐自治格局。完善社会调解员队伍,以做好社区、乡村两极“化矛为和” 事业;健全协调、诉讼、执行仲裁、行政复议、民事诉讼等部门有机连接、交叉配合的多元化矛盾处理体系;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基础功能,创新形成“互联网+网格管理” 服务管理模式,促進城乡基层治理数字化、网格化、规范化水平。[6]
法治时代下,枫桥镇为建设数字化、现代化的新型治理机制,构建了联合调解中心组织网络,健全了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智能高效整合了社会治理资源,运用数字平台优势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为此,枫桥镇综治中心设置了社会矛盾多元化解领导小组,以枫桥镇联合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联调中心”)作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体,内设综合信息指挥室,负责与全科网格员直接联动对接;联调中心下设志愿者调解、专业行业性调解、枫桥司法所(人民调解室)、律师调解(俞岚工作室)、品牌调解(老杨调解室)、枫桥检察室(刑事和解室)、枫桥法庭(诉前调解室),加大完善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乡镇(街道)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决机制。
2008年,枫桥派出所成立“老杨调解工作室”,后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三位一体的矛盾化解中心,利用治理数据进行矛盾排查与风险研判,构建表达诉求、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民情通道。社会自治须以源头治理为核心,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与调和化解整合机制,实现诉源治理。
枫源村作为“枫桥经验” 的发源地之一,在探索村级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新模式进程中最先提出了网格化管理模式,运用“三上三下” 的枫源模式民主治村,于每月12号定期举行村民述事活动,由村委组织,两委干部、网格员、村民共同参与,形成了“定期办事、规范办事、开放议事、民主议事” 的办事风格。枫源村设有便民设备,方便为村民提供法律、交通、警务安全等服务。枫源村依托信息化手段,与镇综合信息指挥室联动,四个平台实时办理,视联网实时会商,雪亮工程实时监控,实现了村镇两级的治理联动。[7]
群防群治的基础是群众自治,规范化、科学化、责任化的群众自治组织自建立之始就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充分发挥群众力量,运用广泛的群众基础构建“群众自治+智能数据” 一体化平台,在数字法治背景下具有社会自治的基层治理内在逻辑。
杭州“武林大妈” 依托“线上数字治理”“基层治理四平台” 和街道研发的“E治武林” 小程序、“武林大妈民情码”,完善提升了警网协同“小脑” 功能,[8]成为都市版的“枫桥经验”,其与城市大脑相协同,最终实现了“矛盾不出楼道、问题不出街道” 的社区群众自治模式,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枫桥经验” 基本内涵;嵊州市通过架构市、镇、村三级“村嫂”,实现了“村嫂” 志愿服务全覆盖,开展“村嫂” 警务助理试点,深化越乡警务管家治理;开展“村嫂引领” 志愿服务文明行动,构建起“村嫂志愿服务+文艺、平安、文明、和谐、发展” 联动治理模式,实现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建嵊州版“枫桥经验” 的实践方案。新昌县儒岙镇成立了以“天姥义工” 为参与主体的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通过与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绘成和谐共治的基层蓝图。
作为基层治理的方向盘和主心骨,“枫桥经验” 在社会综合治理的神经末梢—村镇之中发挥着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作用。不同时代赋予了“枫桥经验” 不同的内涵,但本质仍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鲜明工作定位,无论是“枫桥经验” 产生之初的调和阶级矛盾,改革开放后的维护社会治安,还是新时代的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 始终蕴含着法治、德治、善治思维,以扬弃之哲学思维不断赋予时代新的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 的核心要义,运用数据科技是“枫桥经验” 的时代特征。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示范答卷和担当改革治理使命的“枫桥经验”,因国家治理目标的要求而不断变化演进,在中国乡村和社区基层“以和为贵” 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枫桥经验” 始于枫桥镇,传播于全国,最终走向了国际,极具创造性和生命力,在不同地域能够根据地方民情转换为地方性基层治理经验,不会出现“南橘北枳” 的现象。立足于社情、民情、国情,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枫桥经验”,深刻蕴含着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哲理与华夏“和” 文化的血脉刻度。
三、“枫桥式派出所”专群结合的数智治理模式
新时代,“枫桥经验” 一以贯之的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基层治理的村社图景下,公安机关为实现“探本溯源找矛盾、系统综合解纠纷、依法治理讲民心” 的综合治理目标,创新发展出了“枫桥警务模式”,加强和改进了基层工作并创建了“枫桥式优秀公安派出所”。“枫桥式派出所” 以党建为统领,以公安机关为专门机关,密切联系群众、在工作中逐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提升基層治理水平。[9]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诸暨市架构“基层治理四平台”,以“放管服”“最多跑一次” 等便民措施深耕基层,综治工作平台、市场监督平台、综合执法平台及便民服务平台作为乡镇(街道)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中枢神经” 涵盖了村镇县市全域,治理范围由大及小、由内及外、由近及远;治理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乡村建设等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
四、总结
始于“一村之计” 的“枫桥经验” 逐渐发展为“一镇之谋”“一省之策”,后又上升为“一国之治”。换言之,“枫桥经验” 源于乡野,却能以磅礴的生命力走向全国、远扬国际,在中国不同的乡土地域内生根发芽,创造出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地方治理样板,探索出以群防群治为路径的“枫桥式乡镇”。在数字法治政府的时代图景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作为“发展硬件” 助推基层构建出了“枫桥式派出所”,生动演绎出了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亘古不变的民情定律,深刻诠释了党领导群众、依靠群众、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情怀。
参考文献:
[1] 马荣春,周建达.“枫桥经验”:预防犯罪观的重要启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0(1):60-70.
[2] 浙江省公安志编纂委员会.浙江人民公安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徐忠友.“枫桥经验”诞生前后[J].党史纵览,2020,(2):
19-22.
[4] 余钊飞,罗雪贵.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历史演进[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3):47-54.
[5] 高铭暄,傅跃建.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实现进路[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 37(4):1-10.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7-12(001).
[7] 《枫源村志》编纂委员会.诸暨市乡村志:枫源村志[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
[8] 李洁.杭州拱墅全域推进片区治理新模式[N].浙江法制报, 2002-09-02(002).
[9]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N].2019-05-25(003).
作者简介: 曾凯南,女,汉族,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