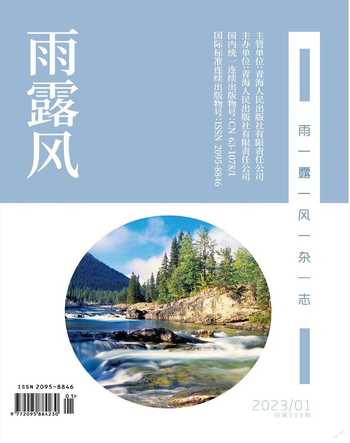论肖江虹小说中的悲剧色彩
2023-05-30何雪
2018年,肖江虹凭借其民俗“三部曲”中的《傩面》斩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在民俗“三部曲”中,作者描写了蛊镇、傩村、燕子峡的传统习俗文化,表达了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没落的惋惜之感。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55,在肖江虹笔下,赵锦绣和颜素容的悲剧性、城市化影响下传统技艺的失传、农民挣扎求生的艰苦状态,都展现出面对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们的坚守与抗争。悲剧不会让读者产生愉悦的心境,也不会带来舒适的阅读感受,但能从中找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了解作者对底层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展示出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一、女性悲剧
女性人物描写在肖江虹作品中所占比例较少,大多是以男性人物形象为主要描写和叙述对象。但在《蛊镇》和《傩面》中,女性叙述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不管是嫁为人妇,面对丈夫外出务工的留守妇女赵锦绣,还是决心在城市打拼立足但被迫回到家乡的颜素容,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悲剧性色彩。
(一)留守妇女赵锦绣
赵锦绣,一个勤劳能干的留守妇女,主动承担起家里的责任与重担。她不仅要照顾公婆和儿子,家里的农活也全落在她肩上。在赵锦绣观念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作为家庭妇女,赵锦绣辛勤劳动,为家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劳力。正如戴锦华与孟悦所谈道,“家庭几乎是专为女性而设的特殊强制系统,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制意味”[2]6,女性在家庭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忽视与压抑。在肖江虹小说中,我们仍能看到囿于家庭而无法展示自己真正女性价值的赵锦绣。
面对丈夫的背叛,赵锦绣选择的是忍让,甚至想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处理。当赵锦绣质问丈夫时,她内心极度渴望王四维站出来与自己辩解,甚至希望丈夫欺骗自己。种种行为都显示出赵锦绣将全部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寄予在丈夫身上,作为女性的主体性在赵锦绣身上完全消失。
赵锦绣在维持摇摇欲坠的家庭中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女性意识,把自己置身于从属地位。她对自己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妻子、母亲、媳妇的身份上,唯独忘记了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把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作为生命全部,这是赵锦绣无意识状态下接受和形成的观念。
(二)“归去来”的颜素容
率先离开故乡踏上城市道路的颜素容,她最大的梦想是扎根大城市。在她的眼里,故乡的一切都无法与城镇相比,她轻视傩村的一切。在颜素容为扎根城市而打拼奋斗时,却因患病而不得不离开都市。颜素容认为只要自己努力打拼,终会得到这个城市的接纳,可命运不但不给她努力奋斗的机会,还要夺走她的生命。无奈之下的颜素容回到曾经逃离的傩村,回到自己最看不起的乡村,看到秦安顺制作傩面,还不忘嘲讽几句“都哪朝哪月了,还鼓捣这破烂货”[3]260。颜素容在意识深处始终倾向城市,颜素容总认为“城市的月亮要比傩村的圆”,她是一心奔向城市却被拒之门外的脆弱女性。回乡与秦安顺相处期间,她慢慢沉下心来重新认识自己生长的故乡,深入接触傩村的传统文化。看到家乡美丽自然风光,也感受到濃浓的乡里乡情,更为秦安顺身上的生死观所震撼。是秦安顺让颜素容放下对傩村的芥蒂,重新找回属于她的心灵栖息地,可秦安顺的离去却让她再次陷入迷茫与绝望。命运就像一双无形的手置于颜素容的头顶上空,看到她找到一点希望就随之将其毁灭。
颜素容处于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想要奔向城市而被抛弃,想要回到乡村而无归属感,甚至发现自己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正如小说开头描述一样,颜素容高跟鞋踏在归乡石板上发出压抑闷响,身上的红裙好似傩村一朵妖艳的蘑菇,她与故乡的静谧与美好景色是违和的,她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故乡,而是处于“城乡中间层”的尴尬位置。对她来说,远方是无尽的,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二、城乡变迁带来的悲剧
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传统乡村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肖江虹描写出贵州独特的传统文化遗产与它面临消亡的处境。在《蛊镇》中,有对最后一代制蛊师王昌林制蛊与寻找下一代制蛊师的描写,《傩面》中讲述了最后一代傩面师坚守与傩戏的凋零。
(一)传统文化没落
在民俗“三部曲”中,作者着力描写了随着城乡变迁人们不断涌向城市,致使继承传统民俗文化的人极少,甚至后继无人的现实境况。作为蛊镇制蛊最后一代传人,王昌林还在坚守与传承,可是却找不到传承技艺的下一代蛊师。他最后的心愿是制成一道蛇蛊,关于蛇蛊的传说,都认为这道蛊能“颠倒时序和返老还童”。面对年轻一代的离去无能为力,唯有制成这道蛊,在年龄上重返青年,继续守护乡村和传承祖辈留下的技艺,这是年老一代技艺人的愿望。蛊镇老人告诫人们“不要轻易越过豁口,一线天的那头有吃人的妖怪,红头绿面,口若血盆”[3]178,这是老人想要守住自己村庄的善意谎言,可是人们还是没有抵住外面世界的诱惑,离开了蛊镇,甚至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面对青年一代的相继外出,蛊镇陷入一片死气沉沉的状态,传统文化沦落到无人继承而失传的悲凉境遇。
秦安顺作为傩村的最后一位傩面师,一直坚守自己作为傩面师的职责。对于他来说,傩面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精神的归属。对于独自一人生活的秦安顺来说,面具下母亲与父亲的生活琐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安慰与补偿,甚至坚信这一张老旧的面具能接通另一个世界,傩面带给他的不仅是一种责任与守护,更是一种心灵的皈依。他总是跟自己说“唱哪样唱哟!没人听得见,狗日的秦安顺唱给狗日的秦安顺听”[3]304,这些都是秦安顺心里的无奈与悲痛。在无声无息中走向生命的末端,这是他作为最后一代傩面师的无声告别,也预示着傩戏这种民间传统就此凋零。作品中对老一辈的坚守与担当给予了巨大的赞赏,但对他们独自的坚守与离世展示出深深的哀婉之情。
(二)生态环境破坏
“面对现代社会,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现状,‘民俗三部曲中,人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环境的和谐共生,渗透着原始的生态美,也表现出作品的生态思维。”[4]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对生态意识做出回应,《悬棺》中能明显看出作者的生态意识观念。
在燕子峡,鹰燕是保证人们粮食丰收和不受饥饿的保障,燕子峡人民与之和谐相处,从未做出任何伤害鹰燕的行为,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型。但是,来向南偷采燕窝贩卖这一举动给燕子峡和曲家寨两族带来巨大变动。采集燕窝使燕子峡的鹰燕逐渐离去,“那些黑点慢慢变淡了,天边终于失去了鹰燕的影子,只剩下枯瘦冷漠的岩壁”[3]220,燕子峡人因此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又过上了挨饿、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来向南把偷采来的燕窝卖到镇上,正是知道人们的“需求”,才会动这一恻隐之心。从来向南破坏燕窝这一举动来看,这是断绝了燕子峡的生存之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这是破坏生态平衡,打破了生物链循环的错误之举。县上派人对燕子峡人的搬迁进行动员与劝导,并打算在燕子峡修建电站。对于县级工作人员来说,修造电站是人类的一项壮举,因为这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一大奇迹。但殊不知,这一举措是人类的愚蠢行为,在寻根作家返回自然与返回传统的两大主题中,强调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而非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生态意识背景下,作家立足贵州具体情况,在《悬棺》这一作品中流露出明显的生态意识,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底层农民挣扎的悲剧
燕子峡人有着坚韧的意志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面对常年饥饿威胁,他们坚强努力地活着。在这里,庄稼收成全看天意,如果燕粪充足,雨水足够,今年的粮食就足够生活,不用忍受饥饿的折磨。可这样的生活稳定性太弱,没有保障。为了求活,要面对流传久远的攀岩精神文化被游客亵渎,在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坚守方面,只能选择其一。
(一)物质生活的艰难
燕子峡所处地势极其特殊,这里没有厚实肥沃的土壤,经过暴雨的冲刷留下的只有成片的悬崖与石头。面对贫瘠的土壤,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免遭受饥饿,这是不可摆脱的自然悲惨命运。
燕子峡人所取的名字也具有一定象征意义,来辛苦、来畏难、来高粱、来稻谷这些名字,寄予了农民对粮食的深切渴望,也铭刻了他们艰难的生活处境。名字背后暗含着人们饱受饥饿的折磨,害怕缺乏粮食,寄予对食物充足的美好愿望。燕子峡祖先遭受灾难被困在山洞时,年老孱弱的一辈主動放弃生的希望,以保护青壮年、女人。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自己的存活只会抢夺后代子孙的生存空间,他们的选择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十分伟大的,但抉择背后的原因只有无尽的心酸与无奈。这种自我牺牲行为与鹰燕殉崖是何等相似,其背后隐藏着的是现实生活压力的无奈之举。在来畏难的记忆中,摘野菜是常有的事,粮食缺乏只能靠野菜充饥,好不容易遇上茂盛的野菜也会感到无比欣喜。“鹅儿肠、车前草、蛤蟆菜、黄芽尖,这些饭桌上的常客”[3]237,足以窥见他们艰苦的生活,可以看到粮食缺乏带来的饥饿问题一直困扰着燕子峡人,这是底层农民无法摆脱的艰难生活境况,所谓的摘野菜却叫“向土地讨口吃的”,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和不挨饿。肖江虹小说立足于底层人民生活,强调从多角度展现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正如相关评论者谈到“他关注底层、悲悯底层,不是与创作潮流、社会现实断裂和对抗,而是顺时随俗,在感同身受中书写社会的剧变。”[6],从而进行作者的人性思考。
(二)精神信仰的放弃
燕子峡人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留在燕子峡,保护祖先的悬棺,继续生活在这片饱含深情与信念的土地上;要么离开燕子峡,寻找一片易于生存的栖息地。但现实是,鹰燕离开了燕子峡的土地,也许明天回来,也许再也不回来了,没有了栽种庄稼的肥料,全村再一次陷入缺粮的处境中。最后迫于生活的压力,燕子峡与曲家寨两族人还是妥协了,在痛苦与挣扎中放弃了自己的故乡。在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方面,他们不能两全,只能舍掉其中之一。
燕子峡的岩壁上留下的是祖辈与命运和现实抗争的痕迹,这是属于燕子峡独有的精神印记,寄予着燕子峡人的信仰与归属感。但最终来辛苦向现实妥协了,主动劝告两寨人搬迁,这是在物质压力下放弃了精神的守护,看到大水淹没村寨,水中漂浮着的棺木,燕子峡人心中极其痛苦。来高粱选择留下,不愿离去,他带着自制的木翅膀从崖上降落,与燕子峡祖先一同沉入河中,用自己的生命来坚守和维护祖先遗留的信念。
在肖江虹的“民俗三部曲”中,物质与精神同样重要,但在经济与物质的影响下,人们还是被迫放弃了属于整个族群的信仰,如《蛊镇》中青壮年不愿学习和继承历史悠久的制蛊技艺,而是奔向城市寻求生活来源;《傩面》中梁兴富只顾将傩面具推向市场,而忘记了傩面中丰富的深刻意义。不管是来辛苦选的择离去,还是来高粱选择的坚守,都无法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四、结语
王杰提出“悲剧冲突是悲剧艺术的核心情节,也是悲剧美构成的核心要素”[5]203,在肖江虹的民俗“三部曲”中,正因为城乡间的对抗与冲突,才出现蛊镇、傩村、燕子峡三个地方的人们与现实抗争、搏斗的一系列故事,但最终都无法逃脱毁灭与消亡的悲剧性结局。作者并没有直接展现悲剧性场景,而是探讨在城乡变迁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变化给乡村,尤其是乡村人民带来的变化。肖江虹在作品中将视点聚焦于乡村人民,展示他们在城乡冲突中不屈服于现实,奋力反抗与搏击的斗争精神,是对底层人民处境的关怀与思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处于城乡冲突中的农村人究竟该走向何处,作品中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作者对当下现实问题的涉及与叩问,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民俗“三部曲”中的悲剧色彩,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也是他将悲剧性色彩从个人人生意义的感受转化到社会性的价值意义,这是肖江虹作品的一大贡献。
作者简介:何雪(1997—),女,贵州黔西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注释:
〔1〕来风仪.鲁迅杂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肖江虹.悬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4〕杨芸.生态批评视域下肖江虹“民俗三部曲”研究[J].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8(03):3-6.
〔5〕王杰.美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6〕陈国和.肖江虹:擦亮人性之光的贵州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4):25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