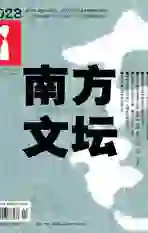新时期阎纲文学评论探析
2023-05-30梁向阳夏华阳
梁向阳 夏华阳
年逾九秩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从事文艺活动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他直到现在仍然笔耕不辍,还出版《我还活着》散文集①。新时期是阎纲“评论人生”的高光时期,他一直身处文学现场,发表了许多重要的作品评论,坚定地为新时期文学发声与护航。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呼吁加强文学评论力量,编辑出版评论丛书,促成《评论选刊》诞生,为新时期文学评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出“在场者”的评论声音
从1949年至今,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七十多个年头。作为文坛的“常青树”与“在场者”,著名评论家阎纲先生一直与当代文学同行。“在场”是西方形而上学体系内部“存在论”问题的一种概念表述,是指“存在呈现于此时此刻(当下时刻和当下场所)”②,强调的是空间与时间上的当下性。阎纲退休之前长期在《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中国文化报》等文艺报刊从事编辑工作与评论工作,因为身份的特殊性,他见证了当代文学的许多重大事件,参与了许多重要作品的争鸣与讨论,对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历史进程都有着直接的感受与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的重要“在场者”。
1950年,年轻的阎纲在家乡陕西礼泉县开始了文艺宣传工作,并在1951年出席陕西省首届文艺创作者代表会议并领取奖项。1952年,阎纲作为“调干生”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系统学习文学专业的理论知识,为以后的评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阎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协,进入《文艺报》从事编辑与评论工作。1961年底,阎纲与王朝闻、李希凡、侯金镜等评论家在《文艺报》上对《红岩》进行过系统评介,他还在1963年出版过《悲壮的〈红岩〉》一书。应该说,“十七年文学”期间,是阎纲“评论人生”的起步时期。正是因为长期“在场”,阎纲才能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1975年,阎纲结束了干校生活重返文坛,参与《人民文学》复刊工作,并担任编辑。“文革”结束后,文坛乍暖还寒,思想解放还未全面展开,《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班主任》发表后,招致诸多反对、批评之声。阎纲在《班主任》遭受非议的时候,站出来撰写了《谨防灵魂被锈损——为新作〈班主任〉叫好》,进行评介与支持,称《班主任》正是“提醒人们严肃注意孩子的彻底解放的问题,能不激起家庭、全社会、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滚滚思潮吗?”阎纲坚定地为“正视现实生活,勇于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落俗套的《班主任》拍手叫好”③。《班主任》作为“伤痕文学”的开篇之作,其引发的反响与思潮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与阎纲等评论家们的支持与阐释也有直接的关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到来。新时期是思想解放、人性复归的文学时代,文学迎来了勃勃向上的黄金时代。随着《文艺报》的复刊,阎纲重返《文艺报》担任编辑工作。阎纲许多重要的文学评论文章,均写于这一时期,如《不妨解剖一个——论“写真实”》《“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小说出现新写法——王蒙近作》《〈灵与肉〉和张贤亮》《为电影〈人到中年〉辩——对〈一部有严重缺陷的影片〉的反批评》等。这些文章对应着当时的作品争鸣,这不仅说明阎纲是“在场的”,也说明阎纲作为“在场”的评论家参与、触发乃至引领了当时的文学思潮。
1979年由《人妖之间》作为导火索引发的“写真实”的争论,正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文学思潮争论的焦点。伴随着思想解放,1950年代、1960年代关于“写真实”的讨论又开始重新被关注与评估。“‘写真实’无疑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界最热门的话题。”“多数文章肯定了这一口号的正确性,否定了过去对这一口号的批判,指出这是现实主义的核心。”④阎纲在文章《不妨解剖一个——论“写真实”》中讨论什么是“写真实”,讨论“真实”的标准,指出:“真实不真实,实践出真知”,进一步提出:“认识表现为曲折的实践过程,文藝创作亦复如此。”号召文艺界,“把有尖锐争议的作品提出来大家公开讨论”⑤。这些观点为当时“写真实”的讨论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意见,也可以看出阎纲敏锐的洞察力与对文艺思潮的精准把握力。
阎纲正是秉持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理念开展文学评论,发掘优秀作品,为有争议的作品发声。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阎纲发现并极力推荐的作品。这部短篇小说在发表之初,也没有逃过和《班主任》一样被批判的命运。阎纲第一时间站出来,撰写了《“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其鸣不平。称赞小说中的“李铜钟”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同普罗米修斯一样都是“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称这部作品“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它的价值在于“作者具体写时,怎样把‘真实’和‘崇高’艺术地结合起来”⑥。阎纲在评论张贤亮当时颇有争议的作品《灵与肉》时称:“他念兹在兹的,是恩格斯的话:‘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比之一般的‘伤痕文学’来,他更忧愤深广。”“张贤亮所操的现实主义,无疑是深化了的。”⑦同样,在为电影《人到中年》作出辩护性时,阎纲评论《人到中年》:“为歌颂而暴露”,并由此指出:“直面人生,正视社会矛盾,实在是发展文艺创作的必由之路。”⑧他关注王蒙具有意识流色彩的新作《夜的眼》《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蝴蝶》,准确地概括出王蒙新作是一种方法上的借鉴,认为王蒙新作是“现实主义的新品种,并没有告别现实主义的几个真实性的要求”⑨。举此重要几例,可以看出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在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立场下,阎纲既有作为一个评论家所具备的敏锐目光,又有敢于发声、敢于引领文学潮流的胆识。
阎纲文学评论的语言也非常有特色。对于具体作品的评价,阎纲总能通过犀利、简洁且富有诗一样澎湃的语言,对作品进行敏锐、生动、精确的评论判断。他评论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时,这样辩护:“嗟呼!已诺必诚,不忧其躯。壮哉!真正共产党人的侠风义气!”⑩同样对于高晓声系列小说中的人物“陈奂生”,阎纲评论道:“陈奂生终日劳碌,半生清苦;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时来运转,受宠若惊;眼花缭乱,呆头木雕;好心办事,事与愿违。世道大变,人情难测,一身清白的农民,掉进‘关系学’的五里云雾。”11这都展现出阎纲文学评论生动、鲜活的语言特色。刘再复在评价阎纲的评论风格时说:“在历史转变时期,文学更需要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更需批评的生气、活力和战斗力。”“新时期文学是在清除极左的血污中开拓自己的道路的,它首先要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它需要不带学院气的犀利的‘时文’。”12白烨对阎纲的评价亦如此:“他引人注目的是:仗义执言,不避锋芒,义愤中深含识见;实话实说,不落俗套,平朴中自有文采。他把真情与诗意揉成一体,带来了一股清新引人的文评新风。”13就连阎纲自己总结对文学评论的要求时也认为:“唯八股之务去,行文体之改革,引诗意和真情入文,推倒呆滞生硬的评论之墙。”14这都是其文学评论富有活力与诗意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之初,倘若没有阎纲这些激情且富有战斗性的文学评论的挖掘与阐释,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可能会被埋没。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在场者”,阎纲不仅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关注与评介,还特别善于总结新时期之初文学的鲜活特征,梳理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经验与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中篇小说的兴起》《长篇小说印象》《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给一位短篇小说作者的复信》《姹紫嫣红又一年——一九八〇年的中篇小说》《文学八年》《文学十年》等重磅文章中。在文章《长篇小说印象》中,阎纲看到进入新时期长篇小说落后的现状,指出要总结经验教训,长篇小说缺少的是塑造“艺术典型的社会新人形象”,并且“要创造人物典型,首先要把人当成人”15。这为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阎纲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作《文学八年》的发言,用发展的、整体的文学观将1976—1984年以来的文学演变概括为从“解放文学”向“改革文学”的过渡,根据新时期八年以来文学发展的经验,提出:“文学地写,艺术地写,写出真实的现实,不论用什么手法。”16其后,在1986年“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文学十年》中,阎纲也是立足全局,用发展的眼光观察文坛,把1976—1986年以来的文学概括为“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文学观念的恢复与扩大”“创作方法的革新”三方面“横竖三条线,相互交错”的文学图景,指出新时期文学:“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的深化是从“回归到现实主义特性,增强人民性”到“人道主义的涌起”再到“人道主义的延续”下“自觉的现代文明意识”17。这种人道主义便是尊重主体性,尊重主体的创造性,是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因为“文学主体性话语突出体现了启蒙主义关于普遍主体与自由解放的信念与理想,‘主体性’‘人的自由与解放’‘人道主义’几乎是当时的相关文章中出现最多的术语,且这三者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主体性表现为人的自由创造性,而人道主义则是对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肯定)”18。这个声音契合了1980年代中后期所倡导的“主体性”“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
总之,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在场者”,阎纲积极介入当代文学现场,敢于为有争议的作品发声,为新生的文学现象保驾护航、开辟道路,展现了作为“在场”的评论家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二、重视评论队伍建设
作为评论家的阎纲,十分关注新时期文学评论地位与发展,重视新时期评论队伍建设。1980年12月,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阎纲作《文学四年》的报告。在此报告中,阎纲深感文学评论地位低下的境况,为文学评论现状鸣不平:“一般文学评论者地位不高,文学编辑地位更低,我自己既是编辑又搞评论,算是‘引车卖浆者流’吧!正由于此,我讲话顾虑不多,有勇气为小说评论和小说编辑鸣不平。”“我们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不能自馁……我们只有深入研究小说创作的现状,才能有力地推动小说创作的发展。”19
之后,在1984年12月29日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阎纲更是进一步呼吁要有“创作自由”与“评论自由”。他提出:“要改变评论落后的状态,必须实行改革,必须有评论自由的保证。”“要产生科学的、说理的评论,要产生充满自信、激情、壮志和豪情的评论,要产生富有个性的评论,要产生大评论家和评论大才,其思维必须进入自由状态,必须有百家争鸣和政治民主的保证。”20阎纲强烈呼吁提高文学评论地位,呼吁进入新时期要有科学、说理、自信、激情、个性的评论。阎纲在评论界早早提出“个性的评论”,他虽未形成专门关于评论“个性”的系统论述,但已喊出评论要有“个性”与“自由”的呼声,这非常具有先见之明。事实上,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絕不是背向发展;文学创作要繁荣与发展,文学评论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正如刘再复所言:“构成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应当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一群冲锋陷阵的评论家,就是伟大的文学新潮的一部分。在这一评论家群中,阎纲是杰出的,他的呐喊并不白费,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呐喊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文化动力之一。”21正是由于阎纲等一批评论家们的努力,新时期文学评论事业才会披荆斩棘,迈向新的征程。
在关注文学评论地位与发展境况的同时,阎纲还合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为老一代评论家们出版评论选集。与此同时,他还促成新时期全国第一家文学评论选刊《评论选刊》的诞生,助力青年评论家的成长。
1982年,阎纲与冯牧、刘锡诚合作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出版了陈荒煤、胡采、冯牧、洁泯、朱寨、王春元、李元洛、谢冕、陈辽、张炯、缪俊杰、王愚等十多位老评论家自选集。在这套丛书的序言中,阎纲提到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当代文学评论的经验,扩大当代文学评论的队伍,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促进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并谈道:“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相互借重。”22这套丛书之所以选取很多有分量的老一辈评论家的选集出版,就是为新时期文学评论发展铺路。这套丛书出版以后,受到文学界的广泛赞誉。
除此之外,1984年阎纲促成了《评论选刊》的诞生,并担任这本刊物的主编。在《评论选刊》创刊之时,阎纲便在发刊词中称:“近年来评论家们,特别是中青年评论家,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阔,专题的开掘越来越深入。他们从创作论、作家论、文学史和批评史的撰写,到国内外评论信息的交流、文学评论方法的革新,都显示出实绩和潜力。文学评论的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23《评论选刊》成为广大文学评论家们争鸣的平台,也成了新的评论力量一展才能的舞台。当下许多著名的评论家,如李敬泽、王晓明、白烨、张志忠、南帆、黄子平等,当年都是《评论选刊》遴选出的坚锐力量。《评论选刊》对中青年评论家的扶持,使得新时期文学评论队伍不断壮大。在创立《评论选刊》时,阎纲还考虑了一个刺激文学评论事业发展的方法,这便是设立评论奖项。尽管在新时期的1980年代已经有了表彰文学创作的“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全国性文学大奖,但为文学评论家颁奖却很少见。阎纲在《评论选刊》的发刊词中提议:“《评论选刊》呼吁为当代文学评论举办全国性的评奖,或对其优秀论文、著作和优秀评论家颁发国家奖。”“《评论选刊》愿为这一评奖的实现尽其绵薄。”24虽然这一愿望当时没有得以实现,但在《评论选刊》的呼吁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率先设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激励着广大评论家的热情,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评论事业的良性发展。
1985年秋,阎纲借调河北省文联,在《评论选刊》与《文论报》上组织和转载了几场争论(论争),其中便有引发激烈讨论的刘再复的“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这些争论(论争)活动,无疑激发了文坛的批评活力。
由此可见,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在场者”,阎纲用充满激情的工作方式,为文学评论家队伍的壮大、为文学评论事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塑形”新时期陕西文学
作为从陕西走出去的“陕籍”文学评论家,阎纲与当代陕西文学的关系可谓渊源深厚。早在1960年代开始,阎纲便与柳青有所接触,几次探望柳青。从1960年夏天第三次文代会上阎纲与柳青的直接接触,到1978年最后一次在北京病房探望柳青,阎纲与柳青在一次次交往中逐渐熟知。1981年,阎纲出版《〈创业史〉与小说艺术》的研究专著,就是对这位故去的陕西文学精神导师的致敬。
进入新时期,阎纲在关注全国文坛的同时,对陕西文学特别关注。尤其是1983年,阎纲应《宝鸡文学》之约,因有感于陕西新时期文学处于闭塞与落后的状态,撰写了《走出潼关去》一文。阎纲在文中指出:“尽管潼关的无形的城墙那么厚,城门关得那么紧。太厚,太紧,污浊的空气进不来,新鲜的空气也进不来。我们的文学天地太小,我们的艺术眼界不宽。”阎纲是陕西老乡,自然“不加掩饰地流露对自己乡土艺术的偏爱”,但他也指出陕西文学短板在于“诚实无欺但伤于太实,出于泥土却失之太土”。在艺术选择上,阎纲希望陕西作家“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下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25。阎纲号召陕西作家学习已故著名作家柳青先生敢于吃苦、献身艺术、耐得住寂寞的精神。这一文章喊出了陕西作家要“走出潼关、走出陕西”的口号,指出了当时陕西文学创作的短板,极大地激励了陕西文学的发展。这篇文章爱心切切,直到现在仍振聋发聩。
曾任鲁迅文学常务副院长的著名作家白描回忆,在阎纲喊出“走出潼关去”的口号后,陕西作家们开始以行动反思自己,正视创作。这一口号喊出后最具有标志性的一次活动,便是1985年秋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促进会”。这一活动促成了“路遥投身《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贾平凹开始写作《浮躁》,京夫动笔《八里情仇》,程海酝酿《热爱命运》,邹志安写作《多情最数男人》”,而白描也开始了《苍凉青春》的写作。陈忠实在1985年冬天“在写作《蓝袍先生》过程中,突然勾起对白鹿原早年生活的记忆,写作《白鹿原》的念头瞬间而起”26。可以这样说,正是阎纲喊出“走出潼关去”的一声秦腔,点醒了陕西作家,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从此,陕军开始东征,“文学陕军”的品牌叫响全国。
阎纲与新时期以来多位陕西重要作家交往从密,不遗余力地关注、鼓励他们的创作。阎纲对路遥的关注主要在1980年代,且主要集中在关于《人生》的探讨方面。《人生》发表之前的1981年10月,阎纲受《文艺报》之命回到西安,与陕西作家进行了一场“农村题材创作”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路遥提出农村与城镇“交叉地带”的概念。《人生》发表后的1982年8月17日,阎纲给路遥写信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称路遥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阎纲论及高加林的形象时称:“既象(像)保尔·柯察金,又象(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他断定《人生》是“一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青年人探讨‘人生’道路的作品”27。阎纲对《人生》的判断概括是准确而深刻的,这些话语后来均成为解读《人生》的重要观点。
阎纲与陈忠实的交往始于1976年。因《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事件,《人民文学》杂志需要重新组稿,作为编辑的阎纲前往西安,曾向陈忠实约稿。但阎纲对于陈忠实创作的实际关注,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1993年《白鹿原》出版后,阎纲在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长篇小说新作讨论会上,称《白鹿原》“是个里程碑!”28随后阎纲将发言撰写成《〈白鹿原〉的征服》,称这部作品:“它既是心灵史,又是社会史。”“《白鹿原》的诗魂在精神,在发掘,发现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生命的精神、赖以存在的精神,使得本民族其所以不被击倒、被消灭,而延续数千年直到今天的‘民族精神’。”这种在《白鹿原》中体现的民族精神,被阎纲概括为“生存、处世、治家、律己和自强不息”29。阎纲对于《白鹿原》的相关论述,是准确而具有深度的,对《白鹿原》精神内核的论断,仍启迪着广大读者与评论者。事实上,《白鹿原》魔幻兼具历史与现实的创作方式,也正应验了阎纲当年要陕西作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创作忠告。
阎纲对贾平凹较早的关注,是在贾平凹《满月儿》发表之时。贾平凹《满月儿》发表后,“阎纲撰文称贾平凹是真‘作家’‘关中才子’”,“平凹语言了得,诗意的白话入耳入脑”,“他的想象力上天入地,他的思想奇特,是禅,你猜不准的”30。之后,阎纲在1980年撰写的《贾平凹和他的短篇小说》一文中称贾平凹的可贵之处在于:“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尽管他仍在孜孜不倦地继承和借鉴。”阎纲鼓励年轻的贾平凹:“希望他更上一层楼,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进军。”311984年7月中旬,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贾平凹作品讨论会上,“阎纲则一口断定贾平凹是‘关中才子’,他惊叹他文学作品的独特和丰富,他祝愿这位才子型作家更攀高峰,说他的作品今后应该朝‘博大’方面推进,应该建树起‘大家’的风度”32。
阎纲对贾平凹的真切关注,给其后来的创作有莫大的帮助。即使在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引起极大争议的时候,阎纲还是力挺贾平凹,称《废都》为才子书:“废都,才子书,对荒诞世相的再现见怪不怪,对丑恶灵魂的曝光煞是无情,给异化为宿命论的文人骚客画像造型,给新时期新犬儒主义者唱挽歌,敢于耻笑如此类群不過一个大‘废’。”阎纲从文学史角度敏锐地注意到:“《废都》的出现是文学坚守社会化同时趋于平民化、私密化的一个转折,是文学多元竞放的又一标志。”阎纲在肯定与鼓励的同时,也客观地评价《废都》“愤世嫉俗,婉曲多致,但堕‘恶趣’,性描写空前露骨,妇女读者多有折辱之感”33。阎纲对《废都》的评论一语中的,切中要害。阎纲对贾平凹这位“大作家小弟弟”的关注与诚恳批评,激励着贾平凹的创作不断进步,使得他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终成大家。
新时期以来,阎纲还把目光投注在陕西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如评论刘成章的散文时称:“它是无韵之信天游。”“它是散文诗,是黄土诗魂的风味散文。”34评论作家程海的小说《热爱命运》时称:“意识的流动愈加自由,象征意味益渐强化,甚至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却一步也离不开生活具象的尽管貌似随意的素描。”35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阎纲对新时期陕西作家与作品关注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倾注的特别情感。当然,阎纲还对李星、莫伸、和谷、邹志安、王蓬、高建群、王海等人的评论与创作,都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阎纲对于新时期陕西文学所起的作用,真可谓功莫大焉。贾平凹言:“他爱文学,更爱文学人才;爱家乡,爱家乡的面食,爱家乡的秦腔,可以说,阎老师对我的创作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对我的成长影响非常大,也是终生的良师益友。”36也诚如白描所言:“如果说柳青是文学陕军的精神导师,阎纲则可以看做是文学陕军的塑形师。”37贾平凹与白描的声音,也可以视为陕西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的共同心声。
结语
文学评论工作,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力量。对于新时代评论工作而言,阎纲的“评论人生”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它启示我们的文学评论者,要俯下身子,成为新时代文学的“在场者”,既要敢于呼应时代,为书写时代气象的优秀文学作品发声与护航,又要善于引导文学风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出文学评论的力量。
【注释】
①阎纲:《我还活着》,太白文艺出版社,2022。
②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第541页。
③⑤222324252731阎纲:《阎纲短评集》,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第32、67-68、253、376-377、376、283-287、244-247、73-74页。
④吴义勤:《“写真实”与“真实性”》,《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
⑥⑦⑩阎纲:《小说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37-244、347、240页。
⑧1114151620阎纲:《文学八年》,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第322、280、556、135-136、530-543、511-512页。
⑨阎纲:《文坛徜徉录·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83页。
1221刘再复:《时代,呼唤着阎纲式的批评家(序)》,载《文学八年》,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第3页。
13白烨:《有胆有识有声有色——评阎纲的文学批评》,载《文学警钟为何而鸣》,作家出版社,2012,第5页。
1733阎纲:《文学警钟为何而鸣》,作家出版社,2012,第209-210、260-261页。
18陶东风:《“主体性”》,《南方文坛》1999年第2期。
19阎纲:《文坛徜徉录·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538-540页。
2637白描:《“在场”的阎纲》,《文艺报》2022年8月15日。
28阎纲:《与陈忠实对话〈白鹿原〉》,《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5期。
29阎纲:《〈白鹿原〉的征服》,《小说评论》1993年第5期。
3036魏锋:《贾平凹与阎纲》,《陕西工人报》2022年8月23日。
32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一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第248頁。
34阎纲:《余在古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98-205页。
35阎纲、李若冰、王愚等:《程海小说十人谈》,《小说评论》1991年第6期。
(梁向阳、夏华阳,延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