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在杭州
2023-05-28沈烨
沈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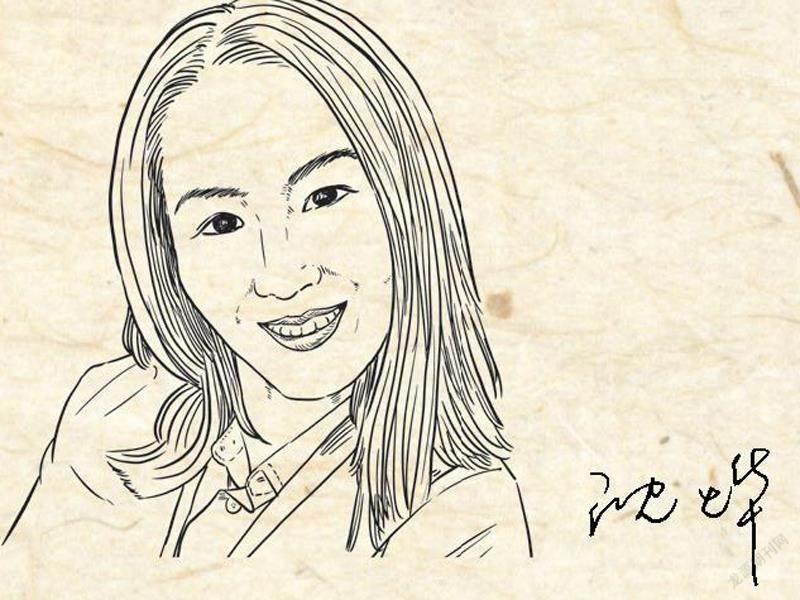


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來的一批女性作家,仍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她们以笔为剑,快意江湖;她们斗争,也犹豫;她们反抗,也逃避。时代的光影和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她们一直保持着思考与探索,无时无刻讲述着人性的光辉。
今人的回望和总结是粗粝的,这些不足以概括她们留下的文字和给予我们的力量。每当我读着百年前的女性之音,总会欣慰,也会悲戚。那一代女性的书写可能无法在结构和意境上创造深度,却能在情感上抵达无穷的远方,带给后世长久的共鸣。
庐隐便是其中一位令人瞩目的先驱。庐隐的笔调总是那么哀伤,写尽了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心路情感历程;她惯用书信体和日记体,更直白地展露人物的情绪和性格;她也常常把个人的经历和体验投射于笔下的女性角色中。苏雪林曾评价庐隐的作品“布满了哀痛、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庐隐的文字之所以让人战栗,与她充满悲剧的人生不无关系。
一个出生时就被亲生母亲视为“灾星”的女孩,她的一生注定充满了崎岖和坎坷。庐隐在成名作《海滨故人》中,借主角露沙的童年经历披露了自己悲惨的童年——被忽视、被嘲讽、被压制,也借五个女孩在爱情面前的迷惘揭露了那个时代女性所面临的苦与难。哀伤、挣扎、困惑弥漫在庐隐的各类作品中,她也因爱上有妇之夫郭梦良而决绝走向生命的另一个难题,而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接受另一段不被世人看好的爱情时,她又品尝了生活中一地鸡毛的苦痛,最后在生产中死于庸医之手。可是,庐隐明明是那么可爱,她“性格极其热烈”“一生英风飒爽”,难道她就不配拥抱人间的欢欣吗?
我心疼庐隐,总想在这世间寻访与她有关的阳光。所幸,这阳光从杭州洒下。
1930年,经过了两年的鸿雁传书,而立之年的庐隐终于接受了比她小九岁的青年诗人李唯建,彼时,她带着第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正热情地开拓着自己的事业与生活。李唯建的爱是庐隐走出苦海的菩提叶,他们结婚了,以爱之名。婚后,庐隐和李唯建远赴东瀛度蜜月。年底,因为经费不支,他们回国了。新婚夫妇租下了杭州湖滨路崇仁里的一处住宅,把家安在了西湖边,她们打算与湖光山色相伴,长居于此。
此时,庐隐正怀着身孕,许是波光粼粼的湖面安抚了她的心,又或是山与水的柔情鼓励了她,庐隐依旧笔耕不辍。在杭州期间,庐隐写下了以好友石评梅和高君宇爱情故事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玫瑰的刺》。创作上的突破让庐隐对生活有了更大的信心,她满怀期待地憧憬着未来的一切。1931年5月,庐隐在杭州生下了她与李唯建爱情的结晶,他们为那小小人儿取名“瀛仙”,以纪念从日本来到杭州的这一段神仙之旅。
庐隐的悲剧性有一种命定的意味,她是一个出生在20世纪现实主义荣光里的人,却一直做着一个19世纪浪漫主义的梦,这样的冲突最后常常指向悲剧。谁曾想,杭州浪漫悠闲的日子只持续了半年,生活的压力扑面而来,为了养家糊口,庐隐接受了上海一个女校教员的职位,于1931年7月离开了杭州。
不过,身虽远,庐隐的心却始终栖居于杭州。一年之后的一个秋日,庐隐深感自己“像是负重的骆驼,终日不知所谓地向前奔走”,不多考虑,她与丈夫李唯建携两位好友坐上了火车,去往西湖畔,寻访心灵的安适。为了纪念这一段旅程,庐隐写下了散文《秋光中的西湖》,发表在当年的《申江日报》副刊《海潮》。这一趟杭州之旅非常短暂,却令人难忘。一行四人于午夜时分到达杭州,住进了湖滨旅馆。
第二天一早,庐隐和李唯建探访了湖滨路上昔日的故居,往事纷至沓来,她细细品味,既感慨又惆怅。近旁的西湖像一剂良药注入了庐隐疲惫的身心,渐渐地,她忘了自己是一只骆驼,她变成了紫燕,“翱翔在清隆的天空中,听见神诋的赞美歌,觉到了灵魂的所在地”。庐隐事无巨细记录着杭州之行——泛舟西湖,楼外楼用餐,参观净慈寺,坐山兜子上山……字里行间充满着欢欣与留恋,她与杭州,终究是实现了灵魂的契合。
然而,现实总会适时围困住浪漫的一瞬,很快,他们就要整理行装返回上海,返回不堪的生活了。对庐隐来说,这时的西湖,“成为了灵魂上的一点印痕,生命的一页残史”。告别总在眼前,但杭州之行收获的愉悦足以让庐隐在日后细细咀嚼。
人生总是充满着彷徨与失落,所谓理想的人生并不是泛泛之辈的选项,因为即使是庐隐这样的天选之人也无法真正触及,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庐隐是不幸的。但是,庐隐也是幸运的,她于万千灵魂中遇见了所爱,坚定地按着自己的心意生活,也得了西湖山水的眷顾,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静谧与惬意。
同样,杭州也是幸运的,杭州因秀美与传奇,接纳了无数有趣的灵魂,也因此成了他们生命中的最佳回忆。庐隐会永远记住杭州,记住心灵沉醉的那一刻;杭州也会记住庐隐,记住她烂漫的笑容,记住她小小的身躯,记住她无尽的能量,也记住她在秋光中的那一次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