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潜水艇》:想象的秩序和敞开的空间
2023-05-22马媛慧
马媛慧

书 名:夜晚的潜水艇
作 者:陈春成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页 数:224 页
定 价52 元
ISBN9787542669964
“秋天是水族的夜晚。那些纷乱的鱼群,奔跃倦了的海豚,负载山丘的巨鳌,乃至鲸鲵蛟龙,在清秋的凉意中,都深深地沉下去,潜入夜一般的深渊,开始安眠。”幽深而安宁,独自在寂静中慢慢地潜下去,沉入适意又微茫的心緒之中。这是陈春成贪恋的一种氛围,也是他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表现出的独特质感。《夜晚的潜水艇》带给我们的感觉类似西方印象派的画作,没有狰狞宣泄和奋力呐喊,只有情感的淡淡晕染。比起一般小说中线条感的明晰叙事,《夜晚的潜水艇》充满了思绪的漫漶。这种源于静观、沉思、遐想的审美风格,无疑是面向自我的内向型创作,独处时无限放大的主体思致与小说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是一致的。
古典氛围里的现代困境
攀援草木,游荡茂林,蹚水过溪,仰逐云雾,《秋山晚翠图》《溪山行旅图》,中国士人笔下的山水画成为陈透纳奔跑跳跃的天地;禅院、经文、碑刻,寺庙与城市,出世与入世,交织在《竹峰寺》山林间的潜流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废弃的耽园隐隐透露出明清动荡之际中国士人沉溺玩艺的世纪末情绪;《尺波》仿佛是荆轲刺秦的另一个版本;《传彩笔》嫁接了神笔马良和江淹的故事;《裁云记》中走出了蒲松龄笔下幻化成人的狐狸;《红楼梦弥撒》向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中国的文学圣经《红楼梦》致敬,《音乐家》从伯牙子期的知音之谊演绎出苏联音乐家的精神乐境。对联、诗话、酿酒、铸剑、原典、古书……长期浸淫古典文化使得小说文本具有空灵澄澈的审美意味,汪洋而舒缓的语言富于诗的质地而蕴藉音乐的流动之韵。初读《夜晚的潜水艇》很容易被作家营造的古典氛围所吸引,但古典文化的运用只是陈春成经验的一部分,小说着意最深的是对现代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呈现。

首篇《夜晚的潜水艇》讲述的是一个富商被博尔赫斯的一首诗击中,资助潜水艇寻找诗中被抛向大海的硬币,最后因潜水艇失联而终止的故事。过了好多年,这个神秘消失的潜水艇通过画家陈透纳生前的回忆录得以重现,潜水艇的沉没无疑是对陈透纳想象力被永久扼杀的隐喻。《竹峰寺》围绕“我”的“藏钥匙”和慧航和尚的“找碑”两条线展开叙述,“我”和慧航都是因为“失去”所以要“藏”。《传彩笔》不仅讲述的是叶书华的故事,还关联了读中文系的“我”和将软文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叶书华儿子。《裁云记》里“我”的日常需要时刻警惕云彩的形状是否合规,“我”的精神却常常沉溺于“洞穴”的深渊。《李茵的湖》对“失去”的演绎同时在“我”对李茵的感情变化和李茵追寻过往的两条线上演进。《尺波》以“熬夜”写物对人的役使,以“鬼火”写权力话语对人的规约。《音乐家》全篇都是权力/艺术、理性/情感、逃匿者/追捕者的对照书写。小说中大量并置结构的使用创造了一种相互参照和相互阐释的语境,共同指向人物“失去”后内心的落寞。陈透纳以悲戚的口吻悼念自己无法再来的想象力:“没有比那些幻想更盛大的欢乐了。我的火焰,在十六岁那年就熄灭了,我余生成就的所谓事业,不过是火焰熄灭后升起的几缕青烟罢了。”躲进竹峰寺的“我”为老屋和县城在现代化剧变中的面目全非而怅惘,高楼大厦使记忆无所凭附:“什么会留下,什么是注定飘逝的,无人能预料,唯有接受而已。”品尽诸神盛宴的叶书华只觉人间寡淡,寂寞虚空,李茵妄想依靠事物之间的联系寻找记忆中的过去却宣告破产,古廖夫盛大的演奏会不如说是一场迟来的追悼会……消沉的落寞在文本中挥之不去,小说展现出那些可能构成“失去”的外在力量,爱、文字、权力、现代化,是如何造成主体的压抑,并使主体感受到环境中潜在的威胁,产生秩序变动的不安感和迷惘感。
想象的破与立
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夜晚的潜水艇》让我们看到想象到底可以走多远。门上的木纹是将军的头盔,大理石的纹理是河流与山脉,马桶里的水是湖上的漩涡,“我”想象自己在画中攀岩登峰,在热气球里穿云过雾,如果说这还是一种事物之间相似性的联想式想象,那么接下来“我”进入到了想象本身之中。“有一晚睡前,我看了好久莫奈的睡莲,梦中我变得很小很小,在那些花瓣间遨游,清晨醒来后枕边还有淡淡幽香。”类似通感式的想象在整部小说集里俯拾皆是,“他听到急剧的刹车声,嘴里就会涌起浓烈的橡胶味;器乐一响他眼前就游动着一团团色块,颜色随着曲调变幻;有时嗅觉和触觉也会联通,如闻到柏油味时他手心便感到一阵黏稠,几乎无力张开。”
文中想象力令人惊异的地方在于直接消解了虚构和现实的界限,让想象的世界参与现实生活,构成现实的一部分。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 马尔克斯在他的短篇小说《光恰似水》中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悲剧,居住在大城市的孩子托托想要像在卡塔赫纳(加勒比港口城市)一样能够自由地划船,每当父母外出,托托和小伙伴就会打碎电灯泡,“一股像水一样清澈的金色光芒从破碎的灯泡里流出来,孩子们让它一直流淌,直到在屋里积到四掌深。”被电灯开关放出的水源源不断地流溢出来,终于淹死了这群孩子。光恰似水,像马尔克斯笔下的这个隐喻一样,虚构以自身特有的强有力的逻辑介入了现实,成为一种解构的力量。
陈透纳在脑海里建造了一艘潜水艇,给潜水艇“安装”和“设计”发动机、舷窗、探测仪,完工后夜夜驾驶这艘潜水艇航行,“那晚我们在北冰洋的冰层下潜行。我忘了设计取暖装置,结果第二天醒来,感冒了。”“有一天晚上,我爸和朋友小酌,很晚还没回来。我很焦急。因为如果我把二楼的空间转移到深海的潜艇中去,原先的位置会变成怎样,我没有想过。也许等我爸上了楼,打开门,会看到一片空白,或满屋的海水。”陈透纳与自己的想象融为一体,会因航行想象中忘记取暖而在现实中感冒,会担心想象里空间的改变引发家里海水倒灌。《音乐家》中盛大的音乐会几乎使我们忘记这是古廖夫精神崩溃后的“乌有”幻想,存在于现实中的追捕与逃匿的阴影始终与心灵乐境里纵情游荡的酣畅构成紧张与自由的有序二重奏,现实中的高压不仅没有被抽离,更成为与想象本身狭路相逢的对手,以至于当古廖夫像紫翅椋鸟一样化为灰烬时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和突兀,那种在音乐幻境里的体验到的狂喜、痛苦与忧虑仍然萦绕在我们心头,久久无法散去。“所有小说都来源于想象”,想象在陈春成这里早已超出了艺术构思和表达方式的维度,具有了本体的意义,能够轻而易举跨过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沟壑,“只要将幻想营造得足够结实,足够细致,就有可能和现实世界交融,在某处接通。”
《竹峰寺》和《传彩笔》展现出作家对历史的重新想象和重新理解是如何突破历史本身的限制的。《竹峰寺》虚构了碑的故事,说《覆船山房随笔》中有载,写经生陈元常“见彩蝶落于佛头,乃大悟,急索笔砚,闭门书经,三日而成。”从此经文被刻在碑上供后人瞻仰,陈春成又以晚明书法家、笔记材料《枯笔废砚斋笔记》为佐,使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陈春成的杜撰,“写到那块碑时,觉得必须得有这么个典故,但是又没有,只好编了一个。”陈元常被蝴蝶击中的刹那一如“我”找到藏碑时惊喜、释然又舒展的心境。
到了《传彩笔》,陈春成对想象历史的方式作了变形。江郎才尽的“真相”乃是因为江淹在传彩笔的指引下写下了无数伟大的篇章,卻因文字本身无法示人而被误认为才尽。通过“我”摘录的博客,叶书华伟大的创作和心路被我们所看到和认识,对江淹故事的翻转“揭露”了江郎才尽的“真相”,而“我”对叶书华博客的完整摘录又何尝不是一种翻转,“有而不示”和“无有而无示”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不能被世人看见的文字得以重现、不能被认识的“真相”得以理解,叶书华困于文本,最终通过想象创造的文本获得了超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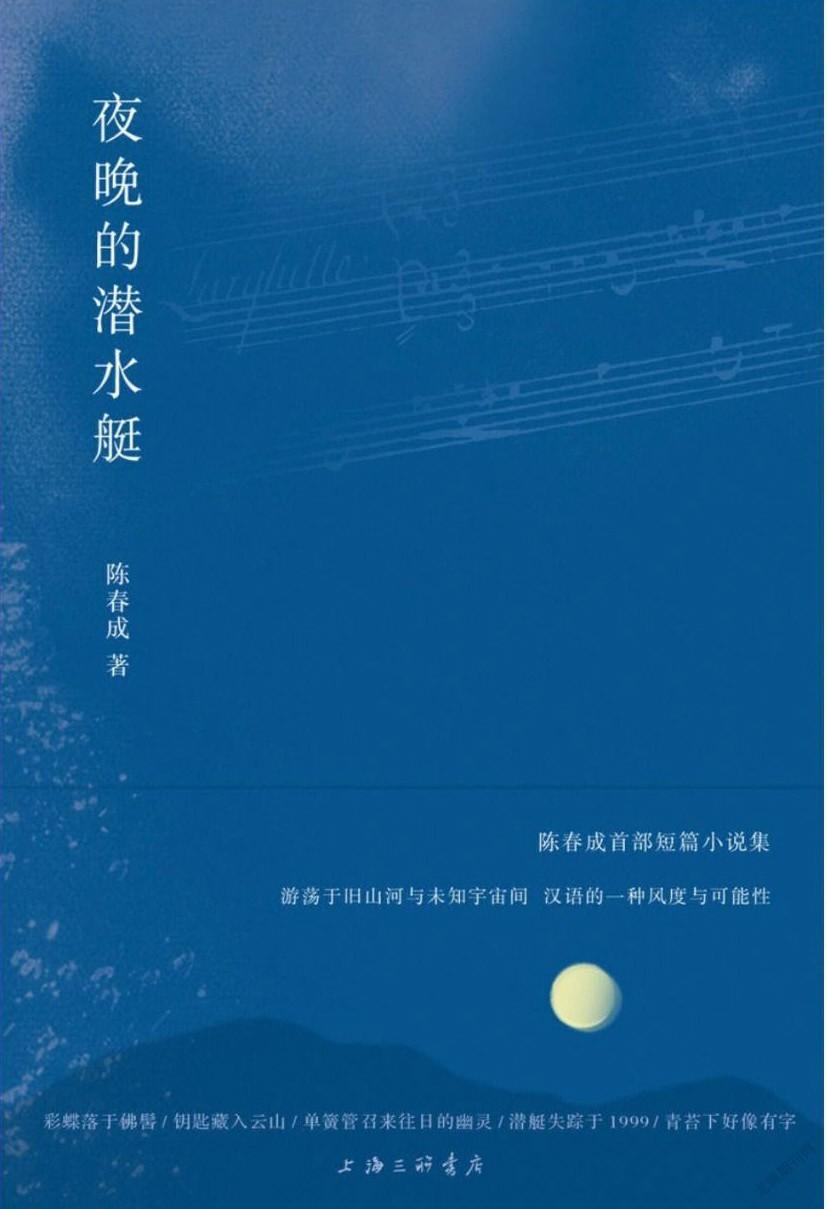
有趣的是,陈元常和江淹的故事都是嵌套在小说的一级叙事之中的,同样的套盒结构还有《裁云记》里老者的故事、《音乐家》里的“似是故人来”。《裁云记》里在修剪站工作的“我”始终无法静下来去钻研知识,于是去拜访了老师生前的好友,从和老者的交谈中得知了老者是如何穷尽一生破解对联的谜题后,“我”不再害怕深不见底的洞穴,决心投入所有的寿命去研究感兴趣的知识。《音乐家》的主线是警察的追捕,“似是故人来”里到访的穆辛其实是古廖夫神经病症发作时的臆想,穆辛并不存在,而是尚未受到审查迫害的古廖夫的化身。穆辛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段插入的臆想,古廖夫开启不断的“返魅”,挣掉现实的沉重枷锁,重新回到音乐创作的自由中去。并置结构里嵌套一个小故事,这个手法几乎出现在每一篇小说里,其中《夜晚的潜水艇》比较特殊,富商与陈透纳的故事像博尔赫斯扔出的硬币的两面,按照硬币所规定的逻辑隐秘发展,最终共同走到了一个失落的现实。博尔赫斯的硬币是并置结构的元结构,在其他篇中,倒转过来,通常是并置结构中嵌套了一个故事,对套盒里故事的想象比对整体故事的想象更加丰盈和有力,人物往往是在这个故事里找到一个支点,用以平衡自我面对现实压力和内心不安时的处境。从叙事上看,套盒里的故事构成了微妙的转折,它们与整体叙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却对整体叙事作出反向书写,赋予了人物超出困境的突破之径,淡化了文本带给人的消沉印象,从而完成了主体对自身重建的过程,这是隐藏在文本深层的由想象力生成的逻辑秩序。
诗的起承转合与无限生成
小说中还存在一种独特的精神空间,这个空间比套盒故事更近一步,走向意义无限生成的可能。“坐了几个黄昏,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有一种消沉的力量,一种广大的消沉,在黄昏时来。在那个时刻,事物的意义在飘散。在一点点黑下来的天空中,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你先是有点慌,然后释然,然后你就不存在了……如果你在山野中,在暮色四合时凝望过一棵树,足够长久地凝望一棵树,直到你和它一并消融在黑暗中,成为夜的一部分——这种体验,经过多次,你就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古怪的人。”这段出自经验的对暮霭之中人的肉身所具有的分明重量与感官所承受的混沌不清的描述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幽暗的、模糊不清的,主客交锋的时空。如果我们细读文本,就能发现这种感受以不同的样态几乎投射于每个故事之中——是个体的渺小无以对抗外界的压力(《夜晚的潜水艇》《音乐家》)、无以完全自拔出自然之力(《竹峰寺》)、无以创造永恒于流逝的时间(《裁云记》《李茵的湖》)、无以抵御宿命的冷艳(《红楼梦弥撒》)、无以封存纯粹的欲望和快乐(《尺波》《酿酒师》)而沉入到远离现实生活,心事飘忽无法安放的状态。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体会过这些时刻,感受过其时身心的疲惫和消沉。但是在《夜晚的潜水艇》中,这种感受各自演变出了另一条轨迹。洞穴从深渊变成探索无限可能的通道(《裁云记》),平行的命运联系虽是曲径,标定了既定的命运轨迹,却在通幽处找到另一种范本式的对照(《夜晚的潜水艇》《竹峰寺》),伟大的文字永不可及,正开启了精神创造生生不息的闸门(《传彩笔》),盛宴必散而其本身也是意义之义(《红楼梦弥撒》),记忆联通起溃散的时间并将其打磨出晶莹和粗糙的质地(《李茵的湖》)……在消沉感极具饱和行将散落于情感固有的秩序之际,一种具有全新可能的空间向我们敞开,以其不明的语义标示了可能走向的每一条路径,继而催生出故事内部对意义自洽的重建的可能。

“可能性”本身就是这种感受的最大创造。“蜻蜓与水面将触未触,一截灰烬刚要脱离香烟,骰子在桌面上方悬浮,火焰和海浪有了固定的形状,子弹紧贴着一个人的胸膛,帝国的命运在延续和覆灭的岔口停顿不前而一朵花即将绽放……”陈春成着迷的是一种临界状态,包括黄昏时的“灵魂出窍”,在临界时刻,事物之间包括人在内的差别都泯灭了,所有的秩序、规则统统被瓦解,这同时也意味着会有新的东西在积蓄力量,而我们可能从中得以汲取和重塑,世界也会呈现出新的面向。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酿酒师》中陈春醪最后酿出的酒对人的泯灭。“酒是水酿出的诗”,“曼妙的开头,宏大的承接,玄妙的转折和虚无的收尾”,诗有起承转合,最后必有收尾,但诗所生发出的意义是无穷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和敞开的。在此意义上,陈春成写作小说时对想象的理解和运用想象的方式与之是同构的,它们都是要消解现实对人的特定规约,从而开启新的可能性。因而,无论是在形式还是意义上,回到和重温内心发生震颤的时刻,回到临界之地,回到敞开的空间,也是小说中以不同面貌反复出现的——是值得注意的,它意味着一种解放和重建,续接起诗与世界的对话,在宇宙的浩渺、天地的广阔和秩序的失散、世情的浮沉之间找到与自我对话和纾解心灵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