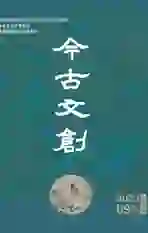《剪灯新话》与瞿佑的文艺观
2023-05-18黄静
【摘要】瞿佑的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摹写元末的社会动乱以及文人命运,一个个短篇故事凝结着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多方面的思想观念,如惩恶劝善、因果报应的宿命观,托言鬼怪、批判世道的鬼神观,重视文华、炫才逞技的文学观,重情重义、死生相随的主情观等,展示了瞿佑丰富的思想世界,表现了乱世文人的生存状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瞿佑;《剪灯新话》;乱世文人心态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9-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9.004
瞿佑,字宗吉,号存斋、吟堂、乐全叟等,原籍山阳(今江苏淮安),后徙居钱塘(浙江杭州)荐桥街。生于元至正元年(1341年),卒于宣德二年(1427年),享年87岁。瞿佑多才多艺,却一生流落不遇,抑郁不得志。其创作的小说集《剪灯新话》记录了一些瞿佑从好事者口中听闻到的故事,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这些闻见经他加工创作,融汇了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思想感悟。因此,以《剪灯新话》为文本来反观瞿佑的思想怀抱,从中探求瞿佑的宿命观、鬼神观、文学观、主情观等,对于《剪灯新话》和瞿佑研究的深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惩恶劝善,因果报应的宿命观
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瞿佑遭此乱世,对战乱灾难和社会黑暗都有很大的感触,所以其创作的《剪灯新话》一方面是想记录社会动乱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故事来惩恶扬善。
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表明自己创作的主旨是:“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友人凌云翰为《剪灯新话》作的序中也说:“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惩恶劝善是瞿佑作为一个乱世文人的责任与担当,而他实现惩恶扬善的方式之一就是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佛教自产生之后,就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行了长达数千年的融合,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入,不但佛教故事成为明清小说的题材内容,而且许多佛家观念也成了文学家创作的思维模式。
佛教对《剪灯新话》的影响,诚如葛兆光所言:“宗教与文学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联姻,前者刺激后者的想象,并提供大量神奇瑰丽的意象,因此,尽管文学家未必都是宗教的信徒,但仍然会受到宗教的影响,而一旦文学家受到宗教的影响,便往往会出现宗教式的思维、情感、意象不断渗透文学领域的现象,使文学作品极为浓重地表现出这种与宗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感情色彩、意象群落。”
元代科举废除,儒生地位低微,知识分子的意志理想在乱世中旁落,寻不到仕进前途的瞿佑开始反观儒家的文化观念,主动接受佛教因果观念的影响,以因果论世事,寓劝惩,探索新的价值观念与文艺创作方法。
《三山福地志》中山东人元自实“生而质钝,不通诗书”,但家产颇丰,他曾借给同乡缪君二百两银作路费,因乡党相处之厚,未要求写文券。“至正末,山东大乱,自实为群盗所劫,家计一空”,元自实于是前去投奔已经发迹的缪君,缪君却因元自实无文券拒绝还钱。元自实走投无路之际动了杀缪君的念头,后因心怀慈悲隐忍而归,百般无奈之下投井自杀,幸至三山福地,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自己前世在职之时,因为文学自视甚高,不肯引荐后辈,故而今生懵懂不识字;前世以爵位自傲,不肯接纳游士,故而今生漂泊无依。今生缪君此行不义,不出三年,时运变革,大祸将至。
《令狐生冥梦录》中有个叫令狐生的人刚直不阿,不信神灵,其凶恶的邻居乌老病死之后,因为家人广做佛事竟然死而复生,令狐生因此赋诗以讽。后来地府闻知此诗,请令狐生至,令狐也得以趁机观览地狱,亲眼目睹了那些生时作恶死后受到残酷惩罚的阴森恐怖之象,看到了地狱中的因果报应。
《富贵发迹司志》中何友仁在富贵发迹司亲耳听见司主和判官讲述因果报应的断案过程;《永州野庙记》中毕应祥除妖去害,延寿一纪;《太虚司法传》中冯大异因为正直被任命为太虚殿司法;《爱卿传》中罗爱爱因为集孝顺与节烈于一体,投胎转世为男子,得以再续前缘。
瞿佑在《剪灯新话》中讲述此类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故事不在少数,通过这种因果循环的宿命观来达到惩恶劝善的教化目的是瞿佑創作的重要思想特点,也体现出佛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凝结在士人及民众的心理结构中,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二、托言鬼怪,批判世道的鬼神观
《剪灯新话》收录故事的时间范围为元大德年间(1297—1307)至洪武七年(1374),其中一半以上的故事发生在元末最为动荡的至正年间(1341—1370)。瞿佑正是在这段战火中出生成长起来的,他亲身经历了避乱的波折与辛酸,这些苦难之下,他蕴蓄了丰富的情感和素材。明初,朱元璋为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实行文禁,在严刑峻法的重压面前,文人们为避免遭祸,于是学习唐人小说,借写鬼怪神仙、闺情艳遇来委婉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情志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瞿佑的《剪灯新话》中就有许多篇章顺应时代潮流,借鬼神来批判世道,叙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水宫庆会录》中,一位名叫余善文的白衣秀士,颇有才名,被广利王邀请进南海龙宫为新建的宫殿撰写上梁文,在宴会上余善文才惊四座,获得众神的一致好评,得到广利王设宴重谢。《水宫庆会录》作为《剪灯新话》的第一篇,有着深刻的隐喻含义。首先,余善文其实是擅长文学的瞿佑的自我真实写照,文中全篇皆录的上梁文也是作者着意表现自己的文学才赋;其次,对贫寒儒生礼遇有加的神仙广利王则代表瞿佑对统治阶级的殷切期望。《旧唐书》记载:“(天宝)十载正月,四海并封为王……义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广利王。”从国家层面上推崇南海祭祀实际上是在宣扬王权君威,所以神仙广利王一定程度上象征统治阶级的护佑。元代知识分子地位极低,明代天下稳定后,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由开始的礼遇转变为轻慢,甚至杀戮,《水宫庆会录》中蕴含的深意不言自明。同时,广利王来源于道教神仙谱系,瞿佑创造这一礼遇儒生的神仙形象也表明瞿佑的文艺创作受到道教鬼神观的影响。《修文舍人传》讲述书生夏颜博学多闻,性气英迈,然而名分甚薄,日不暇给,客死润州,死后他的鬼魂来到人世与友人交谈,告诉友人自己已经隶职冥司,并且详细描述冥司的情形“黜陟必明,赏罚必公,昔日负君之贼,败国之臣,受穹爵而享厚禄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积善之家,修德之士,阨下位而困穷途者,至此必蒙其福。”后来其友人在夏颜的劝说下,生病后不复治疗,数日而终。文中夏颜的鬼魂讲述的冥司情景与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友人宁可放弃生命也要前往阴间更是深刻地讽刺了现实的黑暗。《牡丹灯记》记叙奉化州判符君之女的棺木因为战乱被临时安放,后鬼魂寂寞,遂化为精怪害人的故事,黑暗的世道造成了鬼蜮横行,又反过来损害世道,最终乔生延请高道开坛做法,将精怪驱捽而去。
明代洪武朝文字狱较多,瞿佑出于全身避祸的心理,借助道教神仙思想来劝善惩恶,批判黑暗的世道,表达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无论是佛教因果论还是道教鬼神观,瞿佑的文艺创作都完成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儒家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并没有抱守儒家思想一成不变,瞿佑在自己不得志时,也依旧从事自己的文字劝惩事业,他援佛道二家思想入于文学创作,体现了复杂圆融的文艺观。
三、重视文华,炫才逞技的文学观
瞿佑出生、生长于战火之中,即便几经辗转流离,他都未曾放弃求学,这首先离不开生活环境的熏陶。瞿佑出生于明经世家,自幼便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并且转益多师,据《归田诗话》记载,年少时曾从王叔载、其叔祖瞿士衡、祖姑丈杨仲弘等人学诗,且经常随长辈拜会名家大儒,其才华获得颇多赞誉称赏。这样的教育环境不仅使瞿佑在才学上有所进益,而且也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学观。
广泛的唱和交游也增长了他的诗学才赋。少年时期瞿佑曾多次参加云间诗社的唱和活动,如杨维桢与凌云翰有香奁诗八首,瞿佑也和有香奁诗八首,凌云翰的咏雪、咏月诗,瞿佑也曾唱和过,在切磋唱和中,他的诗艺不断精进。对此,瞿佑在《归田诗话》中感激地说凌云翰的赐教、奖劝之功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瞿佑一生虽辗转流离多地,但他也因此能够不断与当地的文人相互交流,博采众长,锤炼诗艺,即便是在短篇小说集中,瞿佑也着力表现自己的诗才,炫耀文华。
第一,瞿佑的诗学才赋表现在《剪灯新话》中的诗词韵语中。《剪灯新话》全书有二十一篇小说,其中插入的诗词歌赋高达七十余首,甚至《水宫庆会录》《联芳楼记》《秋香亭记》等篇中韵语超过全篇字数的三分之一,其凸显文学才赋的创作意图显而易见。这些诗词韵语也极富艺术价值,首先,这些韵语众体皆备。词有《金缕词》《木兰花慢》《齐天乐》《沁园春》《临江仙》《满庭芳》等不同曲调;诗歌古体和近体皆全备,又分为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等不同类型;骈赋对仗工整,音律和谐,这些韵语错落在文言小说中,显示出瞿佑的文采斐然。其次,这些韵语风格多样。如《联芳楼记》中的《竹枝曲》带有清新的民歌意味,《水宫庆会录》中的 “上梁文”语言典雅,对仗工稳,《天台訪隐录》中的诗词浅易明白,各色的诗文风格与多样的人物故事相得益彰。传奇小说中诗词韵语原本可有可无,除去之后并不影响基本故事情节的发展,但是瞿佑连篇累牍的穿插,或仿效前人,或自创新诗,使这些诗词韵语成了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如翠翠与金定重遇后不方便倾诉衷情,只能借诗词隐晦达意,薛氏姐妹以诗词与郑生调情,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另外,一些原有的诗词经瞿佑稍加改动,便能够与小说意境相符,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如《鉴湖夜泛记》中成令言与织女的对话等,这些诗词韵语都是瞿佑有意在炫耀自己的诗才文华。
第二,瞿佑的炫才意识还体现在他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身上。瞿佑笔下的人物多是较有文化的阶层,如《龙堂灵会录》中以歌诗在吴地闻名的闻生,《华亭逢故人记》中富有文学的全、贾二子,《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中善于吟咏的滕生,《天台访隐录》中粗通书史的徐逸,小说中“余善文”“成令言”的名字则更能直接透视出瞿佑的炫才心态。《三山福地志》中的主人公元自实是唯一一位愚懵不识字的人物,但他前世也是以文学自视甚高。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亦是较有文化的阶层,如吟咏不辍的薛氏姐妹、织女等形象,她们与男主人公志趣相投,诗词唱和,成就了一段段可惊可叹的佳话。
在文化环境的熏陶下,瞿佑培养起深厚的文学素养并以此为傲,他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创作才赋表现在小说《剪灯新话》中,无论是写作模式还是小说内容,都成功地展现出瞿佑的文学功力。文章中大量的诗词歌赋,既能为小说语言添彩,又能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四、重情重义,死生相随的主情观
元末虽遭战乱,但社会环境相对自由、宽松,瞿佑也因此交友颇广,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同为云间诗社成员的杨维桢。杨维桢名擅一时,写诗主张性情说,认为诗歌创作要依情而出,这种性情说对经常互相唱和的瞿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表现在小说中即是有情便可以突破生死界限。
此外,杨维桢香艳的创作风格对瞿佑也颇有影响,瞿佑的作品中多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浓郁艳丽,反映出瞿佑尊情、重情,重视人的自然欲望的文艺观念与创作风格。
《剪灯新话》中描写爱情故事的篇幅较多,人与人相恋如《联芳楼记》《渭塘奇遇记》《翠翠传》《秋香亭记》,人与鬼怪遇合如《金凤钗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爱卿传》《绿衣人传》,约占全书篇数的五分之二。
瞿佑在小说中正视人的自然欲望。《联芳楼记》中苏州薛姓富商之女兰英、惠英姐妹在楼上玩耍时,看中船上的郑生,便投下一双荔枝表示爱慕之情,当夜,二女从楼上垂下一竹兜吊郑生上楼,“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在这里,瞿佑并没有把兰英、惠英塑造成大户人家的小姐一般恪守礼教规矩,而是敢于正视自己的欲望,大胆追求肉体上的欢愉。《金凤钗记》中兴娘则更为直率,半夜约会崔生并威胁其就寝,一系列坦荡追求情欲的人物形象反映出瞿佑主情尚真的文学观念。
瞿佑笔下的女子大胆追求爱情,为爱死生相随。《渭塘奇遇记》中王生本是世族子弟,收租途中被一酒肆主的女儿相中,她见王生奇俊,便心生爱意,后相思成疾,最终魂逐王生入梦,“执手入室,极尽欢谑”。《翠翠传》中刘翠翠与金定为爱舍弃生命,双双殉情。《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中卫芳华死后依然追求幸福,其魂魄与滕穆回乡共度三年美好时光。《绿衣人传》中绿衣人与赵源前世不能相守,今生以精魄之身也要再尽夫妇之情。这些女子都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且能够为爱情突破生死界限,这种执着追求爱情的精神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剪灯新话》是一部情感丰富的作品,瞿佑的自序中说此书是要供自己阅读,不做外传,既是在这种前提下完成的作品,则更容易带有个人抒情色彩。正视个人欲望,大胆追求爱情,为爱死生相随,这种主情观已经突破了传统儒家学者“礼”的束缚,向“人”回归,体现出瞿佑进步的创作观念。作为熟读圣贤书的文人,瞿佑虽然开始反观儒家文化,向佛道二教寻求解脱之道,但他又没有完全摆脱儒家伦理纲常的藩篱。如《渭塘奇遇记》的结尾,王生与酒肆女订婚,明媒正娶,结为正式夫妻;《联芳楼记》中虽然薛氏二女大胆追求郑生,最终却也没有逃离礼法的规束,要求郑生托人前去提亲,三媒六礼,问名纳采,完成婚礼的各项程序,为他们的爱情披上合法的外衣,这表现出瞿佑尊情重情的主情观是戴着镣铐在跳舞,无法真正超越当时的社会风尚,同时也反映出乱世中瞿佑真实的文艺创作观念。
总之,瞿佑《剪灯新话》以元末动乱为时代背景,书写兵火之余文人士子们的悲欢经历,故事情节极幻极真,既真实地反映了瞿佑的乱世经历,又光怪陆离地展现了其宿命论与因果论思想;既反映了其主情的进步观念,又展示了其重文的情感态度。透过《剪灯新话》一个个短篇故事,展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瞿佑的生存状态与思想世界,也体现出瞿佑反观儒家思想,对佛道采取较为圆融态度的文艺创作观念。
参考文献:
[1]瞿佑.归田诗话[M].明刻本.
[2]杨维桢.东维子文集[M].四部丛刊本.
[3]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934.
[5]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76.
[6]乔光辉.援道、释以消儒——《剪灯新话》之《鉴湖夜泛记》主题解读[J].明清小说研究,2021,(4):77-197.
作者简介:
黄静,女,山东临沂人,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