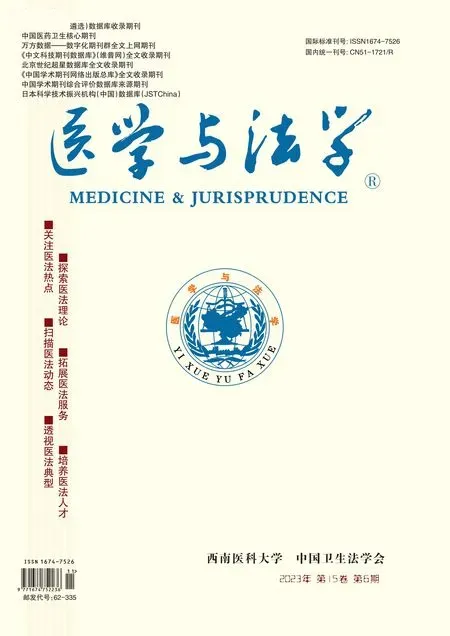提供假药罪的疑难问题研究
2023-04-24雷英君邓毅丞
雷英君 邓毅丞
药品安全与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息息相关。为完善我国药品治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作《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修改了部分涉药罪名,从立法层面严密对药品的监管,其中明确将“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明知是假药而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行为确立为提供假药罪,规定依照生产、销售假药罪处罚。2022 年3 月两高发布《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作《药品解释》),对《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修改涉药犯罪的相关问题作了解释,然而却并未完全解决提供假药罪在适用中所存在的问题。准确理解和把握提供假药罪的规定,解决本罪在刑法理论和司法适用上的疑难问题,对实现立法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立足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与《药品解释》对提供假药罪的规定,本文主要围绕本罪中的主体问题、“假药”认定、主观“明知”的判断三个方面的疑难来展开研究,期能供理论与司法实践借鉴参考。
一、提供假药罪的主体问题
提供假药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刑法条文对本罪行为主体的表述为“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看似仅限自然人为主体,但刑法解释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的工作,对刑法条文的解读不能拘于条文本身,而应立足于所在章节甚至整个刑法体系。刑法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对本节罪名的单位犯罪进行了规定①,同时《药品解释》进一步明确本罪的行为主体为“药品使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②,因此提供假药罪既可以是自然人犯罪,也可以是单位犯罪,本罪行为主体为特殊主体,即药品使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然而,如何界定“药品使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尚未明确,因此确有必要对提供假药罪的主体展开分析。
(一)提供假药罪的身份犯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如何界定“药品使用单位的工作人员”尚未达成共识。其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应对该主体作限缩解释,将其限于用药单位中对药品有管理使用权限的人员。本文对此持肯定意见,本罪的自然人犯罪主体应仅指用药单位中具有药品管理使用权限的人员,其他一般工作人员不属于本罪的行为主体;且在认定上,应当以具体职权为判断标准,而非简单地以是否属于用药单位职工进行判断。
将“药品使用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限制解释符合刑事立法目的。刑法之所以将提供假药罪的行为主体与前款生产、销售假药罪作区别规定,就是为了在增加假药犯罪行为类型的同时,适当缩小刑法打击范围。[1]部分学者同样赞成这种观点,认为不得将该主体泛化解释,否则将不当扩大刑法打击面。“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应限于对药品有支配权限的人员,其他无相关权限的人员仅能成为本罪的共犯。[2]
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应当将其他一般工作人员纳入本罪的行为主体范畴,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即便是这些单位内的勤杂工、护工等人员实施提供假药供他人使用的行为,同样对本罪所侵害而须予保护的法益有现实威胁;其二,将单位内无药品管理权限的人员解释为本罪的行为主体未超出文义解释的范围[3];其三,行为人具体职权,外人一般无从得知,因此若第三人仅能判断行为人是该单位的工作人员,但无法分辨是否具有相关职权,则其对行为人提供药品使用的行为有合理的预期[4];其四,若不对行为主体作扩大解释,则将出现刑事处罚漏洞,使用药单位中没有相关权限的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将假药提供给他人使用的,不能以犯罪论处[5]。
然而,持反对意见者的上述理由存在诸多漏洞。第一,若仅从对保护的法益的现实威胁而言,即使是一般主体,无须进行“药品使用单位的”限制,实施同样的行为依旧会对该法益产生威胁,但刑法显然未作此规定;第二,文义解释仅能确定大致的限定范围,但刑法解释并非仅依靠文义,而是应综合刑法体系和刑法目的来进行考虑;第三,第三人能否分辨行为人是否具有药品管理使用职权是主观认识层面的内容,但行为人是否具有药品管理使用职权为客观事实,不得将二者混淆。若单位内无相应职权的人员明知药品为假药仍将其提供给他人使用,甚至该行为人故意冒充药品使用单位中有药品管理使用职权的人员而使第三人陷入错误认识,依旧不能构成本罪,只能成立一般主体可构成的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等。如在受贿罪中,若行贿人误以为机关中的其他人员是行使国家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而进行贿赂,其受贿人也不会构成受贿罪,而只能依据具体情况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诈骗罪。所以,对本罪犯罪主体进行限缩解释并不会出现刑事处罚漏洞,相反,每一个罪名都有其特定的规制范围,只是对相关行为人不得以本罪处罚,但可认定构成其他罪名,因而不得将“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扩大解释。
(二)提供假药罪的单位犯罪问题
我国法律并未对“药品使用单位”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作《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可知,药品使用单位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及其他药品使用单位。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是指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单位,如各级医疗服务单位、疗养院以及急救站等。④一些省级的相关规定如《湖北省药品管理条例》,其规定“药品使用单位”是指依法登记成立并使用药品的从事疾病预防、戒毒、康复保健等活动的单位以及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医疗机构等;⑤《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的规定与湖北省规定无二致⑥。从这些规范性文件中可知,药品使用单位还应包括药品检验机构。⑦有学者指出,只要是依职能具有用药权限的单位,即属于药品使用单位。[6]也有学者补充,药品使用单位还应包括临时获得用药权限的单位,例如临时设置的医疗救助点和药品检验点。[7]学界对“药品使用单位”的范围界定争议不大,只要该单位依据职能获得用药权限,无论其权限是持续或临时获得,均属于“药品使用单位”的范畴,具体包括医院、各级卫生服务机构、妇幼保健院、疾病防控中心、戒毒所、疗养院、急救站、血防站、计生服务站、药品检验机构以及临时设置的药品检验点和医疗救助点等。因此,这类机构(单位)若明知是假药而提供给他人使用的,符合提供假药罪的主体构成要件。
二、提供假药罪中假药的认定
为与我国《药品管理法》的修改接轨,《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原刑法所规定的“假药”是指依据《药品管理法》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学界就这一修改展开了广泛讨论,主要围绕删除该条款后《药品管理法》与《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之假药认定的关系、两法的衔接、刑法中之假药认定的标准,以及可能出现的由法定犯变为自然犯的转向等问题。然而,《药品解释》再次补充,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假药认定依据,为《药品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⑧《药品解释》这种看似对原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假药认定规定的恢复,是否意味着条文中假药的认定与前一致等问题,是影响理论与司法实践的重要问题。
(一)提供假药罪中的假药应作实质性认定
本文认为,《药品解释》对假药认定的规定并非对原刑法条文的简单恢复,而是与《药品管理法》的修改接轨而实质认定提供假药罪中的假药,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药品管理法》的修改说明了我国假药认定的实质化倾向。2015 年的《药品管理法》额外规定了6 项“按假药论处”的情形,其中存在多项不符合国家药品管理程序规定的“形式假药”。⑨随着国家对药品犯罪的深入研究和热点案件的助推,这一规定终于在2019 年对《药品管理法》的修订中得以删除⑩,更新后的《药品管理法》更多聚焦于对所谓“实质假药”的认定[8]。
其次,从《刑法修正案(十一)》到《药品解释》中的有关假药认定的规定,进一步表明我国刑法意义上的假药应当采实质认定标准。有学者认为,本次修正案的修订删除了原刑法中有关假药认定标准的做法,旨在使假药的认定由《药品管理法》对刑法的刚性制约变为柔性制约,但《药品解释》的发布使得假药的认定又回到了过去形式化认定假药的状态。[9]需要明确的,是《药品解释》并非是对原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假药认定规定的恢复。原刑法规定的假药认定标准自1997 年一直沿用,由于《药品管理法》的前置法地位,此前的所谓“实质假药”和“形式假药”被一并认定为刑法上的假药。《药品管理法》的修改使原刑法中所规定的“按假药论处”的假药没有了前置法依据。在此次修正案将相关条款删除后,《药品解释》规定刑法中的假药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认定,是与2019 年《药品管理法》对假药认定的实质化倾向契合,而非对原刑法条文的简单恢复。[10]
最后,采取实质认定标准能够控制刑法处罚范围。提供假药罪的增设扩大了药品犯罪的刑法处罚范围,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虑,应当进行适当限缩平衡。此次立法并非是对提供假药的首次规定。2014年两高发布的药品犯罪司法解释,将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明知是假药而“有偿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销售”,却未将“无偿提供”假药给他人使用的情形纳入犯罪处理的范围。[11]有意见反映,实践中存在在捐赠、义诊等活动中将假药无偿提供给他人使用的情形,为了对其进行规制,必须将“无偿提供”假药给他人使用的情形也纳入刑法处置的范畴,[11]因此,刑法特别增设了提供假药罪。同时,《药品解释》进一步明确,提供假药罪中的所谓“提供”,是指行为主体明知是假药而“无偿”提供给他人使用,“提供”与“销售”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无偿提供,而后者为有偿提供。[12]由此,刑法对药品犯罪的处罚增加了“无偿提供”假药给他人使用的行为类型。在此情况下,对本罪中的假药采用实质判断标准能够对假药进行限缩认定,从源头上减少了本罪犯罪对象,从而起到控制刑法处罚范围的作用。
(二)提供假药罪中假药的实质认定标准
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被侵害的法益,而“法益”界定是刑法研究的基础,必须紧扣本罪的法益来确定假药的实质认定标准。本文认为,本罪是以侵害应被保护的个人法益为主的犯罪,因此本罪中假药的实质认定标准必须紧扣应被保护的个人法益,即与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关联。
通说观点认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保护复合法益,即国家药品管理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2]由于提供假药罪处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从法条位置出发,许多学者认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主要保护法益应当为药品管理秩序。[13]其实不然,罪名的体系位置只能为我们确定应被保护的法益提供参考,但不能起决定作用。刑法中也存在许多罪名中所侵害的法益与其在刑法中所处位置不相符的情况,如重婚罪。刑法将重婚罪设置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中,依照体系位置应当将重婚罪所侵害而应予保护的法益解释为个人法益,但如此解释存在严重问题。例如,若重婚罪仅侵害个人法益,个人对自身的法益有处分权,是否意味着在双方放弃自己的权利同意对方重婚的情况下即不构成犯罪,显然并非如此。因此,越来越多学者主张重婚罪所侵害的是秩序法益,即我国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故仅从提供假药罪的体系位置来确定其所侵害的法益并不合理。
实际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涉药犯罪的规定已经采取了将秩序法益和个人法益区分的思路。[14]《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将原来《药品管理法》中规定依照假药论处的“形式假药”的情形和其他违反药品管理规范的行为,单独确立为以侵害秩序法益为主的妨害药品管理罪。[13]也有学者结合妨害药品管理罪的行为类型指出,该罪是从原来的生产、销售假药罪中分离出来的,其法益也是从中独立的药品管理秩序[15],更侧重于对人的生命、健康的保护[16],因此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所侵害的主要法益应为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药品管理秩序则仅处于次要法益的地位,故在提供假药罪中应当主要保护个人法益,本罪假药的认定标准必须与个人法益即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关联。
(三)提供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假药罪中的假药不宜作等同认定
提供假药罪与生产假药罪、销售假药罪虽共处于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条文中,但由于相较于后两者,提供假药罪在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使其假药与后两者中的假药在认定上不能机械等同,而应达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标准。
提供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假药罪在对法益侵害的程度上存在差异,故将其中的假药作不同标准的认定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前文已述,通说观点认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保护包括国家药品管理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内的复合法益。[17]生产、销售假药罪中的假药由一般主体生产、销售,通常数量较大且直接流入药品交易市场,对药品管理秩序产生直接冲击,同时会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提供假药罪一方面其行为主体是用药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存在主体限制;另一方面,《药品解释》明确本罪的提供仅指“无偿提供”,无偿意味着行为主体缺乏利益驱动。两个因素的叠加直接使得本罪中的假药往往数量较少,且最为关键的是一般不会进入市场流通,因而不会对药品管理秩序产生直接冲击。在对秩序法益侵害程度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刑法在其第一百四十一条却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而若将本罪中的假药与生产、销售假药罪中的假药机械等同,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刑罚轻重和刑事责任大小。[18]而在结果无价值论看来,所谓“社会危害性”,就是指作为犯罪本质的法益侵害性。[19]因此,在二者对秩序法益的侵害程度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本罪对个人法益的侵害应当比生产、销售假药罪更强,如此对两罪规定相同的法定刑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另外,从客观解释的角度考虑,刑法将本罪与生产、销售假药罪共同规定在第一百四十一条中,却区分为两款规定,这从立法的构造来看,极有可能立法者对本罪与前款犯罪中的假药在设立之初便有区分意思。
本文认为,提供假药罪中的假药应达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标准,这一标准应为本罪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生产、销售假药罪作为抽象危险犯,仅需行为人实施相关药品犯罪行为即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基本犯,无须有对法益的紧迫危险或产生实害结果。而作为药品犯罪中另一重要类型的劣药,则须达到“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程度,即必须有实害结果的发生才能构成劣药犯罪的基本犯。[14]既然本罪中的假药相较生产、销售假药罪中的假药应当对个人法益有更强的侵害性,必然应当对其有更严格的要求;同时本罪属于假药犯罪,与作为实害犯的劣药犯罪不宜采相同标准。因此,本文认为,本罪中的假药应在二者中间寻求一个平衡标准,即达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
一般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删除原有生产、销售假药罪中的这一标准要求,意味着该罪转变为抽象危险犯。实际上,若将此标准作为本罪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能够在提高人身法益侵害程度要求的同时,达到与实害犯不同的规制效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并不要求出现实害后果,在犯罪类型上属于危险犯,而不是实害犯。[20]实际上,“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只是对行为危险属性的诠释,只要行为的危险性达到了此种危险程度即可。而在个案中对这种危险性进行具体判断时,要围绕涉案药品自身的安全性来考虑。[21]
对于2019年《药品管理法》所规定的4种假药应否认定为本罪的假药,需具体考察其是否满足“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求。[15]如对于药品成份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形,需检测其中的不符成份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危险性:若所增加的是其他既无药效又无危害的成份,或所含成份略少于国家药品标准、但不至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的,则不宜认定为本罪的假药;对于冒充药品的情形,以非药品冒充药品的情形,由于使用人服用了完全无药效的药物,便极有可能其错过了治疗时机而威胁其身体健康,故就有较大可能被认定为本罪的假药;但对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行为,则需进行鉴别——若是将功效相同或相似的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几乎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则不宜认定为本罪假药;对于变质的药品,由于其意味着药品的性质发生改变,故要么失去药效影响治疗效果,要么甚至可能因为变质转化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便极有可能认定为本罪的假药;而对于所标明的适应症或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情形,如果在规定范围内的部分有实际药效,超出规定范围外的部分又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则不得认定为本罪的假药。
三、提供假药罪中所谓“明知”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本罪的行为主体必须“明知”是假药而提供给他人使用,才能成立犯罪。在药品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常常以不知道涉案药品的性质作为辩护理由,但是依据司法推定规则,推定其为明知。[22]《药品解释》第十条列举规定了认定生产、销售、提供假、劣药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行为人明知的几种情形。[16]应当说,司法解释的规定为司法实践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明知提供了指引。主观层面的内容往往难以认定,而《药品解释》的规定帮助司法机关明确了从客观事实推定主观认识的大致规则。
截至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尚无公开的提供假药罪判例。[17]提供假药罪与销售假药罪相比,其在行为上最大的特点仅在于“无偿”提供,而客观上的有偿、无偿与否与主观“明知”的认定并无关联,对这一内容的明确是本节讨论的前提。因此,在《药品解释》所规定的几种认定情形中,除第一项因涉及药品价格不适用于提供假药罪外,剩余几种情形对销售假药罪与提供假药罪同样适用。故本文大胆引用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既有判例展开分析。
(一)向不具有资质的生产者、销售者购买药品,且不能提供所售药品之合法有效的来历证明的
从条文中的“且”字表述可知,“向不具有资质的生产者、销售者购买药品”与“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来历证明”二者应同时具备,才能推定行为人对假药具有主观明知。司法实践中也多是采用这种认定方式。
案例一:被告人马某某通过互联网从秦某(另案处理)等人处,购买各类男性保健品,先后在山西晋城城区叶家小区、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租房,通过微信、阿某六号诚信店铺,以快递收货方式向全国各地销售。至2018 年3 月,累计销售人民币11 万余元人民币。被告人马某某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并不明知假药里含有西地那非成分,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故意。法院认为,被告人销售的产品系以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从不具有资质的生产者、销售者处购买,也不能提供保健品、药品合法有效的来历证明,可以证实其对所销售的产品中含有西地那非成分是明知的。[18]
案例二:被告人王某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向一位在路边推销性保健用品和药品的陌生人购买了两盒“金功夫”、八盒“蚁力神”、四盒“冬虫夏草”、四盒“硬到底”药品并进行销售。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明知其所购买无合法有效来源的产品疑似为假药的情况下,仍然将以上产品在其所经营的亚当情侣性保健用品店内向不特定的人员进行销售,行为人构成销售假药罪。[19]
由审判结果可知,在依据此项情形推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时,必须同时满足“向不具有资质的生产者、销售者购买药品”与“不能提供所售药品之合法有效的来历证明”两个条件。这主要是考虑到不具有资质的生产者、销售者也有销售具有合法有效来历的药品的可能,而刑法由于其处罚的严厉性,应尽可能地精确处罚范围与制裁对象,因此司法解释作了最完备的规定。同时,在上述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下,行为人应当对药品的性质有所警惕,若其未进行确证检验便实施生产、销售、提供行为,应当认定其至少具有构成药品犯罪的间接故意。
(二)逃避、抗拒监督检查的
如何理解“逃避、抗拒监督检查”,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逃避”“抗拒”的行为,《药品解释》尚未明确。我们可以通过刑法对其他罪名的类似规定以及既往司法判例窥知一二。
刑法在数个罪名中有类似规定,如走私废物罪中的“逃避海关监管”,逃避商检罪中的“逃避商品检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的“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中的“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等。从对走私废物罪和逃避商检罪罪状的解读中,可以得知所谓“逃避”,其实就是指将应当经过监管或检验的物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躲避的行为。[23]也即本罪中的“逃避”可相应解释为:将本应经过相关部门监督或检查的药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躲避,以求达到不受监督和检查目的的行为。对于“抗拒”行为,有学者指出,上述罪名中的抗拒行为均为行为人通过暴力等方式“千方百计阻止有关部门或人员的检查”。[24]同理,本罪中的“抗拒”也可作相同解释,即药品犯罪行为人通过各种方式阻止监督和检查。从关于这两种行为的以往规定中可以发现,虽然二者的目的均为规避监督检查,但在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逃避”是指一种较为被动的行为,通常与监督人、监察人不会起正面冲突;而“抗拒”的主体能动性较强,往往指正面对抗相关部门的监管,且或多或少含有暴力因素。
司法实践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两种行为。在“袁某销售假药案”中,公安机关等部门在对被告人袁某所经营的药房进行检查时,被告人为逃避检查,趁检查人员不备叫其父亲袁某某将尚未销售的“特效止咳定喘宁胶囊”960 余盒进行藏匿,企图逃避检查。[20]在“尹某生产、销售假药案”中,被告人尹某通过伪造虚假的药品来源以逃避检查。[21]在“陈某某等生产、销售假药案”中,被告人陈某某作为财务人员,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期间毁灭相关财务账目,阻碍侦查。[22]在“济南爱心医院等销售假药案”中,被告人李某乙为逃避检查,安排医务人员在书写处方签时,以不同中草药药方代替相关药品名称。[23]综合而言,“逃避”所指的方式多种多样,常见如通过藏匿、毁灭药品或相关原料、财物账目,伪造变造药品名单或名称等进行躲避。相对而言,“抗拒”行为所指则往往含有暴力因素。在“牛某、刘某生产、销售假药罪”中,民警出示工作证后,被告人牛某抗拒查处,强行驾车逃离,在逃离过程中撞上警车,其所驾车辆的倒车镜将警察右前臂刮伤,并剐蹭多辆在道路上行驶的其他车辆。[24]事实上,司法实践中鲜见实施“抗拒”监督检查行为的假药犯罪判例。也许是因为在假药犯罪中“逃避”行为的成效较大、风险较低,两相权衡,行为人往往更倾向于通过“逃避”的方式规避监督检查。
概言之,本罪中的“逃避”应解释为将本应经过相关部门监督或检查的药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躲避,常见如藏匿、毁灭药品或相关原料、财物账目,伪造变造药品名单或名称等。“抗拒”则指药品犯罪行为人通过含有一定暴力因素的方式阻止监督和检查。二者均为达到不受监督和检查的目的。
(三)转移、隐匿、销毁涉案药品、进销货记录的
此项推定主观明知情形的规定较为具体,无须作过多解释。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转移、隐匿、销毁涉案药品、进销货记录”与“逃避监督检查”往往无法明确区分。如在“吴某某生产假药案”中,在其他同伙人案发后,被告人吴某某为了逃避打击,将生产加工好的各种假冒品牌凉茶成品转移到其他仓库存储伺机销售。[25]可见,将药品、进销货进行转移、隐匿、销毁处理,往往也是一种常见的逃避监督检查的方式,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在司法认定中无须作明确区分。
(四)曾因实施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受过处罚,又实施同类行为的
事实上,这一要素并非首次规定。2014 年的药品犯罪司法解释曾将两年内实施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规定为假药犯罪的从重处罚情节。[26]但《药品解释》删除了这项从重处罚情节,取而代之的是将该要素增设为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客观证据。对于此项推定行为人明知的规定,需要予以明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受过处罚”是指受行政处罚还是刑罚处罚;二是,何为“同类行为”,需要满足何种条件的相同性才属同类行为。
本文认为,“受过处罚”包括因实施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规定的承继关系以及立法目的考虑,《药品解释》中的“受过处罚”应解释为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在药品解释修改前的司法实践中,曾经出现了同时将过往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受处罚的经历作为主观明知的推定证据和从重处罚情节的裁判。
案例三:被告人孙某某曾因犯生产、销售假药罪,于2018 年6 月26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8 年11 月25 日,被告人孙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来到唐山市路南区启新立交桥易中电子城铁道西侧摆地摊出售性药,公安民警发现并当场查扣待售的藏药伟哥老中医43 盒(10 粒/盒)、纯爷们第二代31 盒(8 粒/盒)、野狼王增大型2 盒(10 粒/盒)、虫草延时片1盒(10粒/盒)、虫草阴茎王1盒(10粒/盒)、德国魔棒1 盒(8 粒/盒)。以上药品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中标示了疾病的治疗作用、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且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经认定,以上产品按假药论处。孙某某的辩护人曾提出被告人孙某某对假药危害认识不足,主观恶性较小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某在两年内曾因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刑事处罚且被人民法院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酌情对其从重处罚,且被告人孙某某应当认识到销售假药行为的危害性,故对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27]
在该案中,法院就将曾因实施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受过处罚同时作为主观明知的推定要素和从重处罚情形。这种裁判实际上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对于同一个客观事实,一方面作为主观罪过的推定要素,一方面又作为从重处罚情节,恐有重复处罚的嫌疑。也许正是基于对此原因的考虑,《药品解释》将这一情形从从重处罚中删去,而转为主观明知的推定情形。因此,综合规定的延续性和立法目的考虑,旧司法解释规定为“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药品解释》中的“受过处罚”也应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其二,通过文义解释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窥探出《药品解释》规定的真实含义。《药品解释》的规定虽然未明确指出“处罚”究竟为何种处罚,但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表述,也即,无论是曾因药品犯罪构成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均可作为推定行为人对假药犯罪有主观明知的要素。“处罚”应为对应前文违法、犯罪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统称。
其三,通过与药品犯罪极其相似的食品犯罪中有关主观明知的规定,可以进一步明确本罪中“受过处罚”的含义。2021 年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具有因实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又实施同种行为情形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明知。[28]食品与药品犯罪在对象、行为方式等各方面均有较大共性,理论中也常将二者共同讨论。食品犯罪中同样规定了与药品犯罪相似的,以曾因实施食品犯罪受过处罚又实施同种行为认定主观明知,且明确处罚包括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对药品犯罪作相同解读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对于“同类行为”的认定,本文认为主要考察两个条件是否相同:第一,对象相同。即均为针对假药实施的犯罪。第二,行为类型相关。最明显例如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属于同一个选择性罪名,生产、销售、提供这几种行为方式联系紧密,在实践中常常相生相伴,实施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视为“同类行为”的范畴,不必限制前后行为均为生产或均为销售行为才属“同种行为”。司法实践中对生产、销售等相关行为在推定主观明知时也是做混同认定。
案例四:被告人金某曾因生产喜炎平针剂等假药于2010 年7 月16 日被河南省新乡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后自2010年以来,被告人金某为牟利通过网络以每板六元价格购进假药喜炎平注射针剂,多次销售给被告人吴某。被告人吴某明知从金某处购进的喜炎平注射液系假药,为牟利仍多次销售给张某甲(另案处理)等人。法院认为,被告人金某曾因生产假药被判处刑罚,在本案中系明知是假药而予以销售,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同时,被告人金某曾因生产假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对其从重处罚。[29]
本案中被告人曾因生产假药受过处罚的事实成为本案认定具有销售假药罪的明知的要素。可见,只要行为对象均为假药,前后行为仅需相关,无需完全一致,即可认定主观明知。但需要注意的是,妨害药品管理秩序行为与生产、销售、提供假药行为则不得视为“同类行为”,因为妨害行为涉及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对象非常多样,且更多关注对制度的违反,与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的行为差距较大。
综上,此项认定药品犯罪行为人明知的情形,其含义是曾因实施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又实施对象相同、行为类型相关的同类行为的,就可认定具有本罪所要求的“明知”要素。
四、提供假药罪的其他问题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问题外,提供假药罪在司法层面还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本罪认定的问题。例如,本罪条文表述为行为主体明知是假药而“提供给他人使用”,其中,“提供”与“使用”的关系为何,“使用”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又如,“无偿提供”的具体含义为何,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与销售假药罪中的“销售”进行区分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出于全面性的考虑,本文一并做简要分析。
(一)提供假药罪中的所谓“使用”
本文认为,提供假药罪中的“使用”是指提供人的行为目的是提供给他人使用,且“使用”仅指直接药用,即为了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或调解生理机能而使用。有学者认为,提供假药罪罪状表述中的“提供给他人使用”包括两个行为,一是提供,二是使用,后者指对患者等对象使用药品的行为。[25]甚至有学者将提供假药罪的立法目的解读为遏制药品使用单位的人员“使用”假药的行为,认为由于《药品管理法》规定,用药单位使用假药的按照销售假药的相关规定处罚,[30]新修正案对本罪的规定实际是为了使行政法与刑法在使用假药的问题上顺畅衔接。[26]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一方面,提供假药行为的重点应在“提供”而非使用,[27]用药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仅需提供假药给他人,至于是直接为他人使用或是第三人自己使用对本罪保护法益的侵害没有差别,对本罪的成立也并无影响。另一方面,过度解读“使用”实为对法律规定的误读。《药品管理法》中对使用假药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医疗过程中“有偿使用”行为的规制,相关司法解释本就将“有偿使用”认定为销售假药,但《药品解释》已明确规定本罪的提供为“无偿提供”,此时对使用的含义应作不同理解。
另外,提供假药罪中的“使用”应当限缩为直接用于人体药用。有学者认为,即使利用的是药品的交换、加工价值等使用行为,事实上也促进了缺陷药品的流通,对公众的人身法益产生威胁,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制,这种观点有待商榷。[28]用于后续销售或者再生产等目的的,不能认定为本罪中的“使用”,若行为人明知第三人将药品用于销售或者再生产仍为其提供,应按销售假药罪或生产假药罪的共犯处理。
(二)提供假药罪中的所谓“无偿提供”
在《药品解释》发布前,有学者认为本罪中的“提供”是将原司法解释对“销售”的扩张解释进行确认,并非增加了新的行为方式,“提供”与“生产、销售”一样隐含着“对价”“有偿”的概念。[29]也有学者认为,本罪中的提供使用行为,包括有偿和无偿两种形式。[30]《药品解释》对此明确,本罪中的“提供”是指行为主体明知是假药而“无偿提供”给他人使用。[31]但“无偿提供”的具体含义为何,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与作为“销售”行为的有偿提供区分,尚未可知。在民法意义上,“无偿”是指“不以相对人给付对价为条件”。[31]对于“无偿”的内涵,刑法与民法可取相同的含义。《药品解释》规定中的“无偿”也应以是否支付对价作为界分标准。[32]同时本文主张,无需相对人给付对价并非指相对人未给付足额对价,而是用药人从未就药品使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提供行为实施给付行为。另外,对提供假药罪的“无偿”需作实质判断,以用药人是否实质存在给付行为为判断标准。在司法认定中,需将形似无偿、实为有偿的销售行为予以排除。
案例五:2014年9月,被告人林某某在台州市椒江区开设了薇妮莎美容会所,经营美容服务、化妆品销售。2017年上半年,林某某通过淘宝购买了麻舒痛乳膏、DERMALCAIN、J-CAINcream(LIDOCAINE)等具有麻醉止痛的药品,后在该美容会所为王某、丁某等顾客做“黑脸娃娃”等美容项目时,使用上述麻膏缓解疼痛,后该美容会所被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获,林某某被抓获,另扣押了外包装盒上均未标注药品批准文号的麻舒痛乳膏、DERMALCAI 等假药。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林某某仅是单纯的购入麻膏,后在做“黑脸娃娃”美容项目中使用该麻膏,该麻膏是无偿使用的,未单独计价,不是销售行为。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某以营利为目的从事“黑脸娃娃”美容项目,使用麻醉药品是该美容项目服务的一部分,应当认定为销售行为。[32]
类似上述案例中的配套销售,或者看似赠送实则将金额计入交易总额的行为,实质为“有偿提供”,而非“无偿提供”行为。一般而言,“无偿”应限于完全赠与的方式,若随着实践的发展有其他行为方式也可进行补充。[33]
五、结语
提供假药罪的增设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药品安全治理体系,为严密打击药品犯罪的法网提供了有效助力。但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只有对其中的要件进行充分解读,对存在的疑难问题予以积极回应,才能避免法律被束之高阁,最终实现立法目的。本文对提供假药罪存在的主体不清、假药认定标准不明、主观明知推定认识不足等直接影响犯罪成立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全文所述,提供假药罪的主体为持续或临时具有用药权限的单位以及该单位中具有药品管理使用权限的人员。提供假药罪中的“假药”应采实质认定标准,紧扣对个人法益的侵害予以认定,且应达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标准。对本罪主观明知的认定,应结合既往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对各项推定情形进行详细解读。此外,提供假药罪条文中的“使用”是指以提供给他人使用为目的,“使用”仅指直接药用。“无偿”指用药人不存在给付行为。
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
②[12][31]参见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
③参见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
④参见2022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条。
⑤参见2022年《湖北省药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⑥参见2021年《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第二条。
⑦参见2001年《关于执业药师资格(药品使用单位)认定申报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⑧参见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
⑨参见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
⑩[15]参见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
[11]参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
[1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
[1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16]参见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
[17]最后检索时间为2023年1月7日。
[18]参见(2019)苏0311刑初42号判决书。
[19]参见(2016)闽0421刑初149号判决书。
[20]参见(2013)贡井刑初字第41号判决书。
[21]参见(2017)闽0602刑初455号判决书。
[22]参见(2015)嘉秀刑初字第247号判决书。
[23]参见(2015)市刑初字第6号判决书。
[24]参见(2018)冀0109刑初372号判决书。
[25]参见(2019)粤0103刑初178号判决书。
[26]参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
[27]参见(2019)冀0202刑初60号判决书。
[28]参见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第五项。
[29]参见(2014)周刑初字第132号判决书。
[30]参见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32]参见(2018)浙1002刑初832号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