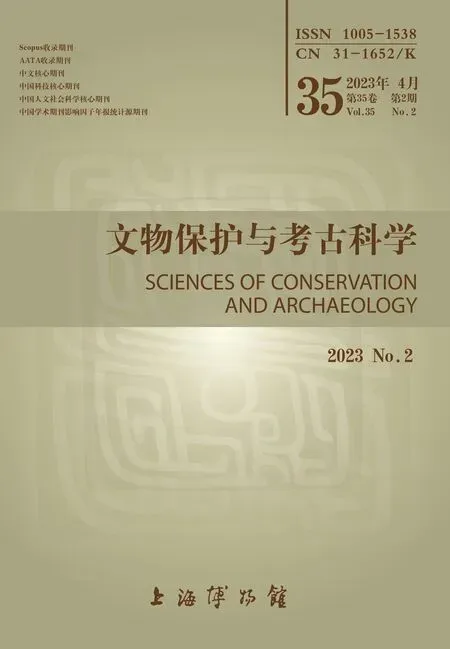红外相机技术在石窟寺与古建筑动物活动监测中的应用
2023-04-24武发思朱非清汪万福赵雪芬岳永强
陈 章,李 隆,武发思,朱非清,汪万福,赵雪芬,岳永强
[1. 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甘肃酒泉 736200;2. 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甘肃酒泉 736200;3. 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甘肃酒泉 736200;4. 甘肃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甘肃临夏 731100;5.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甘肃天水 741000]
0 引 言
生态研究通常需要观察动物活动及其行为,由于动物活动机敏、习性多样,人类无法在充分观察的情况下记录动物活动[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数码影像技术(如自动相机技术或红外相机技术(automated-camera monitoring technology或camera trapping)的发展,红外相机技术作为一种“非损伤性”的物种调查和记录技术,在近30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野生动物研究[2-3]。红外相机技术是指通过自动相机系统(如被动式/主动式红外触发相机或定时拍摄像机等)来获取野生动物图像数据(照片/视频),并通过这些图像来分析野生动物的物种分布、种群数量、行为和生境利用等重要信息[4-6]。目前,绝大多数国家自然保护区均使用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和评估[7-9]。文化遗产领域由于前期研究与历史数据的缺乏,许多文物赋存环境中野生动物活动与多样性状况尚未明晰,动物损害监测与防治研究工作进度迟缓,红外相机监测动物活动的应用更是凤毛麟角,仅见于个别遗产地[10]。
石窟寺和古建筑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证,保存有大量的古代壁画、彩塑、彩绘等文化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文化价值。这些遗产地大多营造在远离市区的偏僻地点或幽静山林中,极易成为鸟类、鼠类和蝙蝠等动物的天然栖息地或避难所,它们在壁画、彩塑等文物表面活动,造成文物本体的侵蚀破坏,长期以来成为威胁文物安全保存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国内、外文物保护工作者针对石窟寺与古建筑动物调查及损害方面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1-14],但动物损害监测与防治还存在诸多困难,具体表现为:1)许多野生动物具有隐蔽性强、活动范围广、机动灵活和主动扩散能力强等特点,无法获取其对文物本体损害的直接证据;2)部分动物有昼伏夜出的习性,夜间很难观察到实体,甚至很难发现痕迹;3)传统的利用肉眼、望远镜等监测手段面临工作人员无法近距离捕捉动物图像、工作强度大且效率低下的情况。因此,使用红外相机技术取代人工拍摄已成为当下遗产地动物监测研究的新途径。
本研究团队自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选取世界文化遗产地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和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苏州紫金庵作为研究对象(图1),将红外相机技术应用于4处遗产地进行动物活动监测,旨在掌握遗产地动物种群特征、活动节律以及为动物防治提供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图1 红外相机技术应用于四处文化遗产地Fig.1 Infrared camera technology applied to four cultural heritage
1 研究方法
1.1 红外相机布设
由于遗产地监测区域文物赋存环境特殊且动物活动范围较大,故采用随机布设法。2018年1月起,开始在遗产地监测点布设红外相机(表1),通过现场观察到的动物痕迹(如足印、食痕、抓痕、落羽、粪便、巢穴等),选择视野开阔前方且无障碍物遮挡的位置布设红外相机。同时记录每个位点的相机编号、布设时间、GPS位点等信息[15]。监测照片将记录每台相机的编号、位置坐标、海拔、相机周边微生境类型等信息[4]。22台红外相机共布设50个位点(表1),每个位点监测4个月左右后,进行电池更换和内存卡数据读取。根据遗产地所在区域的气候特征,四季划分为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月,冬季12月至翌年2月。

表1 各遗产地红外相机布设情况Table 1 Arrangement of infrared cameras at each heritage site
1.2 相机参数设置
使用千里拍(Bestguarder®SG-999V)红外相机,其拍照物理像素为1 200万,视频尺寸为1 080 P。相机参数设置为照片(3张连拍)或视频(30 s)模式,热红外(PIR)感应触发间隔为60 s,灵敏度设置为高。每次安装16节南孚5号无汞碱性电池。
1.3 数据收集
定期将内存卡照片数据按相机位点编号保存,删除相机视野中人为干扰(游客、工作人员)、光线变化、杂物等误拍照片,物种鉴定参考《中国鸟类野外手册》[16]、《中国哺乳动物图鉴》[17];物种分类参照《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18]、《中国哺乳动物多样性》(第2版)[19],如照片不清晰无法分辨物种时,则借助视频辅助鉴定。鉴定之后统计照片数,并将照片按照物种名称重新命名,便于日后查看和分析。
1.4 数据处理
从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剔除相机视野中人为(游客、工作人员)扰动、光线变化干扰等的无效照片,将获得22台红外相机的照片数据进行统计,包括拍摄日期和时间、动物种类、数量等。同一位点的红外相机在野外连续工作24 h为1个相机工作日,同一部相机在30 min内连续拍摄的同种动物照片只定义为该物种的1张独立有效照片(Independent effective photo)[20]。并将照片按兽类、鸟类进行归类统计。采用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index,RAI)作为评估动物物种种群相对数量的指标,计算公式[20]如下:
RAI=Ai/T×100
(1)
式中,Ai为第i种动物出现的独立有效照片数;T为总的相机工作日,即所有相机位点正常工作累计的捕获日。
比较4处遗产地相对多度指数排名首位的物种(优势物种)数据,以月相对多度指数(Monthly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MRAI)和季节相对多度指数(Seasonal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SRAI),分析4种优势物种的月份和季度活动节律:
MRAI=Mi/Ti×100
(2)
SRAI=Nj/Tj×100
(3)
式中,Mi为第i月(i=1~12)4种优势物种的独立有效照片数;Nj为该季节(j=春、夏、秋、冬)4种优势物种的总独立有效照片数;Ti为第i月红外相机工作日;Tj为第j季红外相机工作日。为方便分析物种日活动规律,将某一动物大多数时间在夜间活动,定义为夜行性动物。将一天以每2 h为单位划分为06∶00~08∶00、08∶00~10∶00、10∶00~12∶00等12个时间段[21],日活动节律采用日活动强度指数(Daily activity index,DAI)表示,定义如下[22]计算公式:
DAI=Nij/Ni×100
式中,Nij为第i种(i=1~4)动物出现在第j个时间段(j=1~12)内的独立有效照片数;Ni为第i种动物的独立有效照片总数[23]。
采用Excel 2016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制图采用Origin 2017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1 兽类和鸟类物种组成
2018年1月至2021年6月,4处遗产地22台相机累积工作日9 463 d,其中,莫高窟相机累积工作日2 473 d,炳灵寺石窟相机累积工作日4 199 d,麦积山石窟累积工作日2 122 d,紫金庵相机累积工作日669 d。共获得鸟类独立有效照片7 596张(表2、图2),隶属于3目8科9种,包括6种雀形目鸟类,占鸟类总物种数的66.67%;鸽形目2种,占鸟类总物种数的22.22%;啄木鸟目1种。共获得兽类独立有效照片3 350张,隶属于3目5科9种,包括7种啮齿目动物,占兽类总物种数的62.45%,劳亚食虫目、兔形目各1种。

表2 基于红外相机监测下的各遗产地动物名录Table 2 Animal list of each heritage site monitored with infrared cameras

(续表2)
2.2 物种多度指数
在红外相机记录的18种野生动物中,各遗产地RAI排名首位的鸟类分别是:[树]麻雀(RAI=11.56,莫高窟)、岩鸽(RAI=75.99,炳灵寺石窟)、北红尾鸲(RAI=10.27,麦积山石窟),3种鸟类的独立有效照片数共计3 695张,占鸟类独立有效照片总数的48.64%。相机位点出现率较高的鸟类是岩鸽(16个位点)、原鸽(12个位点)、北红尾鸲(8个位点)。岩鸽、原鸽、[树]麻雀存在集群活动情况,最大数量分别是34只、21只和10只,3只以上独立照片分别为712张、565张、78张。
各遗产地RAI排名首位的兽类分别是:大沙鼠(RAI=35.75,莫高窟)、岩松鼠(RAI=43.17,麦积山石窟)、珀氏长吻松鼠(RAI=43.65,紫金庵),3种兽类的独立有效照片数共计2 092张,占兽类独立有效照片总数的62.44%。相机位点出现率的兽类是岩松鼠(7个位点)、大沙鼠(5个位点)、复齿鼯鼠(4个位点)。统计兽类照片时发现,珀氏长吻松鼠、褐家鼠均具有集群现象,最大数量分别是8只、6只,3只以上独立照片分别为98张与135张。
2.3 优势物种的活动节律
季节相对多度指数SRAI研究结果表明,每年随着温度变化和季节性交替,4种优势物种活动频率均表现为夏季达到最高,冬季最低(图3)。月相对多度指数MRAI结果显示,每年1月活动频率最低,8月活动频率最高,6~7月为活动频率增长期,9~12月为活动频率下降期,2~5月相对稳定(图3)。

图3 遗产地4种优势物种的年活动格局Fig.3 Annual activity pattern of four dominant species at the heritage sites
对4种优势物种日活动节律统计发现,岩鸽、大沙鼠、岩松鼠均表现出典型的昼行性特征,大沙鼠活动曲线呈双峰型,日活动最高峰期为08∶00~10∶00,岩鸽与岩松鼠日活动高峰期均为10∶00~12∶00,岩松鼠在高峰期后12∶00~18∶00保持持续性活跃状态。珀氏长吻松鼠大部分活动时间在晚上,为夜行性动物,日活动高峰期在02∶00~04∶00(图4)。具有夜行性的动物还有:复齿鼯鼠、三趾跳鼠、五趾跳鼠、褐家鼠、大耳猬。蒙古兔为昼夜都能活动,但晨昏活动更为频繁。

图4 遗产地4种优势物种的日活动节律Fig.4 Daily activity rhythms of four dominant species at the heritage sites
2.4 动物物种的危害现状
红外相机照片可记录动物在遗产地的分布、种类、数量、活动轨迹等信息。结合现场现状调查发现,动物活动已严重威胁到遗产地文物安全和赋存环境(图5)。鸟类对文物的危害形式主要包括:1)文物表面造成抓痕;2)筑巢;3)粪便污染腐蚀文物画面,其中的某些物质还可能与颜料发生化学反应。兽类对文物的危害形式主要有:1)鼠类打洞造成文物本体空鼓、破损;2)鼠类活动抓损文物表面;3)粪便污染。
调查中还发现动物类群存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如莫高窟周边为地域开阔的荒漠生境,大沙鼠啃食梭梭(Haloxylonammodendron)、白刺(Nitrariatangutorum),破坏窟顶防沙麦草方格,大耳猬常取食沙生植物幼果、嫩芽等,造成防风固沙综合体系的破坏,影响莫高窟整体的文物赋存环境。
3 讨 论
本研究首次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监测遗产地动物活动,共拍摄到18种野生动物,隶属于6目13科,相较于国内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调查数据,物种数相对较低[24-25]。原因可能有:1)红外相机连续工作时间短,这与本研究监测区域有关,遗产地作为文化游览地,游客参观给相机监测带来了较大的人为干扰,人员流动中容易引起相机触发,电量耗费快,缩短了红外相机独立工作日;2)红外相机空间布局上未完全覆盖许多物种的核心分布区;3)许多物种在遗产地内的种群数量可能较少,不易被相机捕捉到;4)红外相机对小型兽类拍摄效果不佳,如本研究拍摄到的某些啮齿类动物,无法辨识到种。此次共监测到雀科、鹟科、鸦科、鹡鸰科等4种鸟类,占鸟类物种总数的44.45%,这表明红外相机可有效监测地栖性或半地栖性鸟类[26],但实际上非地栖性鸟类数量更多,而这些鸟类是否能被红外相机拍摄到具有偶然性。此外,通过照片分辨还可积累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性别、成幼等种群参数,对进一步研究这些物种的行为习性、种群变化、与遗产地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调查到岩松鼠物种多度指数(RAI=43.17),远高于河北太行山东坡南段(RAI=10.10)[27]、天津盘山风景名胜区(RAI=3.17)[28],蒙古兔物种相对多度指数(RAI=1.58)介于河北太行山东坡南段(RAI=3.49)[27]和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RAI=1.519)[29]之间,说明同一物种在不同地区的种群数量、活动区域等都存在明显差异,可能与调查区域内布设红外相机的数量、网格的大小以及人为干扰等有关[4]。4个优势物种年活动节律均表现为单峰型特征,夏季(7~9月)为活动高峰期,其次为秋季和春季,冬季最低,这与食物资源季节性分布不均[30]及气温变化有关[31]。日活动节律比较发现,本研究中岩松鼠日活动高峰期为10∶00~12∶00,稍晚于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08∶00~10∶00)和天津盘山风景名胜区(07∶00~08∶00),岩鸽的日活动高峰为10∶00~12∶00,早于内蒙古民航机场岩鸽活动(14∶00~16∶00),说明动物活动节律与所处环境息息相关,取决于该物种所在环境中的地形地貌、植被、食物和人为活动等因素[30-32]。
动物活动是影响遗产地文物及赋存环境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国内、外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展了大量的文物有害动物调查工作[33-35],涉及石窟寺与古代壁画、土遗址、馆藏等多种文物类型。如柴长宏等对麦积山石窟及周边环境有害生物进行了系统调查,危害动物为72种,隶属于2界4门6纲12目39科59属,鼯鼠、松鼠、蜂类的危害最为严重[36]。仝艳锋等调查发现,济南华阳宫壁画的有害动物主要以鸟类、壁虎类和蛇类为主[37]。但这些调查均借助于传统的肉眼观察、数码相机拍摄等方式,对于一些活动隐蔽、难以跟踪的夜行性动物类群(如鼠类、兔类、蝙蝠等),无法完成全天候的实时监测,只有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实现动物实体影像资料及活动特征有效记录,便于掌握动物实时活动节律与轨迹,为评估其对文物危害程度及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提供重要依据。
根据红外相机监测发现,危害文物的主要动物类群为鸟类与鼠类,结合其活动特征的前期研究结果,基于石窟寺与古建筑文物安全、赋存环境、美观度等因素,建议从主动预防和被动防治两方面开展针对性的防治对策:
1) “声光电”技术驱赶。超声波会对特定范围内的动物听觉神经系统产生干扰和刺激,使其对超过100 db的声压感到不适,进而放弃食物、水和隐藏之处后不断迁移[12,38]。智能语音灯光驱逐装置可结合闪光、喇叭声或天敌声音恐吓等方式,从视觉和听觉上达到驱逐目的[39]。虽然这种技术短期内对于动物驱逐能达到一定作用[40-41],不过由于这种人造超声较为“机械”,与动物自身发出的厌恶超声相比过于简单且在声波特征上有所不同,对动物而言只是超声噪音,长期效果如何?长期使用是否会产生适应性?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2) 活动环境恶化。借助动物驱逐剂有效成分缓慢持久地释放,能影响动物三叉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的特殊气味,动物闻后产生躲避逃离反应,能有效减少动物栖息和筑巢现象[42-43]。由于凝胶的黏性作用,许多动物身体表面或羽毛、尾部粘附凝胶,存在带到文物表面或对赋存环境构成风险[44],因此驱逐剂的使用需保证与文物间的距离。
3) 人工封堵。红外相机监测发现,洞窟孔洞、古建筑窗格及木质横梁等已成为动物进出的主要通道,因此通过排查石窟寺与古建筑存在的孔洞缝隙,架设不锈钢网屏障,以减少动物的自由进出。阻止病害动物接近文物环境是比较常用且有效的方法。有研究表明,石窟门窗安装纱网后,进入洞窟的昆虫数量可比安装前减少85%以上[45],架设不锈钢网可以在不破坏文物价值和美观度的情况下推广使用。未来动物防治或将逐渐向特定区域内多种措施综合使用发展,形成点面结合、空间互补的综合防治体系,文物保护领域的动物防治才更具科学性。
4 结 论
本研究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1) 本研究共监测和鉴定到鸟类3目8科9种,哺乳类3目5科9种;根据相对多度指数(RAI)确定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和苏州紫金庵典型优势物种分别为:大沙鼠(Rhombomysopimus)(RAI:35.75)、岩鸽(Columbarupestris)(RAI:75.99)、岩松鼠(Sciurotamiasdavidianus)(RAI:43.17)和珀氏长吻松鼠(Dremomyspernyi)(RAI:43.65);
2) 4种优势物种均表现为夏季活动频率最高,冬季最低;月活动节律为1月最低,8月最高,2~5月相对稳定;日活动节律显示,岩鸽、大沙鼠、岩松鼠为昼行性动物,珀氏长吻松鼠为夜行性动物;大沙鼠呈双峰型活动曲线,日活动最高峰期为8∶00~10∶00,岩鸽与岩松鼠均为10∶00~12∶00,珀氏长吻松鼠为2∶00~4∶00。
3) 红外监测结合现场现状调查发现,鸟类主要通过抓伤、筑巢、粪便污染等形式危害文物,兽类常通过打洞、抓损及粪便污染形式对文物造成威胁;建议基于监测数据,探索使用“声光电”技术驱赶、活动环境恶化、人工封堵等措施并评估防治效果,科学防控以降低动物活动对文物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