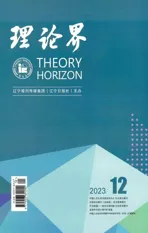论康德许可法则的独立地位及其授权
2023-04-17韦罕琳
韦罕琳
许可法则在康德的法哲学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实践理性的公设,它的角色在于在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选择(Willkür)的客体之间形成某种特定关系,由此来拓展实践理性的应用范围。但关于许可法则的授权性质及独立性地位存在诸多解释分歧。解释分歧产生的原因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和《永久和平论》中关于许可的不同表述。对此主要存在三种解释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许可法则在道德上是中立的(moralische indifferent),因而它的立法属于自然法,但并不属于伦理学,因而并不属于禁止性法则,由此二者在《永久和平论》和《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概念就可以保持一致;但如果《道德形而上学》的体系同时包含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那么许可法则也属于伦理学。〔1〕第二种观点认为《道德形而上学》中的许可性法则的定义是对《永久和平论》中的定义的修正,许可性法则作为“纯然许可的”(bloß erlaubt)是授权性规范(power-conferring norm),〔2〕而《永久和平论》中的许可所指的仅仅是“被允许的”(erlaubt),〔3〕它与“被禁止的”相对应。〔4〕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康德对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利的区分来进行认定,并且认为公共权利的状态是对许可法则的保障,使不法状态顺利地过渡到法权状态;在《永久和平论》中的许可法则所适用的是公共权利,而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许可法则适用的是私人权利;在许可法则的授权属性方面二者具有一致性,但二者涉及不同的行为者和行为种类;此外就禁止和许可而言,在时间上二者所指向的行为也有所区别,一方面,前者指向将来的行为,而后者指向当前的行为,〔5〕另一方面,根据二者在《永久和平论》中的表述,它们并不能同时发生。〔6〕本文将从第二种解释出发,通过对许可法则的授权内容和方式的强调,提供对于许可法则的地位与性质的一种新的解释,即根据其特有的规范对象和方式,许可法则是一种独立的规范,且它的授权需要主体间的同意的限制。
一、作为例外的许可
法权的概念所关涉的是人格与人格之间外在的实践关系以及不同权利主体的选择(Willkür)之间的关系,因而在许可法则的规范结构中存在两种关系,即主体与外在客体的关系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为探明这两种关系,首先需要考察许可法则中的“许可”的含义,其次是许可法则所规范的对象的适法性。在《道德形而上学》出版之前的著作中,有关许可法则的主要论述出现在《永久和平论》第一章的一个备受争议的注释中。其中康德区分了三种法则,即规制法则(leges praeceptivae)、禁 止 法 则(leges prohibitivae)和 许 可 法 则 (leges permissivae),并且在它们的关系中界定许可法则:
但现在,在许可法则中,所预设的禁止仅仅关涉一种法权未来的获取方式(例如通过遗产),但对这种禁止的豁免,亦即许可,却关涉当前的占有状态……我只想提醒自然法权的教师们注意一种lex permissiva[许可法则]的概念,理性使它呈现于其系统的区分中,尤其是因为在民法(法定的民法)中,经常使用许可法则,但伴有如下区别,禁止法则独自成立,且许可不被当作限制条件(如其应当那样)纳入那个法则,而是被投入此法则的例外之中。〔7〕
康德将许可作为禁止的豁免,将许可法则作为禁止法则的例外。因而,原则上为法权所规范的行为要么是被要求的,要么是被禁止的。基于一定的理由,允许豁免某些应当适用禁止法则的行为或情形。但康德在此注释中对于许可法则的限定并不意味着它被区分为私法上的许可和公法上的许可,而是一般地讨论许可法则在法权规范体系中的定位及其依附地位。如果此注释所讨论的许可只适用于公法,那么注释的第二段不应当在民法的范围内阐述禁止法则与许可法则关系。
维吉兰提尤斯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讲座笔记》也表达了这种例外的和一般性的立场。笔记中对于法权法则的区分更为详细,不仅从规范对象的角度,而且也从禁止法则的分类的角度严格限定许可法则的地位和适用范围。人的行为被认定为自由的,是因为它们立于道德法则之下,这个联结表明行为的善与恶。据此笔记采用一种三分法来描述自由行为的种类,即善的行为、非善的行为和中性的行为(adiaphoron)。〔8〕行为的善被区分为积极的善和消极的善。前者表明行为符合特定的法则义务(leges obligantes),后者表明行为不与义务的法则冲突,且既不是恶的也不是积极意义上善的,即消极意义上善的,中性的行为归属此列。由此笔记认为许可法则所规范的是不违反法则的所有行为。认定的理由在于若非例外,那么所有的行为要么是合法的要么是不合法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合法行为都被规制法则与禁止法则涵摄。但是它们同时又是自由的行为,这意味着中性的行为也应当具有规范它们的法则。
然而,笔记对禁止法则的区分因为一对形容词而变得模糊,即“universales”和“generales”。这两个拉丁文形容词都有“普遍的、一般的”含义。“universales”意义上的禁止法则拒绝任何例外,“generales”意义上的禁止法则允许某些情形成为适用禁止法则的例外:
但是有些禁止法则是绝对的(universales),在所有的情形下都有效,因此,任何例外都是不可能的且在这里也根本不考虑许可法则;其他的是一般的(generales),即在绝大部分案例中(一般意义上)禁止是善的。这里,诸例外是可设想的,且与它们有关的法则是:不被禁止的就是本身被许可的,即行为不是被要求的或被禁止的,而是一种放弃。〔9〕
根据笔记对它们的解释,本文将“universales”意义上的禁止法则解释为绝对的禁止法则,将“generales”意义上的禁止法则解释为相对的禁止法则。后者在一定的条件下承认许可为其例外。笔记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例外。第一个例子是允许某种强力成为禁止法则的例外。在自然状态中,也就是在权利被建构之前,并无权利存在,因而这时需要某种强力将所有人带入公民状态。第二个例子是保存生命或紧急避险。若某物对于任意两人的生命保存至关重要,且此二人皆未占有此物,在自我保存的自然冲动的刺激下,二人不可能按照普遍法则而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许可他们彼此拥有强制对方的权利,由此构造一个保存生命的权利。〔10〕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强力可以构成禁止法则的某种例外,此时的准则符合许可法则。
笔记在对许可法则的限定上与《永久和平论》中的限定有所不同,它们的区别在于对例外的限定。笔记一方面通过对自由行为的区分划定了许可法则的一般的适用范围和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许可法则并不被当作禁止法则的例外。通过对禁止法则的分类,笔记将例外限定在相对的禁止法则的特定情形中,这在《永久和平论》中并没有得到体现。但这两种对许可法则的处理并没有显明许可法则也是对行为课以义务的法则。虽然笔记为许可法则提供了其特有的行为规范领域,但是中性行为如何与义务发生关系,许可的行为如何是义务的行为?这个问题没有在笔记中被解决。相对的禁止法则虽然允许某种例外,但这并非取消禁止法则的普遍法则地位,而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允许例外。就此而言,这种许可的含义与《永久和平论》相同。但这只不过是禁止法则的豁免,这种许可的规范效力并不依赖许可法则本身的规范效力,而是依赖禁止法则的规范效力。
二、许可法则作为实践理性的一种独立规范
《永久和平论》中的许可虽然被当作禁止法则的例外,但这样的许可也可能是被要求的许可。《道德形而上学》中的许可指的是“既不被要求也不被禁止”。〔11〕因此,鲁施卡认为关于许可法则的主流解释,即例外论,错误地使《法权论》中的许可依赖先前作品中的许可,尤其是《永久和平论》中的许可。〔12〕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永久和平论》中的许可所指的是哪种类型的许可,这从文本来看是不清楚的。《法权论》澄清了这个问题,且具有如下意义。首先,通过“被要求”的许可和“既不被禁止也不被要求”的许可的区分,可以限定许可法则的适用范围和规范对象。其次,根据许可法则所规范的对象之独特性方面,此区分暗示了许可法则具有独立地位的可能性。最后,这种区分显示了许可法则与其他两种法则在规范方式上的区别。
某种不违背义务且既不被禁止也不被要求的行为是许可的行为,即纯然许可的(bloß erlaubt)。〔13〕虽然此定义确定了许可并非禁止的例外,但是它还不足以确定许可法则是一种独立的法则。原因有二:第一,许可的行为是不违背义务的行为(licitum),这种行为是自由的行为,因为它是一种不受相反命令式限制的授权,即一种道德能力(facultas moralis)。〔14〕但如果其中的义务指的是禁止法则和规制法则的义务,那么许可法则难逃例外论的命运,即使“不受相反命令式的限制”也可能表示某种豁免,这种权限也可能指禁止法则或规制法则的某种授权;如果它们指的是许可法则的义务,那么从这个消极的定义中并不能发现许可法则的义务和其课以义务的方式。第二,既不被禁止也不被要求的行为被等同于道德上中性的行为(indifferens, adiaphoron, res merae facultatis)。〔15〕但一方面中性行为在道德上是无关紧要的,另一方面许可法则不是自然的法则,而是道德的法则。那么,许可法则作为一种道德法则是否可以对道德上无关紧要的行为课以义务?此问题直接与许可法则的独立法则地位相关,因为如果许可法则不能对这样的行为课以义务,那么行为人可以直接凭借他的喜好来决定其行为,并且它们只受禁止法则和规制法则的约束。若要确立许可法则的独立地位,仅从“既不被禁止也不被要求”这个方面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确定“不违背义务”的含义。对此含义的确定依赖许可法则的规范方式与授权内容的独特性。
除了上述对许可以及许可法则进行界定外,在《法权论》中,许可法则被提升到实践理性的公设的地位:
1.把我的选择的任何对象都当作客观上可能是“我的”或“你的”来看待和对待。〔16〕
2.如此对待他人是一个法权义务,即外在的(可使用的)东西也能够成为任何一个人的“他的”。〔17〕
康德把表述1 称为实践理性的许可法则,它给予我们一种权限,即把义务强加给所有其他人的权限(Befugnis),权限的内容是强制他人放弃使用我们选择的某些对象。〔18〕鲁施卡将此权限等同于预备概念中的道德能力(facultas moralis)。道德能力区别于物理能力(facultas physica),后者指的是在物理上可能的移动。同样,道德能力也被区分为道德上必然的和道德上偶然的,前者指的是被要求的许可,后者近似于“纯然的许可”。所以,道德能力就是指某人可以做许可法则所允许的事情的能力。〔19〕鲁施卡通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condominiums)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能力,即在关于此权利的法律被制定之前,我们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利。〔20〕此外,他还把道德能力中的“道德的 ”(moral)解 释 为 “理 智 的 ”(intelligible)。如果许可法则规范主体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不仅是主体与选择对象的关系,而且还是理智世界(intelligible world)中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感觉世界中发现某个主体占有某物,但许可法则所规范的内容不仅指这种事实上的占有,而且也包括理智的占有。〔21〕
许可法则不会使得选择的对象成为无主物(res nullius)。〔22〕所谓无主,意指它不可能成为任何人选择的对象,而非其被第一次占有之前的状态。但在这种情况下,许可法则并不是在授权,而是避免一切选择的对象成为无主物。也就是说,在物理上使用选择对象的方面并不存在绝对的禁止,否则外在的自由将与其自身矛盾。〔23〕许可法则的规范结构中并不包含选择与其对象的关系,因而更谈不上在它们之间有什么绝对的禁止法则。这与预备概念中对许可法则的规范对象相对应,即中性行为。许可法则与中性行为的规范关系仅仅表明主体的一种能力,即主体可以在物理上占有其选择对象的能力,它与禁止法则无关。这并非授权,也无须授权。
如果许可法则仅仅关涉主体对其选择对象的物理的或经验的占有,那么即使没有许可法则,我们也可发现选择的对象并非无主,主体以“归己”(appropriatio)意志占有选择的对象。〔24〕因此,许可法则作为一种授权的规范,授予主体物理的或经验的占有之外的另一种权限。许可法则所规范的只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符合康德对法权概念的说明,即法权概念意指选择之间的形式关系,而且也根本不考虑任何质料。〔25〕鲁施卡对所属关系的强调以及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举例,忽视了构成许可法则的真正内容,即在主体之间对相互课以义务的许可。康德不是通过所属关系来确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通过先行确定主体之间授权许可的范围和内容,来确定所属关系。
表述1与表述2首先都表达了一种相互关系,即选择的相互关系。因为许可法则的授权关涉其他主体,它所授予的权限必须在主体间存在。其次,许可法则不同于禁止法则与规制法则,它们可以独自从法权的普遍原则中分析出来。许可法则毕竟关涉选择的一个对象,尽管我们不考虑选择的质料,但我们无法从法权的普遍原则中找到这个对象。但它不是选择的公设,这意味着许可法则也应当符合实践理性的普遍法则的规范形式。这恰恰是授权的内容所体现的形式关系,即主体间相互强制的义务形式,虽然对此形式有一个范围的限定,即主体间可相互施加义务的范围,但是它同样符合法权的普遍性测试。主体之间就某物的处置可以相互课以义务,这种义务也应当是可普遍化的义务。表述1 所表达的是在每个可能的“我”和“你”的场合的直接关系,表述2从命令发布者的角度表达“我”与每一个可能的“他”的关系,许可法则授权内容中的义务在这些场合都成立。所以,许可法则的授权内容表明它课以义务的方式的独特性,即它间接地通过授权主体自身在他们相互之间课以义务。然而,它所施加的东西毕竟是义务,从这个角度看,许可法则也是普遍的法则,因而理性希望这个法则作为原理而生效,即作为实践理性而生效。〔26〕
三、许可法则的授权与同意的限制
通过许可法则的授权可知,它并不直接对主体课以义务,而是授权主体之间相互课以义务。这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限定了许可法则的适用范围。所以,许可法则所涉及的义务依赖主体之间对相互承担的义务的同意。莱利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其政治哲学的基础,道德的至高无上表明政治与公共法律正义创设了消极自由的支持环境,依据消极自由,任何人基于将会产生适当的外在行为的动机而遵守为理性所命令的义务,因而“政治义务”并不依赖同意,客观的道德法则是义务的最终原因,至少只要涉及外在的行为,政治不仅为客观的道德法则创造了环境,而且它也执行部分的道德法则。〔27〕这似乎表明,不论是禁止法则与规制法则还是许可法则,只要它们都是普遍的道德法则,那么它们所规定的义务都是以客观的道德法则为最终基础。但莱利在义务方面对同意的排除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道德行为,客观的道德法则并不能直接规范非道德的行为,例如单纯地喝牛奶的行为。对这种行为的道德评价依然具有一定的基础,即牛奶的所有人已经合法地占有此牛奶,此合法性不仅在于占有行为不违背普遍的外在自由的法则,而且主体之间已然拥有相互强制的权限。第二,许可法则涉及选择的一般外在对象,所以不能分析地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中推导出许可法则。康德将许可法则设定为实践理性的公设,按照许可法则的授权,主体之间相互施加的义务是主体本来没有的义务,这表明此类型的义务不是直接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中演绎出来的,相反这类义务的成立需要主体之间就相互负有的义务达成的同意。第三,禁止法则与规制法则直接对主体课以义务,这表明主体可以直接将它们作为强制自己(如对自己的义务)和他人的依据,而无需他人的同意。但许可法则若无其独特的授权内容,就外在之物的归属而言,主体之间也将不会有相互的义务。因而,一方面根据许可法则所规范的对象,存在某种类型的与道德行为无关的义务,另一方面根据许可法则的授权,这种类型的义务只能以主体之间的相互同意为基础。
根据许可法则的规范对象,主体之间可以相互强制道德上中性的行为,由此实践理性通过这个授权可以扩展到非道德行为。但许可法则本身并不能使这项义务成为现实,尚需其他条件使之在主体之间变为现实。通过许可法则授权的内容可知,这种义务只能在主体之间起作用,因而它本身并不指向主体与其自身的关系,而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某一单个主体而言,对此施加义务行为的授权依赖其他主体。康德认为,外在的和偶然的占有中的单方面的意志不能用作对每一个人的强制法则,因为这样的强制法则会损害以普遍法则为基础的自由。〔28〕除非主体之间相互同意放弃对他人占有之物的使用,否则这种义务只能建立在占有者的单边意志上,占有者成为对所有其他人的命令发布者。对这个命令发布者而言的许可法则,同时也是对所有其他人的禁止法则。这不仅与每个人以普遍法则为基础的外在自由冲突,而且也与普遍法则本身矛盾。许可法则的授权表明需要一个普遍的(allseitiger)意志以作为立法的意志,它也是先天必然联合的意志,〔29〕它并不能从主体的单边意志中被推导出来,因为它并不是某些主体相互同意的结果,而是普遍同意的结果,实践理性将这种普遍同意作为一个理念包含在先天联合的意志中。许可法则的授权在规范对象方面为这种普遍的同意划定了界限。
结语
许可法则因其特有的规范对象和规范方式而区别于禁止法则与规制法则,仅仅依据对相关概念的澄清并不能确立它的独立地位。许可法则涉及一般的选择对象,此对象的概念并不包含在普遍的自由法则中,所以康德将许可法则设定为实践理性的公设,将其作为生效的实践理性的法则,并且赋予其独特的规范方式,即授予主体之间相互施加义务的权限。这与禁止法则和规制法则直接施加义务不同,此授权表明一种间接施加义务的方式。许可法则的授权表明主体之间需要对此授权同意,它们与选择的对象有关。许可法则的授权暗示了在主体之间有一种作为理念的普遍同意。这种普遍同意不能从经验的偶然的单边意志中被推导出来,相反它可以构成一个作为外在立法的先天联合的意志。所以,当涉及选择的对象时,理智的占有和许可法则的授权都要求普遍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