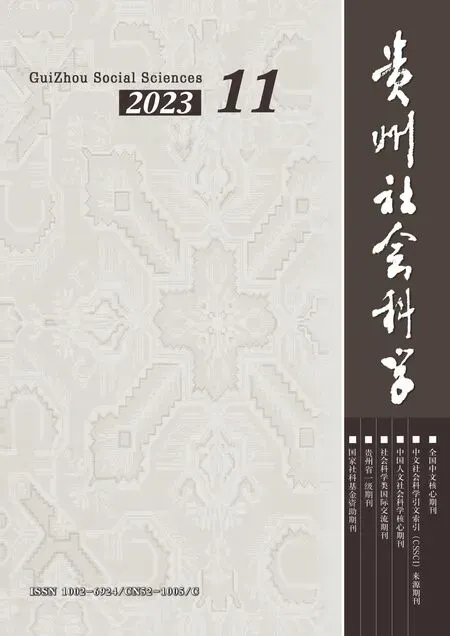古代部族社会的秩序及社会治理研究
——以西南地区方志材料为中心的考察
2023-04-17岳小国
岳小国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当下,“治理”研究已日益成为人文社科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议题,并“得到相关研究者的基本认同,成为国际学术界最为前沿的一门‘显学’”。[1]随着主流学界赋予“governance”(治理)以更丰富和宏观的理论意图,治理理论逐渐关联到地方(local)、社会(society)、次国家(sub-national)、国家(national)、全球(global)等诸多论域。[2]在我国古代史研究方面,也有学者对古代治理的含义及其变迁进行了梳理,并驳斥了当下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中国历史上只有统治而无治理,或者说统治就是治理,治理就是统治,并进而认为治理只是当代国家的产物,古代没有。[3]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在阶级对立还没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地区,主要依靠社会自治管理有限的公共事务。“越是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社会自治权越明显”。[4]我国西南地区古代部族的社会治理即属于此种情况。它比较贴近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关于社会治理的概括:“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从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5]鉴于此,本文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王朝国家控制力量比较薄弱的西南地区古代社会,社会治理的逻辑是怎样的,这些部族是如何活动于自己所统治的世界的里?
本研究中的西南地区古代社会主要包含两类群体:一是在元明清时期发展为土司者,即那些“原为土著之酋长,归顺中朝,因而予以秩官者”;[6]200二是既未被封建王朝直接统治,也未受土司管辖者。前一类如滇南建水纳楼土司、湘西施溶州田氏土官等,后一类如湘西、贵州等“苗疆”地区的一些族群。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以前封建王朝羁縻统治下的西南地方政权及部族中,所谓“国”,如夜郎古国,实际是酋长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地区,包括许多分散的、半独立的部族,不一定是完整的、统一的国家。此外,“关于西南夷地区的部落时代,历史文献的记载十分贫乏”。[7]因此,本研究主要选取西南地区方志、文献,以及中外民族志中有关部族社会生活及日常运行的一些记载,这些部族组织有一个共同特征:游离于中央王朝统治之外,换言之,王朝国家对其控制及影响较弱。
一、西南地区早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古代西南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客观上型塑了与之相适应的地方秩序及社会治理方式。换言之,古代的社会治理既和自然因素有关,也和社会文化因素联系紧密。
(一)自然环境
西南地区以山地为主,历史上僻处荒隅,舟车罕至,一些区域长期与“汉土隔绝”,“不通声教者千余年”。[8]《宋史》中曾有描述:“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9]14171以云南为例,其“古在要荒之域,蛮夷居之”“族姓繁多”,并且“境域辽阔,山岭纵横,寒暑悬殊,交通不便,统驭深感困难”。[10]云南土官明显多于西南其他地区,这与当地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中央王朝统驭困难等因素不无关联。又如,东川位于滇黔川三省交界地,蛮夷所居,地方石山林立、溪峒深阻。乾隆朝《东川府志》将该地描述为:“内负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金沙绕其北,牛澜抱其东,危峦矗巘,重围迭拥,加以幽箐深林,蓊荟蔽塞。”[11]西南地区古代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计和生活。清代的辰州地处湘西深山之中,土地贫瘠,生产技术落后。根据地方志文献记载:“辰地山多田少,农民刀耕火种。方春,砍杂树举火燔之,名曰剁畲,火熄乃播种,其田收获恒倍,然亦不能尽。然自始耕至秋成,鲜片刻之暇……高坡侧壤,广植荞麦、苞谷诸杂粮,虽悬崖之间亦种之……冬则伐山、渔水。岁稍歉,则入山采蕨、挖葛根漉粉以充食”。[12]由此可见,西南山地生存环境艰苦,人们需根据土质、地貌状况合理安排植种、农时及采集活动,以保障其正常生活的需要。
历史上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常常影响到民众(尤其是外来者)的健康与安全。清道光朝《广南府志》中记载:“广南列于烟瘴之地,则以寒暑不常、山水异性故也。近城数十里犹易调摄,若皈朝、剥隘、板蚌等地尤闷热,春夏有青草瘴,秋深有黄茅瘴,直至霜降后乃消。初起时有形如蝃蝀,人遇之,急伏地合口可免,闻其气香如糯饭,即罹其毒,大抵因七情六欲,劳苦饥寒,本体原虚,故邪气易入。”[13]诸如此类恶劣的烟瘴环境,“盗贼之所出没,瘴疠之所熏蒸也,难矣哉,倍蜀道矣”。[14]这些烟瘴之地盗贼出没,其通行难度甚至数倍于古蜀道。此外,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影响到官员赴当地履行管理之职。元宪宗四年(1254),朝廷命兀良哈台征降夷地,遂“各设土官,置金齿都元帅府领之。有所督,委官入其地,交春即还,避瘴气也”。[15]50-51可见,古代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时常威胁到人们的生命。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类环境也形塑了当地剽悍的民风,并对民众与外界交流构成了巨大障碍。直至明代,散居湖广地区山谷之间的土民,仍性耐苦寒,其俗“居常则渔猎腥膻,刀耕火种为食,不识文字,刻木为契,短裙椎髻,常带刀弩为威”。[16]生活在湘西山地的苗民,尤善锻铁为刀剑,操木为弓弩,出入每喜佩刀携枪,性格非常勇悍。
(二)社会环境
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孕育了当地特殊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当地族群多元及其文化差异性的特点。横断山区由于沟谷纵横,普遍形成了以河流或以“沟”(即山谷)为单位的沟域文化带。“沟”在当地不仅是一个人群系统及文化单元,也是一个语言单元。“高山峡谷地貌不仅造成地形的险峻、破碎,也带来了地形的阻隔性和分散性”,由此造成了“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甚至两个相邻的沟即便语言相同,“在口音和习俗上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17]举例说来,在横断山北部不仅有人口众多,操康方言的康巴藏族以及操安多方言的藏族人群,同时也包括木雅、嘉绒、扎巴、尔苏、多须等其他藏族人群支系。当地族群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在地方谚语中也有所体现:“一条沟,一种话,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一山一文,一沟一寺,一坝一节”。[18]概括地讲,西南地区这类人群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他们仍保留着自已独特的语言(或称“地脚话”);二是这些人群支系人口数量均不大。[19]与之相邻的苗山、瑶山地区的自然及社会环境则为:万山岪蔚,高凌霄汉,幽深险阻,迥绝人寰。由此也造成了“其人不但与汉族断绝往来,即其同类蛮族,相距略遥,亦即不相闻问。是以同一苗人,而风气各殊,同一瑶人,而言服互异。甚至望衡对宇,亦风习语言各异”。[6]115险恶的地理环境阻隔了当地族群与外界的交流往来,同时也形成了苗、瑶群体内部习俗上的差异。其实,关于这类现象,早期的历史文献中也有记载或关注。成书于西汉前期的《史记》即对当时的西南夷状况进行了描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嶲”“昆明”等部落“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20]2991该文献资料充分展现了早期部族社会族群众多,居住分散,互为君长等典型特征。
西南地区贫瘠而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迥异于内地平原地区,被视为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地。为此,封建统治阶级及文人墨客还对该区域的部族人群使用了大量“污名化”的言辞及称谓,并给这些群体贴上了愚昧、落后、野蛮的标签。这一现象在各类方志文献中尤为突出:蛮夷在衣着、形体方面,“散居岩谷,无衣服,以木皮蔽体,形貌丑恶”;[21]95在心理与性格上,“蛮獠多诈而少实,负争而好斗”,[22]“其人贪忍居心,犬羊成性,是以抢夺劫杀视若泛长”,“多蠢悍贪暴,性情独异”,而且“叛服不常,劫掠成性”。由此,官府及文人墨客常警告人们,“林深蛮恶,不可轻至”。[23]151-153这些充满了蔑视与想象的记载也折射出西南部族社会同内地在组织结构、内部秩序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差异性。
二、古代部族社会的组织与结构
西南地区历史上曾存在过众多“蛮夷”王国或部族组织。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中,嶲、昆明部落“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20]2991这些部落大多为互不统属的“化外野蕃”。到了唐代,此类状况大体依旧,在滇西,“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四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24]43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相对偏远、交通闭塞的区域仍存在一定数量的部族组织。
(一)部族头人
部族组织多由酋长或头人领导,不同地区、族群对这些酋长的称谓有所不同。在湘西土家方言中,“官长曰冲,又曰送,又曰踵,又曰从。若吴着冲、惹巴冲、乐师冲,即吴着送、吴着从,云云”。[25]450《元史》《明史》中记载了一些部落首领、土司的土语名字,如湖广地区的散毛宣抚司墨来送、桑植荒溪诸洞墨色什用(“什用”即“送”的别音)、永顺宣慰司第十代土司彭福石冲等。《大定县志》中有关于贵州水西土酋、土官官制及称谓的记载,“夷书曰:君长曰蔺,称为苴穆,犹克汗、骠信也。大部曰穆濯,次曰骂裔、次曰奕续,通称为峨。其臣总号曰阿牧”。[26]不同族群对其头人的称谓各异,但这些头人在部族组织中的作用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部族组织的运行及管理中,酋长或头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政治、教化、化解日常纠纷等多方面影响着部族的生存和发展。《云南志略》中记载,“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21]89然而,酋长的权力通常不是世袭获得,而是源于其自然权威。这是由于管理体现为依赖权力的力量进行的活动,而酋长的管理权力由全体成员产生,其管理代表了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不惟如此,酋长的管理权亦非强制手段,是纯粹道德性质的、父亲般的。故而,酋长权力的作用主要依赖于权威的力量。[27]在王朝国家所能影响到的范围内,封建统治者有一套选立酋长的标准。宋嘉泰年间,湖南安抚使赵彦励曾奏请选立酋长,“湖南九郡皆通蛮夷,请择土豪有智勇、为人所信服者立为酋长,借补小官以镇抚之”。[25]439由此可见,智勇、为人信服系封建王朝认定的酋长标准。在民族学(志)材料中,也留下了大量与之相关鲜活的记载——这些相较我国古代西南地区,虽有时空差异,但仍具有较强的比较或参照价值。譬如,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的三岩部落中,每个“帕措”(即父系血缘组织)都有一个大头人,他们由公众推举产生,成为大头人的条件主要包括:体格健壮,械斗中有勇有谋,德高望重,并且口才出众。大头人还要经常参与谈判,处理帕措之间的仇杀或纠纷。[28]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认为,考察与对比头人作用的最佳方法,是将其权威分解为若干独立的功能范畴:法律事务、军事事务、经济事务、日常行政决策。在每个领域,头人通常都会扮演一个角色。[29]184-189这表明,部族社会头人的管理范围较宽,通常是一个“多面手”。然而,在一些部族组织中酋长或头人可能并非惟一重要的角色。贵州水西地区的部族由“君长”“部”“目”“臣”等重要职位构成。根据《万历实录》卷482记载,当地还有“四十八目,千五火头,九扯、九纵诸党”。在这方面,中外部族组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国外的民族志材料显示,在努尔人社会,除酋长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领导角色——“长老”(the elder),他们是地方风俗习惯方面的权威,凶杀争端中联合行动需要领导和建议时得听长老的,还有季节性的迁徙、在何处建立营地、主持婚礼,执行献祭等,长老的作用均不可或缺。同样是位于非洲的恩瓜托社会,行政村落的首领都是以前酋长的后裔——他们也被称作“王室头领”,在行政村内部,每个家族群体在长老的领导下管理自己的事情,但行政村所有事情均在头领的整体控制之下。[30]东南亚克钦人的“当权者”总是政权或教权的掌控者,在世俗方面,其可分为酋长和长老,在宗教方面,有各等级的祭司、占卜师、通灵者。其政教关系体现为,酋长事实上没有教权,然而他的权力却源于其在宗教中的角色;占卜师没有政治权力,然而,他却处在一个有相当政治影响的地位。[29]83
此外,西南部族组织大多存在一种重大事务集体协商的机制。在三岩藏族社会,事关帕措之间“偿命金”的谈判,涉事帕措所有成年男子均要参与。通常,对于一项有待解决的争论来说,只有在全体一致情况下,决定才能达成,因为参与的头人是双方讨论的人员。他们不断地进行谈判,都各抒己见,直到达成共识。[31]概而言之,上述部族社会在管理或运行方面存在一些共性特征:酋长的作用不可或缺,然而其内部也实行一定的“民主”程序。而且,正如下文将论及的,在一定范围内,社会控制的缺乏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弱化上。[32]
(二)部族内部的等级结构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演进,酋长之位由原来的众人推举逐渐转变为在其血亲氏族内部传承。而且,酋长世袭的观念逐渐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云南金齿百夷中,“酋长死,非其子孙自立者,众共击之”。[21]91而且,这一阶段的部族组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部已产生了等级观念。根据《蛮书》记载:弥诺国边海国也,“呼其君长为寿”,“王所居屋之中大柱,雕刻为文,饰以金银”,而“百姓皆楼居,披婆罗笼”。[24]231史料揭示该王国的社会结构不甚复杂,但王与百姓在地位上已有明显差别。此外,在《百夷传》中,关于不同族群间身份高低、贵贱差异的描述更为具体和周详。当地“所用多陶器,惟宣慰用金银玻璃,部酋间用金银酒器。凡部酋出,其器用、仆妾、财宝之类皆随之,从者千余,昼夜随所适,必作宴笑乐”,“凡生子,贵者浴于家,贱者浴于河,逾数日,授子于夫,仍服劳无倦。酋长妻数十,婢百余,不分妻妾,亦无妒忌”。[15]88-96由此可见,部族社会民众间身份和地位的高低体现在生活器物、婚宴习俗、育儿仪式等多个方面。上述部族内部已诞生了贫富、贵贱阶层,并且其组织结构开始趋于复杂化。在贵州乌撒地区政权组织中,作为管理阶层的土目可细分为多个层级:一是辅佐君长分理重要事务的大臣,如行政、军事、祭祀等方面;二是四大部首领,主要是按山脉对地域进行的划分;三是由四正四副组成的“八大土目”,四正主要为嫡出的四大首目,四副则由庶出者担任,并得到君主分封;四是“二十四属目”,他们由八大土目之庶出辈承担。此外,乌撒境内来自最基层的小土目,主要由八大土目、二十四属目的分支构成。这些群体虽属贵胄,但没有基层行政权力,可获得供衣食之用的田土。然而,他们之中一少部分也可能上升为“正宗”土目。[33]该部族组织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主改革时期。
(三)氏族大姓
部族组织大多由氏族大姓构成。根据相关资料记载,“西南蛮族多以族姓关系,集居同一地段。此种制度当然由古代宗法社会制度及部落制度之下遗传而来”,而且,蛮人族居组合之“势力较之汉系民族似尤伟大”。[6]65如巴蜀之向氏、冉氏、田氏、蒙氏、文氏、雷氏、叔孙氏,贵州之龙番、罗番、石番、方番、蒙番、程番、张番,滇之龙、傅、尹、董各姓,在历史上皆有所谓“七部”“七番”“四大姓”之称。又如,唐时的“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34]5280而松外蛮“尚数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凡数十姓,赵、杨、李、董为贵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长”。[35]6321这些集居蛮族有一个重要特点:“尝以一族占据百数十里之地,形成一种‘血系的部落’。”[6]65对此,《宋史》中亦有记载,“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喜险阻,善战斗。部族共一姓,虽各有君长,而风俗略同”。[9]14241该区域不同君长领导下的部族“共一姓”,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或有着血缘关系认同。这对地方秩序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封建统治者常利用“蛮夷”间的血缘关系对其进行统治。在清代,湘黔苗疆地区的治理之道即在于,“凡一寨之中,必择立诚实苗头一人。如两姓同寨,则每姓各一人。令其约束散苗,安静守法”。[36]
综合前文所述,在西南部族社会,血系关系、世袭制、等级制等紧密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当地历史上集族权、政权、兵权为一体的统治机构。在历史上,西南地区社会政治秩序不稳定,加上王朝力量影响较弱,作为社会组织的氏族大姓团体活动趋于活络,而元明清时期作为强宗大姓的土司即产生于这类部落组织。[37]
三、古代部族社会的习俗及日常秩序
西南地区古代部族社会的外婚制、鬼巫信仰,以及礼教缺失等是其社会生活中的几个显著特点。
(一)婚俗与信仰
历史上,西南地区部族间多实行外婚制,同一部族内部严禁通婚。如唐代的“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娅”。[24]96族外婚为部族间联合、结盟,抵抗外来威胁创造了有利条件。部族内部巫术盛行,人们普遍畏惧鬼神。“其俗不祀先,不奉佛,亦无僧道。”[15]98《新唐书·南蛮传》云:“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在蜀地,人们认为水中有水神,它可使人患染疾病。邛都县“余多恶水,水神护之,不可污秽及沈乱发,照面则使人被恶疾,一郡通云然”。[38]311因水神存在,人们不敢污染河水,甚至认为河水照面也会沾染恶疾。《百夷传》中对云南及周边区域百夷群体的相关风俗也有记载:“征战及造作用事,遇日月食则罢之,毁之”,其俗,“不祀先,不奉佛,亦无僧道……无医卜等书……有事惟鸡卜是决。疾病不知服药,以姜汁注鼻中。病甚,命巫祭鬼路侧,病疟者多愈,病热者多死”。[15]98-110当地人敬畏自然,日食、月食等自然“异象”甚至还决定着部落的征战大事。人们生活中遇大事则采用鸡卜的方式决定,如病重,则求助于巫术。这类习俗和《五溪蛮图志》中对苗人的记载非常相似。在祭祀中,湘西苗人常屠杀牛、猪、羊等作牺牲,其杀牛祭最为隆重。而且,人们还因祭祀时间(长短)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牺牲。遇祀事,“或三年、五年一祭,屠宰牛、羊、犬、豕及诸禽兽。一日为羊鬼,二日为猪鬼,三日为牛鬼”。[39]每逢节日,也要宰牲祭祀,“二月社日,祭伏波将军之弟,曰祭花鬼。用羊、豕、鸡、犬。三月杀白羊,击鼓吹笙曰祭鬼……六月中炊新米,宰牲,亦曰祭鬼。九月九日,合寨宰牲祀重阳,以报土功”。上述祭祀仪式通常均由部族酋长主持,也即是说,酋长往往也是部族的宗教首领。譬如黎州蛮,“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9]14231早期的鬼巫信仰等宗教形式有助于部族事务的管理,酋长政、教身份合二为一,无疑大大增强了其在部族内的地位和影响。
在民众日常生活中,遭遇自然灾害,诸如久旱不雨等,人们应对的主要方式是借助宗教的力量举行求雨仪式。“天旱不雨,蛮人谓系龙王降灾,于是而有毒鱼之举……鱼以水涸被毒,龙王必怜而降雨也。”毒鱼时,江河两岸男女老少辄数千人,皆华服盛饰。捕鱼者竞捕,唱歌者赛歌,“欢呼震山谷,亦极一时之盛。”此风俗行甚远,桂北、黔南及洵柳诸苗、瑶,“无不行之”。[6]91-92在湘西地区,类似求雨这样的传统习俗,一直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初。在永顺,人们认为祈告土王求天赐雨时,需杀一头牛,并举行隆重仪式。人们求雨的另一种方式与上文桂、黔地区相似,发动众人到溪河捉鱼,据说鱼捕多了,上天就会怜悯鱼类降下雨来。[40]宗教仪式有助于纾解早期民众遭遇困境时的心理,同时这类活动也可使整个氏族部落团结、凝聚为一个整体,实现部族社会最大程度的整合。
(二)礼与“法”
在日常礼俗方面,早期的部族社会虽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但因长期远离王朝国家的文治与教化,未系统接受内地儒家思想,其行为呈现出“野蛮”的一面。根据明代云南地区的资料记载,“男女浴于河,虽翁妇叔嫂,相向无耻。子弟有职名,则受父兄跪拜……夷人有名不讳,无姓……不知时节,惟望月之盈亏为候……”。[15]96-108这些部族尚无礼仪、教化等传统,甚至“刚愎嗜杀,骨肉之间一言不合,则白刃相剸”。[21]87可见,在早期社会,因长期处于“化外之地”,科学及文化知识匮乏,在内地官员及文人墨客看来,这类部族习俗中多带有伤及风化或是违背家庭伦理方面的内容。
虽说古代部族社会“缺少”相应的礼俗,然而,其“法制”却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蛮人创制刑法,为时最古,其用亦最酷”。[6]101《尚书·吕刑篇》亦曾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灵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也即是讲,与黄帝同时之蚩尤已创造了“杀头”“截耳”“琼面”等几种刑法。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之刑法,系苗创制,亦无不可”。[6]111这类观点未必准确,但它揭示了一个现象:西南少数民族的“法制”产生较早。根据西南地区的历史文献记载分析,各族群“刑法”或规制的演进似乎并不同步。在云南的一些夷族中,“众杂羁无统略,有仇隙,互相戕贼”。[41]可见,早期人类杂处一地,无统纪。在黔州之西的东谢蛮内部,“赏有功者以牛马、铜鼓。犯小罪则杖,大事杀之,盗物者倍偿”。[42]而在云南西南的百夷中,“刑名无律,不知鞭挞,轻罪则罚,重罪则死(或杀,或用人扱杀,或用象打,或投于水,或以绳帛缢)。男妇不敢为奸盗,犯则杀之”。[15]81这些部族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虽然大多无明文刑律,但其对“罪”的责罚,同样能达到一定的震慑效果。
(三)“军事”活动
集会是部族社会“军事”活动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相关运作及程序如下:临时发生军事警报或紧急要公,召集之法为,“由蛮酋砍木刻画,其形略似关刀,谓之‘砍木刻’”,使人传示辖区各寨。“急着加枯碳、鸡毛;又急者,加辣椒、火绳;尤急者,则烧之使燃。”寨目观此,登楼擂铜鼓,召集寨民。若“事缓者,鼓声连续而缓,事急者,一连三挝,断而续,声急而厉”。[6]89-90寨民若闻急挝声,无不奔走骇汗。父唤其子,兄唤其弟,各家出代表一人,聚集鼓楼前。在云南的蛮夷部族中,“邮传一里设一小楼,数人守之,公事虽千里远,报在顷刻”。部族民众无军民之分,聚则为军,散则为民。“遇有战斗,每三人或五人出军一名,择其壮者为正军,呼为‘锡剌’。锡剌持兵御敌,馀人荷所供。故军行五六万,战者不满二万。”“裹革兜,被铜铁甲,用长镖干弩,不习弓矢。征战及造作用事,遇日月食则罢之,毁之。”[15]83-86这类情况实为近代军事组织及军事活动的雏形。《华阳国志》中亦有相关记载:“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也即,邛人的七个部落。“征其人为兵,每部落编为一‘营’,故称‘七部营军’”。[38]311诸如邛人的“征兵制”、军事编制等带有集体军事性质的活动,构成西南地区习俗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持续并深刻影响到元明清土司时期。除此,部落社会已开始重视“军事装备”。云南的夷人,“善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标枪劲弩,置毒矢末,沾血即死”。[21]90这也是部族之间应对频繁械斗、仇杀等活动的军事策略及现实选择。
四、部族间的械斗、仇杀与社会整合
在古代西南社会,自然地理环境恶劣,资源稀缺,部族间的械斗、仇杀近乎为一种“常态”。某种程度上讲,部族内部的团结及社会整合主要建立在部落间的仇杀或冲突基础之上。
(一)资源稀缺的古代西南社会
古代西南地区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相对封闭的交通条件,导致外界先进的物质技术条件及社会观念难以传入。此外,资源禀赋匮乏也是西南边疆地区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生活与社会秩序。概括地讲,非稳定或半失序状态为历史上西南部族社会的一大特点,而资源匮乏或资源稀缺又是影响部族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南地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土地资源很有限。以康藏高原为例,根据民国时期的资料记载,当地大部分区域处于高山地带,总面积的一半“甚不适宜于各种农业作物之繁殖”,河谷地带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下才可耕种,而“河谷地仅占全康面积之十之二三,且被绝壁斜坡占去大部,可耕之土,又仅得十之二三……是故西康粮食奇之,至于不能供给每方公里一人之需要”。[43]人多地少,粮食产出又少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生活和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在资源稀缺、竞争加剧的社会中,人们的活动往往呈现出强烈的“侵占”色彩。[44]西南地区资源稀缺导致的直接后果为:社会上乞讨人员增多,劫杀现象普遍。在这一地区,“虽每年种杂粮两次,然一家之计均不能满足,每届青黄不接之际,大半苦于无粮,仰屋兴叹,饥耐以到粮熟,成为习惯,足食之家全境不过数户”。[45]故而,每当此时,这些人便举家外出乞讨,直至所得粮食加上家中的储存量够吃一年时,方返回家中。[46]在食物产出不足,靠乞讨仍无法满足生存需要时,偷盗、劫掠便不可避免。以历史上的康巴地区为例,当地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又因远离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中心拉萨,中央王朝的影响无法深入,历史上的劫杀现象屡禁不止。在川藏南路与北路之间毗邻巴塘的地方有一个叫三岩的“野番之地”,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原因,该部落在清晚期以前仍属于“化外野番”,部族间“互为雄长”,“以抢劫杀人为雄,历不属藏亦未附汉”。[47]《清实录》等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三岩的记载:当地民风剽悍,常常对川藏大道过往的行人“施放夹坝(即强盗)”。根据乾隆中后期成都将军特成额的陈述,三岩“境壤延袤,南北五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群番散布,不下一千数百户,其间素行伙劫”。[48]三岩毗邻由成都入藏的官道(即川藏南路),正是这些“贼匪”严重影响到川藏大道的安全。乾隆三十五年(1775),“萨安(即三岩)贼匪屡放夹坝,竟于驻藏大臣常在住宿之地劫掠巴塘副土司特玛骡马”。[49]当地甚至还错抢过达赖喇嘛的茶包、马匹,以至于清王朝不得不驻兵三岩要隘,“严加约束,至伊等每岁应交达赖喇嘛备赏之项”。[50]“劫掠成性”的三岩夹巴在清代中后期一直构成区域社会的重要隐患,引发清王朝数次派兵征剿,并于宣统三年(1911)成功将该地改流。[51]在西南地区历史上,诸如三岩这类自然地理条件恶劣、资源稀缺型社会,人们对财物的渴求相当强烈,进而影响到地方社会的秩序。
(二)部族间的械斗与仇杀
资源稀缺往往导致相邻部落群体之间关系紧张,彼此的竞争、摩擦及冲突异常激烈,一些冲突甚至演变为械斗或是世仇。在地方文献中曾有分析,由于夷人“顾嗜利,绝礼让廉耻,掷片肉于地,争趣若犬承欢”。这一带有夸张和歧视的解释揭示出西南部族社会利益争夺之情形。此外,历史文献中对西南部族间仇杀的解析还包括,“性猜疑,好雠杀,操戈群行,报复不已”。[52]这些均体现了古代部族社会尚械斗、嗜仇杀的特性。
《隋书》中有关于附国习俗的记载:“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53]附国在今天的金沙江流域川滇藏交界地区,为隋唐时期的一个部族政权。当地房屋建筑也被赋予了实施复仇及御敌的功能,足见该区域部落间的争斗应为一种常态。《新唐书》中也有关于蛮夷部落(松外蛮)仇杀状况的记录:“凡相杀必报,力不能则其部助攻之。祭祀,杀牛马,亲联毕会,助以牛酒,多至数百人。”[35]6322由此可见,部族间的械斗、相杀通常源于个体间的纠纷与争斗,继而扩展至整个部族。部族社会械斗、仇杀频繁,历史上一些蛮夷部落因此还形成了“好带刀剑,未尝舍离”[34]5274的习俗。而且,部族间的仇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清代的档案文献中,“以抢夺劫杀视若泛常”“顽狠好斗”等描述与刻画往往构成统治阶级对湘西苗民刻板化的印象。[23]151该区域“打冤家”习俗主要体现为:“苗人偶遇争竞不平,深仇夙怨,欲拿人抵事,骤难即得,而忿不可释,则有所谓打冤家者。即定例所云‘穴斗’也。椎牛醴酒,邀致亲朋,或数十,或百余众”。[54]事后,这些苗人“拜神歃血,各息争斗”。若不然,则“仇衅百出,祸延累世,报复无已”。“拜神歃血”止息争斗仪式展现了宗教信仰在解决部族仇杀方面的重要功能。
(三)部族冲突下的社会整合
在学界存在一种观点:“部族间发生仇杀的区域通常都在山区,山是一种障碍,文明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等强加的一切束缚和统治,在山区不复存在。”[55]该观点可理解为:仇杀是那些远离现代文明,不被现代国家统治的部族社会的“专利”。中外大量民族志材料亦证实了这一论断。在氏族部落时期,那些游离于王朝统治之外的部落组织社会整合程度较低,整个社会呈一盘散沙状,而部落之间常态化的械斗及内部的祭祀、婚姻圈的扩大实际上有助于部落内部的团结和整合。在民族志材料中,一个典型的例证为:三岩藏族对于因械斗、仇杀致死者,通常要选择室内葬的方式,借尸励志,以强化父系血缘组织的团结、整合及内部的战斗力。[56]这也应证了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的观点:超越村落、家族的地区性联盟,通常是在联姻、械斗中形成的。械斗冲突也可实现跨村落、宗族的团结与结盟。仇杀、械斗看似造成地方社会一盘散沙,实则表达了“一种复杂的社会冲突和紧张关系”。[57]也有学者立足于部落酋长的作用,对仇杀现象的功能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政治制度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世仇机制,它受被称为“貂皮酋长”机制的调节。[58]
部落社会的整合还取决于构成部落凝聚力中的情感因素,而亲属关系规则则是部落情感的基础,是对地域酋长和最高统治者效忠的基础。[59]古代部族社会的整合具有以下特征:社会的凝聚力主要来源于人们的血缘关系认同,以及对部族头人的忠诚度。这是因为,父系血缘关系的自主性功能及凝聚作用,能够将分散的个人或群体组织在一起。
五、结 语
在“无国家”(non-state)或国家权力影响较弱的部族社会,其内部运行状况如何,或者讲,其是如何实现内部治理的,为本研究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在笔者看来,在传统的部族社会,文化、习俗等是与社会的规则管理相关的一个独特的治理领域。托尼·本尼特亦曾指出,文化是道德、礼仪、行为准则等领域的制约手段,有其制度化的治理关联(institutionally embedded relations of government)。文化领域由管理构成,系特定的规则领域。[60]西南地区古代部族社会管理内部事务的方式,可视为与文化相关的治理范畴。部族组织在日常运作中,将其组织机构、宗教信仰、婚制习俗,及血亲关系等抽象概念、规范,与象征等纳入到一个共同框架内,并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体系相关联,构筑地方秩序的基础。
西南地区古代社会的秩序与整合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部族组织中自身所包含的维持稳定和秩序的结构。如贵州黔东南传统社会中的“三根支柱”:“鼓社”是一种氏族外婚制团体,由同宗的一个或几个村组成,是苗族古代社会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议榔”即议定公约,是苗族社会议定法律的会议,由一个村或多个鼓社进行;“理老”汉语直译为长老,其熟习古理榔规,办事公正,其才能和威信主要体现在纠纷解决上。建立在地方组织之上的鼓社政教制、议榔立法制和理老仲裁制是苗族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61]二是地方文化与习俗中所蕴含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湘西苗族地区民间宗教中通过白帝天王进行神判、血誓等习俗。[62]三是部族之间的械斗、仇杀,以及矛盾冲突中形成了部族内部的团结与整合,同时也构成了区域社会的动态平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