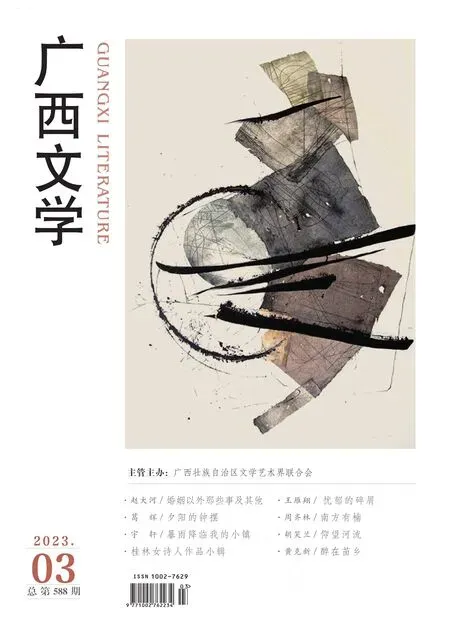南马都尔
2023-04-16周楷棋
周楷棋
——献给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
大半个学期前,我在新生见面会上记住了小霞,但彼此没有交谈。几天后,我为了确定该学期的选课而旁听了她导师的一节课,但因内容晦涩难懂而弃选。我虽然记得这个人,但从未在后来系里的各种会议或讲座上见到过她的身影。
一段时间后,一位老朋友来打听报考小霞导师的事,我顺理成章地从系里的通知群添加了她的联系方式,并打听了一些报考事宜,但也仅限于此。秋日渐深,因为无法和远在他乡已经上班的女友相聚,我只能在学校孤独地度过二十六岁生日。那个晚上,我在学校外的海滩上徘徊,仰望着飞马座的“秋季四边形”直到深夜。第二天夜里,小霞意外地在微信找上了我,举着镜子似的询问了一些报考我导师的注意事项。我们不再捂着话匣子,从考博的艰辛聊到读博的艰难,又从院系里的八卦聊到各自的生活状况,这才发现彼此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爱好。我们聊王家卫电影中的镜头运用,聊庵野秀明作品中的致敬与继承,聊如何简单地理解尼采的“永劫轮回”,聊《星球大战》系列后传的糟糕表现和国产科幻电影崛起的原因。她总是热情地回应各种话题,言谈中不乏灼见,却又有一种孩童般的稚嫩,像一位返老还童的贤士。我们相见恨晚,从晚上九点聊到凌晨两三点。我想,茫茫宇宙中一定有谁写下过这句名言:两颗彼此吸引的小行星即便相隔亿万光年也会互相接近,并在最终碰撞时迸溅出比永恒更炽热的火花。
当小霞分享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时我则察觉到困意,因为自己相关的体验在她面前过于贫乏。小霞滔滔不绝地向我展示了与埃及金字塔、巨石阵以及摩亨佐·达罗的合影,又提到自己曾游览过南马都尔——位于南太平洋的神秘城市遗迹。我对这个地名有印象,但因疲倦无意深谈。她则给我发来一张屈身在石头废墟边上比“V”字手势的照片,说:
“我在南马都尔的石头缝隙中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起初像许多人聚在一起反复吆喝,一会儿变成了箭矢破空的锐响,下一秒又像是空调外机在闷哼。”
我听得莫名其妙,试图将之解释她在南马都尔的神秘氛围中将海浪拍打礁石或者海风吹动树叶的声音主观地幻想为了宇宙的声音,但被严正地驳回了。那晚的聊天最后草草结束,末尾她发来一句“也许是我错了”又很快撤回。我因为疲倦无力也无意追问,只感觉自己一定在童年时就已经读到过南马都尔。因为心血来潮,我只睡了不到五个小时就起床并径直前往图书馆,凭印象查阅了馆中所有关于“未解之谜”的藏书,这其中九成以上的故事都已被年龄、阅历和知识证伪。我本以为能在“百慕大三角”“尼斯湖水怪”“巴巴多斯棺材”“复活节岛石像”“尼比鲁星”等耳熟能详的条目侧畔找到答案,但却扑了个空。只有几本我确信并未读过且出版年份较晚的“未解之谜”类书籍中提到了南马都尔,文字的描述也远不及过往的那些“外星人”“虫洞”或是“史前文明”来得离奇和吸引人,只是在重复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位魔法师受绍德雷尔人之邀兴建南马都尔,他使巨石腾空而起,从远方的采石场飞临当地。后来我又了解到另一种少见的说法:两位双胞胎巫师建造了南马都尔,但他们以巨龙而非法术搬运巨石。还有一种说法是:建造南马都尔和绍德雷尔人偶然观测到的奇异天象有关……
在奇幻遍地而又无从回忆的童年,南马都尔的本相被那些过度发挥的奇幻事迹遮蔽了。如今,其神秘的本色仿佛已被弃置不理,只有实际可考的遗迹形象存在至今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实世界则比小霞更早地肯定并解读了南马都尔的神秘,其多次出现于洛夫克拉夫特、梅里特等奇幻作家的笔下,又在某款魔幻历史策略的电子游戏之中被设计为一座提供增益的城市,甚至被世界气象组织用于台风命名。这种被“建构”的传奇故事也许亦遮蔽了其本质上的神秘,毕竟很少有人会去窥视、倾听石头的缝隙,或者探究“群岛之间的宇宙”有何深意。我并不是完全不愿相信小霞的话,只是暗中嫉妒生活无忧的她为何能经历神秘,而从童年始便向往,且更需要这种体验作为突破压力和焦虑之匙的我则在二十余年的生命中一无所获。每个晚上,我都要枕着被预约的压力入眠,而南马都尔遥远到无法在每一个明日来临时还能被记起。比起自由自在的她,我更希望自己是被神秘拯救的人。
2
那晚之后,我和小霞成了朋友。我们没有再谈起南马都尔,但经常聊至深夜甚至凌晨,分享各种日常趣事和生命体验。不过,即便住在同一栋宿舍楼,我们却只像两个无意打破数百米距离的网友,不仅从不在现实中碰面,更从未有人提出过要出来约饭或游玩。我性格内向而她朋友众多,所以这种默契的距离再合适不过。有本叫《吸血鬼关系》的小说写道:“吸血鬼的孩子永远比人类的孩子听话,因为他们从不在外过夜。”《文学物理学》里有一章则写道:“量子纠缠即是最简单而深厚的情谊。”这段时间,系里频繁开会且要求签到,而签到表上属于小霞名字一栏的空白也逐渐醒目起来。我问起此事,她说一来去系里的路太远,二来自己也不在乎综测分数,三来相比于讲座更喜欢读书。我羡慕而又嫉妒,时而会将这种情感转化为发愤的动力,但总是坚持不久。
有些感情会比惊鸿一瞥的火花更快地燃烧殆尽。有个晚上,我肚子很饿,想起小霞昨天说自己买了一箱很好吃的面包,便想去问她要一块充饥。小霞答应了,却说会把面包放在四楼楼梯口的外卖桌上。我感到奇怪:她住在四楼最靠里的房间,离楼梯口的距离很远,为何要费劲把面包特地放到楼梯口而不是让我到门外取。也许她因为熬夜长了痘,也许只是不想见我,最后那块面包吃起来味同嚼蜡。也许这并不是在普通朋友之间值得被刨根问底的事,但我却耿耿于怀,也许在沉闷和煎熬的日子里,猜心的妄想反而是种乐趣。第二天下午,我又故意问小霞借一把剪刀,她果然又说要把剪刀放在楼梯口的桌上。我说不必麻烦她奔劳,就让自己到她宿舍门外来取即可。她过了快一个小时后才又回复,说自己导师刚才突然急找她到系里商量一个调研项目的事,并暗示我还要谈上很久。见她有意躲避,我便知趣地放弃,但浅埋心中的怨种已然生根。到了深夜,她又主动找我聊天,问我是否还需要剪刀并自然而然地扯到了别的话题。我意兴阑珊,但仍积极回应她的热情。她忽然说起自己在埃及阿姆尔清真寺参观时,在寺内的石柱中也听到过类似南马都尔的声音,但我立刻意识到这不过是博尔赫斯在《阿莱夫》中引用过的桥段。我揭穿这点,这一次她却不坚持己见,只是发来几个轻松的表情,说自己可能听错了,就像在南马都尔的时候那样。我惊异于向来原则鲜明的她居然主动否定了自我,但这比起对我的有意疏远来说也不算什么。
3
仿佛远离不可知,远离南马都尔,我们就能维持着舒适的关系,但因为两天后的一次偶然,我对小霞的怨恨便如雨后的竹笋般疯长起来。那天晚上系里有个讲座,而我碰巧坐在了小云旁边。小云是我一个比较聊得来的同学,也是小霞的好朋友,我曾经在小霞的社交媒体动态上看到过两人结伴出游的照片。讲座散场后,我们一起走回宿舍,我在学术上的话题逐渐枯竭时转移了话题,故作随意地谈起小霞,但并不透露自己和她的关系。小云坦诚地透露了自己和小霞的挚友关系,并称赞她是一个直率的人。我又随口问她俩最近是否出去玩,小云说两天前本来想约小霞去扬明广场购物,结果因为那天午后天气太热,自己便到小霞的宿舍做客,和她边吃零食边看了一个下午的电影。我旁敲侧击地确认了具体时间,确认那正是我向小霞借剪刀的下午。我又想,也许她只是习惯了熬夜,或是为了一个和小云无关的理由而有意避开我,我能理解任何原因,但无法感到宽慰。
本来,就像是暧昧的南马都尔之谜,在艰辛的日子里本来并不是特别值得被追问。但小云又提起,两天后她们还要在学校的咖啡店借电影消磨周末的午后时光。这使我想起一种说辞:“上帝不会替你做决定,但会给你做决定的机会。”相比能够灵活解读教义的僧侣,我更像个输急眼后要为霉运讨说法的赌徒,真正想讨回的是面子而非本钱。到了那天,我像往常那样走在明暗相交的林荫路上,只觉得自己变成了侠客或是法官。我这样设想:要首先去店里点一杯奶茶,并要在吧台处和她们发生有距离的眼神互动,由此造成不期而遇的事实,这样才能自然地走过去寒暄两句,并要以小云不知道的方式暗示小霞自己已经知道她在撒谎,最后方能从容离开。这种自我意识过剩的恶意散发着比巨魔芋花更刺鼻的恶臭,但倘若能使小霞从此开始讨厌自己,那便是我得胜了。
咖啡店里放着悠缓的流行音乐,许多人都昏昏欲睡,但她们正并肩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分享着同一个耳机的左右耳并不时地嬉笑着。我点好奶茶后便有意靠在吧台前并转对她们的方向,但始终没有被两人注意到。我不耐烦,径直穿过大厅坐到她们面前,以侵略性的姿态出现并打招呼。她们都抬头看我,小云显得意外,但小霞的表情则难以形容,像是错愕中带着几分困惑和茫然。小云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我说想来点杯奶茶顺便消磨时间,等会儿要去系里找导师聊论文的事。说话时我的余光瞥向小霞,却见她困惑不减之余更平添几分厌恶,就像在忍受超市导购不请自来的热情。这让我越发愤懑和困惑。
我故意又问她们在看什么,并转向小霞,问是不是我前几天推荐的那部《躯壳》。小云说是《穆赫兰道》,但小霞没说话,望向我的眼神中更多了几分敌意。我恍然大悟:她就像是在看着一个陌生人。我有些忍无可忍,站起来返回吧台询问我的奶茶是否已做好,却只得到了否定的答复。见她俩正看着我窃窃私语,我便又不平地走回去,直截了当地感谢小霞在报考问题上提供的帮助。她愣住,有些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看我的眼神越发怪异。
也许是意识到情况不对,小云像是为了打破尴尬似的主动将我俩介绍给彼此。心怀怨气的我脱口直言自己和小霞已经很熟。没想到小霞立刻反驳,说她是第一次见到我,不存在很熟之说。我反问她,是否经常从深夜聊到凌晨的关系也不能算熟。小霞短暂地愕然并立刻否认了,说从来没和我在深夜聊过天,并直言我的唐突已经打扰到她们。我忿忿地质问,说聊天记录绝不会有假。她叹了口气,又问了一遍我的名字后便掏出手机翻看起来。我有那么一瞬间侥幸地猜想小霞只是性格直率而又备注错了名字,但她将手机转给小云看了两眼后便递到我面前。手机屏幕上亮着她和我的微信聊天框,映入眼帘的却只有我添加她后咨询报考事宜那晚的聊天记录。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拨,却发现已经到底了——除了那夜的试探,见证着相识后每一个深夜的聊天记录都不存在。
我脑袋嗡地一震,觉得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有一颗狡猾的心。为了向小云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疯子,我掏出手机自证清白,但紧接着就像在悬崖边上一脚踩空似的坠了下去:我手机里的聊天记录也只到同一夜为止。我顿时头晕目眩,觉得周身的一切都像未解之谜,都像南马都尔那样不可理解。看到她们的身影飞速下坠、消失在一片灰白中,我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瞬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跌倒。
4
在学校医院醒来时已近深夜,医生坐在床边,说我在咖啡店晕倒后便被送来了医院,一直睡到现在,并转达系里的吩咐,说为了保险起见让我在医院待上一晚,我唯唯而应,对医生的话左耳进右耳出,只是在脑海中拼命地想留下刚才的所见,但梦境从被察觉到的一瞬间开始就是残缺的,回到现实则加剧了残缺。医生走后,我躺在床上探望窗外清冷的夜色,把校园虚化成了另一个世界,想象着视线越过田径场落向远处的宿舍楼,落在小霞那间可能彻夜明灯的宿舍。我想起梦中的星辰、山脉、雨林、海滩和她,仿佛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人们往往不相信梦境,但在获得不可理解的体验后却又乐于归谬为其影响。对于刚才的梦,我无法确凿地表达自己的判断,只觉得仿佛是一直期待着神秘的我得到了预期之外的回应,即那神秘的现象以反神秘的方式出现了。当体验和事实二律背反时,即仿佛逼迫着我去选择其一。如果说梦境终究是潜意识为了圆谎而设,那也确是一种选择:为了修补现实,需要用荒诞说服荒诞。
我依稀记得她俩似曾站在床畔看我,后来又只剩小霞一人。她没有动唇,我的脑海中却响起了她的声音。她向我道歉,表示自己并非有意为之,只是犯了一个错误。她让我想象黑夜里站在一片广阔的荒原上。我照做了,按着她的引导踏上碎石和枯草的平地,头顶着横贯天际的乳白色银河,眺望位于远处连绵山脉下坐落着的一座遗迹。“她”说,自己和小霞初遇于此。她又让我抬头,沿着银河向上继续想象那无垠宇宙,说仍隐约记得自己的故乡就在这片璀璨天际之中,但既不知其所在,也记不起其状貌。从星辰中的每一个角落眺望,宇宙都是瑰丽的,但其本身则是一片无界的黑暗,任何星光都会在身入其中后变得邈远而难以企及。也许是在这虚无的深空中漂流了太久,她失去了很久以前的记忆,不再记得自己的故乡、同胞每一集漂流的原因和目的。在永恒的折磨下,她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力都逐渐钝化,那些在无尽的黑暗中不断出现、接近而又远去、消失的天体和生命,最后都变成了记忆中被永恒点缀后仍然会逐渐模糊的刹那。
就当记忆逐渐被漫长的时间消磨殆尽之际,她又似过往的无数次那样缓缓靠近着深空中一点微渺的星光。但这次,她遇到了一颗蔚蓝色的星球,其表面的海洋和陆地唤醒了对故乡的想象。她穿过大气层,像流星那样坠向地表,坠向埋葬着古老文明的荒原,坠向那时正在荒原上拍摄古城和星空的小霞。没有实质形式的她乘着一阵风进入了小霞的身体,后者对她的到来则一无所知,只像是打了个冷战。
她就这样成了小霞身体里看不见的租客,但并不能影响房东的意识和行为。起初,她对这种共生似的新体验十分好奇,在随着小霞云游天下、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她遍识人类文明的人文和科学奇观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并不为这个世界所知。通过学习和总结,她认为现代人类文明大多以理性主义和权谋政治两大特征为基石,而与前者相悖的事实或者会在现实中以后者主导的方法被抹去和遮蔽,或者会被主观建构为标示着“神秘”的文化符号而失却了其本身的神秘。不过,身为异乡人的她却能从一些细腻的现象中发现实体下的阴影,比如马尾藻海深处的巨大阴影,中美洲神庙石刻中的神秘讯息,古代南亚文学经典中的异常天象……但她并不快乐,即便在随小霞观赏一些科幻影视作品时仍能获得短暂的共鸣和舒适,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还是悄无声息地蔓生于无处不在的陌生和空虚之中。漫长的漂泊之后,她终于在宇宙的某处遇见了和自己类似的智慧实体,但却无法与之进行有效的交流。失去了身体和语言的意识比失去了意识和语言的身体还要悲哀,因为其更清晰地体验着悲哀本身。她感到孤独,宁愿与亿万年前的缥缈星光,而非此在的熙攘世界为邻。
她沉沦渐深,意识又开始钝化。但当小霞踏上南太平洋的波纳佩岛,在雨后的黄昏步入那边滨海雨林时,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在这座远离现代文明的小岛上,闷热的林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湿气,鸟兽的鸣叫声也时常模糊不清。借着小霞的眼睛,她得见了那片建筑在岛屿东南方的古代遗迹,那些精心雕琢的黑色石块以科学家不能理解的实体姿态存在于斯,整齐、有序地堆砌成一处处高台、墙壁和祭坛,以近千年的沉默宣示其毋庸置疑的神秘。那神秘在任何现代人眼里都被简化为知识型的两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建造了南马都尔。但当英语流利的向导介绍南马都尔的起源时,她不仅对那对巫师兄弟的传说产生了兴趣,更直觉而真切地感觉到两兄弟和那两条运送巨石的飞龙的骸骨就埋在遗址附近的水底。她在不被这理性的人间所认可的神秘中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但这也是另一种悲哀。至于宇宙的声音则纯属意外:小霞脚下一滑,靠手指抓住身旁的石墙才免于跌倒的同时,耳朵靠在了墙缝上。她从缝中听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喧哗,小霞却毫无知觉。她坚信只有故乡的声音能与自己的灵魂产生共鸣,只有故乡不会欺骗自己,只有故乡会给她在漫长的旅途中以家的允诺,只有来自故乡的声音能让她振奋。她有一个让自己坚信的理由:在听到石缝中的声音后,她逐渐发觉自己可以短暂地控制小霞的身体而又不会使其意识知觉,起初只有几秒,然后是十几秒、几十秒,甚至几个小时。在那之后,她短暂地拥有自己的生活,但这需要以代替小霞承受人间的喜怒哀乐为代价。这里不是故乡,她感到无所适从,只想回到南马都尔,回到星辰之间。有一次,她随小霞读到了博尔赫斯的《阿莱夫》,并猜想世界上可能还有其他类似南马都尔的存在。因为《阿莱夫》的影响,小霞居然真的动身前往阿姆尔清真寺瞻仰,她借机听遍了寺内的每一根石柱,什么也没有。
随着她的叙述,我仿佛也站在湿热雨林中的齐踝水坑中,但却想象不出断壁残垣的具体状貌。她说:“你只需要想象南马都尔的中心有一扇圆形或方形的门,那就是整座城市的意义。很久以前,我偶然来到地球的同胞成为传说中的魔法师或巫师,建造了这座城市。在某种机缘下,那扇门终于帮助他们重返星辰,回归故乡,而其他目睹了门后景象但无法进入的绍德雷尔人才是南马都尔‘群岛之间的宇宙’之名的来源。直到今日,故乡的声音仍透过‘门’传过来呼唤着我。”她还认为,也许还有其他的异乡人造访过地球,所以也可能还有其他的“门”被埋藏在拉帕努伊、罗布泊、纳斯卡这样的地方,也可能在不知名的他处。只有建造者的同胞能感知到故乡在“门”后的呼唤。
我并未做出信与不信的选择,只是问她什么是“错误”。她说自己由于过分思念南马都尔,以至于有一个晚上伴着小霞在海边踱步纳闲时,一厢情愿地将正在痴望星空的我误认为也是来自天外的子民。我说自己只是在放空焦虑并思念亲人,她欲言又止,最后只说觉得我身上散发着和她相似的孤独,又问我是否记得自己故乡的模样,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不再追问,只是说自己因为一时好奇而把我也当成了异乡人,并后知后觉地才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会给小霞和我带来困扰。我说以小霞的身份在人世间偷渡光阴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她则觉得在这颗熙熙攘攘的星球上许多生命并不比曾在虚空中独自漂流的自己过得幸福,所以便不愿再将由未知产生的压力传递到他人身上,并说自己从一开始就会把和我的聊天记录都删除,没想到还是惹来麻烦。她再次向我道歉,表示已经向小云澄清,并会设法让小霞淡忘了下午的事。我本来隐约觉得她的叙述中有一些似有似无的缺陷,但伴随着梦境的突然结束,其就此遗失在乍醒时泥泞的意识之中。
5
那晚我醒来后依然很困,便又很快睡去,第二天临近中午方醒。我觉得精神饱满,恍若睡了几天、甚至几周。医生批准我离开,但吩咐要多运动,少熬夜。窗外骄阳炽烈,我看了一眼手机,觉得自己一定是在晕倒后做了一场异常漫长的梦,梦见了小霞、小云和一个与自己同样孤独的灵魂。我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和小霞之间存在过短暂的友情。而从现实角度来看,昨夜的梦更像是我为妄想进行的强行解释。有时候,梦境和真实难以区分,尤其是一切都成为过去之后,分辨的代价远远高于以自我否定为代价回归生活的正轨。尽管我仍然不明白为何自己手机和电脑上的聊天记录会同时消失,但这浑然天成的现实仿佛在暗示着追问的徒劳。
我不得不放弃纠结这段友情之谜的真实,在理性的顺水推舟下将其解释为谵妄和幻想的结果,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病,只是选择主动与神秘保持距离。我打心里对与南马都尔及有关的一切敬而远之,也不再关心任何未解之谜。对处于人生瓶颈期的自己来说,这些只能满足精神,却不能填饱肚子。我于是继续投身煎熬的学习和生活中,继续为了毕业焦头烂额。我没有再和小霞聊天,只是会在欣赏科幻、奇幻影视时想起那些荒诞到真假难辨的夜晚、说辞和梦境,觉得也许是平行世界的我偷走了自己的深夜。从小云口中得知,小霞对她表示那天其实是和我开玩笑,只是没想到发生了意外,我顺应梦境点头称是,并婉拒了她想找个机会再邀我俩相聚的提议。
也许是十天、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之后,我看到一条新闻:一支科考队在本市依澳岛上的厚沙湾考古遗迹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这条新闻还伴随着一些隐秘的流言蜚语,暗示这次的考古发现不仅“重大”而且“离奇”,即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土层中发现了一件不属于同时期的人工制品,也就是“欧帕兹”。起初我对此并无再多好奇,但第二天,新闻报道了一则台风预警,说一场名为“南马都尔”的超强台风已经在太平洋上生成,并预计在后天深夜到达本市,其风速和范围都大得异乎寻常。同一天,小霞在社交媒体的动态上说自己即将和朋友到依澳岛上度假数日,并对可能的台风体验感到兴奋。也许是对连日积累的疲劳和挫败感的反叛,以及这一系列和南马都尔有关的神秘暗示,我渐渐产生了一个隐秘的执念:要去依澳岛。
在台风预计登陆的那天下午,我乘车前往依澳岛。公交车驶上大桥,城市、陆地被无情抛向过往,阴沉且诡谲的乌云在岛屿方向的天空中聚拢。白色的海鸟在岛屿边缘的红树林丛盘旋,车窗的温度也凉了下来。南马都尔的海滩上也有红树林,它们的支持根深扎入泥,那些呼吸根在诗人的视野朦胧时就会被误认为是成群结队的瘦小人影。
厚沙湾考古遗址位于岛东北方的沙滩上,但唯一可达的道路已经封闭,保安询问我的来意,说遗迹及博物馆最近不对外开放。我承认自己没有勇气在旁边的密林和山丘中鲁莽地探寻通路,认为即便侥幸入内也会被赶出来。我只是个普通人,需要按部就班地生活,而欧帕兹注定与我无关。我觉得沮丧又无可奈何,发脾气似的反思那不成熟的登岛执念从何而来却又没有结果,只觉得耳边的风声正一点点儿地变大,树林也开始窸窸窣窣地不堪其扰。但我仍想在岛上走走,或许是想再见到小霞,仿佛她就是神秘可能性的守门人。
我漫无目的地来到另一片海滩上,想在此熬过残损的白昼。海滩四周满目荒凉,东南角有一片茂密的红树林,绵延汇入了一个小山头,北侧的路边坐落着几栋民宅。海风越来越大,路边的旗子猎猎作响,每一次卷起的海浪都淹到比上一次更高的滩位。红树林猛烈地晃动着,一座被孩子遗弃的沙堡垮塌了。乌云的颜色从海平线处陡然变深,云层断崖的暗处还闪烁着间断的金光。天也开始变黑,末日的压迫感扑面而来。我不想再待,准备转身离开时却在凛冽风声中听见了一阵神秘的海中异响:似乎有人站在喧闹的十字路口吹笛子,伴随着某种交通工具在启动时发出低沉但顺滑的引擎声,还有如说唱般节奏轻快但意义不明的呢喃。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陷入了震惊与呆滞,过了很久才意识到远处的民宅二楼上隐约站着一个人。那借着小霞身体注目着我的她,因为我又依稀听到被劲风吹碎的细语。她说,在依澳岛东南方向的海底深埋着另一座比南马都尔更古老且不为人知的遗迹,其完全没于泥沙之中,建造者不是她的同胞,也不知来自何方,只有那枚在厚沙湾被数千年前的祖先和今人相继发现的齿轮型制品可能是其存在着的唯一暗示。我向她提出了那个即便在现实中也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什么连我自己手机和电脑上的聊天记录也会消失。她说:“你已经知道答案了。”我追问:“但听到声音的是我。”她反问我:“你还能丝毫不差地记起过去的每分每秒吗?”我说这连伊雷内奥·富内斯也做不到。她说:“也许你因为来了很久而早已厌倦追寻,又或者从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我曾在深夜里反复追问,但你——或者是另一个你,总说已经不记得了。”
我已经想不起自己究竟被偷走或是偷走了多少个夜晚和白昼。她转身进屋,向我作最后的告别,说要离开小霞的身体,乘上台风“南马都尔”,借助逆时针的风向飞往真正的南马都尔,在那里找到回家的方向。我没有挽留,与她真正达成共情的同时也感觉到了亘古苍凉的疲惫。
6
我已经想不起那晚是如何赶回学校的了。只记得到了凌晨时分,窗外狂风呼啸、轰隆作响,像是有一列无穷长的火车载着一名看不见的客人向东南方驶去。我还是睡着了,窗外的巨响轰鸣入梦,梦中却什么也没有。台风消散的那天,有一条新闻报道说,在南太平洋海底火山活动引发的次生影响下,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波纳佩岛东南部附近的海床发生了塌陷,南马都尔遗迹大半沉入了水底。同一天晚上,我在系里的讲座上遇见了小霞。我们遥遥对视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我们之间的故事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连南马都尔也不复存在。
在星光疏淡的夜空下,校园中的一草一木都真切无比。我一个人走回宿舍时自问自答地下定决心:要像在宇宙中永远漂流那样努力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