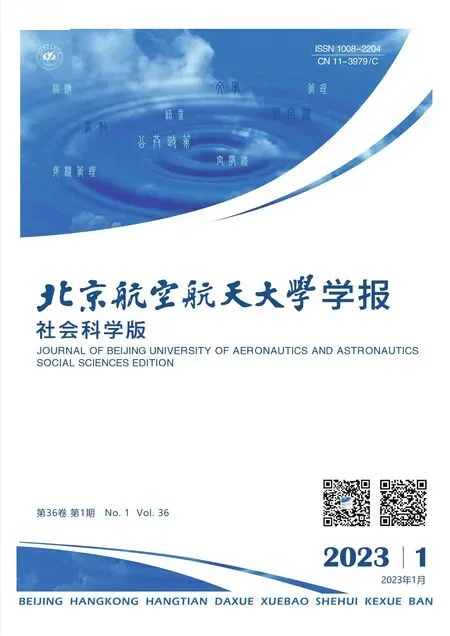信息网络犯罪侦查规则的发展面相
2023-04-06梁坤
梁 坤
(西南政法大学 刑事侦查学院,重庆 401120)
2022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两高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22年《意见》”),其中许多条文涉及侦查规则的更新。从此类规则的发展面相来看,一方面具有明显依附传统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超越传统而独特生长的样态。如何看待这类规则与常规侦查规则的关系,以及对这类规则的未来发展应持怎样的认识,是需要审慎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信息网络犯罪侦查规则对传统的依附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深化,侦查规则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侦查规则越发迈向精细化,而信息网络犯罪侦查规则的体系化建构便是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尽管如此,这类规则中的许多内容仍然反映出了对传统的依附,2022年《意见》的内容也不例外。
2022年《意见》第1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前的调查核实过程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及查封、扣押等侦查措施。这其实就是要求侦查工作必须符合立案前只能开展任意侦查的法理,从而排斥强制侦查的适用。由此,2022年《意见》关于立案前调查核实阶段相关措施的规范,与传统的侦查法理和规则完全契合,呈现出明显的依附性。
2022年《意见》第15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通过远程网络视频等方式开展询(讯)问,并制作好笔录。考虑到远程形态下的笔录制作比较特殊,2022年《意见》非常详细地要求,办案地公安机关应当首先将询(讯)问笔录传输至协作地公安机关;笔录经被询(讯)问人确认并逐页签名、捺指印后,再由协作地公安机关协作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将原件提供给办案地公安机关;询(讯)问人员收到笔录后,应当在首页右上方写明“于某年某月某日收到”,并签名或者盖章。如此一来,远程询(讯)问的推行,变化的只是取得言词证据的环境,而办案程序中以书面笔录承载言词内容的证据要求则并未展现出实质性的差异。
综上所述,传统的侦查规则仍然对信息网络犯罪的侦查规则具有强大的辐射力。换言之,适用于信息网络犯罪的部分侦查规则实际上就是传统的侦查规则在信息时代的自然延伸。
二、信息网络犯罪侦查规则对传统的超越
信息网络犯罪毕竟具有特殊性,2022年《意见》中的相关侦查规则也从多个方面展现出了对传统的超越式发展,并且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侦查管辖的连接点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25条和第26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实践中,侦查管辖也是对应审判管辖的连接点,作为侦查程序启动的依据。不过,信息网络犯罪往往具有鲜明的“链条性”特征[1],这便导致难以对犯罪仅作狭义的理解。于是,根据2022年《意见》第2条规定,侦查管辖的连接点在网络环境下出现了扩张。例如,相较于2014年《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2022年《意见》将“犯罪过程中其他涉案人员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也纳入了管辖依据,从而使更多的公安机关有了侦查管辖权。
第二,调取数据的安全性强调。对于面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电子数据调取,2022年《意见》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经公安机关信息化系统传输数据电文的实践做法进行了认可[2]。这种做法虽然方便了电子数据的调取,但是也必须考虑数据固定与传输的安全性问题。为此,2022年《意见》第14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需要通过载明调证法律文书编号、单位电子公章、完整性校验值等保护电子数据完整性的方式来提供电子数据,而且法律文书和电子证明文件也应当使用电子签名、数字水印等方式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这样的规定回应了理论界关于电子数据调取行为全程留痕的呼吁[3],与传统的侦查取证流程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
第三,涉众证据的折中式收集。近年来,信息网络犯罪的涉众特性越发明显,许多案件中的证据也呈现巨量分布样态。为此,在无法逐一收集证据的情况下,2022年《意见》第20条和第21条作了特殊安排:一方面,对各类证据材料而言,允许按一定比例或者数量选取证据,但需要对选取情况作出说明和论证;另一方面,在足以认定有关账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的情况下,允许根据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交易记录和其他证据材料所显示的接收资金数额来认定犯罪数额。与常规侦查中全面收集证据的基本要求不同,2022年《意见》结合信息网络犯罪的特点,对取证程序进行了务实的折中处理,从而产生了与侦查传统较大的差异。
三、信息网络犯罪侦查规则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对常规的侦查规则而言,信息网络犯罪的侦查规则既存在明显的依附性,又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超越。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侦查规则与类罪的关联度的深化。
从刑事实体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根据罪名而展开的,并且总共构成十大类犯罪。与此不同的是,刑事程序法的规范从总体上并未建立在不同罪名抑或不同类型犯罪的基础上,而是整体适用于所有的犯罪。
当然,也存在个别的例外规定。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9条、第64条、第75条、第85条、第150条规定,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的侦查程序中,对辩护律师会见、证人等作证、适用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而言,便存在特殊的侦查规定。由此可见,根据类罪特点建构适度超越常规程序要求的侦查规则,与程序法的既有规定及法理并不冲突。
近年来,除信息网络犯罪的办案规则外,以类罪为基础而建构的侦查规则不断涌现,司法实践也呼吁推出相应的类罪证据规则[4]。例如,近年来,公安部便独立或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涉及非法集资、洗钱、经济犯罪、毒品犯罪、妨害文物管理等类型案件的侦查规则。出台这些规则的原因,无不是在于相应案件的侦查存在特殊性,常规的办案规则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
这种规则建构的思路在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除笔者着力分析的2022年《意见》外,“两高一部”近年来还以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办案指引的形式,就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跨境赌博犯罪等案件以及电子数据的收集、审查与判断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
综上所述,信息网络犯罪的侦查规则在依附常规办案规则的基础上,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超越,并不能算作一个新鲜事物。以2022年《意见》中相关条款为代表的侦查规则的发展与完善,反映了刑事程序法近年来基于类罪的特点而进行精细化、专门化建构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