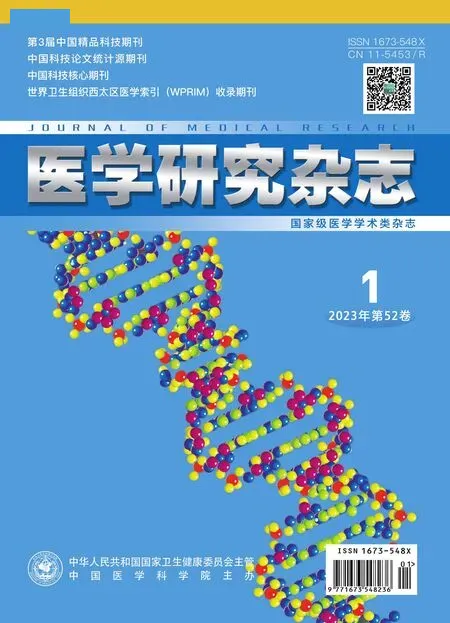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2023-04-06王静钰马艳萍
王静钰 马艳萍
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mia,CMML)是一种罕见的恶性克隆性造血干细胞疾病,主要表现为持续的单核细胞增多症和髓系前体细胞发育异常,具有向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转化的潜在风险,是最常见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增殖性肿瘤(myelodysplastic/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MDS/MPN)[1]。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唯一可能治愈CMML的方法,但由于年龄、合并症、并发症以及患者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临床应用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除此之外,CMML目前的治疗选择十分有限,主要包括对症治疗、羟基脲和去甲基化药物(hypomethylating agent, HMA)。得益于基因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分子异常在CMML患者中不断被发现,为疾病的精确诊断、危险度分层、疗效判断等提供了新的依据。研究表明,超过90%的CMML患者存在基因突变,涉及表观遗传调控、RNA剪接机制、细胞信号转导、转录调节、DNA损伤等多个环节[1]。尽管针对突变基因的靶向治疗已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由于CMML分子遗传学特征具有高度异质性而缺乏特异性,多数情况下无法将其直接作为治疗靶点。因此,寻找特异性高、毒性低、疗效相对确切的靶向治疗策略十分必要,本文就CMML靶向治疗药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一、去甲基化治疗
HMA包括阿扎胞苷(5-azacitidine, AZA)和地西他滨(decitabine, DAC)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唯一批准的用于治疗CMML的药物。DNA异常甲基化可通过影响参与细胞周期、细胞凋亡、DNA修复及基因组稳定性基因的表达,促进肿瘤发生。作为胞嘧啶核苷类似物,DAC和AZA可以在S期取代胞嘧啶掺入DNA中,不可逆地结合DNA甲基化转移酶使其功能耗竭,改变DNA甲基化模式,后者还可作用于RNA以干扰mRNA和蛋白质代谢,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并诱导其凋亡,是针对CMML表观遗传学机制的非特异性靶向治疗手段[2]。
HMA的广泛使用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CMML患者的生存情况,但其疗效仍不尽如人意。研究表明,其总体反应率(overall response rate, ORR)约为50%,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 CR)率不足20%[3]。此外,虽然HMA可以通过影响DNA甲基化和基因表达促进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但无法从根本上减少体内突变基因的负荷,也无法阻止分子事件的继续累积,因此疾病进展不可避免[4]。尽管如此,通过更精细的分层诊疗、药物联合、新药研发等手段来提高HMA疗效的努力从未间断。Duchmann等[5]进行了一项包括174例CMML患者在内的大规模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表明,基因型为TET2突变/ASXL1野生型的患者具有更高的CR率和更长的总生存期,而ASXL1突变与ORR较低有关。因此,进一步探索对HMA具有最佳治疗反应的疾病亚组非常关键。此外,由固定剂量Cedazuridine(一种胞苷脱氨酶抑制剂,可以提高HMA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DAC组成的口服制剂在一项Ⅱ期随机试验中表现出与标准剂量DAC相似的安全性及疗效,有望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治疗依从性,同时改善整体生存结局[6]。
二、特异性分子靶向治疗
1.GM-CSF抗体:在对CMML患者的髓系祖细胞进行体外培养时,NRAS、KRAS、CBL等RAS通路基因突变的CMML细胞体现出对GM-CSF的高度敏感,其自发性或外源性GM-CSF刺激后的集落形成能力明显增强,而加入抗GM-CSF抗体可显著抑制该过程[7]。上述研究结果提示,GM-CSF可能是从外在的细胞功能层面抑制CMML发生、发展的潜在靶点,尤其是对RAS通路基因突变的患者。此外,CMML患者体外高自发性集落形成能力与较差的总生存期和无白血病生存期显著相关,并且与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及外周血存在原始细胞等预后因素比较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8]。因此,靶向GM-CSF的治疗值得进一步探索。Lenzilumab是一种人源化的GM-CSF单克隆抗体,一项多中心Ⅰ期临床试验纳入了15例难治性及不适合或不耐受HMA治疗的CMML患者,Lenzilumab单药治疗未出现严重不良事件,15例患者中有1例达到部分骨髓反应,3例达到临床获益,ORR为33.3%,在RAS通路突变的CMML患者中可能具有更好的治疗反应[9]。由于该研究包含了难治性CMML患者,其疗效仍需在更大样本量的临床试验中进行验证。
2.JAK抑制剂:约10%的CMML患者存在JAK2突变并产生功能增益,但研究发现,在无JAK2突变的多种情况下仍可观察到JAK-STAT通路的过度激活。例如RAS相关基因突变的CMML细胞对GM-CSF高度敏感,而GM-CSF受体可通过异二聚体形成激活JAK2,引起下游信号分子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5(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STAT5)磷酸化并触发信号转导过程。此外,研究表明,CBL蛋白(一种E3泛素连接酶)可以通过LNK介导使活化的JAK2泛素化,下调其稳定性和信号转导过程,而CBL错义突变导致其功能缺失可以增加JAK2蛋白水平,促进JAK2信号通路的激活,并且加入JAK2抑制剂可以显著减少CBL缺失小鼠体内的异常造血细胞,减缓髓系白血病发展[10]。上述研究结果提示,RAS通路基因突变的患者也可能成为JAK抑制剂的潜在获益人群,此类药物可能对包括JAK2突变在内的相当一部分CMML患者具有积极作用。一项使用JAK抑制剂Ruxolitinib治疗CMML患者的Ⅰ/Ⅱ期临床研究证明了其安全性和潜在疗效,根据MDS/MPN国际工作组的疗效标准,50例CMML患者中有19例(38%)至少达到临床获益,43%达到脾脏反应,并且在增殖型CMML和发育异常型CMML的亚组中疗效相似,在既往接受过HMA治疗的患者中同样也观察到了临床获益[11]。Assi等[12]对包含17例CMML患者在内的MDS/MPN队列接受Ruxolitinib和AZA联合治疗的疗效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其ORR为57%,患者耐受性良好,为CMML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
3.髓系细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兴起为癌症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这类药物可以通过阻断免疫检查点通路所涉及的受体或配体,重新激活T淋巴细胞,唤醒强大的免疫防御体系以杀伤肿瘤细胞。但由于与实体肿瘤具有不同的免疫逃逸机制,这一抗癌利器在恶性血液病中尚未体现其优势[13]。白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B4(leukocyte 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 B4,LILRB4)是一种在正常单核细胞、肿瘤性单核细胞、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pDC)中限制性表达的免疫抑制受体,尤其在AML的M4或M5亚型中表达明显升高,可以通过APOE/LILRB4/SHP-2/UPAR/ARG1信号通路抑制T淋巴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促进肿瘤性单核细胞的免疫逃逸和侵袭[14]。在白血病小鼠模型及人白血病细胞的体外实验中,LILRB4缺失或被相应抗体阻断可阻止AML发展,并且不会对正常细胞形成显著干扰,可能是由于正常单核细胞与白血病细胞中LILRB4的信号通路有所不同[14]。Chien等[15]对CMML患者中LILRB4的表达情况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组及MDS患者比较,CMML患者中LILRB4 RNA水平明显增加,进一步为靶向LILRB4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CMML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IO-202是首个靶向LILRB4的单克隆抗体,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关于IO-202单药治疗复发/难治性AML和CMML患者的多中心、开放标签的Ⅰ期临床研究(NCT04372433)。此外,RNA测序表明,在CMML患者中免疫检查点CTLA-4与LILRB4的表达呈正相关,抗LILRB4单抗和抗CTLA-4药物的联合应用可能具有更好的疗效[15]。
4.靶向CD123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白细胞介素-3(interleukin-3, IL-3)由活化的T淋巴细胞产生,在造血平衡的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作为IL-3受体的α亚单位,CD123在AML、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瘤等多种恶性血液病中存在过表达,并且与AML预后不良有关[16]。在20%的CMML患者骨髓中可以观察到CD123过表达的pDC克隆,它们属于白血病克隆的一部分,并且与较高的AML转化风险密切相关[17]。目前针对CD123的靶向治疗在AML和MDS的临床前研究中已体现出较高活性[18, 19]。Tagraxofusp是由人IL-3与截短的白喉毒素形成的融合蛋白,具有靶向CD123的细胞毒性作用,即使对CD123低表达的AML细胞,Tagraxofusp也高度活跃[18]。目前正在进行一项Tagraxofusp治疗CMML或骨髓纤维化患者的Ⅱ期临床试验(NCT02268253),阶段性数据显示,18例患者中,脾脏反应率为100%,CR率为11%[20]。
三、CMML的潜在治疗靶点
1.PI3Kδ:在多种恶性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 PI3K)通路被异常激活。PI3Kδ是由调节亚基和催化亚基p110δ组成的异二聚体,主要在白细胞中表达,具有相对较高的特异性[21]。一项在CMML细胞系中单药使用PI3Kδ抑制剂Umbralisib和联合使用JAK抑制剂Ruxolitinib的体外实验发现,白血病细胞系对Umbralisib的反应随着PI3Kδ表达的增加呈增加趋势,在对Ruxolitinib缺乏活性的细胞系中,Umbralisib可协助增加其抑制作用,提示在CMML中联合抑制PI3Kδ和JAK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靶向治疗手段[22]。另一种PI3Kδ抑制剂Pictilisib在临床前研究中也显示出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明显改善MDS/MPN小鼠白细胞增多、贫血和脾脏肿大的症状,是否可用于临床试验值得进一步探索[23]。
2.MCL-1:Bcl-2家族蛋白在调控线粒体途径的细胞凋亡中具有关键作用,根据结构和功能不同可分为BH3-Only蛋白、抗凋亡蛋白(如Bcl-2、MCL-1)和促凋亡蛋白(如BAX、BAK),不同蛋白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线粒体膜的通透性和细胞凋亡的倾向性[24]。研究发现,在Bcl-2抑制剂维奈克拉(venetoclax,VEN)耐药的AML(尤其是M5亚型)患者中,RAS/MAPK通路的激活可导致MCL-1蛋白水平升高并增强耐药细胞的稳定性,MCL-1基因沉默或使用MCL-1抑制剂可以根除耐药克隆并恢复AML对VEN的敏感度,提示RAS通路基因突变的单核细胞克隆可能通过MCL-1来逃避细胞凋亡[25]。Sevin等[26]通过BH3分析技术发现,CMML患者外周血中肿瘤性单核细胞的凋亡倾向较正常细胞降低,但在MCL-1抑制剂作用下CMML细胞可恢复凋亡,在小鼠模型中也显示出一定治疗活性和安全性。此外,部分CMML中存在RAS/RAF/MEK/ERK MAPK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研究表明,联合使用MEK1/MEK2抑制剂和MCL-1抑制剂可以在不损害正常单核细胞的情况下协同促进CMML细胞的凋亡,而这种协同作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促进MCL-1蛋白的降解来实现的,MCL-1可能是CMML极具潜力的新治疗靶点[26]。
3.骨髓微环境修复机制:很多情况下恶性肿瘤不仅仅由基因突变直接导致,而是遗传、表观遗传和微环境变化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关于CMML治疗靶点的探索多集中于白血病细胞内部的分子事件,或许可以突破细胞本身的限制,以肿瘤细胞外围的致病机制作为治疗靶点,如细胞间的相互作用、组织间的分子介质等。骨髓微环境是调节造血过程的关键因素,有研究表明,骨髓微环境中细胞因子、非造血细胞的异常以及炎症、缺氧等均参与了MDS的发病[27]。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和巨噬细胞是骨髓造血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白血病进展过程中伴随着骨髓MSC功能的退化,并且在骨髓内输入健康的MSC可通过对巨噬细胞重新编程促进骨髓微环境的恢复,改善造血功能并延长小鼠的生存时间[28]。徐若豪等[29]通过体外细胞学实验证实,多数CMML患者骨髓成纤维集落形成单位产生数量明显降低,提示骨髓MSC功能受损可能在CMML疾病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骨髓微环境修复机制中的关键成分是否能够成为阻止CMML患者疾病进展的潜在作用靶点值得进一步探索。
4.炎症因素:MDS和CMML患者在疾病确诊之前可能存在不确定潜能的克隆性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 of indeterminate potential, CHIP)。研究发现,CHIP与多种炎症表现相关,如系统性硬化症患者CHIP患病率明显高于健康人,MDS或CMML患者在确诊前的5年内慢性炎症的患病率也高于对照组[30,31]。CHIP究竟是这些免疫性疾病发生、发展的使动因素,还是慢性炎症背景下的衍生产物?虽然这一问题尚不明确,但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双向影响,CHIP可能促进炎症状态的产生,全身性炎症也可能驱动克隆选择过程而促进肿瘤发生,由此,靶向炎症途径中关键因子的治疗可能具有同时抑制肿瘤发展和改善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双重作用。
四、展 望
目前CMML的治疗选择相对有限,缺乏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法,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治疗靶点被发现,如GM-CSF或其受体、JAK/STAT信号通路、免疫检查点、特定细胞分化抗原、抗凋亡机制等,但相应的靶向药物在临床实践中尚未得出确切结论,甚至仍处于设想或体外实验的探索阶段,因此仍需开展深入研究。此外,继续挖掘CMML所涉及的关键病理生理过程有助于寻找更多新的治疗思路,如CMML的基因突变无明显特异性,那么相似的分子遗传学背景如何导致截然不同的疾病表型,不同基因突变如何产生相似的临床表现,遗传学、表观遗传学、造血微环境等不同层面的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具有怎样的贡献,还需要进一步实验验证和阐述。此外,具有不同临床特征的患者可能对药物的治疗反应不尽相同,在临床试验中细化患者分组将有助于寻找该药的最佳获益人群,最大程度发挥分层治疗、个体化治疗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探索不同的联合用药方案也有利于取得更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