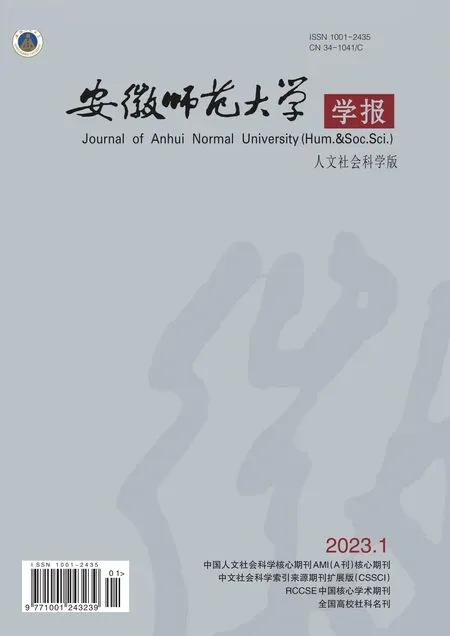“诗各有体,不可混一”
——山水诗、田园诗、田家诗的类型规律*
2023-04-05陈文忠
陈文忠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山清水秀的诗意江南,催生了幽美的山水诗;乡土中国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宁静的田园诗和淳朴的田家诗。山水诗、田园诗、田家诗,是中国诗歌史上题材相联,旨趣相近、风格最为相似的三类作品。因此,今人往往把山水诗和田园诗视为一派①参见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田园诗与田家诗则视为一家。有的学者虽明确指出山水诗与田园诗描写对象不同,但具体论述时又合为一体了②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8页。。其实,从诗歌史看,这三类诗歌渊源不同,体性不同,艺术旨趣和精神风貌也有本质区别;从诗学史看,对三类作品体性的异同,古代诗论家即有深入论述,今人钱锺书更有精辟论断。本文先简要考察古今诗学对三类诗体的论述,再借鉴朗松的“类型的晶化成型规律”理论,以典范作品为例,参酌钱锺书的论述,对三类诗体的类型规律作比较阐述。艺术创造贵在具有独创性,审美眼光贵在发现独特美。明确区分三类诗体的异同,在作品鉴赏和诗歌史研究时,就能做到体性明确而边界开放,既见其同而更见其异。
一、“诗各有体,不可混一”
中国诗学有严格的辨体传统,得体与失体,甚深微妙,间不容发。山水诗、田园诗、田家诗同样如此。这三类诗体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诗篇标题、题材归类到体裁定型逐步演进的过程;山水诗与田园诗,始者分而论之,继而连类对照,在对照中强调各自的体性特点。
(一)诗体的形成过程
“山水”作为诗题,出现较晚,亦不多见。《诗经·国风》有《山有扶苏》《山有枢》《泉水》《扬之水》等等,但并无以“山水”为题的诗篇;且虽题中有“山”有“水”,只是比兴之句,而非吟咏对象。直至盛唐皇甫冉《题画帐二首》中,方见题画诗《山水》一绝:“桂水饶枫杉,荆南足烟雨。犹疑黛色中,复是雒阳岨。”①彭定求等:《全唐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29页。在《全唐诗》中,以“山水”为题的作品,似仅此而已。
“山水”作为专论诗歌题材的概念,晋宋诗学已较普遍。《世说新语·容止》中孙绰论庾亮诗有“玄对山水”之语,《游石门诗序》之道人论游石门诗有“因咏山水”之说。最早从理论上论述山水诗的兴起和特点的,当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②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前句讲山水诗的渊源兴起,后句讲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的艺术特点;而在阐明诗体源流的“明诗”篇中,论“体有因革”时讲“山水方滋”,自然表明“山水诗体”的兴起成熟。
“山水诗”作为独立的文体概念,见于王昌龄《诗格》,曰:“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运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③王大鹏等编选,吴小如审订:《中国历代诗话选》(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8-39页。这段话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明确提出了“山水诗”的概念,“山水”一词由此发生了从“题材”到“体裁”的转变;而且阐述了山水诗意境的景色选取、运思特点和创造过程,比之刘勰的描述更为深入。山水诗的发展,经过宋初的大小二谢,到盛唐的王、孟,已达到高度成熟的化境,这应是《诗格》正式提出“山水诗”概念的现实基础。唐宋以后,“山水诗”作为独立诗体,已成为诗家常谈。如白居易《读谢灵运诗》:“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洩处。洩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④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页。在后世的诗话诗评中,有的把“山水诗”称为“游山诗”。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⑤沈德潜:《说诗晬语》,载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50页。云云。在不究概念统一性的古典诗学中,这是常见现象。
“田园”一词,同样经历了诗题、题材到体裁的演进。东汉张衡的抒情小赋《归田赋》,不仅在辞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在山水田园诗文史上也具有多重意义:一是在田园诗正式产生之前,已把“归田”或“田园”作为诗文题目;二是对山水风光的描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山水诗;三是它所表现的赞美隐遁的主题,则直接导致了陶渊明《归去来辞》和《归园田居》。此后,“田园”“田舍”一词,频见于陶渊明的诗题,如《归园田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等等。“田园”一词,由此开始从“个别诗题”转变为“一类题材”。至盛唐,终于出现了大量“田园诗”和“田园诗人”。
从体裁意义上论及田园诗的,当发端于钟嵘《诗品》评陶渊明一章。其曰:“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实。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①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这里的“田家语”,似对流行见解的否定;但由于它所评论的对象是作为“田园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加之《诗品》在诗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为体裁的“田园诗”和“田家诗”应是由此发端而来。此后,从唐代王维的《田园乐七首》《春日田园》《淇上即事田园》直至南宋范成大的《田园四时杂兴六十首》等等,以“田园”为标题的诗作大量出现,标志着“田园诗”作为一种体裁的确立和发展。
“田家诗”不同于“田园诗”,如果说田园诗的主人公是归隐田园的文人士大夫,那么田家诗的主人公则是世居乡村、力田务农的农夫。乡土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田家诗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诗经·豳风·七月》。《七月》全篇用“赋”的手法,以节序为脉络,铺叙了西周一个农民家庭一年四季的“田家生活”。首章就展示了一幅繁忙的“春耕图”:“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在内容上,姚际恒《诗经通论》指出:《七月》中有“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田家生活,无不具备。在艺术上,方玉润给予高度评价:“今玩其词,有朴拙处,有疏落处,有风华处,有典核处,有萧散处,有精致处,有凄婉处,有山野处,有真诚处,有华贵处,有悠扬处,有庄重处。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晋、唐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见臻此境界。”②方玉润:《诗经原始》(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6-307页。在方玉润看来,《七月》不仅是田家诗之祖,也是田家诗的最高典范。除《七月》,《魏风》中的《十亩之间》、《小雅》中的《甫田》《大田》都是描写农桑劳动的农事诗和田家诗。
秦汉以后,“田家”一词,频见于诗题和诗句中,如西汉刘章的《耕田歌》、陶渊明《西田获早稻》“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云云。至唐代,“田家诗”大量涌现,如王维《渭川田家》、孟浩然《田家元日》《田家作》、储光羲《田家杂兴》《田家即事》等等,它标志着作为独立体裁的田家诗的正式确立。不过,由于不少诗人以“田家”为题的作品,写的并不是“田家苦”,而是“田园乐”;因此,古代诗学中“田家诗”与“田园诗”两个概念往往混而不分。直至清代,依然如此。沈德潜《说诗晬语》曰:“援引典故,诗家所尚,然亦有羌无故实而自高,胪陈卷轴而转卑者。假如作田家诗,只宜称情而言;乞灵古人,便乖本色。”③沈德潜:《说诗晬语》,载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下),第549页。这里的“田家诗”,实质是指陶渊明“羌无故实而自高”的“田园诗”。“田家诗”与“田园诗”,有“苦”“乐”之别,对二者作明确区分的是今人钱锺书。具体观点,后文再论。
(二)诗体的连类比较
始者分而论之,继则连类对照。较早把山水诗和田园诗连类而论的是诗人白居易。不过,他对山水诗和田园诗的连类,不是审美异同的比较,而是对诗歌创作中“溺于山水、偏于田园”倾向给予批评。白居易《与元九书》论六义之道的兴衰时写道:“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④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1页。白氏诗学强调“美刺比兴”,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重视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讽喻性。因此,他表达了对谢灵运“溺于山水”的山水诗和陶渊明“偏于田园”的田园诗的不满之意。白居易基于伦理主义的批评不免偏狭;但他把山水诗与田园诗连类对照,正说明两种诗体已经各自成立,各有体格,各具风貌。
此后,对山水诗与田园诗,或分而论之,或连类对照,代有其人。元代方回的大型唐宋律诗选《瀛奎律髓》按题材把诗歌分为49 类,其中有“山岩类”和“川泉类”,把山水诗又细分为“游山”和“玩水”两类,田园诗则告阙如。方回《瀛奎律髓序》曰:“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⑤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田园诗的阙如,可能与选诗的体裁限制有关,也与方回注重“诗格”的选诗标准有关。
从诗学理论上对山水诗与田园诗作连类对照,并揭示各自的审美特点,初见于清初王士祯。王士祯力主“诗各有体,不可混一”,从风格和渊源上对两种诗体诗作明确区分。他写道:“为诗各有体格,不可混一。如说田园之乐,自是陶、韦、摩诘;说山水之胜,自是二谢。”①何世璂:《然灯记闻》,载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在王士祯看来,田园诗与山水诗,不仅题材不同,而且各有传统,各具体格:写作田园诗,应当接续陶、韦、摩诘的传统,写出“田园之乐”;写作山水诗,则应当接续二谢的传统,着意“山水之胜”。王士祯的看法体现了诗学的辩体传统,并对清代诗坛产生深刻影响。沈德潜《说诗晬语》即分而论之,论田园诗曰:“假如作田家诗,只宜称情而言,乞灵古人,便乖本色。”论山水诗曰:“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蜀中山水主险隘,永州山水主幽峭,略一转移,失却山川真面。”②沈德潜:《说诗晬语》,载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下),第550页。云云。
钱锺书则更进一解,从《谈艺录》到《管锥编》,先后提出两个命题,对山水诗与田园诗、田园诗与田家诗,分别进行连类比较。这两个命题以经典的钱氏句式,通过精选的语词和鲜明的对比,精辟揭示了三类诗体的艺术特点和微妙关系。
关于山水诗与田园诗,钱锺书提出了“山水之赏别于田园之乐”的命题。在论述谢灵运《山居赋》时,他写道:“‘昔仲长愿言,流水高山’云云。按此节以山水之赏别于田园之乐,足征风尚演变;‘惜事异于栖盘’,‘孰嘉遁之所游’,即谓隐遁之适非即盘游之胜。”③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89页。所谓“山水之赏别于田园之乐”“隐遁之适非即盘游之胜”,精当地揭示了山水诗与田园诗在艺术旨趣和审美情调上的区别。
关于田园诗与田家诗,钱锺书提出“劳农力田异于逸农行田”的命题。在比较储光羲与王维的田园诗时,他写道:“储太祝诗多整密,惟《同王十三偶然作》第一、第三首、《田家杂兴》,淳朴能作本色田夫语,异于右丞之以劳农力田为逸农行田者。”④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页。所谓“淳朴能作本色田夫语”“劳农力田异于逸农行田”,同样精当地揭示了田园诗与田家诗在艺术旨趣和审美情调上的区别。钱锺书的这两个论断,言简意赅,论旨鲜明,立足文本,囊括历史,包含丰富的理论历史内涵,足以启发我们对山水诗、田园诗、田家诗的审美特征做深入思考。
丹纳说:“只有详尽的例子才能提供明确的观念。”⑤[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丹纳后辈、法国文学史家朗松,对丹纳观点做了理论升华,提出了著名的“类型的晶化成型规律”:
类型的晶化成型规律——三个条件:若干杰作、一套有利于别人进行模仿的完善的技巧、一套统摄这套技巧的权威理论。第一个条件居于支配地位,使后两个条件得以出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作品是在此之前出现的作品的复制品,或者是用它们的碎片拼凑出来的东西。⑥[法]朗松著,徐继曾译:《朗松文论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页。
朗松所谓“类型的晶化成型规律”或“类型规律”的形成,亦即从“若干杰作”中可以得出一种“文体类型”的一套技巧和一套理论,用以作为新作品创造的原则和艺术鉴赏的方法。用歌德的话说就是:“真正的艺术品包含着自己的美学理论,并提出了让人们藉以判断其优劣的标准。”⑦[英]约翰·格罗斯编,王怡宁译:《牛津格言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本文拟从钱锺书的命题出发,参酌古代诗学,提供“详尽的例子”或“若干杰作”,力求从中概括出三类诗体各自的技巧和理论,并对三类诗体的类型规律作比较阐述。
陶渊明(365—427)是田园诗之祖,谢灵运(385—433)是山水诗之宗,田园诗的成熟独立早于山水诗。为论述方便,先说山水诗,次说田园诗,再说源远流长的田家诗。
二、山水诗:“山水之赏别于田园之乐”
“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区别,钱锺书以“山水之赏”与“田园之乐”对举,以“盘游之胜”与“隐遁之适”对举。“山水之赏”的“赏”,是盘游观赏之“赏”,就是在行旅盘游途中,游览观赏山水之胜;山水诗的艺术特质,就蕴含在“盘游观赏”的“赏”字之中。一个“赏”字,揭示了山水诗的创作情境和审美特质。
中国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国度,江河蜿蜒盘旋,山岩千姿百态,是中国最鲜明的地貌特征。山水进入诗歌,始于《诗经》,如《小雅·采薇》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文心雕龙·物色》视其为“写气图貌”的典则。不过,从“物色”到“景色”,从“写山水”到“山水诗”有一个发展过程。“诗文之及山水者”,钱锺书分为三个阶段:“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继乃山水依傍田园,若茑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谢灵运《山居赋》……皆‘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即指此也。终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袁崧《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①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7页。山水诗的发展,与之相仿佛,“山水诗是在结合着表现生活的要求上成长出现的。最初作为诗歌内容的起兴,之后形成更广泛的结合,最后在大量的作品中才出现一些单纯写山水景物的诗篇”。②林庚:《唐诗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从诗体发展史看,从东汉到晋宋,山水诗又经历了从游览诗、行旅诗、招隐诗、游仙诗、玄言诗、再到山水诗的发展过程③[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104页。;同时,在创作上它充分吸收了从游览诗到玄言诗的艺术因素和艺术经验。
曹操的《观沧海》是最早的一首独立完整的山水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浩洋动荡涵于淡朴之中,有吞吐宇宙气象;在艺术上,似非单纯写景,而是赋中有比,英雄登临,赋王霸之志,志在容纳,以沧海自比。晋宋之际,诗体的因革之功首推谢灵运。谢灵运在出仕或盘游途中,游山水,观山水,写山水,成为中国第一位山水诗人,提供了山水诗的艺术范例和规则。“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以名山秀水为背景,盘游、山水、观赏,是山水诗的三大要素:盘游是创作契机,山水是描摹对象,观赏是审美态度;作为抒情主体的盘游观赏之人,则是钟情山水、有闲情逸趣,更是生活富裕、悠哉游哉的士人或文人。正如小尾郊一所说:“谢灵运出身于当时被称为‘王谢’的豪族,是地主阶级之一员……即使在隐栖中,生活也不会感到困难。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悠然地游览山水。使他作出那种山水诗的,虽说是他的文才,也可以说是他经济方面的富裕。可以说,山水诗一般是由贵族阶级的趣味所产生的。”④[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第106页。谢灵运的山水诗,就是这位作为贵胄之后的诗人,在悠闲的盘游途中,游览观赏山水之胜的艺术结晶。这便是山水诗这一审美类型最基本的“晶化成型规律”。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是谢氏山水诗的杰作之一: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
俛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
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⑤谢灵运著,顾绍伯校注:《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下引谢灵运诗皆出自本书,不再一一作注。这首诗写于元嘉元年(425)的春天。这一天,诗人自南山新居经过巫湖返回北山故宅。一路上,游览山水,观赏美景,兴致无厌,直有与物俱化之想。开头两句,写清晨从南山出发,傍晚到达北山,点明题目,也点明行程。“舍舟”以下十四句,写诗人途中舍舟登岸,眺望湖光山色,细腻的笔触,细致入微地描摹出一幅江南春色图。开阔的洲渚,茂密的松林,蜿蜒的蹊径,淙淙的流水,嫩绿的初篁,新鲜的蒲茸,自娱的群鸟,美丽的春景,络绎不绝,像一个个镜头展示我们在眼前,读者有“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之感。最后六句,诗人借景抒情,发出孤游无侣之叹。而“山水之赏”,在行旅途中游赏山水之美,则成为全诗的中心。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作为谢氏山水诗的经典之作,呈现出谢灵运山水诗在结构、技巧、风貌上的基本特色。在结构上,先叙出游行程,次写山水美景,最后或发感叹或谈玄理;在技巧上,以细微的观察作精工的描摹,“有点像一个旅行记者,一路上随处用精妙的照相技术拍下新鲜的风景镜头”①林庚:《唐诗综论》,第59页。;在风格上,意象清新自然,语言工整精炼,鲍照所谓“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谢灵运的山水佳作不少,如《七里濑》《登池上楼》《游南亭》《登江中孤屿》《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石门岩上宿》《入彭蠡湖口》等等,无不写景优美,风格清新,脍炙人口。
谢灵运是中国第一位山水诗人,也是最杰出的山水诗人。严羽《沧浪诗话》所谓:“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但严格地说,谢灵运之作并非篇篇完美无瑕。前人对他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有句无篇,即佳句多而名篇少,传诵的多是写景名句;二是造语生僻,即过于求新奇、尚巧似而有生造词语之嫌;三是玄言的尾巴。山水诗脱胎于玄言诗,经历了从“玄对山水”到“游赏山水”的过程。他的山水诗尚未摆脱玄言诗影响,最后往往拖个“玄言的尾巴”。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诗写诗人游石壁山寺院后,入湖驾舟返回旧宅途中所见的夕景,是一首典型的谢氏山水诗:从要素看,盘游、山水、观赏,三者俱足;从结构看,出游、赏景、谈玄,有条不紊。山水美景的动态游赏,则是全诗的核心:“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语言清新,意境优美,如初日芙蓉,自然可爱。但结尾的“谈玄”,与前面的写景,若接若离,有断裂之感。倘与苏轼《题西林壁》相比,两篇作品在情景交融、理趣盎然上,尚有一间之隔。
不过,谢灵运在山水诗发展史上的开创之功和宗师地位是无可争议的。王渔阳有经典论述,②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116页。在他看来,谢灵运之于山水诗,始则“创为刻画山水之词”,继则“宋齐以下,率以为宗”,终则唐代山水之奇怪灵秘皆“滥觞于康乐”。
唐代是诗国的高潮,也是山水诗高度发展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山水诗人,创作了一大批更纯熟、更具神韵的山水诗。短篇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孟浩然《宿建德江》、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杜牧《山行》;中篇如王维《汉江临眺》《终南山》、杜甫《望岳》、王湾《次北固山下》;长篇如杜甫《龙门阁》、李白《蜀道难》等等,都是山水诗中的杰作。
经过唐代这批大家的匠心揣摩,山水诗创作终于达到辉煌的顶点和艺术的至境。清人朱庭珍《筱园诗话》曰:“夫文贵有内心,诗家亦然,而于山水诗尤要。盖有内心,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探天根而入月窟,冥契真诠,立跻圣域矣。”③朱庭珍:《筱园诗话》,《清诗话续编》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4页。这是一个深刻的见解。唐代的山水诗就达到了这个境界:超越形似,致力神似,追求神韵;诗人对山水的刻画,不滞于山容水态,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同时,诗人成了山水的朋友,山水成为诗人的化身;“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人和山水达到融为一体的化境。如王维的《汉江临眺》:“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①王维著,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下引王维诗皆出自本书,不再一一作注。这首诗是王维融画法入诗的佳作。诗人胸中有一段浩然广大之致,起笔以宏阔的视野,大处着笔,把汉江给予诗人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写了出来。中间两联皆写景,而前联尤壮,足敌杜甫、孟浩然《岳阳》之作。“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前句雄阔,后句缥缈,像一幅水墨画,把南国水乡空气的湿润和光线的柔和表现得恰到好处。前六句雄俊阔大,似甚难收拾,却以“好风日”三字作结,余韵悠然。
沈德潜《说诗晬语》曰:“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略一转移,失却山川真面。”②沈德潜:《说诗晬语》,载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50页。不过,无论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南朝山水诗,还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无论是写永嘉山水或永州山水,还是写辋川山水或蜀中山水,盘游、山水、观赏,是山水诗共同的三要素;在盘游途中观赏名山秀水,进而写出不同地域山水的性情和精神,是山水诗共同的艺术要求。这也是动态游赏的山水诗不同于静态逸乐的田园诗的基本区别。
三、田园诗:“田园之乐别于山水之赏”
“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区别,正好与之相对:“田园之乐别于山水之赏”。以“田园之乐”与“山水之赏”对举,以“隐遁之适”与“盘游之胜”对举,以“静态逸乐”与“动态游赏”对举。“田园之乐”的“乐”,是复返自然之“乐”,是隐遁闲适之“乐”,是安贫乐道之“乐”。田园诗的艺术特质,就蕴含在“田园之乐”的“乐”字之中。这是远离市朝、复返自然的快乐,也是躬耕园田,安贫乐道的快乐。一个“乐”字,昭示了田园诗的创作动机和审美特质。
因此,田园诗不同于山水诗,也不同于田家诗:田园诗的主人公是归隐田园的逸人贫士,田园诗的精神旨趣本质上是一种隐逸文化。陶渊明是第一个表现“田园之乐”的田园诗人。钟嵘《诗品》所谓:“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实。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③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古代隐者,或游于山林,或退隐田园,要以退隐田园者居多。为什么?作为乡土社会的中国,人和土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人从土中来,又回到土中去,故乡故土是生命的最终归宿;退隐田园就是还归故乡,还归故土。陶渊明是退隐田园,躬耕南亩,以质朴的“田家语”写田园诗的第一人。他既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是“古今田园诗人之宗”。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陶渊明《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以故乡故土为背景,田园、躬耕、乐道,是田园诗的三大要素:田园是生活依赖,躬耕是人物活动,乐道是精神旨趣;作为抒情主体的“乐在田园”之人,则是摆脱名利、归隐田园,然而尚需躬耕自资、生活清贫的逸人隐士。山水仅供悦目,田园尚可饱腹,这也是田园诗人不同于山水诗人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小尾郊一写道:“山水诗一般是由贵族阶级的趣味所产生的。因此,陶渊明的不曾隐遁山水,以山水美为乐,虽说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因为生活不够富裕之故。同样地,虽说他也渴望隐栖,却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回到生活之基的田园。这样,他的诗才,便开始歌咏起这种田园生活来。”④[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第106页。陶渊明的田园诗,就是表现诗人复返田园后,躬耕南亩,安贫乐道,乐在田园的艺术结晶,亦是把自己的生活本身作为诗来观照的生活文学。这便是田园诗这一审美类型最显著的“晶化成型规律”。
《归园田居五首》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写于辞去彭泽令后的第二年。首篇总写归耕之乐,次篇写交往淳朴,中篇写耕作实感,四篇写探访遗迹,末篇写耕余之欢。诗中情境非具有农村生活和躬耕体验者不能道;在艺术上,则集中体现了诗人淳真、冲淡、旷达的风格。以故乡农村为背景,田园、躬耕、乐道,田园诗的这三大特点在组诗中融为一体而意味无穷。《归园田居五首》因此而成为田园诗的典范,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方东树《昭昧詹言》曰:“此五诗衣被后来,各大家无不受其孕育者,当与《三百篇》同为经,岂徒诗人云而哉!”①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所谓“当与《三百篇》同为经”,即《归园田居五首》与《诗三百篇》一样,均可奉为诗国经典。《归园田居·其一》是组诗之冠,也可视为诗总序,最为读者传诵: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②陶渊明著,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7页;下引陶渊明诗皆出自本书,不再一一作注。一幅安享“田园之乐”的村居图。“返自然”三字,道尽复返园田之乐;“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村朴之语写尽田家野老景色。方东树《昭昧詹言》对此诗有极高评价,对全篇又有精彩的细读:“此诗纵横浩荡,汪茫溢满,而元气磅礴,大含细入,精气入而粗秽除。奄有汉魏,包孕众胜。后来惟杜公有之……‘少无适俗韵’八句,当一篇大序文,而气势浩迈,跌宕飞动,顿挫沉郁。‘羁鸟’二句,于大气驰纵之中,回鞭亸鞚,顾盼回旋,所谓顿挫也。‘方宅’十句不过写田园耳,而笔势搴举,情景即目,得一幅画意。而音节铿锵,措词秀韵,均非尘世吃烟火食人语。‘久在’二句接起处,换笔另收。”③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第106页。围绕“田园之乐”这一中心,娓娓道来,逐层分析,诗艺诠释,细致入微。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诗人出“樊笼”,返故乡,归田园,开始躬耕自资,安贫乐道的生活,写下了一系列歌唱“田园之乐”的诗篇。如《移居》《怀古田舍》《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饮酒·其五》《读山海经·其一》等等。再以《读山海经·其一》为例: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共十三篇。首篇写孟夏之日,躬耕之余,兴会所至,览传观图的惬意情境,是后十二首之纲。绿树、众鸟、耕种、摘菜、饮酒、读书,王士祯《古学千金谱》对诗篇表现的“田园之乐”作了亲切的演绎:“时当初夏,草木宜长,扶疏之树,绕我屋庐,不但众鸟欣然有此栖托,吾亦爱吾庐得托扶疏之荫。既耕田,复下种,还读书而候古人,吾庐之乐事尽矣。车大则辙深,此穷巷不来贵人,颇迥故人之驾。欢然酌酒,而摘蔬以侑之,好风同微雨,俱能助我佳景,乃得博欢图传,以适我性。如此以终宇宙,足矣。若不知乐,又将如何哉!”④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下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1页。诗篇把“田园之乐”表现得令人神往,评家把“田园之乐”演绎得淋漓尽致。
田园诗的发展进程与山水诗有所不同。山水诗到唐代方臻化境,田园诗则在陶渊明笔下已达至境。南朝三百年间,除陶渊明而外,几乎没有可称述的田园诗。唐代以后出现不少田园诗人,但其精神风貌远不及陶渊明。沈德潜《古诗源》论及陶诗影响,曰:“清远闲放,是其本色,而其中自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几及处。唐人王、储、韦、柳诸公,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⑤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2-183页。在沈德潜看来,陶渊明“清远闲放”的作品,是田园诗的最高典范,其“渊深朴茂”之风神,唐代诸家均难以企及。不过,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山居秋暝》、储光羲的《田家即事》《田家杂兴》、韦应物的《滁州西涧》,以及杨万里的《初夏睡起》《桑茶坑道中》、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等等,仍是田园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王维的《渭川田家》最能体现陶诗神韵: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夕阳西下,夜幕将临之际,诗人面对一幅恬然自乐的田家晚归图,油然而生羡慕之情。诗的核心是一个“归”字:牧童牛羊归,田夫荷锄归,野老静候家人归;田家“闲逸”的归家图,引发了诗人归田园、返自然的内心冲动。王世贞评曰:“田家本色,无一字淆杂,陶诗后少见。”①转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译》(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渭川田家》确是王维田园诗中“瓣香陶柴桑”的得意杰作。
深入把握田园诗的特征,可把“田园诗”与“园林诗”作一比较。“田园”一词,有“田”“园”之分;田园诗与园林诗的区别,“主要的是田还是主要的是园”。林庚指出:魏晋以来士大夫“雅好园林”,但他们的“园”,大多是“庭苑园林”之“园”,而不是“躬耕田园”之“园”;在描写“庭苑园林”的诗中,“绝大多数情况,田在这里并不是以田的性格出现,而是以园的性格出现”。②林庚:《唐诗综论》,第61-62页。如沈约《行园诗》:
寒瓜方卧垄,秋菰亦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初菘向堪把,时韭日离离。
高梨有繁实,何减万年枝。荒渠集野雁,安用昆明池③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41页。。前六句写“行园”所见:寒瓜、秋菰、紫茄、绿芋、初菘、时韭,“菘”即白菜,均为“田园”作物,故颇似一首“田园诗”。然而,从最后两句的“万年枝”和“昆明池”可以见出,作者身在“田园”而心在“庭苑”,眼中所见是“园圃”中的观赏之物,而不是“田园”中的躬耕所获。因此,这首诗本质上是士大夫“雅好园林”的“园林诗”,而非贫隐士“躬耕田园”的“田园诗”。沈约的《宿东园》、萧纲的《夜游北园》、庾信的《寒园即目》等等,大抵如此。这些作品旨趣有深浅,描写有详略,诗艺有巧拙,但诗中的“园”,均非隐逸之士的“躬耕田园”之“园”,而是达官贵人的“庭苑园林”之“园”。
至此,可以对山水诗与田园诗的类型规律及审美异同作一比较,至少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从抒情主体看,作为山水诗的“盘游观赏”之人,应是一位钟情山水,有闲情逸趣,更是生活富裕,悠哉游哉的士人或文人;作为田园诗的“乐在田园”之人,则是一位摆脱名利,归隐田园,然而尚需躬耕自资,生活清贫的逸人隐士。陶谢之别,即在于此:“渊明性本恬淡,康乐情甚热中。恬淡而家国遭变,故放志田园,而常怀难言之隐;热中而仕途偃蹇,乃寄情山水,而多愤懑之词。”④顾学颉:《顾学颉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第二,从审美要素看,以名山秀水为背景,盘游、山水、观赏,是山水诗的三大要素:盘游是创作契机,山水是描摹对象,观赏是审美态度;以故乡故土为背景,田园、躬耕、乐道,则是田园诗的三大要素:田园是生活依赖,躬耕是人物活动,乐道是精神旨趣。
第三,从审美态度看,山水诗偏于风景的客观描写,田园诗偏于自然的主观写意;严羽所谓“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斯波六郎有精要的发挥:“渊明是主观的、概括的、以全身心来接触的;与此相反,谢灵运是客观的、局部的、以感觉来对待的。”⑤转引自[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第109页。
第四,从审美意境看,山水诗和田园诗都追求一种“静”的境界,但山水诗的“静寂”,不同与田园诗的“闲静”。中国的游仙诗、招隐诗、田园诗和山水诗都着意表现“静境”,但意境风貌,各不相同。正如小尾郊一所说:“陶渊明描写得最多的是闲静和穆的自然……这种闲静的境界,与仙境和隐栖地的闲静不同,表现了农村闲静和穆的样子。仙境和隐栖地的闲静,是脱离俗尘和人事的静寂。陶渊明的闲静,是虽在人事俗世之中,而又超脱于它们之外的闲静,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这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的静寂境界也是不同的。”①[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译:《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第107-108页。
抽象的理论概括,具有条理分明要言不烦的长处,但它以牺牲具体性和特殊性为代价。在运用“类型规律”分析具体作品时,必须充分警惕理论的陷阱,以免削足适履。
四、田家诗:“劳农力田异于逸农行田”
“田家诗”与“田园诗”的区别,钱锺书以“劳农力田”与“逸农行田”对举:田家诗的“劳农”,不同于田园诗的“逸农”;劳农的“力田”,不同于逸农的“行田”。“田家诗”就是以淳朴的“本色田夫语”,表现“劳农力田”艰辛困苦的作品。如果说田园诗的特质在于表现“逸农行田”之“乐”,那么田家诗的特质就在于表现“劳农力田”之“苦”。
中华文明是一种的农耕文明。一块田、一间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本色的的生存方式。男耕女织的田家生活,也最先成为诗歌题材。相传尧帝时代的《击壤歌》就是一首“劳农力田”的“田家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古诗源》)诗的前四句以四个排比句,生动描述了原始先民力田劳作的辛勤生活。华夏民族就是在人与土地的这种循环中,在劳农力田的辛勤耕作中,生生不息,顽强奋斗,逐步发展过来的。如前所述,《诗经·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也是一首“四时田家诗”,叙述了农夫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和艰苦生活。《七月》第一章“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和“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即衣食双起,管领全诗。民以食为天,重农是中国的传统。两汉以后,历代都有“农事诗”和“劝农诗”。陶渊明《劝农》诗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莫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情理深远,殷殷之意,溢于言表。
唐宋以后,随着土地不均,社会分化,贫富对立,出现了大量反映“田家苦”的“田家诗”。唐代如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宋代诗坛“田家诗”更多。仅钱锺书《宋诗选注》就选入20 余家近30 首。如梅尧臣《田家》《田家语》、刘攽《江南田家》、陈师道《田家》、杨万里《悯农》、范成大《催租行》《后催租行》、章甫《田家苦》、赵汝鐩《耕织叹》等等。杨万里的《插秧歌》,便描绘了一幅全家齐上阵的“劳农力田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衰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②杨万里著,周汝昌选注:《杨万里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18页。
梅尧臣的《田家语》则可视为“田家诗”的宣言书,诗人借“田家之言”,把悲叹“田家苦”的“田家诗”,与歌咏“田园乐”的“田园诗”,做了明确区分:
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诏书来,生齿复板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韣。
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朴;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间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
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①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开篇第一句,就把表现“田家苦”的田家诗与抒写“田家乐”的田园诗做了明确区分。以《田家语》为类型范例,田家诗与田园诗的类型区别,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人言田家乐,尔苦人得知!”(陈师道《田家》)田家诗与田园诗的第一个区别,是诗中主人公不同:田家诗的主人公是世居乡村、力田务农的农夫;劳农、力田、田家苦,是田家诗区别于田园诗的基本特点。从唐宋田家诗看,田家诗的田家“苦”,至少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劳农力田的艰苦,二是饥寒交至的困苦,三是赋税徭役的悲苦。梅尧臣的《田家语》,不仅把表现“田园乐”的田园诗拒斥于反映“田家苦”的田家诗之外,而且把田家的“三重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唏嘘不已。
田家诗与田园诗的第二个区别,是表达方式不同。如果说田园诗大多是“自述体”,即抒发诗人自己的“田园乐”;那么田家诗则大多是“代言体”,“代言”田家的种种“苦”。田园诗的作者大多是退隐田园的诗人自己,故以自述为主,把自己的生活本身作为观照对象;田家诗的作者大多是“悯农”的文人士大夫,故以代言为主,或作为田家的朋友,抒写他们所见到的田家的艰辛。《七月》的作者就是如此。针对传统的周公说,方玉润《诗经原始》指出:“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换言之,《七月》的作者绝非位居冢宰的周公,而是躬亲陇亩、深知劳农之苦的农家之人。梅尧臣《田家语》便是一首典型的“代言体”诗,“序”曰:“……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云。”章甫的《田家苦》同样如此:
何处行商因问路,歇肩听说田家苦。今年麦熟胜去年,贱价还人如粪土。
五月将次尽,早秧都未移;雨师懒病藏不出,家家灼火钻乌龟。
前朝夏至还上庙,着衫奠酒乞杯珓;许我曾为无日期,待得秋成敢忘报。
阴阳水旱由天公,忧雨忧风愁煞侬;农商苦乐原不同,淮南不熟贩江东。②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刘攽的《江南田家》与章甫的《田家苦》,主题与表达同一机杼,都是“录田家之言”,写“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的主题。《江南田家》曰:
种田江南岸,六月才树秧。借问一何晏,再为霖雨伤。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
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痏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③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第53页。
读《田家苦》和《江南田家》,令我们想起杜甫的《兵车行》和“三吏”“三别”。在艺术精神上,田家诗确实继承了杜甫以来关注现实的新乐府传统。
田家诗与田园诗的第三个区别,是生活情调不同。唐宋田家诗的主题是多样的,除写“田家苦”,也写“农家乐”。不过,“劳农”的“农家乐”,不同于“逸农”的“田园乐”:这是安居乐业的快乐,是春种秋收的欢乐,是古朴生活的怡乐。英国诗人柯珀有句名言:“上帝创造乡村,人创造城市。”④[法]让·德·维莱编,施康强等译:《世界名人思想词典》,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乡村是天然的,城市是人为的。丰年的自耕自足,和睦的田家生活,古朴的乡村习俗,清新的田园风光,常常情不自禁地流淌在诗人笔下。杨万里的《插秧歌》就不能说没有“劳农”春种的“农家乐”气氛。陆游的《游山西村》、陈造的《田家谣》、利登的《田家即事》、翁卷的《乡村四月》等等,都是表现农家乐的名篇。词人辛弃疾还写了大量以“农家乐”为主题的词。如《清平乐》“茅檐低小”、《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平凡质朴的乡村人物,丰富多彩的乡村图景,跃然纸上。今天诵读,依然余香满口。
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唐宋田家诗中最杰出的作品,也是田家诗的“集大成”之作。诗前小“引”交代写作背景:“淳熙丙午,沉疴少纾,复至石湖旧隐,野外即事,辄书一绝,终岁得六十篇,号《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绝句,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组,每组十二首。作品在当时已广为传诵,并很快出了注释本。宋人顾世名《题吴僧闲白云注范石湖田园杂兴诗》云:“一卷田园杂兴诗,世人传诵已多时,其中字字有来历,不是笺来不得知。”①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第203页。
钱锺书对组诗作了高度评价:“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仿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达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②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第193-194页。以诗史为背景,阐述了《四时田园杂兴》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征。
不过,与其说《四时田园杂兴》是“田园诗的集大成”,不妨说是“田家诗的集大成”。其一,从风格看,“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正是“劳农力田”的田家诗的特质,与“逸农行田”的田园诗有本质区别;其二,从结构看,它来自《豳风·七月》,《七月》正是反映“劳农力田”的乡土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家诗”;其三,从内容看,它来自诗人的“野外即事”,来自对“劳农力田”的观察,写的是“一年四季农村劳动和生活的面貌”,而不是诗人自己躬耕田园、安贫乐道的“田园之乐”。下面以“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为序,每组举一首,借斑窥豹:
吉日初开种稻包,南山雷动雨连宵。今年不欠秧田水,新涨看看拍小桥。
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屋上添高一把茅,密泥房壁似僧寮。从教屋外阴风吼,卧听篱头响玉箫。③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376页。
诚如钱锺书所说,“《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仿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达成一个总结”。其中不乏“逸农行田”式的作品;但是,劳农力田的“田家苦”与春种秋收的“农家乐”,则是《四时田园杂兴》的重心所在,也是写得最精彩、最为传诵的作品。
“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东篱之内是“农家”,东篱之外是“田园”,举目眺望是“山水”。山水、田园、农家,连为一体,不可分离。这是华夏农耕文明和乡土中国最本色的生存环境,也是“山水诗中有田园,田园诗中有山水,田园田家难分离”的现实根源。但是,作为艺术创作,“诗各体格,不可混一”;山水之赏有别于田园之乐,劳农力田有别于逸农行田。山水诗、田园诗、田家诗,具有不同的构成要素,不同的诗中人物,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的类型规律,并形成不同的艺术传统。与此同时,它们具有不同的精神意趣和审美价值,我们既要欣赏刻画精工、得其神似的山水诗和自然质朴、悠然自得的田园诗,也应重视“泥土和血汗气息”的田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