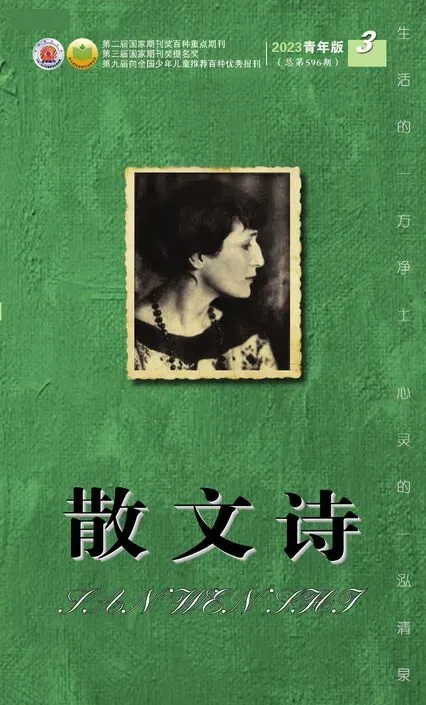第四维度
2023-04-04◎图、文/黄佳
◎图、文/黄 佳

等待发型 180cm×160cm 布面油画 1992 年
第一空间
在生活和工作中, 我一直在恪尽职守, 像钟摆一样梭巡于工作和家庭之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在创作中不断往前推进, 开始有意地将心理意识的问题屏蔽掉, 从繁琐的生活抽离出来, 在同一块色域上重复涂抹不同的色彩, 最后隐入同一色彩之中, 让所有最丰富的色彩, 都隐藏在最“虚无” 的同一色彩之中。
我试图将造型语言精练化、 纯粹化, 减少到最小的基本的线和面, 运用笔触的韵律, 不断重复在触摸画布的细枝末节中, 在不知不觉中, 隐现出的细微之间的色润变化, 将作品本身的形式注入了富有特色的暗示性意义, 也是对人们在情感状态之下感受到时间痕迹中, 色彩与空间层次的体验。
不论真实还是虚无, 色块之间被剥离、 突出、 演绎, 这些细节被赋予神秘性, 想象延续创造, 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观者在看的过程中, 分不清绘画与现实的瞬间感觉, 从而动摇观者的内心, 对正处于时间和空间中的观者的身体, 产生更强的感知意识。
老 屋
小时候, 妈妈把我放在乡下外婆家。 回城读书以后, 每到假期, 我都祈盼着回到乡下那栋开启我幻想之门的老屋, 去拥抱曾经给了我温暖和挚爱的外婆。
老屋是一座旧时的拜祭堂, 它的门前有一个大的草坪, 是晒谷场和放草垛的地方。 推开两扇临街的大木门, 进入一个天井, 天井就像一扇窗口, 春天, 我们常站在堂屋, 窥看天井外碧蓝的天空, 看小鸟从天井飞过, 看天井瓦片间隙中长出嫩绿的小草, 看下雨天大人拿来木桶接屋檐滴水, 一滴急似一滴地化成水波纹, 像在笑, 在唱。
绕过天井, 是一间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堂屋, 屋顶呈三角形, 足有两层楼高, 整个建筑近乎刻板的外表下, 里面住着两户充满了生气的人家(足有二十多口人)。 站在堂屋, 房子分成左右两边, 结构对称, 外婆一家住在右边,从堂屋第一间房进入, 穿过两间房, 然后从第四间房走出来, 居中的屋, 是没有窗的, 很高的屋顶上, 亮着几片明瓦。
整栋房子, 除堂屋和天井外, 没有一点阳光的气息。 只有当阳光从天井照到堂屋时, 整栋黑灰色的建筑物里面, 才有了一点红色的光芒。
每到星期六的黄昏,我们小孩子就跑到屋后菜园里, 看那水塘披上薄雾。夜幕自远而近, 看远山渐入朦胧, 我们望着远山,阴森森的, 依稀可见的那条小路延伸到山里, 仿佛又藏着无边的希望。 我们只盼着一个人影的出现,就齐声高喊:
外——公!
我们等待着外公回来。

日常·窥视 115cm×108cm布面油画 2004 年

日常·合影 115cm×108cm 布面油画 2004 年
当外公走进堂屋, 无数双小眼睛已经睁得溜圆,纷纷盯着外公的布袋, 希望他能带给我们一些小花片之类的零食吃。 有时,看到远山移动的人影, 就像雾里看花, 朦朦胧胧的, 也常常喊错了人。 这样的好时光总是很短暂的。 不久, 外公就去世了。 那时, 我六岁。 所有的亲人都回到了老屋, 大人们哭成了一团。 在送殡的路上, 披麻戴孝, 走了一圈又一圈, 直到我们这些小孩走不动了, 被邻居送回来, 这时, 我才对死亡有了初步的认识。
透过蚊帐, 我望着头顶上朦胧月光投射在明瓦上, 就像一双明亮的眼睛穿透灵魂, 一瞬间, 灵魂的束缚被解除, 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明瓦, 就像漆黑的云海中飘荡着的几片白帆, 仿佛要载着我飘向天边, 我开始在脑子里狂想各种梦境。 此时, 生命已经融化在漆黑的寂静与寂静的漆黑里。 我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一切, 世界没有别的, 就只有这几片白帆。 我想飞翔, 却又害怕飞离, 我使劲地拽着被子, 真希望身边有一堵人墙将我深深地埋入。 埋入, 不愿出来。 忽然, 听得蚊帐顶上嗖嗖声响起, 白帆慢慢地消失了, 一束亮光照到了蚊帐的顶上。
外婆蹑脚、 噤声地坐在我的身边。 大舅站在床边, 一手拿手电筒, 一手拿棍子, 正在蚊帐顶上飞舞着, 一会儿, 只见一条一米多长的菜花蛇被大舅捉了出去。
学 画
父亲常常感叹自己生不逢时, 因此, 他的遗憾须由我这个长女来填补。从小学到高中, 为了学画这件事, 我不知挨过父亲多少次的骂, 因此, 看到画笔就生厌, 我常站在家中墙上的一面小镜子前, 望着镜子里可怜巴巴的自己, 想着乡下的外婆和老屋里的趣事, 不知不觉地掉下伤心的眼泪。
在单位, 父母是很让人羡慕的一对, 我妈还是单位的文艺骨干分子。 我和大妹是在乡下外婆家长大的, 由于个子矮小, 皮肤黝黑, 没进过幼儿园,不会唱歌跳舞, 回到城里, 我变得更拘谨, 不爱讲话, 与城市同龄孩子相比, 显得有点呆如木偶, 而内心却很反叛。 记得刚从乡下回到城里的时候,见到父母、 邻居, 我从来不喊, 大家都说: “这孩子, 怎么像个哑巴?”

女人与皮鞋·之一 73cm×60cm 布面油画 1989-1990

站立的女人 180cm×160cm 布面油画 1996 年
一日, 全家在吃晚饭的时候, 我看到父亲严肃的表情, 心里上下打着鼓, 饭也吃不下去。 这 时, 父 亲 开 腔了:“你为什么不喜欢画画? 我小时候想学画都没有条件, 现在我给你创造了条件, 你却不学, 你想气死我吗?”我轻轻地回答:“我不喜欢画画!” 父亲睁大双眼望着我, 问到:“那你喜欢什么?” 半天过去,我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我喜欢体操!” 父亲无可奈何地望着我, 然后, 用手指着窗台对我说:“你把一只脚放到窗台上站直, 如果能坚持半小时, 我可以不要你学画。” 我走到窗前, 奋力抬起右脚, 搭在齐胸高的窗台上, 心想, 这下, 我一定要好好给自己争口气。
秒针在嘀嘀嗒嗒地走着……
我抬头望着桌子上的小闹钟, 时间才过去十分钟, 我的腿已经开始哆嗦起来, 我咬着牙, 扭头看看两个妹妹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饭, 还不时朝我做鬼脸。 爸妈一边争论我的前途, 一边注视着我站立的腿。 又过了十分钟, 左脚实在支持不住了, 急得我歪着倒向墙壁。 妈妈心痛地走到我面前, 稳稳扶住我。 这时候, 我的左脚像有成千上万只蚂蚁钻入脚心。 我用双手使劲揉搓腿脚, 好不容易, 脚才好受些了, 而我的心却更加麻木了。
原本以为学习体操比学习绘画好玩一些, 谁知才站一会儿, 腿就受不了, 我在内心感叹: 要学好一样东西,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我看着父亲那黑白分明的双眸正望着我, 他温和地走到我面前, 摸着我的头, 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要好好地学绘画, 做一个艺术家, 要知道前面的乌龟在跑,后面的乌龟才跟着爬, 要做好妹妹的榜样。”
含着泪, 我方点头默认。
春去秋来, 难得一个假日, 我们全家踏着秋日金色的阳光来到岳麓公园, 在绿色的树叶和红色的枫叶树下漫步。 我望着阳光透过枫树洒满大地,心中一片欢喜。 我和妹妹俯身, 在地上挑捡各种颜色的枫树叶, 只听到父亲的声音从后背传了过来:“佳佳你看, 那边有一对白鹤雕塑, 你去把它写生出来。” 我朝着父亲指给我的方向望过去, 那是白鹤泉, 岳麓山的一个景点,此时的白鹤泉边, 欣赏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个时候, 这种环境, 父亲叫我去写生,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我既担心画得不好丢了父母的面子, 又惧怕父亲的威严, 只好拿着速写本, 慢慢地移动脚步。 走过去, 看那白鹤、 水池、 天顶上倒映的白鹤画面,和漫天的暮色, 我执笔凝思, 却紧张得脑海里一片空白, 再好的景色此时也不能在脑子里沉淀, 只有心在加速跳动。 就这样, 我像一个木偶般立在人堆中, 茫茫然不知如何下笔。 这时, 父亲走了过来, 我匆匆地在画纸上涂抹了几笔, 算是完成任务, 结果, 遭到父亲严厉地批评。 在那么多人面前被骂,我真恨不得有一个地洞让我钻进去。
对于学习绘画, 有段时间我曾经感到极度痛苦, 每当全家出去游玩的时候, 我总是找出各种理由, 让自己留在家中, 以免出去丢丑。 而父亲为了锻炼我的胆量, 培养我的自信心, 常叫我拿着速写本去街道和菜市场写生。 父之令, 大如天,没办法,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写生。

台球桌(局部) 60cm×85cm 布面油画 1985 年
有时, 我也不免自我安慰:不就是画画吗!又不是上战场。这样一想, 心就平静了许多。 接着, 我开始搜集各种图片, 学着画漫画, 画一些中国仕女图, 久而久之, 居然在学校小有名气,许多同学开始索要我的作品, 拿回家中, 挂在墙上欣赏。 此时, 我的自信心也增强了不少, 对待画画这件事, 也不那么生厌了。
进入高中, 父亲花了几毛钱, 买了个巴掌大的维吾尔族女青年石膏头像, 他认真地示范、 讲解素描的基本技法。 我的素描学习,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后来, 父亲找熟人帮忙, 让我加入青少年宫学习班学习绘画。
高中毕业后, 父亲让我在家补习绘画, 准备参加来年的美术高考。 我一个人呆在家中, 倍感无聊, 又要受到父亲的监视, 就一心想摆脱他对我的管教。 于是, 我鼓动父亲带我到湖南师大找老师学习, 经老师介绍, 我进入长沙人民艺术专科学校学习。 当时, 艺校的地址在渔湾市农民房, 离我们家有二十多里地, 父亲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一辆二八式的旧单车, 自己动手给我做了一个画夹, 然后, 用三夹板锯了一个长方形木盒子钉上, 再用锯子从横切面锯开, 装上搭扣, 切出一小段皮带做把手, 这样, 我就有了一个画箱。
第二天, 我剪了个男式发型, 穿上夹克衫, 背着画夹, 骑上二八单车,威风凛凛地开始了我新的学画历程。
半年后, 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油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