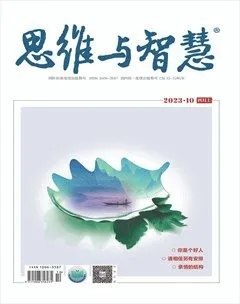桌柜
2023-04-04石泽丰
石泽丰
桌柜是母亲的嫁妆,至今还放在她睡过的房间里,紧挨着一方墙壁和她的床。上面的梳妆盒盒盖早已不知去向,一把断了好几根齿子的木梳平躺在盒中,与这桌柜、与这房间里母亲曾经用的一切一样,在日日蒙尘。
桌柜的面板是由两块木板拼成的,当初,木匠将它们拼得严丝合缝。时隔五十多年,那木匠呢?没人知道。自从父亲离世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三年前,她生活不能自理时被我接进了城里。桌柜因为松散,两块木板的缝隙增大了许多,已容得下花生米从中掉落。面板下面是两个木质的抽屉,母亲常常用它来放针线剪刀之类的物什,以便在那些日子,她冬夜坐在床上,就能随手为我们缝补衣物。抽屉下面,是一个两层的柜子,柜子里放的多半是我们日常换洗的衣服,也有母亲为我们纳的千层底。好多次,我看到她蹲在柜前,弯着腰,打开柜门,侧身用一只手伸入柜中,摸出一件东西来,又摸出一件东西来。
现在,柜门不管用了,它们对开着,耷拉在那里,不能碰,一碰,準能脱落。柜中早已没有任何衣物了,是何时清理完的?我记不清楚,或许我根本不知道。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桌柜的空。母亲收纳在里面的我们那些细碎的生活去了哪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的消失难道就是这般无声无息?前些日子,我在深夜做了一个关于桌柜的梦,梦见自己正在母亲的桌柜里找一样东西,如四十年前的那番模样,侧蹲在柜前,打开柜门,把手伸进去摸了又摸。我摸了好久,仍然没有摸到要找的东西,哪怕后来我把头伸进柜里看了一下,也一无所获。我有些心急,转过头朝房外喊母亲,问她把我的东西放在桌柜的哪个角落里了。我喊了一声又一声,就是无人应答,房门是开着的,日光在房外……我被自己深陷的某种孤独所惊醒,缓慢地回过神来,虽然是一场梦,但它逼真得让我后怕,我仰躺着,目光穿透暮色直抵房顶。而此刻,母亲正在离我不到六公里的养老中心卧床,一想到她不能动弹有些时日了,我的心里就像塞满了铅一样,非常沉重。那一夜,我默默地,默默地流了很长时间的泪水。
因为桌柜,我的童年有了些许甜度。那是有一次,小姨来我家做客,她在必经的桥头商店里,为我买了一纸包糖果(足有两斤多),母亲收下糖果后,把三分之二的糖果偷偷地塞在了桌柜下层的一个拐角处,上面用衣服盖着。如果不是她后来哄我时从桌柜里拿出几粒糖果来,我还真的认为小姨就只买了那么一点点糖果给我。从那以后,我就始终认为,桌柜的某个拐角处,肯定有我想要的东西。即使我没有找到,我喊来母亲,她随手一摸,定能把东西找出来。在这次的梦中,我没有如愿。倘若桌柜也有感情,当我两手空空地抽出双手的时候,不知它的内心是否也藏着痛。
母亲已记不清过去的事了,她也不再关心桌柜,不再关心这个世界了。而我,却偏偏在桌柜这件家具上难以释怀。我在想:一棵树,常常因为人间的喜事被伐倒,做成屋梁,做成床,做成餐桌,做成座椅和板凳……母亲的婚事,让一棵树成了她出嫁的桌柜。一段木料,在经过老木匠的劈刨之后,成了一个器具,它走进了母亲的日常,与她进出的门框、夜半掩上的木门,与她装水的桶一起熬着时间。没想到五十年过去了,它竟然熬散了卯榫,熬干了自己最后一滴水,静静地待在那里,静静地回味着深藏于器具深处的记忆。
(编辑 余从/图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