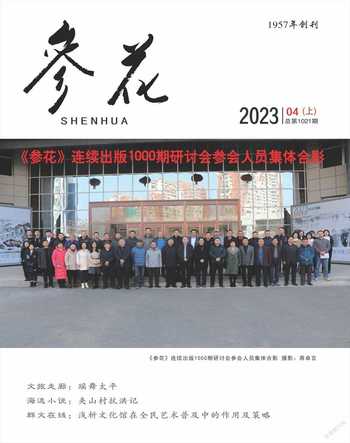民族器乐在戏曲舞台中的应用
2023-03-26高春梅
民族器乐与戏曲艺术皆是中国传统艺术,二者的演进历程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脉络紧密相关、不可分割,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随着大众对戏曲艺术的审美不断变化,民族器乐在戏曲舞台中的应用不再是以往的单一“从属”,而是相互为引的适度革新。本文分析戏曲舞台对民族器乐的适切应用,主要从理论层面对民族器乐进行合理的、全方位的探究。
一、戏曲舞台中运用民族器乐的主要类型
(一)打击乐器——戏曲舞台“总指挥”
戏曲舞台中应用的民族打击乐器主要包含锣、鼓、板等。配合戏曲演出需要,使用不同材质、不同大小的打击乐器,呈现出来的舞台演奏效果不尽相同。以鼓为例,鼓腔越大,音色越沉,鼓腔越小,发音越脆。鼓应用在戏曲舞台,多是使用桦木或者槐木与牛皮制作板鼓,而后与响板进行搭配。这样,当同时击打板鼓与响板,音质呈现不仅震撼大气,可以一下子抓住观众的听觉神经,还可以带给观众极大感染力,让观众的情绪随着音质沉浸入戏。[1]在戏曲舞台中,由一人同时击打板鼓与响板,便称之为“司鼓”——戏曲舞台的“总指挥”。有时,司鼓左手敲击檀板,右手击打单皮鼓;有时,司鼓双手执鼓签,交替击打。配合戏曲演出需要,时快时慢,轻重得当。因而,一般情况下,司鼓不仅把控戏曲乐队的“武场”,如大锣、小锣、堂鼓等,还一定程度指挥了戏曲乐队的“文场”,如二胡、三弦、月琴等,使戲曲舞台文武相合,相得益彰。即便是戏曲演员的唱、念、做、打,也可以说是在司鼓的指挥下徐徐进行。
(二)弹拨乐器——戏曲舞台“主力军”
一提及弹拨乐器,大部分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琵琶——中华民族传统弹拨乐器之王。细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琵琶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不同时代发展背景下,都凭借着独特的音色与演奏技法占据重要演奏位置,还因为其本身具有十分鲜明的“戏剧性”特质,与戏曲艺术结合严丝合缝,利于凸显戏曲演出内涵,丰富戏曲演出层次,对情节的推进恰到好处。[2]所以,将琵琶视作戏曲舞台“主力军”,借助其独特的演奏音色,为戏曲演出添砖加瓦,与打击器乐以及其他传统乐器相比,都更加具有灵活性与综合性。既能烘托欢快主题,又能急转直下,营造一定的凄美意境。以豫剧《秦香莲》为例,使用琵琶为戏曲舞台伴奏,不仅可以细水长流式地通过平缓音色呈现,刻画主人公秦香莲坚韧、勇敢、善良的一面,还可以随着剧目情节推进,根据舞台演出实际需要,对剧目内涵进行揭示,这显然是其他器乐无法轻易比拟的。[3]从此角度探析民族器乐在戏曲舞台中的应用,自然就是利用琵琶的唱奏结合、模拟唱腔、代替帮腔等,最大程度贴合戏曲主题,配合演员人物形象塑造需要,以提高戏曲舞台表现力为要,丰富戏曲乐队应有色彩。
(三)拉弦乐器——戏曲舞台“头把弦”
板胡是我国传统拉弦乐器之一。细观我国传统戏曲文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戏曲艺术发展脉络中处处都有板胡的身影。在戏曲音乐中,板胡常发挥“托腔保底”效用,被称作戏曲舞台伴奏的“头把弦”。由琴杆、弓、琴轴等组成,琴杆粗短,琴弓稍长,多用红木或者紫檀木制成琴杆,薄桐木制成琴面。音质嘹亮、高亢,既能独奏,又能伴奏,风格鲜明。在戏曲舞台中应用板胡,主要是根据剧目的实际演出需要,以配合演员唱腔变化为基础,完成对演员表演的有效“托举”。[4]以豫剧《大祭桩》为例,板胡紧紧托住演员的演唱腔调,配合演员唱腔变化,时而翻高,时而降低八度,使得戏曲舞台的整体音乐走向层次鲜明,旋律个性。此外,二胡也是我国传统戏曲乐队中十分常见的拉弦乐器,与板胡有着极为相似的演奏特征,只是在戏曲音乐表现上差别明显。如二胡的琴桶相对更大,音色多样。演奏者借助娴熟的演奏技法,不但可以演绎出宏大嘹亮的戏曲音乐,还可以通过技法改变演绎出悲切深沉的戏曲音乐。并且在二胡独奏时,基于二胡乐器的独特音色,赋予二胡器乐戏剧效果,发挥其调控节奏、气氛的主要作用。
二、民族器乐在戏曲舞台中应用的作用及表现
(一)指挥舞台演出
民族器乐在戏曲舞台应用的第一层作用是指挥整个戏曲舞台的演出节奏。毕竟在戏曲舞台上,剧目演出需要配合相应的乐队伴奏,方能与演员演出状态融为一体。[5]所以,发挥民族器乐在戏曲舞台上应用的指挥作用,科学突出民族器乐使用效果,民族乐器演奏者要正视自身演奏乐器在整个戏曲乐队中的重要位置,而后根据戏曲演出需要,配合戏曲舞台演出氛围,对整个戏曲乐队的器乐演奏进行调控。以鼓师为例,由于鼓经常是戏曲音乐的领奏乐器,用鼓打击出有规律的鼓点,可以对演员演出以及其他乐器演奏者进行节奏把控引导,烘托戏曲演出独有氛围。因此,以鼓师在戏曲开场时重点增强打击乐演奏为引,整体表演的循序渐进展现便有了较好的前导设计。[6]正所谓“戏曲伴奏鼓先行”,花鼓戏开场锣鼓,鼓师使用锣鼓点,以板鼓为导,营造与主题表达相契合的舞台气氛。而在演员演唱引导方面,鼓乐主要突出板鼓节拍调控作用,响应演员人物形象塑造需求,将打击乐持续贯穿于戏曲演出全过程,看似不显,实则掌控。
(二)伴奏全部唱腔
戏曲舞台上,演员的唱、念、做、打通常都需要一定的夸张化处理。演员是否能唱得好,唱得精,往往可以决定戏曲舞台演出效果。因而,民族器乐应用于戏曲舞台第二大作用,便是民族器乐可以精准捕捉演员唱腔的意蕴核心,完成对演员唱腔的全程伴奏。[7]细化而言,在戏曲演员演出过程中,民族器乐要负责在合适的节点、合适的场景、合适的唱段,与演员唱腔“合二为一”。以梅兰芳的惯用鼓师白登云、琴师徐兰沅为例,二人不仅为梅兰芳大师司鼓、伴奏全部唱腔,鼓与琴并称梅师的“左膀右臂”,后续还为王凤卿、赵燕侠等名家大师的唱腔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甚至成为知名戏曲流派唱腔创作的主要参与人员。当然,除了鼓师、琴师外,其他民族乐器在戏曲舞台演出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唱腔伴奏作用。如京胡在戏曲音乐中的应用,其不仅与月琴、三弦合称为京剧伴奏“三大件”,京剧舞台上处处都有其身影。板胡在一些豫剧、评剧、秦腔、河北梆子等戏曲乐队伴奏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主奏作用。
(三)配合演员表演
严格来说,将民族器乐应用于戏曲舞台,最主要也最外显的作用是配合戏曲演员舞台表演。而这一作用在鼓师的“主指挥”引导下,多通过以下两种形式逐层实现。笔者在此主要从演奏出不同的“锣鼓经”与演绎出不同的戏曲“曲牌”两方面展开细述。
1.演奏不同的“锣鼓经”
戏曲舞台上的“锣鼓经”——戏曲乐队打击乐泛称,常使用板、鼓、大锣、小锣等音响组合出不同演奏节奏,用于对戏曲舞台演出氛围的应然烘托。或是烘托緊张、不安情绪,或是烘托活跃、跳动情绪,或是烘托欢快、闲适的戏曲气氛。常见的有慢长锤、四击头以及急急风等。随着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人们的戏曲审美发生变化,后续戏曲记谱法产生基于仓、台、扎等之上的新的记谱方法。民族打击乐器演奏时,不同的锣鼓经可以使用不同的具体打法,发挥不同配合作用:其一,配合演员演出动作。以“旦上场”为例,主要由单皮鼓与檀板领奏,小锣进行辅助配合,演奏节奏十分自由,常见于青衣上场动作配合。其二,烘托演员演出气氛。以“急急风”为例,为烘托表现戏曲舞台紧张气氛,常使用专门的锣鼓经带领观众迅速进入戏曲情境。“阴锣”则是利用锣鼓器乐独有的音色,塑造并烘托一种黑夜里摸索行进的焦灼感。[8]其三,突出演员人物情感。以“搓锤”为例,多用于表现人物着急的情绪,“紧锤”则多表现人物焦虑不安的情绪。
2.演绎不同的“曲牌”
此处的“曲牌”又称“牌子”,是对我国各种自古传承至今的曲调名的泛称。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曲牌各有专名,丝毫不乱。如《点绛唇》《银纽丝》《桂枝儿》等。曲牌总数数之不尽,且每一个曲牌都有自己独有的唱法、句法以及字数等。在实际演奏应用时,可以根据演出需要填写新的曲词,用以配合演员演出需求,最大化地提升演出效果。将不同曲牌的不同配合演出作用进行细分,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配合演员动作表演需要。以《小开门》为例,主要应用在演员演绎写信、拜贺、行路等舞台动作;而《大开门》则是应用在演员演绎升堂、升帐等舞台动作。其二,烘托演员演出情绪。以《朝天子》为例,主要表现出一种朝堂场景或狩猎场景所独有的庄严、肃穆之感。[9]其三,托举演员思想情感。以常用的《哭皇天》为例,主要表达人物形象的内在悲切之情;《夜深沉》则是表现人物在特定气氛下的愤怒感,京剧《霸王别姬》中,为表现虞姬舞剑时的悲戚与愤慨,就巧妙使用了这一曲牌,收获了绝佳的器乐伴奏效果。
三、民族器乐在戏曲舞台的多元化应用发展
(一)作曲编排创新
将民族器乐运用于戏曲舞台,不但可以通过民族器乐的节奏分明突出戏曲唱腔的明快、多变特点,还可以一定程度地扩展戏曲艺术的创新实践效果。所以,进一步剖析民族器乐在戏曲舞台中的多元化应用,实际上就是借助民族器乐不断丰富戏曲艺术的体裁与内容,使戏曲艺术内容为王,音乐为骨,真正意义上体现出二者的融合发展效果。使戏曲形式、戏曲题材等随着地域特点、语言特点,生动发展、演变出多种戏种类型,百花齐放。如民族器乐借鉴传统戏曲的脸谱化、写意化、符号化,对器乐内涵进一步凝练;而传统戏曲借鉴民族器乐的表现风格、编排要素,不断对戏曲表达进行升华,从而促生一些更加具有时代气息的都市戏曲、时尚戏曲,契合现代观众个性审美,引发观众对戏曲文化的强烈共鸣。[10]如新戏曲《三少年》,在该戏曲舞台的“采黄花”段落,就有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碰撞、融合体现,对传统曲牌成功改编。具体而言,将传统的“西皮原板”的“过门”,通过更加突出的环境描写与意境渲染,配合人物心境完成了创新。并且戏曲舞台的整体结构编排,还隐隐透露出对一些与主题表达相契合的现代管弦乐演奏效果的借鉴,全方位提高戏曲舞台感染力与震撼力。
(二)摆脱公式思维
虽然民族器乐在音高、定弦、音色等方面表现出灵活性、生动性。但是,将不同的民族乐器在戏曲舞台上进行演奏配合不难发现,大部分民族器乐都有一套固定的演出配合程式。以打击乐器为例,其应用于戏曲舞台就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演奏程式。而新环境、新形势下,按部就班遵循固定的演奏表演程式,显然不利于戏曲艺术在新时期传承发展。因此,在多元文化思潮碰撞背景下,民族乐器演奏者应该主动学习新的演奏技巧与演奏理念,在戏曲舞台实践中,积极、大胆地应用新的民族器乐演出理念,带给观众新鲜感,拉近观众与戏曲艺术距离,使民族器乐更好地适应戏曲艺术多元化表现需要,助推戏曲艺术绽放新的生命力。如在《梨园春》中,创作者使用“开幕曲”与“闭幕曲”,丰富戏曲音乐演奏结构,并根据戏曲情节演出需要,对所运用到的民族乐器进行演奏程式创新编排,实现戏曲与民族器乐的“新旧融合”。
(三)改造乐器本身
我国民族器乐与戏曲艺术发展至今,除了大量保留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器乐文化元素外,还积极融合了与器乐文化、戏曲文化紧密相关的其他艺术文化内容。如在新京剧作品创作中,创作者不仅保留传统“三大件”,与此同时,还以面向世界,使中国戏曲艺术在世界艺术舞台占据一席之地为导,引入、融合了一定的西方管弦器乐,使民族器乐应用主要根据剧目演出需要而改造创新。以唢呐在京剧舞台上的创新应用为例,在现代京剧《唢呐声声》中,创作者对唢呐的改造不仅展现出我国民族器乐的独树一帜,还适应新时代戏曲唱腔变化,通过对唢呐音高、音色的现代化处理,使其更加贴近主要人物复杂情绪,成为戏曲舞台上的标志性色彩。而在摇滚京剧《荡寇志》中,民族器乐应用不仅对传统乐器本身适度改造,还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戏曲的框架化,将戏曲与杂技、诗歌等进行融合,让戏曲受众耳目一新,改变戏曲艺术传承的“断层”窘境,吸引到一批年轻观众追捧与热爱。跨文化戏剧《情殇钟楼》亦是如此,整体构建一种新的民族器乐应用于戏曲舞台审美格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艺术形式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在新时代背景下有效传承发展的必然。戏曲舞台与民族器乐就是如此,相互滋养、相互借鉴。因而,要想使戏曲舞台尽善尽美,民族器乐多元化发展,音乐家、戏曲家就不仅要将民族乐器与戏曲技艺有机整合,还要更深一层地认知传统戏曲与民族器乐间的关系,从而使民族器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象征,与戏曲艺术相辅相成,为戏曲舞台锦上添花,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田金峰.浅谈民族打击乐器在地方戏曲中的结合与运用[J].戏剧之家,2022(27):37-39.
[2]邹宇.论琵琶在戏曲艺术中的审美表达[J].四川戏剧,2022(02):102-105.
[3]徐宝宝.中国民族器乐在戏曲艺术中多元化发展研究[J].文化产业,2022(07):28-30.
[4]刘佳,罗羽涵.浅谈器乐演奏在江西弋阳腔戏曲伴奏中的有效应用[J].黄河之声,2021(20):38-40.
[5]李洁.琵琶演奏在戏曲中的运用与艺术特点[J].北方音乐,2020(23):52-54.
[6]郑怡.论民族器乐在戏曲艺术中的重要作用[J].长江丛刊,2020(34):8+11.
[7]李蓓.听弦知语声——胡琴艺术与地方戏曲风格相辅之道[J].北方音乐,2020(22):239-243.
[8]刘贝妮.胡琴在板腔体戏曲中的演变——以秦腔、京剧主奏胡琴为例[J].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0(11):227-228.
[9]苗颀.胡琴类乐器在戏曲音乐中的伴奏研究——以河南地区为例[J].曲学,2019(06):143-155+7.
[10]杨帆.中国采茶戏与传统乐器伴奏的音乐鉴赏[J].福建茶叶,2018(02):325-326.
(作者简介:高春梅,女,大专,甘肃演艺集团敦煌艺术团,二级演奏员,研究方向:民族音乐)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