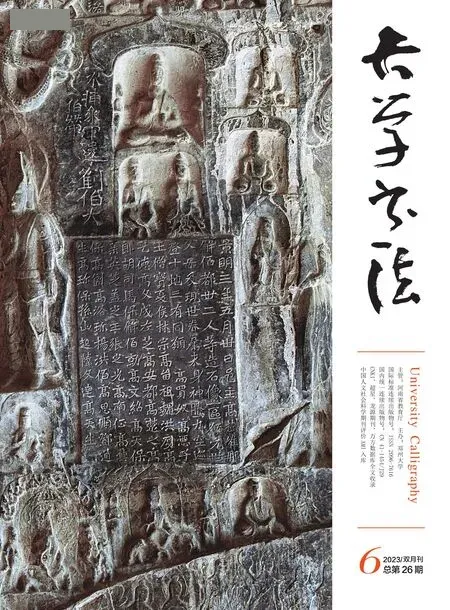五十自述
2023-03-24成联方
⊙ 成联方
姜亮夫先生写过《四十自述》,其四十岁取得的成绩确实令人景仰,而我行年已过五十,真可谓乏善可陈。那我为何还要写呢?我想,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较早的书法博士以及书法博导,不管成绩如何,也把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如实写出来,给后人研究高等书法教育史留些文献,如果有价值当然欣慰,没有价值就与世浮沉可矣!
我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一个农村家庭,虽然在农村长大,但排行小,自小倒没吃过多少苦,一旦写出几个好看的字,就会得到父母、兄长的表扬,这大概就是我喜欢写字的最初动力。
我1987 年(16 岁)考进昭通地区师范学校读书,学校非常重视三笔字教育,几乎每个同学都能写一手漂亮的字。昭通有姜亮夫、谢饮涧、张希鲁、姜澄清这些学者、书法家,而且,谢饮涧、姜澄清都是昭通师范的校友,老师经常向我们讲这些人的名人轶事,所以,十几岁的心灵里就住下了这些昭通名宿。
我也喜欢音乐,于1990 年(19 岁)被保送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师范班,主修钢琴,跟随云南最权威的钢琴教育家李兆仁教授学钢琴,同时拜云南艺术学院樊端然教授学书法,每天都在练琴和写字之间转换,四年就这样飞逝了。我本科毕业到昭通师范专科学校(现昭通学院)教书,校长陈孝宁教授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散文家,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因此,昭通师专有非常好的书画文学氛围,师生常常在一起相互砥砺,书画展览也举办得较为频繁。
我于2004 年考取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硕士,开始接受专业的书法学习。
2004 年考取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而接受的教育
(一)书法所诸师之教诲
我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研究所(以下简称首师大书法所)读硕士,导师是甘中流教授。
我们2004 级只有六个正式生,两三个同等学力,一个班不超过十人,上课的老师远远超过十人,我们开玩笑说这是“精英教育”。
欧阳中石先生只给博士生上课,硕士只能听先生的讲座,先生写字,全所师生都要前去学习,所以,我看过好多次先生写字。
刘守安老师讲《书法美学》,我尤其佩服刘老师的桐城派研究。我写了《艺术创造的唯一性品格与价值论原则的二律背反——书法创作必须思考的首要命题》作为美学结课作业,该文收录于《第三届全国书学学术周论文集》,后又进行修改,以《从价值论原则看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发表于《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 年第4 期。
张同印老师给我们讲隶书课,我写字总喜欢“创新”,被张老师严厉批评过,当时内心不服,现在回想起来很是感谢这样的严师,那个时候认为的“创新”实际上只是“时风”,自己能力不够,深入不了经典,也就分不清什么是“经典”什么是“时风”了。
叶培贵老师给我们讲《书法史》《诗词楹联写作》两门课。叶老师讲书法史很有思辨性,他告诉我们要多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我写了《对民国书法史体例的思考》作为结课作业,15000 字左右的长文,收录于《2005 年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书法论文集》,并被《书法导报》连续转载。叶老师的《诗词楹联写作》课,我非常喜欢,我之前从来不会写诗填词,三四次课之后,我写了《独坐》一诗:“韶光三月映池塘,好景经年绿橘黄;不觉安仁斑两鬓,当初只顾笑江郎。”得到了叶老师的表扬。叶老师的教学方法非常实用,我在云南大学给学生讲《诗词楹联》课,也用叶老师的方法,得到学生们的欢迎。
王元军老师是历史学科班出身,曾供职于中华书局,给我们讲《书法文献学》。我喜欢文献学,和王元军老师的教诲有很大关系,我后来发表于《书法研究》的《沈曾植书学著述编年考勘》一文,写法是受到王元军老师启发的。
解小青老师的《书法文字学》引我进了文字学之门,我后来一直研究《文字学》,尤其想从书法角度研究文字学,是受到解小青老师启发的。
在治学、作文和书法创作上,我均服膺我的导师甘中流教授。甘老师带着我们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要求我们读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这是我学目录学的开始。我在云南大学讲《美术文献学》,也主要讲这两本书。甘老师告诉我一定要读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后来我写了几篇研究“观念史”的文章,就是在甘老师这里打下的基础。
(二)硕士论文《沈曾植书学方法研究》
我的硕士论文是《沈曾植书学方法研究》。研究古代的学术方法,首先要有古代学术史、古代哲学史以及古代历史理论等方面的基础,为了硕士论文,我花了好长时间读这些书,例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
沈曾植为学无所不包而且皆很精深,他给《易经》、佛学、禅宗、理学以及书籍版本学等写的题跋,起初读起来极为费劲,我就暂时放下沈曾植而先去读原典,对原典有些基础之后再来读沈曾植题跋,才慢慢读懂的。
硕士阶段是学术之路的关键阶段,因为本科阶段还涉及不到学术,而博士阶段大概要基本成型,所以,硕士阶段极为重要,只要硕士阶段打好基础,后来的各个阶段就有指望了。
2007 年到云南大学教书,受到“云大学派”的影响
云南大学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名家、大师曾有不少,例如研究庄子的刘文典、研究民族史的方国瑜以及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魁阁学派,在云南大学根深叶茂,我暂且把他们统称为“云大学派”。
我于2007 年到云南大学教书,开始关注这些先生们的著作,也不知不觉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后来写了一些研究云南书法、云南碑刻的文章,例如《业余艺术家的价值》《云南艺术家要说“云南话”》这些小文,便是尝试用“云大学派”的观点进行写作的。
我已指导了多篇研究云南书法家以及云南古代碑刻的硕士论文,也是希望通过书法这个领域深入“云大学派”延续“云大学派”的传统。
2009—201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一)得到导师郑晓华教授以及徐庆平教授、陈传席教授的教诲
刚到学校和导师见面,郑晓华老师给我说:“你一定要成为你这个年纪的佼佼者!”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日记》里,郑老师的这句话平实而深刻,虽然感觉到自己“跳一跳也能够得着”,但是,必须一刻也不能停止!郑老师有一次对我说:“《论语》里有句话: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当时接近四十,听到这句话后压力之大简直无法形容,这么多年来,郑老师的这些教诲时时在耳边回响,我从来不敢懈怠。
我博士一年级的时候,郑老师看我的论文,温和地指出:“写法要新,观点要新,文章要跟上时代。”我刚硕士毕业两年,以为“竭泽而渔”就是好文章,经过导师的指点,才知道“竭泽而渔”仅是基础,重要的是“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郑老师看论文的速度极快,可以在一两分钟之内全部看完,而且马上提出修改意见,我当时被震住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学院派”功力。
郑老师给我们讲《书谱》,我第一次感受到“阐释”的魅力。我之前认为,古代书论都是中古汉语以下的语言,没有太大难度,所以常常轻慢待之,但是,郑老师讲解《书谱》,逐字解释、分析句子、梳理逻辑、划分段落,把整个云里雾里的《书谱》讲得清清楚楚,偶尔用演绎法引申出去,真有沈曾植《刘融斋〈书概〉评语》中的“禅那”风采,我甚为钦佩。我用导师的方法去读宗炳《画山水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好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这是我读博士期间的大收获!后来我回到云南大学教书,讲古代画论、古代书论都用这个方法,很受学生欢迎。我在读博时“恶补”佛典,也是受到导师的启发。
徐庆平教授和陈传席教授给我们讲《学术文献》课。徐庆平教授是徐悲鸿先生的哲嗣,是巴黎大学美术史博士,给我们讲的西方美术史均是一手材料,讲他的亲身经历以及国际、国内的美术掌故,使我认识到仅仅在电脑旁爬梳文献是做不出一流学问的,“见识”对学术研究非常重要。
陈传席老师的美术史研究、美术批评在国内均为一流,而且其涉猎范围远远超出了美术。陈老师颇善作文,评论、随笔、序跋等尤为精彩,我有段时间热衷写小品文,是受陈老师影响。在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说钱仲联先生整理的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有许多错误,陈传席老师非常严肃地说:“钱先生是国学大师,中国首批博导,你指出错误一定要小心,否则会出丑!”我现在正整理沈曾植书学文献,见识了钱先生的学问之大、学问之深,我所指出的钱先生的一些小瑕疵,未必真是钱先生的问题,恐怕是出版社校稿、排印时候的失误也未可知。学术研究的“后出转精”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得以实现的,我很惭愧当时有轻慢之心。
(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选修课
我拿的是哲学博士学位,我读的博士点设在哲学院,所以,哲学院教授的课是必须听的。我选修了《易经》《王阳明传习录》,选听了《说文解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们对经典的解读皆是一字一句进行的,这种读书方法对我有深刻影响。
我读《说文解字》始于中国人民大学,我写的《黄侃书法思想及其书风分期研究》一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1 年第12 期,这是我研读“章黄学派”时延伸出来的课题。
我受到“云大学派”的启发,便对社会学、人类学感兴趣,所以,便选听了社会学课程,我发表于《中国书法》2011 年第3 期的《中国女性书法梗要探研》,便是从社会学角度关注中国书法史上的女性群体而写的文章。
(三)博士论文《沈曾植碑帖学研究》
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沈曾植书学方法研究》时,已收集了沈曾植的不少文献,但均未深入研究,通过和郑老师商量,博士论文继续研究沈曾植,主要研究沈曾植在碑帖学方面的成果。
博士论文对文献要求很高,所以,我每周至少花两三天时间到国家图书馆老馆(北海公园附近)抄录沈曾植文献,其他时间都在人大图书馆网络检索资料、核查资料,如此交替进行的工作持续将近一年,文献工作才勉强做完。全身心投入写作,是从三年级的九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份,当一交稿,自己才猛然一惊,七个月时间竟然没有一天离开过椅子,非常欣慰!
沈曾植是晚清第一流的碑帖学家,研究沈曾植的碑帖学,几乎等于研究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碑刻学和刻帖学。碑帖学文献是书法专业的核心文献,经过博士论文的撰写,为我打下了一定的碑帖学基础。
2012—2020 年副教授期间的学术成果
(一)撰写的论文——从哲学视野转到碑刻学、考古学
由于受到哲学的影响,我博士毕业以后写了一些研究“观念史”的文章。例如,《沈曾植“南北会通”观的审美谱系——从北碑三宗、〈中岳嵩高灵庙碑〉到欧虞褚李》一文,获2014 年“全国第十届书学讨论会”优秀奖(最高奖),《卫恒“古今杂形”对沈曾植书法的影响》一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9 年第9 期。
我也写了一些哲学和书学交叉的文章,例如,《朱熹对沈曾植书法的影响》发表于《中国书法》2016 年第5 期。《从政治哲学转向艺术审美:沈曾植上海时期书法思想的理学化特征》入选2017 年“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关于后者,我写了《探索哲学与书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一文发表在《中国书法》2018 年第2 期,以说明我对此文的方法论思考。
我受到“云大学派”的启发,便关注云南碑刻,尝试用“云大学派”的方法去研究沈曾植,写了《二爨对沈曾植书法的影响》发表于《中国书法》2016 年第11 期,写了《几与原文语气无别——谢饮涧补〈孟孝琚残碑〉所缺八十八字及其可信性探析》发表于《中国书法》2018 年第9 期,并获得云南省社科三等奖;整理了谢饮涧先生手稿《〈汉孟琁碑〉考证续举》在《中国书法》2019 年第4 期发表,也写了《沈曾植所推崇的唐朝名家碑刻及其内在原因》发表于《中国书法》2020 年第10 期。
当我研究了考古学家谢饮涧先生之后,略懂金石学、碑刻学以及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认识到考古学和书法学是紧密相连的,书法专业应该开设《书法与考古》课程,打开研究视野,使书法学科尽快融到社会科学中去。
(二)做教育部项目《沈曾植书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得到的学术训练
我于2017 年申请到教育部项目《沈曾植书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今年底将以《沈曾植书学文献辑集与校勘》专著结项。整理沈曾植这样学者型书法家的文献,会得到校勘学、辑佚学、文字音韵训诂以及书法艺术等全方位的学术训练。其他方面暂且不论,此仅以书法艺术为例,我认识到,“字法”是书法艺术的“学术性”体现,如果仅仅学碑帖上的字,即使笔法精美、字形丰富,也难免简单雷同,书法家要为社会创造具有历史美感的汉字,需要有把传世典籍的“印刷体”进行“艺术化”的能力,沈曾植书法作品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这里。
(三)从自学“文字学”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访学
我学文字学,是从硕士时候解小青老师给我们讲《书法文字学》开始,那时,我到首师大文学院听过几次黄天树先生的文字学课,黄天树先生是裘锡圭先生的博士,我自然就会读些裘锡圭先生的著作。
那时的首师大书法所有个好风气,博士论文答辩、博士后出站的答辩委员都有顶级专家,我只是硕士,每场答辩我都去旁听。在答辩时候听到北京大学高明教授、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董琨教授等点评博士、博士后们的问题,我就会记下来“顺藤摸瓜”,去找文字学经典著作来读。
我到人大读博士的三年期间,日课是《说文解字》,辅助《说文》还读了一些其他书。博士毕业回云南大学教书,我一直给研究生讲《说文解字》,但是只读《说文解字》对书法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不够的,研究篆、隶、楷、行、草五种字体的文字学著作也要读。目前我们能见到的《书法文字学》著作,作为教材是不大实用的,因此,我一直想编写一个打通五体的“书法文字学”教材供书法专业的学生使用。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字学水平,我于2019 年9 月至2020 年6 月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访学,跟随董珊教授学文字学。我给博导郑晓华老师汇报我的想法,郑老师说:“读文字学好,这是书法的根本!”我参与的是文字学博士、博士后的课程,受到了不少启发,可惜疫情爆发,当面向董珊先生请教不多,后来是在网上听董老师讲课、听董老师的学术报告以及读董老师的书,现在自己的水平虽然不高,但已略晓治学规范。
我写的《简化字能用于书法创作的历史证据与现实依据》一文于《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2019 年第5 期全文转载,或许这不是地道的文字学论文,但属于书法文字学论文是没问题的,以后我还会有几篇讨论书法用字问题的文章发表出来。
(四)写小品文
昭通有很深厚的文学传统,例如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的文章写得就极为生动,姜澄清先生乃一代散文圣手,“昭通作家群”闻名于全国,在这个地方长大,自然而然地也会喜欢文学。有段时间我曾热衷于写小品文,拙著《锋芒与沉思》一书中收录了几篇。我的小品文作法,主要向姜澄清先生、熊秉明先生以及陈传席先生学习。
姜澄清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他的《古文笔法》一书,是我研究古文和现代文如何转换的教材,他的《清谈录》《清谈续录》等散文集,我曾模仿过一段时间。
熊秉明先生是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哲嗣,作为云南大学的后辈,我自然会读熊秉明先生的文章。熊秉明先生善多种艺术,且淹通古今、中西融贯,例如他的《看蒙娜丽莎看》之类的文章写得优美至极而且说得透彻,艺术小品文写到这种程度可谓为上乘之作吧!
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博以后,喜读陈传席老师的《悔晚斋臆语》《画坛点将录》《北窗臆语》等书,他的写法已经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审美特征,敢于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一剑封喉”,这种风格我以前没有甚至不敢这样写,所以,陈老师的小品文特别吸引我。
我的好友,昭通学院历史学家唐靖教授委婉提醒我:“小品文写几篇就够了,年轻时要多写大文章!”自此以后,我有好几年拒绝写这种文章了。
(五)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云南省书法家协会的活动扩大了见识
我原本是宅于书斋之人,没太多见识。博士毕业以后,逐渐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云南省书法家协会的活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历练机会,从书斋走向社会,向更多的人学习。
我刚回云南之际,参加了云南省书法家协会的展览评审,见识了云南省书法家协会郭伟主席在古文字学上的功力,他阅读古文字作品几乎毫无障碍,而且,能一下子指出用字之微妙处。当时我刚博士毕业,文字学功底尚浅,只能似是而非,而且,我的文学功底也很浅薄,通过评审工作均暴露出来了。后来我又逐渐参加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学术活动,更加暴露出自己学识之粗浅,眼界之闭塞,得抓紧补课,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2018 年7 月,我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协“第二届高等书法教育论坛”论文大赛评委,使我进一步考虑到书法专业研究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以及写作方法等问题。2018 年11 月,我担任“全国第八届篆刻展”学术观察,并提交了《现状与未来——以全国第八届篆刻展为中心的学术考察》一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9 年第8 期;2019 年12 月,我担任“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文字审读委员评委;2021 年10 月我担任“第九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评委,等等。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使我认识到文字学、文学是书法艺术的基础学问,基础学问不牢,书法艺术也行之不远。
刘熙载在《文概》中说:“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识”的重要性是我参加了业界的学术活动才认识到的,可以说,是业界的学术活动推着我进步的。
自被聘为教授(2020 年)以来,学习重点又加上目录学
我2020 年评上教授,并聘为博导。博导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崇高的,而且学术水准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是,我的学术成就离我心目中的教授、博导还有不小差距。云南大学《思想战线》主编王文光教授在我聘上博导之际对我说,希望我“龙虫并雕”,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我,希望我多“雕龙”少“雕虫”。
文字学一直是我的学习重点,评上教授以后又增加一个学习重点——目录学。
我每次写论文,写得很吃力,甚至有的论文要用去几个月时间,这样下去,一生也写不了几篇文章,然而,学术大师们总能写出很多著作和文章,而且质量都很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我评上教授之后,仔细翻阅《姜亮夫全集》才明白过来,是因为我缺少目录之学而导致的。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2000 年以前会到图书馆查阅纸本文献,2005 年以后基本在网上查找,自己研究的这块由于投入时间多,资料还较熟悉,然而,和自己研究领域只要稍微有点距离就会茫然不知,根本原因是缺少目录学基本功。目录学不仅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用,而且,也是成就学问之“大”的关键。
我现在正撰写《云南书法史》,之前我直接从书法文献着手,文献是否收集完,我心里没底。我经过近两年的目录学研究以后发现,要写地方文化史的著作,应该首先熟悉地方古籍目录,在此基础上,才知道文献收集如何。所以,我花了一段时间研读《云南书目》《云南丛书书目提要》《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以及云南考古资料、云南碑刻文献等,现在基本摸清“家底”,心里踏实下来了,拙著《云南书法史》或许不会太糟。
书法虽然已升为一级学科,但是,由于书法目录学这样的基础学科还不成熟,所以,书法学科要达到一流学科的高度,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认为,书法界要多做基础学科,基础学科丰富了、厚实了,学科水平自然就上去了。
小结
《五十自述》本应该写自己已经做到的事,但文中写了很多将要做的事或者期望做的事,难免有自我吹嘘、自我开脱之嫌。但是,对未来的“畅想”或许能给年轻后进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这是不是也有些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