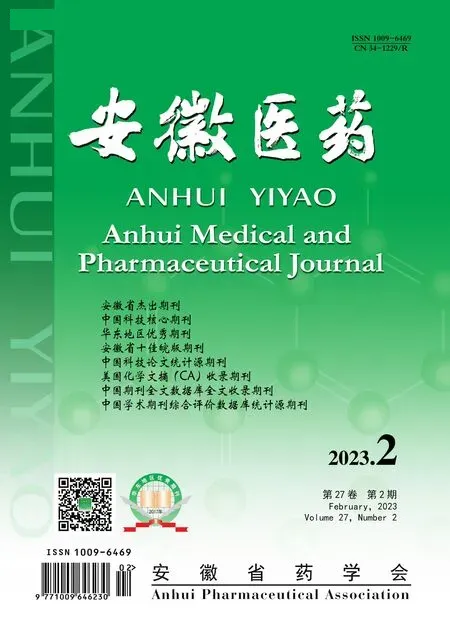乳腺癌导管相关性血栓的研究进展
2023-03-22侯思浩周毅
侯思浩,周毅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也是第五大最常见的死亡原因[1]。由于大部分乳腺癌病人需要接受长期反复化疗,而经外周静脉输注化疗药物对血管刺激性大,长时间输注可能会发生药物外渗、静脉炎等并发症,严重时甚至还可导致皮肤坏死,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同时可能还会影响病人化疗方案的正常进行。因此,目前临床上均推荐使用中心静脉通路输注化疗药物。临床上常用的中心静脉通路包括输液港、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隧道式中心静脉导管及非隧道导管[2]。但是随着中心静脉导管的不断普及,其与中心静脉导管相关的并发症也日益凸显,例如导管相关感染、静脉炎、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导管脱出和断裂等,其中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catheter-related thrombosis,CRT)是中心静脉导管置入后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导管相关性血栓的形成给乳腺癌病人造成了巨大的身心痛苦,如何防治导管相关性血栓的形成成为了广大临床工作者关注的重点。现就乳腺癌病人导管相关性血栓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CRT的定义
CRT是指从导管延伸到血管腔内的静脉壁血栓,导致部分或全部导管堵塞,伴或不伴有临床症状[3]。通常不包括其他常见但通常问题较少的血栓并发症包括:导管尖端周围的纤维蛋白鞘、导管腔内血栓形成以及中心静脉的浅表血栓性静脉炎。
2 CRT的流行病学
总体而言,CRT占所有上肢深静脉血栓的70%~80%,约占所有静脉血栓类型的10%[4]。在一般癌症人群中,与中心静脉导管相关的症状性CRT发生率为0.3%~28.3%,而通过静脉造影检查发现的无症状CRT发生率为27%~66%[5]。而在乳腺癌人群当中,2017年的一项前瞻性研究[6],纳入了539例接受中心静脉导管化疗的非转移性浸润性乳腺癌病人,结果显示有症状的CRT发生率为2.7%,无症状的CRT发生率为8.8%。随着插入技术(例如,越来越多地使用超声引导进行插入),导管材料和设计,维护保养以及与癌症相关的治疗方法的发展,CRT形成的风险将随着时间而继续变化。
导管相关性血栓的形成不仅可以导致病人出现局部症状,包括置管侧上肢及颜面颈部出现肿胀、疼痛、麻木、红斑和血栓性静脉炎等[7],而且会导致10%~15%的病人发生肺栓塞和10%的病人失去中心静脉通路[5]。另外,从经济角度看,CRT的形成也会导致与治疗相关的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显著增加。
3 CRT的发生机制
众所周知,影响血栓形成的三大因素为血管内膜损伤、血流缓慢和血液高凝状态。乳腺癌病人CRT的形成也与这三大因素相关。当中心静脉导管置入血管后,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导致内膜下胶原和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WF)暴露。此外,中心静脉导管的存在导致导管周围血流缓慢和产生湍流,使血小板与附近的内皮细胞接触。血小板与血管性血友病的受体(vWF)结合,导致血小板活化和聚集,激活凝血系统,导致血栓形成[8]。另外,乳腺癌病人自身的高凝状态也会促进血栓的形成。
4 CRT形成的危险因素
与乳腺癌病人中心静脉导管放置相关CRT形成的危险因素分为三类:(1)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因素;(2)病人相关性因素;(3)化疗相关性因素。
4.1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因素中心静脉导管的置入是CRT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9],导管直径、导管材料、导管尖端位置、导管类型、导管置入部位、导管感染等是CRT形成的危险因素。Liem等[10]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较大的导管直径以及较大的导管直径/血管直径会增加CRT形成的风险。这可能是由于大直径的导管会导致更严重的静脉淤滞和湍流,从而触发凝血因子的激活,导致血栓形成的风险增加。相关研究表明[11],与最新的聚四氟乙烯、聚氨酯导管相比,传统的聚乙烯导管更容易导致CRT形成。标准的中心静脉导管尖端应该位于上腔静脉与右心房交界处,而导管尖端的不适当位置也会增加CRT形成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上腔静脉和右心房的交界处血流速度快,当高浓度的化疗药物进入机体时迅速被稀释,降低了化疗药物对血管内皮的损伤,而当导管尖端位于正确的位置时,导管尖端不易与血管内皮接触,大大降低了导管尖端对血管内皮损伤的风险,从而导致CRT形成的风险明显降低[12]。与经中心静脉置管(CVC)相比,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导致CRT的风险更高,这可能是由于PICC较长的置管路径增加了导管与血管内壁的摩擦,使血管内皮损伤的风险增加,进而导致CRT形成的风险增加[13]。Ma等[14]对2 996例中心静脉置管的乳腺癌病人做了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与颈内静脉导管相比,锁骨下导管病人的血栓发生率更高。锁骨下静脉与上腔静脉形成的角度更明显可以解释这一事实。导管经锁骨下静脉穿刺置入,在向下推导管的过程中会损伤血管内皮,而慢性机械性刺激和随后的化疗药物的局部毒性可能导致血管内皮的进一步损伤并易于静脉血栓形成。然而,颈内静脉(特别是右颈内静脉)沿着上腔静脉相对笔直地行进,这使其成为中心静脉导管穿刺部位的良好选择。急性感染的存在越来越被认为是静脉血栓栓塞症的独立危险因素[15]。在一项连续的105例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病人的前瞻性研究中,与导管相关的感染使CRT形成的风险增加了10倍,并且CRT的存在也会使感染的严重程度进一步增加[16]。
4.2 病人相关性因素与没有患乳腺癌的同龄女性相比,患有乳腺癌的女性患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风险增加了3~4倍[17]。癌症病人血液通常呈高凝状态,这主要是由于癌细胞特异性的血栓形成特性以及宿主细胞对肿瘤的炎症反应。癌细胞产生并释放促凝和纤溶蛋白,炎症细胞因子和促凝微粒。它们还表达与宿主血管细胞(即内皮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受体结合的黏附分子,从而刺激这些正常细胞的促血栓形成特性,包括细胞特异性微粒的脱落和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的形成[18]。有研究表明,较少的活动量和肥胖是乳腺癌病人CRT形成的危险因素[19]。接受化疗后的乳腺癌病人可能出现恶心、呕吐、厌食、疲劳和其他反应,这可能导致病人活动量减小和卧床时间增加。而且,由于担心导管移位,许多乳腺癌病人故意减少了置管侧肢体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会导致病人血容量不足,血流缓慢,血液黏滞度升高,血小板聚集增强以及血管壁受损,最终导致血栓形成。肥胖的病人往往会增加导管放置的难度,并且肥胖的病人往往血液黏度偏高,这可能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在评价化疗相关VTE风险的Khorana风险评估量表中,体质量指数≥35 kg/m2是接受化学疗法治疗的病人随后DVT或PE的独立危险因素[20]。CAVECCAS研究结果指出[6],肥胖、高龄、小叶癌的组织学类型、一种或多种合并症(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肝衰竭,肾衰竭、慢性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是乳腺癌病人CRT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
4.3 化疗相关性因素化疗使血栓形成的风险增加了6.5倍[21]。化疗诱导血栓形成的一种理论是:化疗药物对内皮细胞的直接毒性作用导致血管壁损伤,从而引发凝血级联反应,最终导致凝血酶生成和血栓形成[22]。化疗诱导血栓形成的另一种理论是:化疗药物导致肿瘤细胞凋亡,导致血栓前微胶粒释放,组织因子活性增加以及凝血酶的产生,进而导致血栓形成[23]。有研究表明,基于顺铂的化疗方案与多种血栓栓塞并发症相关[24]。还有研究表明,接受蒽环类或基于CMF的化疗方案的乳腺癌病人发生血栓的风险增加[25]。最后,促红细胞生成素、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大剂量皮质类固醇的使用也会使乳腺癌病人CRT形成的风险增加。
5 CRT的诊断
5.1 临床表现导管相关性血栓可分为无症状性CRT和症状性CRT两种类型,其中症状性CRT约占全部病人的1/3[26]。无症状性CRT是指病人在没有任何症状和体征的情况下,通过相关影像学检查(如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静脉造影)筛查诊断出来的。症状性CRT病人通常表现为置管侧手臂/颈部/面部肿胀、疼痛、红斑、感觉异常以及同侧胸壁静脉扩张和充血,部分病人还会出现下颌疼痛[27]。若病人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胸痛甚至咯血,须警惕肺栓塞的存在。另外,当出现导管输液或者抽吸困难时,应立即行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或静脉造影检查,以明确有无CRT形成。由于导管感染和CRT之间的相关性,当病人出现导管感染症状时,如导管穿刺部位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硬结、伴有脓性渗出物,或者出现寒战、发热等全身感染症状,也须警惕CRT的存在。
5.2 血管彩超检查血管彩超检查是诊断CRT的首选方法,其敏感性为78%~100%,特异性为82%~100%[28]。优点:血管彩超检查具有无创、方便、快速、廉价、无放射性等优点,是一种理想的诊断方法[29]。缺点:由于解剖学上的限制(锁骨上段的遮挡),对锁骨下静脉血栓诊断的敏感性不高[30]。另外,由于彩超检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检查结果易受检查者水平的影响。导管相关性血栓的彩超诊断标准[31]:静脉不能压缩、管腔内实性回声,管腔内血流信号充盈缺损,静脉频谱期相性消失或减弱。
5.3 静脉造影检查静脉造影是诊断静脉血栓形成的金标准[32],可清楚显示血栓形成的范围,同时了解瓣膜的功能以及侧支循环建立情况,对制定治疗方案较有价值。但它是一项有创的、昂贵的检查方法,并且容易引起造影剂负荷和放射性损伤,所以临床上一般很少使用,仅适用于无创检查不能确诊但临床高度疑似的病例[29]。
5.4 D-二聚体检测由于D-二聚体水平在各种非血栓性疾病(例如恶性肿瘤、感染、手术或创伤、炎性疾病)中也可能会升高,因此D-二聚体是VTE的敏感但非特异性指标[33]。Dinisio等[34]的研究表明,D-二聚体对DVT诊断的灵敏度为95%~97%,特异度仅为42%~52%,而对PE诊断的灵敏度为96%~99%,特异度也仅为38%~41%。但是,D-二聚体在DVT诊断中的阴性预测值>95%,因此,尽管阳性结果不能用于确认DVT的诊断,但是阴性结果可以帮助排除该诊断[35]。
6 CRT的治疗
导管相关性血栓的治疗目标是降低急性事件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减少后期并发症的发生。导管相关性血栓的治疗包括导管处理、抗凝治疗、溶栓治疗。相关治疗流程可参照《我国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与治疗指南(2019版)》[36]。
6.1 导管的处理根据CRT病人是否继续需要中心静脉通路将其分为两类。对于不再需要中心静脉通路或中心静脉通路失用的病人,最近的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临床实践指南:癌症相关性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指南建议在抗凝治疗5~7 d后移除中心静脉导管[37];而对于大多数仍然需要中心静脉通路的病人,可以将导管留在原处并开始抗凝治疗[32]。还有一些病人存在抗凝禁忌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病人是否需要中心静脉通路,都可能需要移除中心静脉导管。由于急性期血栓易碎,在拔管过程中可能出现血栓脱落导致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需密切观察病人有无呼吸困难、胸痛、咯血等肺栓塞症状,有条件者可选择先行置入上腔静脉滤器,再选择拔出中心静脉导管,该法可大大降低因拔除中心静脉导管导致的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5]。国际临床实践指南指出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专家不建议移除导管:(1)远端导管尖端处于正确位置(在上腔静脉和右心房之间的交界处);(2)导管功能正常(血液回流良好);(3)导管对病人是必不可少的或至关重要的,并且没有发烧或感染性血栓性静脉炎的任何体征或症状。相反,如果存在血栓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导管太短、导管位置异常等),则必须拔除导管[3]。因此,对于发生CRT的乳腺癌病人,拔除导管与否还需要临床医生对病人具体情况以及导管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
6.2 抗凝治疗对于保留导管的病人,目前的建议包括使用普通肝素或低分子量肝素进行几天的抗凝治疗,然后再使用维生素K拮抗剂或低分子量肝素进行至少3个月的抗凝治疗。低分子量肝素是乳腺癌病人的首选,因为它可以更有效地防止复发性血栓形成,并且华法林会干扰某些化疗方案,并且在血小板减少症发生时更难以调整。此外,如果在完成3个月的抗凝疗程后导管仍留在原位,美国胸科医师学会(ACCP)建议以预防剂量继续进行抗凝治疗,直到取出导管为止[38]。有相关研究表明,利伐沙班在治疗癌症病人中心静脉导管相关的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中展现出了良好的前景[39-40]。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和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相关指南均将利伐沙班纳入到癌症病人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中[37,41-42]。利伐沙班的治疗推荐剂量是前3周剂量为15 mg,每日2次,之后维持治疗及降低DVT和PE复发风险的剂量为20 mg,每日1次。另外,EINSTEIN研究的总体数据表明,利伐沙班单药治疗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初始和长期疗效至少与依诺肝素和维生素K拮抗剂的标准治疗一样有效和安全[43]。
6.3 溶栓治疗导管相关性血栓的形成可能会导致导管堵塞。溶栓治疗被认为是维持中心静脉导管通畅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44],但当符合以下所有标准时才考虑溶栓治疗:急性期血栓形成;症状严重;血栓累及锁骨下静脉及大部分腋静脉;病人出血风险低[38]。常用的溶栓药物包括尿激酶、链激酶,以及新型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如阿替普酶、瑞替普酶和替奈普酶[45]。溶栓药物首选小剂量阿替普酶局部溶栓治疗或尿激酶治疗,Ponec等[44]的研究结果显示,2 mg阿替普酶经导管泵入,2 h后,阿替普酶组的功能恢复到74%,安慰剂组恢复到17%。再给药2 mg后,90%的病人功能恢复。没有严重的药物相关不良事件,没有大出血,也没有栓塞事件发生。
7 CRT的预防
ASCO指南推荐常规用生理盐水冲洗导管以防止CRT形成导致的导管阻塞[46]。多年以来,使用肝素盐水冲管和封管以减少导管阻塞一直是护理的标准,但最近的研究表明[47],肝素盐水冲管在减少导管阻塞方面的有效性证据不足。一项最近的关于评估肝素盐水与生理盐水在维持成人病人中心静脉导管通畅方面疗效的荟萃分析共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7 875名受试者,分析结果显示,与生理盐水相比,使用肝素盐水冲管并不能降低导管阻塞的发生率,这可能是由于肝素很难在导管尖端的外侧获得有效的浓度[48-49]。另外,肝素盐水在价格方面要远远高于生理盐水,而且肝素的使用也会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例如:出血、过敏反应、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HIT)等[50]。因此,建议常规选择生理盐水冲管或封管。Dillon等[51]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预防性应用尿激酶能降低CRT的发生率。相反,另一项针对100例接受骨髓移植的病人和接受大剂量化疗药物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试验,未报告预防性尿激酶的任何益处,两组中CRT形成的发生率也相似,肝素组为16%,尿激酶组为19%[52]。可能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证明尿激酶在预防导管阻塞方面的有效性,以及考虑到尿激酶价格昂贵并且具有潜在的副作用,目前的ASCO指南不推荐常规使用尿激酶或其他溶栓药物预防导管阻塞[46]。
是否应该在留置中心静脉导管的癌症病人中使用抗凝药物进行抗血栓预防是目前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预防CRT形成的抗凝药物通常包括胃肠外抗凝药及口服抗凝药。胃肠外抗凝药包括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等,而口服抗凝药包括阿司匹林、维生素K拮抗剂(华法林)、新型口服抗凝药(达比加群酯、阿哌沙班、利伐沙班等)。Lavau等[53]的一项Ⅲ期前瞻性随机试验研究了低分子肝素以及低剂量华法林(1 mg/d)对计划化疗的癌症病人CRT的预防作用,结果显示抗凝治疗显著降低了癌症病人CRT的发生率,并且没有增加严重的副作用。Young等[54]的一项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表明预防性应用华法林与癌症病人症状性CRT的形成或其他血栓形成的减少没有相关性。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9],利伐沙班和低分子肝素等抗凝剂可降低接受化疗的病人PICC相关CRT的发生率。最新的临床实践指南建议不要在留置中心静脉导管的病人中常规预防性使用任何抗凝药物[46,55-56]。然而,ASCO最新的《癌症病人静脉血栓栓塞的预防与治疗》临床实践指南指出[42],大多数住院且患有癌症和急性疾病的病人在整个住院期间都需要预防血栓形成;不建议对所有门诊癌症病人常规进行血栓预防;如果没有明显的出血危险因素,则可以为高危门诊病人提供阿哌沙班,利伐沙班或低分子量肝素预防血栓形成;接受以沙利度胺或来那度胺为基础的化疗和(或)地塞米松治疗的多发性骨髓瘤病人,应为低危病人提供阿司匹林或低分子肝素的药理性血栓预防,为高危病人提供低分子肝素。
8 小结与展望
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是与中心静脉导管广泛使用相关的相对普遍且严重的并发症。绝大多数CRT病人无症状,因此需要临床工作者细致地排查,及时发现并给予正确的治疗能避免更严重的血栓并发症发生。目前对于导管相关性血栓尚无统一的危险因素评估标准。对于CRT的治疗以及是否需要拔除导管需要临床工作者对病人和导管进行全面的评估。CRT的发生不仅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而且还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而减轻这种负担的最有效且可能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是确定高危病人人群并针对其进行预防性抗凝。但目前关于CRT形成与预防性抗凝的研究大部分均为回顾性研究,缺乏大量的前瞻性试验研究,而且目前暂无对于该人群VTE风险评估的统一标准。因此,对于留置中心静脉导管化疗的乳腺癌病人是否需要预防性抗凝以及抗凝药物的选择仍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