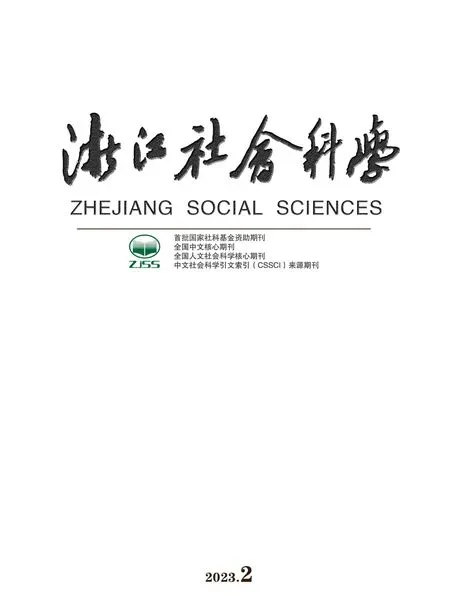个人信息权利的共同善维度*
2023-03-22郑玉双
□ 郑玉双
内容提要 在信息社会的巨大挑战面前,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需要确定个人信息权利的基本属性, 然而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在理论上存在争议。 信息的本质与权利的道德意义是界定个人信息权利需要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 信息是一个解释性概念, 在高度复杂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个人信息所展现的技术、价值和社会维度是展示信息之重要性的基础。 证成个人信息权利依然需要回到自由论和利益论之争的价值框架之中, 但信息社会中技术理性与价值世界的碰撞、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方式转型以及个人人格向数字人格的转变等因素,使得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面临更多难题。 基于共同善的权利观回应了信息社会的法律挑战, 主张个人信息权利的基础在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共同善的双重贡献。 对个人信息权利的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信息社会的发展确立伦理准则和文明规则, 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应体现共同善的价值指引。
我国正深处数字社会的高速建设阶段, 信息已经成为有着重大法律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社会要素。《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是我国通过成文法规范形式对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进行确认和保障的重要努力。然而,围绕个人信息权利的一系列理论议题仍然存在争论, 这些争论背后有一个背景性的证成难题, 即个人信息权利是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权利。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赋权表明对个体之尊严和主体地位的尊重。 个体享有公权和私权等各种权利, 藉此实现个体之基本福祉。 信息对于个人人格发展和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信息权利是否能够成立,则需要回应三个方面的理论疑难:第一,信息对于个体的重要性是否证成信息权利的独立地位;第二,在由信息和数据技术所深度重构的信息社会语境下, 传统权利理论是否能够贡献出一种充分回应技术之挑战的个人信息权利观, 并适应技术发展对法律实践所造成的价值体系调整;第三,如果个人信息权具备受法律保障的独立地位, 那么在技术与法律之价值边界日渐模糊的信息时代, 个人信息权利应当如何配套一种有效的保护机制。 基于对信息和权利这两个关键概念的价值论分析, 本文捍卫一种共同善的个人信息权利观念。 文章试图实现两个理论目标: 一是揭示个人信息权利这种权利主张如果成立, 那么其证成基础在于对共同善的贡献; 二是探讨作为个人信息权利之价值基础的共同善如何影响《个人信息保护法》实践中的价值推理和制度设计。
一、信息的本质
信息是社会实践的构成要素和知识积累的素材, 并为人类实践提供理性化的指引。 什么是信息?我们能够像对待个人生命、健康和财产那样来对待信息吗?答案是否定的。通过权利对财产进行保护体现的是对个体在财产上的特定利益的重视,也与现代社会的财产分配原理相符。然而信息不同于财产。 财产(实体或虚拟)具备一个彰显个体之支配意义的空间结构, 因此财产保护体现的是分配正义,正如罗尔斯所主张的,财产权体现的是对个人参与社会的正义制度安排。①个人信息的实践形式恰恰与财产相反。首先,信息的独立性依赖于一种信息生产、识别和分享机制,否则信息的内涵就会变得模糊。其次,信息需要借助于外在的空间结构才能体现其社会意义和进入法律世界的资格。
由此, 我们就需要回答关于信息之概念或本质的第一个难题。在概念方法论上,个人信息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概念?从法律规定角度分析,这个问题不会产生太多困扰。首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 条对信息的内涵做出了初步界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 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不管这个界定是从公法还是私法视角,至少通过条文形式确定了一些受保护的信息类型。其次,从法律解释或个案分析的角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信息概念的模糊性。
然而,在法理学意义上,对信息的清晰理解首先需要确定其概念类型。 德沃金将法律中的概念区分为自然概念、标准型概念和解释性概念。②信息的确具有一定的自然结构, 但其内涵通常借助于社会实践形式而确定, 所以不能被简单视为自然概念。③标准型概念更容易被接受,因为能够与部门法中的区分相对应, 特别是在与其他权利类型进行对比的时候,比如个人隐私权、数据权或知识产权。但问题在于,恰恰是在类型意义上个人信息与隐私、数据、财产等概念无法清楚区分,所以也引发了个人信息本质的法律属性之争。比如,有学者从民法角度将个人信息权益定性为具有财产性的人格利益。④但从公法角度来看,信息首先是个体的个人自治、生活安宁、获得公正对待等基本权利的外显。⑤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个人信息的类型化区分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其亮点是对敏感个人信息以“概括+列举”的形式做出明确规定。⑥但什么是“敏感”?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必然涉及到对于隐含在信息背后的个人尊严、自主决策、私人空间和交往理性等复杂的价值语境进行挖掘, 否则就会出现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但在实践中被大量过度采集和使用的尴尬境地。
相比之下, 解释性概念是理解信息之本质的恰当方法论立场, 但我们无需恪守德沃金关于解释性概念必须展现概念之最佳价值内涵的要求,而是重点揭示信息概念内涵中的价值结构、技术面向和社会意义。
首先,信息具有不同的价值属性,但其价值主要来自于信息对于个体福利所产生的促进。 信息的本质是能够促进个体福利的具有识别意义的知识性判断。个人信息处于一个复杂的价值域之中,个人信息首先对个人具有价值, 不论是人格属性还是经济属性的信息。个人信息也具有公共属性,通过个人的公共生活发挥其价值。 个人信息的价值属性是法律保护的驱动力,但也是困境所在。
其次,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在现代社会不会变得如此重要。 正是由于发达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信息生产和处理的方式, 才提升了信息的流通属性和商业价值, 但也模糊了信息的人格和人身属性。
其三,信息具有流通性,因此能够产生社会效应。 信息的个人—社会框架是解释信息之概念的外在结构或语境。 个人信息可以用来识别个体的生理、文化或经济特征,个人—社会框架对个人信息所包含的个人利益相关性进行转化。 确立个人信息的社会维度有助于回应以下理论疑难: 信息在传输过程中是否能够保持概念和价值的前后一致性, 以及在社会语境中个人对信息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支配。 基于个人信息的价值和技术维度,信息必然包含着社会内涵。
二、个人信息权利之争背后的价值框架
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需要借助于一个价值支点。 无论个人信息多么重要,从价值衡量、利益冲突和资源整合的复杂过程中提炼出一个以权利为主要推理模式的道德论证过程, 体现的正是权利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信息概念的价值、社会和技术属性都指向了人们在社会中通过信息技术创新来推进共同繁荣的努力。技术应用会存在失范,个人信息的过量收集、恶意泄露和不当使用等,除了对个体造成伤害, 更主要地是损害共同善的实践基础。理论界对共同善的内涵存在不同理解,菲尼斯将之解释为与个人福祉和成就紧密相关的生命、知识、实践合理性和社交等。⑦拉兹将之界定为支撑个人自治的社会共同利益。⑧信息社会创造出一个共同善被深度培育或者重新诠释的空间。 人们进入了一个超空间结构的互动和生产模式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共存以信息为纽带, 以追求共同善的合作行动为载体,致力于实现各种人生成就。不同的共同善概念观会在信息保护的不同阶段和语境下展现不同的规范意义, 信息保护的复杂实践创造了共同善被建构和诠释的各种机会。 权利与共同善紧密相关, 通过对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及其基础的简要分析, 我们能初步确定个人信息权利证成背后的价值框架。
(一)个人信息权利的道德意义
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兴权利形态, 但其权利内涵应符合一般权利概念的基本结构。 虽然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在概念上存在差异, 但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 道德权利为法律权利提供直接或间接的道德依据。⑨在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中,权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请求意义上的主张, 这一请求是法律意义上的, 即权利拥有者对他人的特定主张能够获得法律的支持。⑩但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只是展现了权利实践的结构, 法律对权利的确定和保护是这个结构的呈现, 即通过法律认可权利人的主张, 并将其请求落实在承担义务的特定个体之上。 这个过程同时承载着一定的道德意义, 但并不是每一种法律权利都承载着特定的道德主张或指向特定的道德之善。
如果我们只是把个人信息权利视为法律权利, 那么只需要确认个体在信息事务上能够对其他人提出何种请求便可。 只要能够区分在不同语境之下个人信息能够体现为何种具体的请求,以及哪些主体是这些请求所指向的义务承担者,那么个人信息的权利结构便能确立。然而,如果只是从法律意义上为个人信息权利进行辩护, 可能会陷入到两种权利怀疑论倾向之中。 一种可以称之为价值的怀疑论。 价值的怀疑论并不把权利视为一个具有连贯道德意义的价值概念, 而是在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之中协调不同利益主张的一种机制,信息赋权体现了利益分配的平衡方案,对个人信息权进行限制也是利益调控的正当体现。 个人信息保护也就转化为识别不同的场景, 并确立信息收集和利用的具体边界。⑪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信息保护的迫切任务不是确立信息私权, 而是划定信息侵权的来源以及国家的保护义务。⑫另外一种可以称之为实践的怀疑论。 由于信息技术对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个人权利观念已经无法应对信息流通的社会需求, 因此信息赋权已经失去其正当基础,实践之中也不可行,个人信息当然需要得到必要保护, 甚至是以权利的名义,但在根本上信息权利无法发挥规范功能,所以解决个人权利保护的出路不在于赋权, 而是寻求社会观念的变革。
信息权利的怀疑论并不否定信息的重要价值, 甚至突出了信息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关键角色,但否定信息权利的道德意义。信息权利的怀疑论能够以乐观的姿态拥抱信息社会的巨大变革,并且正确地展现了信息技术对人的行为模式和实践观念的变革。然而,虽然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的互动和实践方式, 权利依然是以道德方式影响人的实践推理。 保护个人的信息权利是对于个人尊严的直接回应, 同时也体现出在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挑战面前,权利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信息权利因为数据流动和信息共享对个人空间的突破,其突出的核心不是个人自主空间的不受侵犯性,而是个人在面对技术对于个人人格和社会交往方式的挑战时, 如何能够更好地参与共同生活和追求共同福祉。 传统的权利理论可能无法应对这些挑战,但这并不是放弃权利之道德意义的理由。权利的道德内涵可能并不能对如何保障权利提供具体化指引, 但法律权利的设定需要权利道德内涵的支持。 对权利之道德维度的忽视会扭曲价值世界与技术世界之间的沟通, 而这正是计算时代的危机和无法承受之重。
权利发挥着价值沟通机制的作用, 权利背后的规范世界包含着各种核心价值, 包括尊严和自由等。⑬权利把规范世界和技术世界沟通起来,为社会主体提供行为规范,“人们基于特定权利提出要求, 其实就是在宣称自己的专属管辖空间不可被侵犯, 而这种专属管辖空间就是人们基于个体之间的平等约束关系而获得的平等自由”。⑭在避免权利的怀疑论对权利的规范力的消解之后,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 权利主张究竟在表达什么价值,或者权利概念如何对价值世界进行组织。权利如同枢纽一般在价值世界和技术世界的复杂关联之中发挥评价指引作用。的确,一个抽象的权利类型在面对这种复杂和剧变的技术实践时确实会引发基于怀疑论的担忧, 但权利概念具有解决价值冲突和实践困境的道德吸引力。
(二)个人信息权利:自由还是利益?
理解权利的道德意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权利究竟是保护个人在特定事务上的自由选择还是该事务所内含的利益。这场争论旷日持久,本文无意介入到这一争论之中, 而是分析自由论和利益论的理论冲突在个人信息权利上如何体现。 自由论体现的是个人信息自决的道德意义, 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对个人掌管自身生活的确认和许可,以及营造一种尊重信息自由的文化。 利益论则体现的是个人在信息事务上的特定利益应受保护的状态,比如生物信息对于身体完整性的利益,金融信息对于个人财产安全和潜在增益的利益。
个人信息权利看起来体现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但自由论和利益论之理论分歧的一个结果是,个人信息权利的基础应当落脚在其中一个支点之上。 自由论主张个人信息即使无助于个人利益的提升,比如个人财富的增加,也应当受到保护,因为个人对信息的支配体现的是个人在自己生活上的主权和信息上免于干预的自由。⑮一个人可以决定将自己的私密信息分享给别人, 但如果个人不行使这种自由,那么他人无权获得这些信息,即使信息本身对于个人来说意义不大。 个人的手机定位、浏览记录和消费偏好等,对于普通人来说商业价值并不高, 但这些信息关乎个人对自身生活的掌控, 信息权利保护的是个体的自主生活:“作为尊重人格尊严和保护人格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个人信息保护集中体现为具备主体性的个体对其信息的自由意志。 ”⑯当个人可以免于外在力量的侵扰时,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尊严得到保障。基于权利的自由论, 个人权利体现了个人在共同体生活中的独特道德地位,彰显了个人自治的价值,也为共同体生活划定边界。⑰
权利的自由论的两个预设使得该理论难以应对信息社会的新兴挑战。首先,权利拥有者的自由在信息社会语境下的概念越来越模糊, 自由是加速信息社会转型的动力之一, 用户利用互联网优势、技术便利和智能环境促进自身福祉,个人的自由参与和获益是信息社会迅速建成的基础, 但信息技术不同于传统社会塑造个体自由的方式。 它的独特性在于个人自由的实体和实践形式被嵌入了技术逻辑,“在大数据模式下, 数据与个人的联系是动态的,而且其变化难以预测,个人信息与客观数据间的界限更加模糊, 信息隐私的保护也更加困难。”⑱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基于自身意愿而不受干预地行动的自由观发生了结构上的变化。其次,个人自由与信息之间的传统关联在新兴信息技术实践中被破坏, 个人信息不再是个人自由提供和分享的对象, 而是在一个密集信息网络中不断被加工改造且反过来构造个人自由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自由观所体现的个体对外在行为空间的支配在信息社会语境下变得非常无力。
利益论的权利观具有回应信息社会之挑战的表面优势。信息与个人利益相关,也能促进社会整体效益, 对个人信息的赋权会改变信息社会的利益格局。按照拉兹等利益论者的观点,权利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是某人的特定利益构成了他人行动的义务,那么此人在该利益上享有权利,这是权利的概念层次;二是对权利的保护,致力于促进一种共同善文化。⑲利益论的权利观强调利益在权利证成上的独特作用,如果我们认可一项权利存在,则意味着特定主体能够主张在某些事项上的请求所承载的利益受到保护和支持。 权利体现特定价值或善好是值得保护的, 通过权利这种方式体现善好的重要性。其次是,权利是一种改变实践推理的价值形式,对权利的捍卫体现对特定利益的认可,同时也要付出维护某种利益而忽视其他利益的代价,比如维护环境利益意味着对经济效益的牺牲,哪怕发展经济会极大提升民众的福祉。 但利益论同样面对很多理论上的困难, 批评者认为利益论无法解释权利概念的独特重要性, 或者无法说明权利之道德意义与利益之重要性之间的裂缝。 然而, 借助于信息社会语境及其对个人人格地位和利益形态所带来的影响, 捍卫利益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也有助于解决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中的一些疑难。在对利益论展开之前,仍有一些实践中的疑难需要做出澄清。
(三)个人信息权利的实践难题
个人信息保护在实践中的确引发很多难题,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背景,但我们应该区分实践难题和理论难题。 实践难题体现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法律上明确指引的缺乏, 加上执法不严、行业发展乱象等,个人信息受侵犯的情形屡屡发生。然而,这个困境可以借助于社会主体守法意识的提高和严格执法而缓解或解决。 随着监管强化和行业自律的形成, 保护个人信息成为强约束。虽然个人信息侵权仍然不断发生,但随着个人信息法律规范的完善,实践难题有望克服。相比之下, 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难题却需要不同的解决思路。
首先, 作为法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现的是个人信息在法律上应受保护的状态, 包括具体形态,比如同意、删除和许可等,以及救济方式,比如删除、赔偿损失等。但个人信息的法律权利内涵应该受到其道德内涵的支持, 否则抽象权利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对应只能依赖类型化判断, 而缺乏一个可靠的证成基础, 并且关于信息权利之边界的判断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分析问题。
其次, 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内涵当然会存在重叠,但鉴于信息社会对人的行动空间的改造,保留隐私的狭义空间意义, 而将个人信息视为个人参与社会的计算性知识判断,在实践中更为可行。⑳个人信息独立受保护是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但隐私、信息和数据等概念在理论上容易区分,在实践中的界限却比较模糊, 个人浏览记录和手机定位等是借助于网络服务或定位设备而留下的具有个人色彩的痕迹,应被视为隐私还是信息,往往存在争议,毕竟隐私或是信息都不是自然概念,而是解释意义的概念。 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价值分析有助于明确这些要素之间的界限。 隐私在价值上突出了个人不被侵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个人的人格独立地位得到凸显。 个人信息则沟通了个人生活空间与社会空间, 所以个人信息保护的重点不在于凸显个人独立地位, 而是在信息流通中确立边界。波斯特将侵犯隐私视为“对调整现代社会信息流动的社会规范”的违反,㉑但这个论断更适合用来保护个人信息, 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深度信息化的进程中, 信息收集和使用活动具有技术性和社会性两个维度, 信息逻辑和社会规范的融合成为必然。
最后, 权利的价值内涵是支撑权利主张之正当性的基础, 但权利实践不只是要体现权利背后的价值要素, 更主要的是如何将这些重要的内容以便于法律规范和保障的方式展现出来, 包括确立权利的法律地位、设计权利救济方案和解决权利冲突等。 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争议点在于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把知情同意作为信息流通和处理的必要条件,但在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服务商提供服务的前提是用户同意他们对信息的收集和处理。 虽然用户同意表明用户对信息条款的接受, 这一做法已经偏离了同意概念的原初结构, 或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现个人意志和自决的同意,“个人信息收集、持有、利用的实践形势导致信息主体授权容易落入形式化, 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实际上难免成为‘一揽子’授权。 ”㉒
三、以共同善为基础的个人信息权利
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与内涵是个人信息保护的灵魂,也是迎接信息社会之挑战的核心命题。在拉兹所提出的共同善权利观的基础上, 本节借助于信息技术应用对人类行为模式和利益诉求所产生的更新, 捍卫一种共同善意义上的个人信息权利观,以回应信息保护实践中所出现的难题。
(一)权利与共同善之间的关系
拉兹认为, 权利的真正价值在于对一种共有的自由主义文化的贡献, 这种文化服务于共同体的成员。 由于权利所服务的个人利益与它们对公共善的贡献, 鉴于这种相互加强的关系的稳定与安全, 有理由把这种权利对共同善的价值视为其证成的一部分, 这使得共同善成为一个决定权利分量的要素。
拉兹的共同善权利观强调了共同善在证成权利上的独特力量,这一观念具有两个特色。 其一,他强调权利在服务于个体利益之外对社会所共享的共同善的独特贡献, 权利概念不只是依附于个人利益, 而是也体现出对共同善所做出的贡献:“权利并不匹配于其要服务的权利持有者的利益,因为所有这种权利是由这种事实得到证成的,即通过服务于权利持有者的利益来服务于其他人,正是这些人的利益对于决定这种权利的分量有贡献。”㉓其二,对权利之实践意义和价值原理的理解有赖于共同善这个概念。拉兹主张,共同善的内容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当然存在着争议, 但其一般性原则至少受到了核心人群的同意, 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共识。共同善划定了权利得到保障的范围,也为权利的证成提供了价值支持。
这种权利观受到了一些批判, 其中一部分来自于意志论。基于意志论的主张,个人权利的独特道德分量体现在权利与个人自治之间的内在关联, 以及权利概念所体现的对个人主体地位的尊重。卡姆主张,利益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权利对个人利益可能意义不大,但应当受到特别的保护,比如言论自由权。卡姆认为“权利是对人的属性的回应, 这种属性本身可能是保护人们利益之所以重要的必要前提”。㉔
然而即使无法完全回应自由论权利观的挑战, 共同善权利观在分析个人信息权益的属性问题上仍具有独特的优势。 作为权利之证成性价值背景的共同善, 在解释个人信息权利是否成立的问题上,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利益论或意志论在解释个人信息权这种新兴权利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上,存在各种局限,但共同善权利观有一个双层证成结构, 即个人利益和个人对共同体文化的贡献, 具有应对个人信息之新兴权益形态的结构优势。第二,信息社会创造出共同善得以实践的新兴语境,如前所述,个人自由与信息反向支配之间存在较大冲突, 共同善作为社会成员共享的利益形态, 是个体免于受信息社会彻底支配的缓冲地带。 社交媒体对个人生活的深度塑造以及个人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改变了自由实践的内涵。共同善的引入可以对信息技术对个体的影响形成结构性制约, 因为信息技术改变了个体自由实践的外在环境, 不利于支持个人自由实践的共同善文化的培育。
共同善权利观赋予信息社会的使命是, 信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应当服务于社会成员的基本善。 对个人自由的促进和生活水准的提升在信息社会中的内涵变得中性, 因为技术支持下的自由观被技术所重塑, 自由实践与技术应用之间的价值关联必须要借助于共同善这个概念才能补足。㉕在人脸信息被采集的情形中, 个体对人脸信息的支配通常让位于采集的必要性判断, 包括价值判断、政策判断和社会共识程度等——如果一个小区屡屡失窃,显然人脸采集的共识度会高。人脸信息的应用、储存、传输和保护等,共同构成了人脸信息应受保护的价值分析框架和社会语境。 个体与外在复杂环境的互动被技术所重构, 个体的利益也不断被社会利益所重塑。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传统对抗性张力——社会约束个体, 个体服从于社会之强力规范——变成了互嵌性张力, 个人无法判断自身的社会性边界, 社会也无法呈现一个清晰的结构来呈现个体性的行动空间。
(二)基于共同善的个人信息权利
基于共同善权利观的基本立场, 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需要把信息社会作为价值实践环境。 在概念上, 个人信息权利指的是个人在信息事务上所拥有的特定利益应当受到权利这一独特价值结构的保护。个人信息包含着技术、价值和社会三个维度,在权利问题上,个人信息指向了个体在信息上的包含价值维度的利益,包括人格利益、财产利益和社会交往利益。 这些利益不只是与个人福祉相关,还贡献于内嵌于信息社会的共同善,个人信息权利体现的是共同善对个人信息利益的支持和证成。 这个证成过程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信息社会重塑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结构上,社会由个体所构成,社会是个人的实践语境。 技术重塑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个人嵌入信息网络之中,个人被赋予信息人格, 以区别于基于个体之独立地位的传统人格。信息人格体现为个体拥有信息身份,个体通过信息传输以实现社会互动和个体接受信息评价等。
第二,从价值视角上看,信息社会符合拉兹所提出的“社会创造之善(socially created goods)”的环境。在价值层次上,基本善的核心要义不会有太大变动,社交媒体仍然是为了促进友谊这种善,外卖平台和网约车是为了便利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但具体的社会善好受社会实践所影响。 按照拉兹的主张,有些价值是由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特定实践支持和创造价值。㉖支持特定善好的实践对这些善进行发展, 这些善在实践过程中不只是存在和外显着,而是不断被更新。 其次,对这些价值的获取依赖于关于这些价值和知识传承的社会理解。这类知识的传承又依赖于拥有社会实践所维持和创造的概念。
拉兹的这个主张具有一定的争议性, 特别是关于价值依赖于实践的主张。 哈瑞尔借助于第二个主张对权利与价值之间的互惠关系进行辩护。㉗信息流通和使用会引发价值冲突, 比如个人对信息的支配与社会主体对个人信息的需求存在张力。信息社会是信息价值被支持和创造的环境,因此信息价值不是对抗其他价值的堡垒, 也不是证成信息权利的排他性力量。所以,理解信息之价值无法借助于价值衡量之框架, 而是在信息社会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调适, 以构建个人信息权利的完整价值图景。
第三, 个人信息权利成为判断信息社会之健康运作的规范依据。 借助于理解个人行动和社会实践的规范理论, 我们可以说个人信息权利是贡献于个人福祉和社会繁荣的价值机制, 保护个人在信息上所拥有的独特利益。 个体融入信息社会的信息生产和流通机制,在参与“社会创造之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归属性利益, 即是个人信息权利。权利是价值实现和保障机制,个人信息权利包含着个人信息价值实现和保障两个领域。
1.个人信息价值的实现指的是个人在信息实践中通过自治的选择和行动来实现福祉。 个人自治是理解个人信息权利的关键概念。 但在信息社会语境下, 自治概念本身所承载的理论争议被赋予新的形式。首先,个人在信息事务上的自治权主要体现为对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同意。 同意表明了个人对信息的支配, 以及相对人对权利人之自治权的尊重。 但同意的要旨并不是为了体现个体对信息的绝对控制, 而是个体参与到共同善事务中的能动性。 信息权利保护个体在信息事务上的能动性,既保护个体的自治决定,也将个体纳入到一个促进能动性的价值环境之中。在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权利的保障不只是体现在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保护个体在信息收集上的知情同意, 或者个体对个人信息的支配, 也体现为个人自治价值与其他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㉘
2.个人信息权利的保障体现在社会和制度两个层次上,二者相互关联,但侧重点不同。 社会意义体现在个人信息事务上形成关于个人信息的整体认知和实践回应, 比如随着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展,通过社会互动和技术公司自觉披露,帮助用户在享受技术服务过程中对自身信息形成准确认知。 个人信息权利的制度层次则体现在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 我们必须承认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规范无法应对信息保护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难题, 毕竟我们进入了信息爆炸时代,个人的消费、金融和医疗数据急速增长,个人信息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法律全面保障在实践中并不可行。 个人信息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在很多领域成为必然, 特别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个人信息保护与公众知情之间不断博弈。㉙基于共同善的权利观,纳入法律保障框架的个人信息应该综合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信息化保障的必要性程度:社会生活已经进入全面信息化进程, 但并不是所有信息都应该列入《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保障的范围。 应受保障的信息与基本善的关联程度有关, 共同善并不是判断信息之利益属性的最终因素, 毕竟信息的价值受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随着以机器学习为动力的自动化决策的深入应用,机器学习算法处理个人信息时会产生“信息溢出效应”,即算法深度应用而对信息的过度解读和开发。㉚这种技术理性主宰导致的溢出性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范围, 需要借助于算法规制的相关理论对技术外溢的公平性进行判断。
(2)个人利益促进和贡献于共同善的可能性:由于不同信息与共同善的关联程度不同, 在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过程中, 应当区分不同信息贡献于共同善的程度和方式。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进行技术和价值层次的双重分析。 个人医疗信息对于分析疾病研究和治疗方案的优化意义重大, 但由于个人医疗信息与个体生理隐私紧密相关,所以应当归入个人隐私,以隐私权的形式加以保护。㉛
(3)信息社会美德和共同善文化的塑造: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的实践方式, 人与技术的关系正在经历从人与技术的并存向人与技术的同构这一模式转型。人类在与技术并存时,通过发挥技术的工具意义而实现人的福祉。 但在人与技术的同构阶段,人的福祉也被技术所投射,人的福祉的内涵发生变化。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传统意义上的福祉观无法与新兴技术语境中的个人权利呼应, 所以需要重构信息社会的美德, 重新确立信息社会的伦理原则。
四、个人信息权利之法律保护的法理框架
个人信息保护是复杂的社会实践, 个人信息权利作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主张, 在技术实践中如何获得充分的法律保障,涉及到很多因素。 《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权利,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个人信息权利目前还无法与实在法中既有的权利体系相融合。 但从权利的一般理论出发, 我们可以确立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和共同善内涵, 从而可以基于其共同善属性来反思相关的制度设计。个人信息保护是一项宏大工程,具体制度安排也涉及多个领域, 本文无法从细节上探讨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完整框架, 仅从法理层面反思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未来。
(一)理解信息社会的本质。 尽管我们对信息社会或者智能社会的内涵还没有形成共识, 但信息社会的到来已成定势, 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和个人权利的意义需要导向信息社会的构建。 社会主体的行为边界、损害的界定和法律责任的承担原理等,都需要结合信息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分析。信息社会是否颠覆了法律的价值体系, 是否改变了人们的实践模式, 由此产生了法律概念内涵的改变,以及信息社会下由政府还是平台来治理,都是新的问题。共同善是信息社会构建的价值因素,信息技术研发和应用都应遵守以共同善为中心的文明准则, 对个人信息具体类型的认定也应体现共同善价值。
(二)重新认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个体人格向数字人格的扩展。 传统人格观已经不适应信息社会, 因为个体在信息产生和使用过程中形成了数字人格。 个人行踪和行动记录都可以数据化和信息化, 意味着个人意识和行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同意”仍然是个人处理信息事务的基本原则,但显然同意的意义需要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同意体现的是个体对个人事务的支配和掌控,但信息技术下的个体同意实际上是一种授权, 即同意信息服务者在收集、加工和使用过程中以服务于共同善的方式形成自我约束。那么,个人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也存在着服务于公共利益而被合理使用的可能。㉜信息时代需要面对的新命题是, 社会参与者如何能以有助于培育个人数字人格的方式共同构建信息社会。
(三)梳理个人信息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关系。体现共同善的个人信息权利是一种道德权利,《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政策和法律框架。 法律权利的保障需要对权利内涵、救济以及冲突解决做出规定,权利的道德意义不能给出具体详细的政策指引, 但可以作为法律权利的背景性价值因素发挥作用, 影响立法者的抉择和法律规范的解释。 个人信息权利的共同善维度是一种抽象的表达, 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出对共同善的重视究竟需要如何具体指引社会主体的行为,比如技术研发者如何开发一种应用。但基于拉兹所主张的价值理论, 信息技术实践是创造价值的过程, 通过对人们参与技术实践所形成的共同善理解, 在具体情境中分析个人信息权利发挥其规范意义的方式, 个人信息权利能够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例如,在“黄女士与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㉝(以下简称“微信读书案”)中,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判决就体现了个人信息权利在信息社会中的复杂价值处境, 以及从共同善维度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腾讯公司开发的微信读书在用户使用微信登录时, 要求用户一次性授权其获取用户的微信好友信息。 微信读书在用户使用该应用程序时, 自动激活了用户的好友关注并向好友分享阅读习惯的功能。 原告主张微信读书的这一功能侵犯了其隐私权, 被告腾讯公司则辩称原告已经授权。法官在审理后认为,微信读书侵犯了原告的信息权利, 但由于阅读记录并非私密性信息, 因此腾讯读书的做法并不侵犯原告的隐私权。
“微信读书案”从个案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之边界的界定做出了有益尝试, 但也反映出从制度层面完善个人信息权利之保护体制的难度和从价值层面理清个人信息权利之社会道德内涵的不确定性。 信息技术公司大量地开发新技术并在移动媒介上应用,比如阅读、音乐分享、短视频等,固然受商业利益所驱动, 但在本质上是参与共同善之社会创造的实践。 个人信息权利在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发挥着构建信息收集者之行为边界的角色。尽管在具体个案中法官的推理是有限度的,但从该案可以挖掘出个人信息权利的共同善维度在个人信息保护过程中所承载的推理意义。 微信读书依附于微信这个社交平台,通过利用微信平台的海量用户推动知识分享和挖掘图书的商业价值。好友之间的关注与阅读分享既是一种知识传播,也具有商业推广意义。 商业运作与知识分享这些不同的价值之间究竟何者优先,是一个从运营商、作者或读者角度可以做出不同诠释的开放性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读书平台的开发是直接贡献于知识这种基本善的。在日常生活中,好友之间的书单分享是促进社会互动和知识进步的主要途径,读书平台通过将这种社会交往方式加以数字化和平台化,极大地提高了图书传播之效率,并借助于算法技术重塑了知识与社交融合的现代模式。
从价值视角反思“微信读书案”及社会各方主体在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上的角色, 可以展现个人信息权利之共同善维度的两重内涵。第一,个人信息创造的过程(阅读、社交和娱乐)是推动共同善之社会实践的动态过程, 正是由于几亿用户的信息实践使得虚拟的图书资源平台可以繁荣, 个人信息是内嵌在知识之创造和实践过程中的增益性要素, 对个人隐私所体现之尊严的保护与个人信息分享所追求的公共善应当达成一种平衡。第二,信息社会的价值关联变得更为多元和多层次,个人行踪的数字化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意义, 网站运营者对个人数字人格的开发和利用尽管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共同善之探索机遇, 但网站运营者对隐私保护的懈怠和隐私披露的漏洞破坏了个体积极参与共同善的良性空间。 仅仅通过完善立法规范和优化司法推理来保护个人信息权利是不足够的。在信息社会的复杂利益格局中,以共同善为中心营造出整全性的信息伦理共识并细化为社会各方主体的明确责任, 形成关于个人信息权利之共同善维度的共识, 是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真正出路。
结 语
在计算时代, 计算力的支配和数据技术的全面运用,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互动方式、行为模式和社会运转的逻辑。数据以无形的方式在流通, 个体行为所汇集的数据使得每个人成为受信息技术影响的潜在主体。 信息具有商业价值, 信息商业化是经济发展和产业更新的动力, 由于信息利用对个人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信息产业化产生了一个公共的正义环境,社会各方主体对信息的流通和分配应该受到符合正义标准的限制。权利体现了共同善,既是信息社会所产生的结果, 也有助于权利观的提升和权利保障的强化。 个人信息权利所有者并不一定会从权利实践中受益, 毕竟个人信息并非都是有价值的,而且不是每个人都会充分行使这种权利。共同善的权利观体现的是对一种言论自由文化的尊重,这种环境让大多数人从中受益,并反过来促进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
②[美]罗纳德·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 页。
③在计算机科学中,信息当然是一个自然概念,无论是从语义角度还是数学角度,信息哲学的一部分研究也是探讨信息是否具有实体,还是只是意义的体现。 但随着信息的范围越来越扩展,对信息的概念分析不得不综合技术、文化和社会等各个视角。 参见[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什么是信息哲学? 》,载[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编:《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上册), 刘钢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2~43 页。
④参见彭诚信:《论个人信息的双重法律属性》,《清华法学》2021年第6 期。
⑤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权益的三层构造及保护机制》,《现代法学》2021年第5 期。
⑥参见王利明:《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问题——以〈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解释为背景》,《当代法学》2022年第1 期。
⑦See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86~89.
⑧[英]约瑟夫·拉兹:《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葛四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2 页。
⑨参见陈景辉:《法律权利的性质: 它与道德权利必然相关吗?》,《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 期。
⑩[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2 页。
⑪参见丁晓东:《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与行为主义规制》,《法学家》2020年第1 期。
⑫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中国法学》2021年第1 期。
⑬参见郑玉双:《人的尊严的价值证成与法理构造》,《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5 期。
⑭张峰铭:《论权利作为要求——超越利益论与选择论之争》,《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 期。
⑮[美]莱夫·韦纳:《权利》,瞿郑龙、张梦婉译,载朱振等编译:《权利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2~33页。
⑯郑维炜:《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属性、法理基础与保护路径》,《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6 期。
⑰[美]罗纳德·德沃金:《刺猬的正义》,周望、徐宗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4 页。
⑱刘泽刚:《大数据隐私的身份悖谬及其法律对策》,《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2 期。
⑲[英]约瑟夫·拉兹:《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葛四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5 页。
⑳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 期。
㉑[美]罗伯特·波斯特:《宪法的领域》,毕洪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 页。
㉒参见张珺:《个人信息保护: 超越个体权利思维的局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 期。
㉓[英]约瑟夫·拉兹:《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葛四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 页。
㉔[美]F.M.卡姆:《权利》,杜宴林、李子林译,载朱振等编译:《权利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8 页。
㉕See Priscilla M.Regan, Privacy as a Common Good in the Digital Worl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5, No.3, 2002, p.399.
㉖See Joseph Raz, Engaging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A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05.
㉗See 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38~39.
㉘参见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 期。
㉙参见郑曦:《刑事诉讼个人信息保护论纲》,《当代法学》2021年第2 期。
㉚参见陈林林、严书元:《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的平等原则》,《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 期。
㉛彭特兰主张可以基于对人们的行为状态推测人们的健康状态,“手机上的某个应用可以悄无声息地寻找行为上没有明显特征的变化,并进而推算是否在发生某种病变。 ”[美]阿莱克斯·彭特兰:《智慧社会》,汪小帆、汪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 页。 但显然这种信息采集方式明显构成了对个人隐私的过度干预。
㉜参见于柏华:《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合法性判准——从〈民法典〉第111 条的规范目的出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3 期。
㉝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 民初16142 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