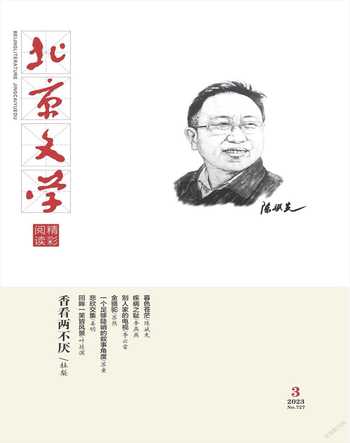金骆驼
2023-03-13苏热

那些带电火花的蛛网越过黄镇,寻着人的气息一路蔓延。挥舞的触手碰到荒漠,像是被四起的黄风刮伤,迅速蜷缩进一旁的小村子里。交织错节的电线嗞啦作响,给村子带来向下亮起的烛火,闪烁人影的黑盒,还有日夜不停的轰鸣引擎。多出来的嘈杂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远处。让他们心头长出来一块石头,就此压住金骆驼的消息,十多年没有人说起。
朝鲁不止一次地告诉别人,自己安了几年的锅子,就装上第一天,看得晃了神,就那么一下。好像是说什么油的。也没啥,就是图个新鲜。但他从来没有把心里的真实想法告诉给别人,怕人笑话,让人说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再惦记金骆驼的话。
朝鲁那天打开电视开关,学着别人的样子,把一个叫遥控的白盒子对着眼前的小黑盒子按一下,画面不停跳转,朝鲁扑哧笑出声:“也就那么回事,和我见过的没法比。”他打了一个哈欠,打算关电视时,画面中正好出现一个窈窕女人,站在沙滩上,顶着烈日,往自己身上涂抹,配着热闹的听不懂的音乐,朝鲁感觉心里被剜了一下。
朝鲁眯着眼睛,弯着腰凑到屏幕前,想使劲往里看,没过瘾,他又赶快绕到电视后面,黑漆漆的机身挡住视线。朝鲁闪回身,广告结束,朝鲁愣在原地,蹲半天,从兜里掏出一根烟,抽几口,才看见眼前呼出的烟雾有一个大洞。
朝鲁挥挥手,一下补平虚空中的缺白。朝鲁朝窗户的方向望去,“和那荒地一样,就是有点蓝。”这是朝鲁第一次见到海的所想,之前都是听说,凭着航沙人的本能,他总觉得除了那遮天蔽日的阴黄外,还有另外的辽阔在等待着他。他虽然不再年轻,失去征服的欲望,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胸膛里有些东西正在慢慢变大,就是这些东西,让他拥有比肩征服的自信。
不管大海还是荒漠。那些所谓探险家的存在只是一时,但他們的盛名却穿越一个又一个的岁月。而那些像朝鲁这类生活这些无言广博身边的人,他们的脸庞却一个接一个消逝融入人眼不可及尽的辽远中。
朝鲁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大海,而是远处白板子上站着的人。在他的认知里,海边也有像是他这样的人的。只是女人身旁的精美的草屋让朝鲁颇为感慨,他知道自己的身影永远不会出现在电视里,让海边的人看到,周围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热闹人群。唯一的归宿就是渐渐消逝在沙漠的阵阵喘息里。
想到这里,朝鲁的眼睛一热,伸手摸了一下,黏在他眼眶下的沙粒划了一下脸,顺着周围的皱纹,簌簌落下。他像是突然惊醒一样,透过窗户,看着屋外立着的一个泛黄的黑木板,那个陪伴他多年,用来航沙的追梦工具。“你也应该老了,肯定老了。”朝鲁往门的方向叹出一口气。
自那以后,朝鲁多次回想电视里的场景,他想知道,那些海边草房子里的人是不是也和他一样,为了一个虚美的传说把自己和沙漠捆绑多年。海里面会有金鱼吗?还是说会有财宝?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终其一生,生活在海边的。他想问问别人,但沙漠风大,每次开口,都会不经意含进一口呼啸的风沙。
在朝鲁小的时候,他总听祖父那辈的航沙人说起金骆驼的传说。那些人蹲坐在炕上,端着银碗,抽着旱烟,双双布满年轮的眼睛发着亮光,语气坚定地说起远方沙漠的事:有人说那是祥瑞的象征,见到它,会得到庇佑;也有人说金骆驼是会带来财富的,凡是它走过的地方,蹄印之下的沙土都埋有黄金;还有人相信,金骆驼本身就是早年商队遗失的财宝所结化的精灵,只要找到它,就能找到价值连城的古董。
航沙人很多不是黄镇人。起初,他们都是为了寻找金骆驼,不知何年何月在黄镇的漫天阴黄中迷路,把根扎进这里,世代做起航沙人。渐渐地,为满足生计,他们搁置寻找金骆驼的想法,开始帮助牧民寻回无意闯入沙漠的牲畜,也会受牧民之托,用沙船运送一些水和吃喝用品。
每当黄沙呼啸的时候,朝鲁就坐在窗户边向外望去。他总能察觉到不远的阴黄里闪烁的人影,发现他们的足迹,望到他们一点点消逝在沙丘之后。当他学会辨识清楚那些缥缈的人形是谁时,这里的航沙人已经都被吹埋进厚厚实实的沙土之中,这其中也包括他的祖父。
朝鲁父亲从他祖父的身体下接过那个两米见长的黄木板,撑起帆,看见上面密密麻麻的窟窿,说这个帆只够承受一人的死去。朝鲁没有明白父亲的意思,他那时只顾金骆驼的踪迹,在黄沙漫天的日子里,使尽全力,想把自己的目光投得再深一些,他没有理由地相信——祖父看见金骆驼了。但他年岁已高,拉帆的手在狂风中不小心脱力,被忽起的大风裹挟的沙暴吹上天,又被狠狠地扔到地上。
父亲通过祖父设下的成为航沙人三道考验时,朝鲁还不记事。在日后的谈及中,祖父满脸的皱纹总是充满欣喜地抖动。祖父和他的同辈都认为父亲拥有着多年难遇的航沙人潜质,他们把寻找金骆驼的希望全部押到父亲的身上。
祖父和他友人离去后,父亲一直惦记着搬开身上的重量。在午夜风暴骤起时拉上窗帘,企图回避那些如炬般闪烁着的目光。他不明白父亲对金骆驼兴趣缺缺,只满足于搬运一些无谓的琐物补贴家用,他明明有着更好的技术,更年轻的体魄,以及更多的时间,来寻找那隐藏在沙漠深处的黄金精灵。
与祖父一辈的最后一位航沙人被风裹进沙崖那天,父亲罕见地落泪了。那一代航沙人只留下五块船帆,其中就包括父亲的那一块,在每个无风的夜晚,朝鲁被金骆驼干扰得不能入眠时,总能隔着墙壁听到父亲的叹息。“唉——嗨。”像是在费力地抓取什么,吃痛,最后不小心放开。
朝鲁听到父亲的死讯时并不意外。那段时间一到傍晚,父亲把沙帆从船上取下来,坐在门前的木槛上,拉起一个角,透过沙帆的洞窟对着沙漠里的落日望去,恍惚一阵,便掩面叹息起来,说起今天运货时,在风沙里遇到的熟人和长辈,甚至有一次,他感觉到妻子的掌纹。那些迷失在沙暴身体里的故人,已经成群结队,在等待他的到来。
朝鲁从学校请了一个月假,用来传承先辈们的航沙技巧,最后用三天时间,再通过父亲的三道考验。在向县中学老师说起请假缘由时,老师并没有听说过航沙人曾经的辉煌。朝鲁手舞足蹈地照着父亲的样子比画出航沙时的动作:装风向标,挂帆收帆,用身体的重量和倾斜来控制船头的角度。老师的惊奇转瞬即逝,朝鲁不知如何作答,也不想对这样一个外人说出航沙人的秘密。
“不是有车或者摩托吗?这样不是拉得更多?”
老师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朝鲁只是不想承认。朝鲁上初中后,支出一下变大。几个牧民从黄镇淘来摩托,依靠晴天的运输,基本上满足这片沙漠上居民的日常需求,朝鲁父亲此时显得多余起来。他学着周围牧民的样子养起羊,拿着铁锹产料,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投进和周围阴黄格格不入的星点白花之中。
老师来访朝鲁家两次,身影就彻底隐在沙漠的另一头,像朝鲁这样莫名其妙退学的孩子在这片阴黄中非常常见。他只能掉转精力,把自己的心血放在渴望而且有能力逃脱阴黄束缚的孩子身上。
朝鲁在掌握挂帆系绳的技巧后,沙漠就像苏醒一样,朝着黄镇的方向喷了半个月的鼻息。
视野不好的情况下,航沙人得不到群星和太阳发来的准确讯息,第二项的方向测验只能作罢。朝鲁父亲卸下沙帆,让朝鲁举起三天,观察呼啸的风沙最后能够堵上沙帆几个窟窿。
第二天的时候,父亲接到村里的消息,说是有个大学生计划横穿沙漠,在阴黄中已经失联三天,而那些参与搜救的摩托,被风沙堵住关节和气管,愣在原地,变成废铁。眼下只有航沙人能够帮忙。而另一个航沙人据说已经搬进黄镇多年,找人的重担只能落在父亲肩上。
朝鲁一夜没有合眼,他的窟窿只被风沙堵住两个,他来到屋里的水缸前,背着身,数着墙上的虚影,只有三个,朝鲁心里不禁发慌,他又举起沙帆,对准右眼,模模糊糊的景象让他产生不好的想法。朝鲁依稀记得父亲当年经过三天三夜的磨炼,沙帆上只剩下两个窟窿。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为不好的天气,他始终坚信自己是驾驶沙船寻到金骆驼的不二人选。多年以后,朝鲁知道这和海上用的帆根本不一样。不管用什么材质来做帆,只要黄风一起,它們立刻就会千疮百孔。沙帆的航行依靠的是先祖的庇佑,而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做航沙人的料。
朝鲁把沙帆交给父亲,并没有向他说明发生的事情。父亲匆匆固定好沙帆,乘着风,一头扎进沙漠的巨口之中。
朝鲁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供他怀念的只是一个失踪的信息。父亲也没有找到那个大学生,等阴黄渐淡的时候,村民们在沙漠中寻见一个涡旋的痕迹,还有一些衣物碎布,没有一点人的气息。
等人们默认最后一个航沙人魂归沙漠,准备离去时,涡旋的中心缓慢浮起一个点。又过几分钟,整个沙船从沙漠里浮了上来。人们意识到,最后一艘沙船还要在这片荒野上行驶一段路。
朝鲁从梦中惊醒,窗外的人声顺着沙子的路径钻进家里。他梦到沙暴把他的家吹垮,所有的门窗吹到天上,垒墙和垒炕的砖块在沙粒的快速捶打下变成齑粉。他在风暴里挥舞手臂,大喊,想要抓住点什么,失重带来的绝望笼罩着他,他的身体被风沙一点点击中,出现裂纹。不知何处飘来的布裹挟住他的全身,他在空中调整方向,着地时,脚趾并没有传来沙粒的触感,他低头一看,是一个黑色的木板接住了他。
人们拖动着沙船,连同父亲的死讯从沙漠深处一同带给朝鲁。朝鲁跌跌撞撞冲向沙船,用脸抚过沙船木板的每一寸黑纹,没有一点温度,也没有任何熟悉的气味。
朝鲁想到父亲曾讲起自己名字的寓意,看向沙漠。人们围站在他的身边,像一堆无言的沙块,他们那些带有同情的注视,在烈风中转瞬即逝。等人们走后,朝鲁抹干眼泪,看着帆上多出来的一个新洞,拍拍手,爬上杆,卸下船帆,带回家里。
父亲离世不到一个星期,村里就买了两辆结实的皮卡,以防大风天里出现意外。朝鲁记得祖父曾谈到过去带着父亲,挨家挨户上门说起接过衣钵的样子。眼下,他已然成为最后一名航沙人,这个要有什么纪念?还是要有什么仪式?朝鲁想不明白,他只能不停地朝着沙漠的方向看去。
没有人见证朝鲁通过航沙人的三次考验,更没有人向他投以尊敬的目光。要在以前,这是他们村子里的大事,甚至要专门从黄镇请一些唱歌跳舞的人前来祝场,庆贺新一代沙漠守护人的到来。
朝鲁步行几公里叩开一户人家的门,见到的只有不解与疑惑。关门声停歇一会儿,几公里之外,又响起了敲门声,像是发问。整个村子几十户人家,得不到一个答案。在他们的眼里,自己的存在已是多余,不如回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干点别的事。朝鲁不知如何作答,在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呆愣愣站一下就离去。朝鲁突然想到自家引以为傲的三次考验,已然成为往日黄风的一部分,而自己朝思暮想的金骆驼,更是成为生怕别人知道的笑话。
想要得到父亲的技术完全不可能。人身上最为珍贵的东西是教不了、体会不到的。朝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养羊身上,航沙比起养羊简单多了。漫天的黄风里,又多出来一阵咀嚼草料的声响。
自那以后,朝鲁的身体在夜里再也没有传出生长的声音。沙漠里日夜不息的沙尘,把他的身形雕刻得精瘦、硬棒,两个眼睛像是沙漠里迎着光亮的石头,手指的关节突出,长成红柳树瘤的模样。固定船帆的线绳经年累月地摩擦,把他的掌纹磨平,在上面留下整齐的线段,让即使不懂手相的人,也能一眼就从朝鲁的手上看出,他拥有整个航沙人的命运。
朝鲁从父亲那里接过的羊,开始还能一年下几个羔,四五年以后,数量就稳定在四十只。大羊出掉小羊才活,不然下的都是死羔。为此朝鲁没少往村里跑,到处问人,得到答复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句话,含糊不清。他到县里,花钱找兽医站的人去接生,最后降下来的还是死羔。
村里开始还派人过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病,还是水草有问题?几圈下来,没有看出一点问题。有些老人背后嚼舌根:“航沙人一共四十个人,还不算朝鲁。”话传一圈,到朝鲁这儿,已经成为诅咒,有人更是直言不讳,说怎么也得四十一只,朝鲁肯定不是航沙人。
朝鲁不信邪,把自己的羊分出去五只,寄养在邻居家的羊圈里,自己每天航沙几里路,往过送料子,看这样自己的羊圈里能不能下新羔。不到一个星期,邻居就让朝鲁把羊带回去。说他的羊来以后,每晚都能听见羊圈里面的说话声,絮絮叨叨个不停,有点吵人。朝鲁只能把羊又弄出去,告诉它们该回家了,让它们自己先往回走。
朝鲁接受航沙人饿不死、吃不好的命运。晚上看着窗外的繁星,他不禁好奇起自己的先辈接受命运的过程。在入睡前的朦胧中,一声脆耳的驼铃将他唤醒,他凑到窗户前,看向外面,只有无尽的死寂在蔓延,
正当朝鲁以为幻觉,回床入睡时,外面又传来一阵悠长的鸣叫,响彻天地,朝鲁的小屋微微发颤。像是骆驼在叫,朝鲁心想。群星的光芒打在地上,沙漠中不知名的结晶以眨眼的频率闪着微光。月光像雪一样落在沙上,在风的作用下明灭。朝鲁想起县里上初中时,地理老师提到的鲸鱼。那个老师因为支教项目才来这里,是大城市人。她来到黄镇边上的沙漠,第一次听到悠长的骆鸣,想到的是海洋里的鲸鱼。在她看来,鲸鱼和骆驼都是无边的广阔里最大的生灵。年幼的朝鲁无法想象出鯨鱼的模样,脑袋里只能把骆驼的形象沾上水,不断放大。
附近住的人家里没有养骆驼的。朝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把右手从衣领伸进去,朝着胸口的地方猛地拍打,等膛脯上传来火辣辣的痛感时,他才穿上鞋,朝门外走去。
没有风,整个沙漠屏住呼吸,朝鲁站了一会儿,就被这安静压得喘不过来气。远处沙丘的背面,投来一个眼神的温度。朝鲁分辨着这个感觉,没有一点熟悉的记忆,他朝着那个方向跑去。
远远地,朝鲁看见一个影子,四条腿,直挺挺地像是放在地上一动不动,在黄色和黑色的交界处等待着他的到来。月色依旧宁静,空气中掺杂一些新的气味,沙土一改往日的冷漠,棉质的触感隔着鞋从脚底向上攀延,朝鲁感觉自己身上的干皮正在被某种湿润磨平,像是母亲的手,舒缓,一下又一下,他的呼吸越来越费力,但身体感觉越来越轻。
“喂!喂——”朝鲁听到有人在喊叫,声音绕着他的耳郭走一圈就离开了。“喂!”朝鲁猛地一惊,这次是一群人的喊叫,等他反应过来,身体已经全部没进沙里,只剩下一颗脑袋留在沙外。
不是流沙,身子上都是浮沙,还没落严实,腿上施劲就从沙里爬了上来。朝鲁想起一种叫梦游的怪事,后悔这几天自己想钱想疯了,身体关不住魂。他回头看看刚刚人声传来的方向,看到一群人的影子。朝鲁的心跳还没有缓过来,不敢上前,只留在原地瞪大眼睛。
这时他好像看到一个父亲模样的影子,站在人群最前面。一股冷气从朝鲁背后升起,朝鲁用力把脚插进沙里,直挺挺地挺直腰板儿,尽力把气势鼓足。
起风了,人群开始消散,化作沙漠中的一部分,父亲的影子留下一句话也融进漫天的沙尘里:“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时候……”
金骆驼是存在的,它比那些羊毛换成的旱烟还要真实。雾气终会消散,而金骆驼却在一个又一个沙丘后等着航沙人的到来。
光凭人自己是无法直视金骆驼的,必须要有沙船的存在。沙帆被风晃动,能摇醒受蛊惑的人,沙船和地面的摩擦,能防止人陷进沙里。这是航沙人经过无数次血的教训得出来的祖训,但朝鲁祖父往上两代人没有一个见到过金骆驼,金骆驼的存在就成为传说,它的出现只存在于航沙人茶余饭后的闲聊和梦乡中。朝鲁祖父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朝鲁自然也就无从知晓。朝鲁用一只脚踏入沙渊的代价,再度让这个祖训显世,只不过,除了朝鲁,已经没有人再去在意。
朝鲁在和友人的一次酒会上谈起这事,他的话始终飘不进席中,轻飘飘地浮在屋子上空。“不就是梦游嘛,有啥稀奇?”“再不济就是让夜游神抓了单,现在人都往堆里扎,哪像他,荒地上守着个破房子等塌?”“噗……怪不得娶不到媳妇儿。”
沙尘在他的鼻腔里打转,朝鲁的呼吸沉重起来,脸憋得通红,他抬起拳头,朝着笑金骆驼最欢的那个人,一挥,不小心击中溜进屋里的一缕干风。
朝鲁没有勇气去向自己的友人挥动第二拳,刚刚的一切是他伸懒腰时攥住拳头的幻想,是对他们否定金骆驼的反击。他跌跌撞撞从屋里出来,又一步一趔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黄风依旧刮着,从远处带来各种各样的气味,可朝鲁闻不到身前哪怕一点的熟悉气味。
每当沙尘们以缓慢的姿势从天上划过时,朝鲁就架着沙船驶进落在地上的阴黄之中。抛下家里因饥饿声嘶力竭的群羊,转而朝着金骆驼所在的群黄漫行。金骆驼出现的时间没有定律,朝鲁只能把自己分成两个,一个顶着烈日,在微微发颤的空气尽头,寻找金骆驼的身影;一个身着星光在地上成片的黑鱼鳞中,想用脚印踏入另一个脚印。
朝鲁在寻证金骆驼的途中,自己又悟得关闭耳朵的技能。沙尘打在耳廓上,落地时发出酥麻的撞击声,他深知这个声音和那些航沙先辈们听到的一样。与此同时,耳朵的闭合隔绝的还有远处的喧闹人声。黄镇浓郁的烟火味飘到村里,村民们嗅到前所未闻的大片钢筋水泥味。他们以黄镇作为起点,向着南边的方向流淌。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起风时满村的叹息。
沙漠上的人,只要听不到声音,就绝不会动心。这是村里人历经十几代,摸索得出的应对海市蜃楼的方法。作为航沙人,这条规则更是深谙于心,朝鲁想不清为啥村子里的人,在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敢离开这里,去往南边一个所知甚少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连自己脚底下的地方都没弄清,金骆驼也没有找到,怎么就离开了?
沙漠的沙尘一寸一寸地向外迈着脚步,像一只瘫倒在地的野兽在渴望食物。朝鲁每天航沙的距离都会比前一天多平移一点,夜里梦中正甜的时候,朝鲁不断地被握成拳状的沙粒,击打窗户发出的动静所吵醒。每当这时,朝鲁也会伸出手,不停地向窗户摇晃的部分回拍过去,企图遮掩沙尘在告诉他是这片地方最后一个人的消息。
黑色的铁蛇在架子上不断蜿蜒,它们嗅不到人的气息,只能把头伸进这片阴黄的更深处。
朝鲁在铁蛇试探甩动的头中终日惶恐,担心这些东西的存在会惊扰于此活动的金骆驼。
铁蛇们盘踞在沙漠的一隅,蜷缩在一起,化成一个披着绿布的蛋。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施工的人,在他们蠕动的黢黑脸庞中,一个巨大的沙漠主题旅游区要在这里成形。朝鲁家的羊在陌生的声音和景象中絮叨不停,眼里露出的神色和看见沙漠里长出的一棵嫩草没什么两样。
一个阴黄欲坠的午后,几个穿着西装的人为了躲避呼啸的沙暴来到朝鲁的屋里,他们叩响房门,还没等朝鲁问清他们的来意,他们就进到屋里,自顾自地站在屋子的中心,像是自我介绍一般,说起项目的规划。
他们说的话很快就超过漏进屋里的沙粒。见朝鲁没有说话,那几个人就一边说着大叔应该没有见过高楼的样子,一边比画,想方设法向朝鲁表达清自己的意思:他们用胳膊在空中摆出房子的模样,用平移的手掌比作马路上的汽车,又不停地跺脚,说人多钱就多,生活就变好……
他们说话的时候,朝鲁一点也没有听进去。他低着头,在琢磨这些人的到来也许是件好事:不明白现状的金骆驼可能会在这里迷路,被那些不知名的建筑材料和电线绊住脚,这样自己遇到的概率多少就會大一些。想了一番,朝鲁意识到这是自己在为他们的到来向沙漠辩解。
听到这几个西装人说自己没有见过世面,朝鲁走进厨房,从扫帚上折下一根草回来,照着地上的一层薄沙画了几条线说:“这是你们住的地方吧。”西装人互相指指点点,对着朝鲁卧室的小电视机忙使眼色。朝鲁抹平地上的线条,用脚又摊过来一些沙子,画了几条线,又蹲在地上仔细地描描细节,其中一个西装人见状惊呼起来,说,这是他偶然翻阅的文献中提到的新一代房屋概念,在第四代住宅的基础上,融合完整的生产办公等特点,邻里之间的协作甚至可以达到相对成熟的生产线标准。但这些都是想法,相关草图设计都不完善。他不明白眼前的这个精瘦男人是怎么弄出来的?
朝鲁笑了,说这都是自己亲眼见过的,里面人干吗,自己都一清二楚,而且不止一次,就在前几天他又见到了。几句话下来,众人唏嘘,心照不宣地待在原地,看着窗外等沙尘暴的停止。朝鲁刚刚画的图让他们以为自己遇到隐世的高人,可细听其缘由,他们都认为朝鲁是在做梦瞎说,草图什么的都是凑巧。
朝鲁没有说谎,他是真的见过。所有的事物原本就有,人们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把他们的形状具象化出来。在朝鲁航沙寻找金骆驼的时候,海市蜃楼在沙漠与天空的尽头随光线不停隐现。沙粒的组合变化,空气中的湿气,月光洒射晶石的角度,海市蜃楼在日夜的流转中始终存在。在这片沙漠中孕育显现的景象,也无不展现着与外界千丝万缕的干系,而这一关联很多时候都超越了时间,让初见者对自己产生怀疑。有的是雕刻精美的亭台楼榭,有时候是板板正正的钢筋水泥,还有时候是不知名的材料融合成的巨状圆柱体,周围还有一些不明的飞行物体。
因为常见海市蜃楼的缘故,朝鲁对所谓的外界发展提不起来多大的兴趣。他的眼界在航沙中一次次被打开,比起村里那些不相信海市蜃楼、只相信自己双脚丈量出尺寸的人,朝鲁的幸运与不幸昭然若揭。在他看来,自己和看到的海市蜃楼没有区别,水汽做的梦淡出时间,才产生海市蜃楼。而他却依靠着对金骆驼的日思夜想,维持着和现实的最后一丝联系。
旅游区建设的声响压不住四处飞逸的沙尘,那些建筑材料在这些黄粒的起舞中坚挺不了几天,大大小小的虫洞就从内而外地把它们侵蚀干净。朝鲁的破败小屋屹立着。机器的轰鸣被裹挟着沙尘的大风吹散,同时迷路的还有到这里来的工人们的心智。
旅游工地的工人们被阴黄干扰得无法开工。在白天,他们在暴晒和沙粒的击打中耗尽体力,夜晚时分躺在床上,他们又被沙漠深处腾起的景象所吸引,在步履蹒跚中一步步走向沙渊,有人就此失踪。外来的车和人得不到沙漠的认可,他们只能从一个迷失走向另一个迷失。
外来人的双脚是找不到沙粒和沙粒之中的缝隙的,他们的身影在沙漠中立不安稳。明明开工之前就做过勘探,施了硬化,可盖起的建筑还是倾斜,彩钢房也被忽起的狂风卷上天两次。工人们的怨声和对失踪的恐惧不停传染,不到两个月,项目的工人们就走了一多半。项目负责人又想从本地人中招些工人前来帮忙,却发现这里除去朝鲁已经空无一人。一股沙漠吹出的微弱气息,就能把这片地区所有的屋子吹响个遍。
面对旅游项目负责人的上门招聘,朝鲁一开始就兴趣缺缺,他只管寻人和救人。比起那些实实在在到手的钱,朝鲁更向往着金骆驼的财宝。航沙人的世界里,钱和财宝不能画等号的,而领着所谓的工资去救人更是违背天道。航沙人得到的报酬从来都是随缘,不能强求。朝鲁计划着如果自己能把航沙传下去,就要在祖训里添一条不能领工资的规则,三代下来,肯定又能成为一条祖训,这是朝鲁第一次想到自己应该招个徒弟,往下传点东西。
沙漠在以另一种方式匍匐扩张着。朝鲁在寻找那些工人的过程中,途经的沙土被船底一遍又一遍压麻,舒缓几天,它们就又开始向外爬行。房子沾染上来自沙漠的气味,午夜时分躺在床上,朝鲁已经能感觉到沙漠那正在流淌的体温。朝鲁深知只凭自己一个人是无法阻止沙漠的侵蚀,航沙人的先辈们正是在日以继夜的航沙中,用船底的摩擦和摆弄的风帆来驯服沙漠,但现在人手根本不够,也不知去何处寻找帮手。眼下,朝鲁只能坐等将来某一天沙漠向外的爆发。
如果招几个徒弟,是不是好一些呢?朝鲁躺在床上,脑袋里惦记着停在外面的沙船,为它的去处产生前所未有的担心。无关金骆驼,也无关驯服沙漠,只和航沙人这一名头有关。
工地的施工声稀疏不少,一些没有活干的工人晃荡着手里的安全帽,坐在地上冲着沙漠发呆,朝鲁有意无意地在他们面前驾驶沙船,但他们的目光总能跳过朝鲁,向着更远的方向迷茫。几次下来,朝鲁已然死心,先不说这些人能不能学会航沙,让这些人拖家带口来到这不毛之地,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航沙人的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的。至于金骆驼,在这些人眼里,也许就是一阵风里吹来的笑话。
黄风围绕工地晃荡不到五天,里面的建筑材料就化作齑粉,与此消散的还有曾经满满当当的人声和味道。沙漠里除沙漠之外,只留下死寂。朝鲁在见到他们第一眼时,心里就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临,只是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快。朝鲁感觉一切发生好似沙崩,他只能坐在门槛上回想之前发生的事,思考将来到沙漠挑战的人的下场。
太阳光嗡嗡作响,沙子在地上窸窸窣窣挪动着身体。不知是不是眼皮沾上沙子,朝鲁在思考记忆和将来的过程中,眼皮越来越重。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听闻到金骆驼的消息,施工队的离去也许是件好事。
朝鲁的鼾声响到第五下时,被突然出现的年轻小伙儿脚步打断。朝鲁眯一下眼,认出眼前没有一点沙粒的高档运动鞋。
“他们都走完了,你在这里做甚?”
年轻人笑了,说父亲因为亏损,着急开发新的项目顾不上管他,他想着正好趁学校放假这段时间,留在这里学航沙。朝鲁忍不住咧开嘴,那些沙漠里的狂风罕见地把原本不属于沙漠的人吹来了。朝鲁摆摆手说,一会儿要去邻居家喝酒,还说这里根本不是他能待住的地方。
朝鲁撑起沙帆,乘着风离开。第二天回来时,他看到那个年轻人学着他昨天的样子,坐在门槛上睡着觉。听到来人的动静,年轻人睁开眼,对着朝鲁的两个被酒精泡大的眼睛说:“师傅回来了?”
这声师傅听得朝鲁心里发颤,他取下沙帆,收好沙船,揉掉脸上的沙粒,对着年轻人说道:“沙船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能弄得了的,后生你行吗?”
年轻人没有说话,走到墙根,将沙船放到地上,把旁边没有收好的沙帆抖开,学着朝鲁的样子,爬上杆,挂好帆,用麻绳在沙船的两头绑好位置。一切完备后,年轻人带着期待看着朝鲁。
“不行,还不够,再用点劲儿,风沙大,别关键时候给吹开了。”见年轻人眼里的光还是闪动着,朝鲁本想问问他知不知道金骆驼的事,想来想去开不了口,他已经记不清上次对人说起金骆驼是什么时候的事。朝鲁还是先让他试试驾船。
年轻人没有相信自己的耳朵,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朝鲁。朝鲁挥挥手, 让他赶快上船。年轻人急急忙忙跑上船,撑起风,正好乘上路过的一阵黄风。朝鲁眯着眼,看见年轻人强扭着身体,颤颤巍巍地在沙上行驶好一会儿,一个转弯没有刹住,才从船上甩下来。
朝鲁感叹着他是个好苗子,加以培养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航沙人。朝魯回忆起自己的祖父在航沙上已是天赋异禀,而父亲更是百年难遇的航沙天才,而自己更是没有在通过航沙人三道考验的情况下,安安稳稳航沙几十年。所有航沙人都做得越来越好,可航沙这行却越来越衰败,现在更是只剩下自己一人。
朝鲁没敢细想下去,年轻人的呼喊声刚好帮助他转移了思绪。显然,他也是对自己行驶的距离感到吃惊。
“师傅!您看看我行不行?”
“这哪行呢,我第一次开的时候,直接在沙上溜了半天。”朝鲁说这话时,脸上有些发烫,可想到脸上晒出的青石色时,腰板儿不由得又硬气几分。
“你这样我教不了啊,还不如现在早点回你家大房子里歇息着。”
年轻人眼里的惊恐流在地上,弄滑了他的脚,一个趔趄摔在朝鲁脚前,这次摔得比航沙那时还要惨,年轻人捂着膝盖,很是疑惑地看着他。
“教不了,教不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弄点其他的。”说着,朝鲁进了屋,关上门。靠着门,朝鲁点着根烟。屋外的脚步踱响几下,就没有了声音,朝鲁拉开门缝,往外看,看见沙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远处的沙丘上,隐约看到一个金色的身影。
这个后生姓张还是姓李?朝鲁琢磨半天,又记得听施工队的人说他爸姓王。这后生好像年轻时候的自己,一脸精干相,只不过比自己那会儿白净多了。算了,算了,图啥。沙漠的呼吸吹来一代代的年轻人,又用风沙在他们脸上雕刻出年轮,究竟谁是谁,什么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朝鲁抬起头,翕动几下眼皮。刚刚往外看时,眼睛不小心落进沙漠的灰。墙的另一边响起羊群的饥饿叫声,他瘫靠在门上,用手遮住了一只眼睛。
作者简介

苏热,蒙古族,现居呼和浩特。文艺学硕士在读,有小说、评论见于各刊。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