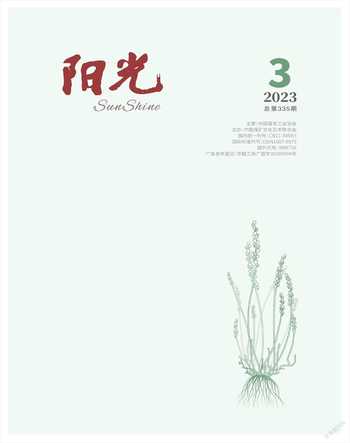藏在窑顶的柿子
2023-03-13雷红玺
雷红玺
傍晚,我偶然经过一家水果超市,居然看到只有在金秋时节才有的灯笼柿子。看着这小小的、红红的柿子,我的思绪不由自主被带到了三十多年前……
那是我刚去徐州,离家求学的第一学期。日思夜念的寒假终于来临,我带着对羊肉泡馍、对家人迫不及待的思念,背上行囊,马不停蹄地挤过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一进院门,就被眼尖的小侄儿阳阳发现了,随之闻声而出的是母亲。母亲似乎老了,又似乎更憔悴了。看到我,母亲的眼圈立马红了,泪水怎么也掩饰不住她急切的眼神,那目光,仿佛要一下子掘出我半年来所有的委屈。趁着姐妹们围着我问长问短的工夫,母亲端上早已备好的饭菜,就在我狼吞虎咽的同时,妹妹不知从哪儿端来了一盆灯笼柿子,金黄的、橘红的、松松软软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我心想:大冬天的,哪来这么新鲜的柿子?看我纳闷的样子,调皮的妹妹问:“你猜,这些柿子在哪儿给你留着的?”我本能地说出了多年不用的红薯窖。谁知妹妹却说:“哪儿呀,刚放了两天就坏了几个,可把咱妈心疼坏了,又放到草厦房梁吊起来,白天怕阳阳发现,晚上怕老鼠,你猜,最后放哪儿了?”“粮瓮里?不可能,柿子怕捂。水缸漂著?更不可能。用水多不方便。咱家没冰箱没冰柜,除了红薯窖,还能有哪儿?”我实在猜不出来,眼睛瞥着灰蒙蒙的窗外,顺口说了一句:“放哪儿也不可能放窑顶上?”没想到妹妹立马高兴地说:“你还真猜对了!”
我一时愕然。
窑顶?不可能!那可是我心中的高危地带。村里的窑洞左邻右舍一排一排连起来,高不可攀。连梯子也买不起的年代,谁没事会上那里?早些年除了雨季担心窑顶渗水,父母会上去看看,我们都没有上去过。只要他们上去,我们就好奇地也想去窑顶看看,但总是被母亲毫无商量余地拒绝,“好好念书,将来到了城里住楼房,比窑顶看得还高还远,就像你爸和你大姐,天天住高楼,咱这窑顶除了杂草,跟前不是村子就是沟,有啥看的?看不远也看不见个啥,可不敢上来,又没有梯子,万一摔了……”
初中我就去了城里上学,再也没见过父母上窑顶。窑顶,在我的心目中,无疑是个禁区。父母不让去,自己不敢去,也没法去。何况每次看见他们在土墙的罅隙中,小心翼翼地寻找坚实的地方爬上爬下,心里不无担忧。人到中年的父母,动作不利索,父亲本是一介书生,从城里回来不太懂农活,母亲体弱,屋里屋外都要操心张罗,我们几个孩子都还没长大,家里干活实在没有一个好劳力,上窑顶无异于主动冒险。
随着考试考学,家里的事渐渐无暇顾及。那年代,为人父母有一地鸡毛的窘迫,身为儿女有焦头烂额的狼狈,为了生存,或者说为了明天和今天不一样,大人孩子,在各自的道路上不辞劳苦地较劲、努力。
还好,我考上了大学,成了家里又一个走出远门的读书人。
眼前听说五十多岁的母亲上窑顶,我怎么都觉得不可思议!
妹妹说:为了保存那些柿子,母亲没少想办法,放室内、放户外、放低处放半空,放来放去,最后试着放到了窑顶上,用干草盖住。还好,没坏。隔三差五就上去看看,摸摸,五十多岁的人了,爬上爬下的不说,还一直念叨家里人都吃过了,就是在外上学的女子没吃上,后悔留的太少、损失的太多。
我的眼泪忽然涌上来……
泪眼蒙眬中,窗外的窑顶似乎有人影晃动。
整整一个寒假,父亲为我,增加了年货的品种和数量;母亲为我搜肠刮肚地变换着饭菜的花样。然而,满满一个春节,无论我吃了怎样的香餐美味,无论我受到了乡邻多真心的款待……三十余年后,我依然清晰记得那年寒假母亲为我存留的那盆柿子。
小小的院落、小小的屋子,或许,它曾被端着柿子的母亲无数次地逡巡;甚至家里的某件家什,也曾被母亲试图用来存放柿子,最终,却被天和地所代替。是的,拳拳爱女之心,上可以昭天,下可以示地。被岁月滤去的,是儿女成长的生涩;被日月见证的,是亘古不变的母爱。回首以往的岁月,我不正恰似母亲手中的一盘柿子,被她如获至宝,被她用心呵护,直到现在,仍然被她高举在天吗?
藏在窑顶的柿子,存在母亲怀里的宠爱,它激励着我固守本色,永不言败——无论身处何境、无论历经风霜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