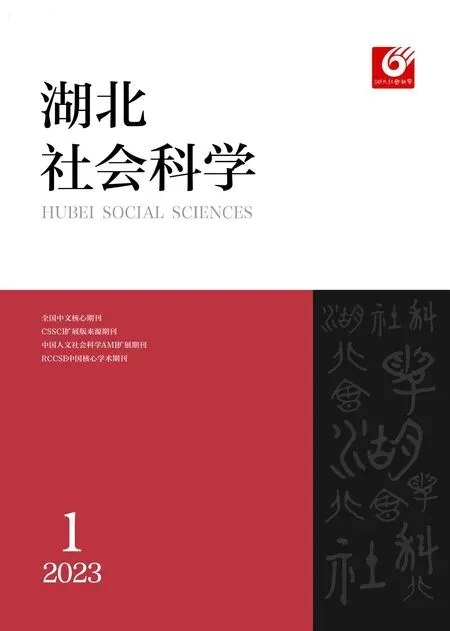布林克长篇小说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建构
2023-03-12蔡圣勤
张 甜,蔡圣勤
“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于1516年发表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一书中,该词词根源于希腊文“没有”和“地方”,意为“乌有之乡”,指代人们在未来世界希望看到而又还未到来的理想社会愿景。这种理想是对现存世界社会秩序的批判和强烈超越。20 世纪2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派独特的思潮出现在西方理论界,对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恩斯特·布洛赫、达科·苏恩文、拉塞尔·雅各比等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对乌托邦进行了新诠释,认为乌托邦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永恒动力,是促成一种希望的行动力。布洛赫认为,乌托邦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希望,乌托邦是一种创化,他的“希望原理”就是要人们不放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1](p143)雅各比在其著作《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中指出,莫尔在其书中设想了一个平等美好的国度,但在现实生活中,莫尔本人却对宗教异端施行了残酷镇压。这样看来,莫尔既是一个乌托邦的缔造者,也是反乌托邦的实施者,可以说,乌托邦文本从其诞生时就包括了它的对立面。[2](p13)“反乌托邦和乌托邦可以说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反乌托邦表现的是黑暗的一面,而乌托邦则更多地表现光明的一面。乌托邦描写的是一个相对于今天的社会更美好的理想国度,反乌托邦描写的则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的国度。如果说乌托邦展示的是天堂,那么反乌托邦展示的就是地狱。”[3](p163)所以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都探讨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可能性:乌托邦是希望的理想社会;反乌托邦则是比现实世界更糟糕的存在,它的作用是警醒现实。两者实际上都寄托了人们的乌托邦精神和对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愿景的追求。
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1935—2015)是南非著名小说家、文学理论家,为南非的阿非利卡文学和世界英语文学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众多国际荣誉:两次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三次荣获南非中央新闻社最高文学奖,此外他还曾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和“法国荣誉骑士军团勋章”。[4](前言p1)
在布林克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写作几经转型。1959 年之前他的创作是传统的阿非利卡民族风格,对周围黑人的生活状况熟视无睹。直到1959 年留学法国,他才第一次以不同视角看待自己的国家。在1993 年的采访中,布林克谈道:“在南非,我接触到的黑人不是劳工就是家里的佣人,……在巴黎,我周围突然有了一批黑人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所掌握的文学知识甚至比我过去七年学到的还要多!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文化上的冲击,而且是一次十分愉快的冲击,它开启了我对崭新领域的探索之旅。”[5]此外,布林克还深受法国哲学家、文学家阿尔贝·加缪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我的作品产生深远持久影响的正是阿尔贝·加缪。”[6](p91)加缪曾加入共产党,其后虽退党,但一直为共产党的“文化之家”工作和演出,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加缪为导师的布林克自然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1968年,巴黎发生了“红色五月风暴”,这场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践行的起始和它全部理论逻辑终结的发端”[7](p903)的红色抗议不仅使布林克进一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成为他写作上的分水岭。“我认识到身为作家我不能孤身一人自怨自艾,更要融入社会中。因而我回到南非,尽管困难重重,我也要挖掘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真正发生的一切。”[8](p50-51)于是他开始思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以及“在一个封闭社会中,作家所要扮演的具体社会和道德角色”,最终决定“去进行更有责任的创作,去探索南非的政治境况和自己对种族隔离的深恶痛绝”,①参见:http://www.encyclopedia.com/topic/André_Brink.aspx。用有力的笔触书写南非受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迫害人们的自我解救,赋予作品乌托邦愿景,表达他对平等、自由、友爱的南非社会的呼唤。
国外的布林克研究具有起步早、关注持续、角度多元化等特点,涵盖南非特定语境下的布林克研究、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叙事研究等内容。国内的布林克研究始于1999年,[9](p43-48)但到目前为止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文学书写研究也仍处于早期,但已有多篇论文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写作,呈现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南非作家试图用笔唤醒人们内心乌托邦理想的图景。②参见:蔡圣勤、吕曰文:《论库切“耶稣系列”小说中乌托邦社会的建构》,载《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 期,第138—150 页;胡忠青、蔡圣勤:《伦理困境:〈耶稣的童年〉中乌托邦社会的表征》,载《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9期,第133—136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达科·苏恩文表示:“乌托邦致力于阐明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人与他们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它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为一个构想的乌托邦寓言式的新型人类关系而呈现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称为‘陌生化’文学类型。”[10](p59)《风中一瞬》《菲莉达》和《魔鬼山谷》是布林克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作品。《风中一瞬》(An Instant in the Wind,1975)以逃亡黑奴与贵族白人女性逃往南非荒野,而后回归开普敦这一过程为主线,揭露了在种族主义与性别政治压迫下,男女主人公对无压迫、无歧视的乌托邦的向往与追求。《菲莉达》(Philida,2012)则以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南非废除奴隶制前后的开普敦为背景,书写了黑人女奴菲莉达面对百般折磨所进行的艰苦抗争,最终到达了理想自由的乌托邦——盖瑞普。简言之,《风中一瞬》和《菲莉达》书写了主人公对乌托邦的向往与探索。而《魔鬼山谷》(Devil’s Valley,1998)则记述了一个从“大迁徙”(1836 年开始的,因英布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布尔人大迁徙)中分裂出来的阿非利卡社区在偏僻的山谷定居,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故事。山谷中道德沦丧,生者与死者共存,半人半兽随处可见,一片颓败,满目疮痍,这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乌托邦社会。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批评理论视角出发,对上述三部作品进行文本分析,探析作品中乌托邦建构的意愿、动机、困境等问题,进而探讨布林克的乌托邦政治理想。
一、布林克建构乌托邦的意愿和动机
布林克是一位坚持“在现场写作”的作家,而南非曾经是武装暴力和意识暴力相交织的国度,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阴云密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异化。在此阴霾笼罩下,受害者难以喘息,他们需要逃离公共领域,解放压抑的生理以及心理需求。哈贝马斯曾界定了公共领域的概念:“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11](p125)可见,公共领域应当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和批判性。但是,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的笼罩下,南非的公共领域话语成为维护白人利益和男权利益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开放性、民主性和批判性。
(一)公共领域的种族迫害
1652 年,荷兰人首次在开普敦建立殖民地,自此荷兰殖民者就逼迫南非土著的科伊桑人和布须曼人成为奴隶,并极力宣扬“白人至上”观念。白人殖民者甚至从《圣经》中寻章摘句,否认黑人的平等权利,宣称“不论是在教会里,还是在国家里,黑人和白人之间决没有平等可言”。[12](p34)白人男性可随意侵犯黑人女性,而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之间的爱情却被严格禁止。在《菲莉达》中,黑人女奴菲莉达因与白人奴隶主之子弗朗斯扭曲的婚恋而备受折磨。作为女奴的菲莉达不能拒绝奴隶主提出的任何要求,除了平日异常辛苦的劳作,还有来自弗朗斯的性要求。正如菲莉达所言:“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会照做,因为你是我的主人。”[13](p10)小说中还有黑人奴隶与白人女性发生关系后被绑在木架上活活暴晒而死的情节。《风中一瞬》也有一处写到,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好友生了黑奴的孩子,被迫嫁人,黑奴也被判处终身监禁,关进罗宾岛;而小说中男主人公亚当所心仪的女孩被随意卖给别人。[14](p106)在充满种族压迫的社会中,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爱情无疑会以悲剧告终。
在《风中一瞬》中,亚当的母亲是科伊桑人(南非土著居民),幼年时曾和族人一起自由生活在广袤的南非内陆,直到白人殖民者逼迫他们成为奴隶,而亚当的祖父Afrika因参加过暴动和谋杀雇主,被残忍处决。也许从一开始,亚当血液里就奔腾着对自由的向往和不屈不挠的韧劲。那么,亚当因何反叛主人并逃离开普敦?据他所言:“我对主人还手是因为一个人迟早会被逼到不得不说‘不’的时候。”[14](p94)主人强迫亚当惩罚自己的族人,后来甚至逼迫其鞭打自己母亲,原因是母亲没听从命令在地里干活,而是偷偷跑去埋葬亚当被冻死的祖母。祖母去世,也是因为主人不允许亚当给她送柴火。他难以抑制悲恸,内心的狂暴如火山赤焰般喷涌而出,他将主人打倒在地,而后接受了“公平”的审判,被判处鞭刑和烙刑,放逐罗宾岛,随后乘机逃往荒野,藏匿于原始森林。但从亚当与伊丽莎白的对话中可以发现他的逃离并非出自本意。“我并非出于自愿,而逃到这片荒野,我只是不得不这样做。在这里,我像动物般求生,但我不是动物,我是人。”[14](p95)亚当被迫离开人类社会以躲避种族压迫和杀身之祸。
在《魔鬼山谷》中,布林克揭露了反乌托邦语境下的残忍种族迫害。记者弗利普·洛克纳来到魔谷,发现此处与外界最明显的不同是没有黑人,后来获悉黑人是不允许进入魔谷的,因为魔谷统治者们担心黑人会“污染”白人血统。这一描述让人联想起1948年当选南非总统的马兰所宣扬的“黑色危险”,他推行彻底的种族隔离政策,“维护白人至高无上的权威,……宣扬若不实行种族隔离,白人种族的高贵血统就会被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污染而引起‘种族退化’;如果允许黑人有平等权利,白人就会被黑色海洋吞噬而陷于万劫不复之境”。[15](p96)他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来维护白人血统,包括禁止不同种族之间通婚的《禁止通婚法》(1949 年)和严禁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性关系的《不道德法》(1950年)。[16](p116)回到《魔鬼山谷》中,小卢卡斯的母亲因儿子的死亡而哭诉:“他做错什么事情了吗?我说的是,他又不是黑人或什么的。”[17](p229)言下之意,黑人就是个错误,是“生而有罪”的。更耸人听闻的是,不幸在魔谷出生的黑人婴孩会被处以石刑,这些孩子被称为“返祖”(throwbacks)。惨绝人寰的反乌托邦描写映射了南非社会的种种罪恶,表达了布林克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强烈谴责,他深信:“种族隔离制度使阿非利卡人缺失人性,这种制度也是几个世纪以来阿非利卡历史上最不合逻辑的。”[18](p92)
(二)公共领域的人性异化和性别政治
雅各比说:“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旅行中没有指南针。”[19](p234)在南非种族隔离和性别政治的阴影下,传统伦理道德均已覆灭,社会制度扭曲不堪,人性畸形丑陋。无论是生的渴望,还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沦为牺牲品。《风中一瞬》中,伊丽莎白逃离开普敦,选择将自己的生存空间由开普敦转移至荒野,等于也逃离开普敦女性受限的生活和地位。这种空间的转移是社会意识、精神秩序和理想诉求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伊丽莎白的丈夫拉尔森赞美她的钢琴天赋,她却不以为然,“开普敦所有的女孩都很会弹钢琴,她们还会唱歌跳舞,要不然用什么来打发时间呢?”[14](p32)开普敦众多贵族女孩多才多艺,并非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只是因为她们生活范围极其受限,实在无事可做,只好学些才艺打发时间。她们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体制下被限制、被物化、被异化,伊丽莎白视其为令人窒息的牢笼生活。再看伊丽莎白的家庭,父亲是贵族官员,生活极其奢靡,将家中黑人女奴当作发泄对象,对此伊丽莎白愤怒不已。她难忍社会和家庭的双重重压,于是嫁给探险家拉尔森,想与他一同前往南非内陆,逃离开普敦。“待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选择,你要么死,要么发疯,就这样,而这两项我都不感兴趣。”[14](p38)母亲对伊丽莎白的决定大为震惊:“一个男人要去探险无可厚非,……但是你,伊丽莎白,你习惯了得体的生活,你是有教养的,你是别人的榜样。”[14](p38)在母亲眼里,去内陆冒险对女性来说是一件很有失身份、很不得体的事情,完全越出了当时女性的生活范围。可见,开普敦是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文明”社会,女性,哪怕是贵族女性,生活空间极度狭窄,在社会和家庭中均被异化、物化、边缘化。
同样,布林克也着墨于黑人女性的苦难,因为她们遭受着来自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的双重压迫,是备受折磨的典型代表。在《菲莉达》中,白人奴隶主声称“奴隶连狗都不如”,[13](p128)菲莉达在白人奴隶主的鞭笞下日夜劳作,还被迫满足主人的性要求,甚至怀孕期间还遭到强暴。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的双重桎梏下,黑人女性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非人辛苦劳作,还要遭受更为残忍的心灵折磨,菲莉达的不幸遭遇是当时南非所有黑人女性生活的缩影。
在《魔鬼山谷》中,布林克用反乌托邦的叙事描述了集权造成的人性异化和女性的坎坷遭遇,将现实中的罪恶推向极致。魔谷里活人与死人生活在一起,这也印证了魔谷社会的非正常化和人性异化,而这种非正常化和异化是魔谷内部集权统治的结果。作为第一代进入魔谷的人,卢卡斯·先知者(Lukas Seer)建立了基于基督教的各种严苛而荒谬的制度,通过每周三“神圣兄弟”举行所谓的“《圣经》学习课程”,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并将女性置于被支配地位,导致谷里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冷漠乃至暴力。魔谷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扭曲人际观念和家庭观念:一个为怀孕妻子偷水的男人会在众目之下被鞭打致死,而杀死儿子的父亲却可以逍遥法外,而他还是一个将魔爪伸向女儿的兽父。魔谷居民对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反应却是:“发生在别人家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事情当然跟外人没有关系。”[17](p354-355)人际关系的冷漠和人心的麻木令人魂惊魄惕。另外,魔谷里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对外来者极其排斥,也不允许居民将魔谷历史向外人言说。利斯贝特·普鲁内祖母正因向记者吐露魔谷历史而被无情杀害,其他人只得三缄其口。
布林克小说中的人性异化不仅表现在高度集权、法律荒谬和人际关系冷漠上,也体现在对女性的压迫上。魔谷里,女性没有任何社会地位,随时可能遭受权势之徒的践踏。而如果她们怀上外界人的孩子,则会被处以残忍的石刑。在受教育方面,她们同样备受压迫,才华无从施展,因为“如果一个女人不知道如何给她的丈夫做一块面包,受教育又有什么用呢?”[17](p125)女性的家庭地位也极低,她们结婚时,丈夫会送她们一口棺木当结婚礼物,仿佛已经明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不幸结局。有一些试图逃到外界接受教育的女性最终都被抓回来,然后被逼疯。记者再也无法忍受魔谷的恶行,借教堂聚会之机向女性发声:“难道就没有一个女性对谷里发生的事情感到不满吗?你们难道也同意这种做法吗?”[17](p356)但却没有一个女性回应,原来在教堂集会里,女性是没有发言权,这意味着女性被剥夺了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机会。集权者通过动用各种暴力手段维护其统治,对异己思想进行残酷镇压,对未觉醒的群众则扼杀其思考能力,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意外”。
布林克在小说中描写了人们对标志着种族歧视、阶级压迫、性别政治的所谓“文明社会”的逃离,以抨击南非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追求自由平等人们的唯一出路就是逃离这一公共领域。所以,亚当与伊丽莎白逃往荒野,憧憬着无压迫无歧视的理想生活,追逐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空间。在与世隔绝的荒野,两人远离开普敦的喧嚣,摆脱了种族压迫,以自由的身份相结合,仿若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力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分裂现实缝合。[20]现实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使他们难以喘息,他们遂逃往荒无人烟的荒野,试图解放自己被压抑的生理及心理需求。《菲莉达》中,女主人公在奴隶制废除后,选择逃离白人控制的公共领域,寻找自由的乌托邦——盖瑞普。由此可见,布林克笔下的乌托邦冲动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与超越,小说中的主人公只有逃离公共领域,才能摆脱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导致的人性异化和物化,实现乌托邦理想。
二、布林克的乌托邦建构困境
(一)自我认知困境
乌托邦本质上是对人类和谐幸福生活的展望和对未来的思考,而要开展这种展望和思考,人类首先要完成自我建构。在布林克小说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何方去等自我认知难题横亘在主人公面前,只有解答了这些问题,他们才有可能完成乌托邦空间的构建。
《风中一瞬》中,亚当与伊丽莎白对自我身份的思考、探索与建构,透视出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下人们的自我认知困境。人与人之间由于肤色与阶级的差异,被分为三六九等。但在“非文明”的荒野,一切压迫与阶级消失了,一切都还原到了最原始的状态,伊丽莎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女性,亚当也不再是身份低微的黑人奴隶。此时,两人是否能够拨开云雾,走出困境,明确自己和对方的身份呢?
进入荒野第三天,伊丽莎白发觉镜子里的自己变得陌生,因为周围环境彻底变了,不再是熙熙攘攘的开普敦,不再是每日各种酒会派对,而是荒野,无穷无尽的荒野。“人有没有可能这么快就对自己如此陌生呢?”[14](p45)她已经开始了在荒野中的自我探索之路。伊丽莎白和亚当相识之初,仍深受种族主义影响,认为黑人必然是奴隶,自己作为白人女性,身份地位自然与黑人不同。但在荒无人烟的野外,伊丽莎白身边有且只有一个黑人的时候,她担心遭到黑奴的报复:“我知道你在等待机会,但我警告你,我会盯着你的。如果你胆敢……我甚至会以死抵抗。你听懂了吗?你没有权力,我怀孕了,而你只是个奴隶。”[14](p21)亚当正是为逃离种族压迫而来到荒野的,没想到在此时再次陷入身份困境,再次变成开普敦的奴隶。“奴隶”二字深深刺痛了亚当,“奴隶,奴隶,你只会这样说。我已经受够了,你听到了吗?你没有权力这样使唤我。”[14](p21)“我是被当作奴隶,并不是一出生就是奴隶。”[14](p53)他从骨子里拒绝这个身份。伊丽莎白和亚当分别以开普敦式的“文明”观念理解对方,彼时两人均陷于自我身份的困境中。伊丽莎白需要用白人高贵的身份保护自己,她对亚当既鄙视又恐惧。亚当对伊丽莎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伊丽莎白的傲慢态度让他厌恶,基于善良的本性他虽然不会伤害伊丽莎白,但内心仍然鄙视毫无荒野求生能力的她;另一方面,因为离开人类社会太久,他想从伊丽莎白口中知晓开普敦的生活,所以她也是荒野里文明社会的窗口。
作为白人女性,伊丽莎白对黑奴的痛苦所知甚少。在开普敦,她甚至对他们熟视无睹。刚到荒野时,伊丽莎白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还是高贵的白人,与亚当相处过程中总是不禁表现出优越感。而后在漫长的探险路上,她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与照顾她的亚当朝夕相处,尤其在流产期间,在亚当无微不至的照料下,伊丽莎白慢慢被亚当的真诚与勇敢打动。他们暂居荒野小屋时,有次亚当外出打猎整日未归,伊丽莎白开始惶恐不安。而当看到亚当在暮色中归来,伊丽莎白便按捺不住内心兴奋:“我替你担心,怕出什么意外,怕你会受伤。”[14](p113)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亚当的关心,经历一路坎坷,伊丽莎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白人女性,她已从代表“文明”的白人变成一个有血有肉、与自然为伍的自然女性。在亚当眼里,伊丽莎白也变成了平等的伴侣。两人后来的结合也说明他们摆脱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
在《菲莉达》中,菲莉达也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织就的大网中迷失了自己,陷入自我认知困境。现实生活中,她是赞第府列特庄园的黑奴,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在少主人弗朗斯的引诱逼迫下与其保持亲密关系,并为他生下孩子。她沉浸在弗朗斯编造的虚伪泡沫中,幻想着自己可以摆脱奴隶身份,成为弗朗斯的妻子,成为自由人。当菲莉达看到弗朗斯的家谱时,执意要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去,“这本书只是一堆名字,弗朗斯,没有说什么白人和奴隶”。[13](p37)菲莉达在与弗朗斯的关系中产生了超越现实的幻想,认为自己可以逃脱黑奴的命运。但生活很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菲莉达以痛击。弗朗斯被父母安排迎娶一位对家族发展有益的千金,而菲莉达则被当作累赘,主人污称其孩子并非弗朗斯的,她甚至遭到其他奴隶的侮辱。菲莉达终于在痛苦中幡然醒悟:“我从来不是能决定去哪里,什么时候去的那个人,这总是取决于他们,总是取决于别人,而永远不是我。”[13](p62)她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就是按照主人意愿去干活,遭受主人对她做出的一切行为。“我是一块编织物,由别人编制摆布着。”[13](p65)分裂的幻想和扭曲的现实,加重了她的身份焦虑,让她陷入了自我认知的困境中。
亚当、伊丽莎白与菲莉达都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的双重压迫下,陷入了迷雾般的自我认知困境。幸运的是,他们摆脱种族主义、性别政治和追求自由平等的强烈渴望,渐渐充实了自我认知,使他们完成了新的自我身份建构。但是,在《魔鬼山谷》的反乌托邦语境中,山谷居民的乌托邦梦想就显得十分苍白,因为反乌托邦集中了现实世界的所有罪恶,集权者抹杀了人们寻求自我认知的可能,让人们在模糊的历史中陷入乌托邦建构的困境。
(二)政治文化困境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南非社会的宗教信仰也沦为维护种族主义的工具,白人奴隶主宣扬南非黑人是受上帝诅咒的“天生劣等”,只能成为白人奴仆。《菲莉达》中,《圣经》成为白人压迫黑人的神学依据,白人是上帝指认的统治者,而南非的黑人被描述为“生而有罪”的人,他们要服侍奴隶主,等待最终的审判日,陷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中。小说中,奴隶主康纳里斯频繁向奴隶们诵读《圣经》,鼓吹白人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其目的是为了驯化黑人,使其顺从主人的意志,没有反抗之心。
在弗朗斯为菲莉达编织的美好泡沫里,菲莉达会成为他的妻子,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宗教背景下,他们的结合完全有违宗教伦理、有违法律,是被绝对禁止的。终于,现实刺破了泡沫,菲莉达被迫杀子,被当众侮辱并被转卖到南非内陆。在遭受白人迫害的过程中,菲莉达渐渐意识到,基督教的捆绑让她——一个黑人奴隶——根本无法触碰平等和自由的生活。
被转卖到南非内陆后,菲莉达结识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拉本,拉本认为,当穆罕默德与“他的子民对话时,他与穷人对话,与奴隶对话,与老人对话,与疾病缠身的穷苦人对话,与遭受苦难需要帮助的人对话”。而白人奴隶主“总是对我们说上帝会照看我们,但事实并非如此。上帝照看的是白人,不是我们”。[13](p186)他表示“我们在一起,没有主人或者奴隶,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人”。[13](p184)这种人人平等与博爱的思想在菲莉达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于是她摒弃了基督教。
“反乌托邦小说在本质上是作家对人类理想社会构建与当代社会中集权主义统治和科技发展导致人的道德沦丧以及幸福及自由受到重创所形成的新的矛盾的文学反思。”[21](p90)在《魔鬼山谷》中,寻求乌托邦理想无异于天方夜谭。布林克描述的魔谷是黑暗的反乌托邦世界,它是一个比南非现实更糟糕的所在,集现实社会的罪恶于一地,并且将这种罪恶推向了极端。魔谷不仅是黑人的禁区,也是白人尤其是女性的地狱,集权者用宗教枷锁,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让乌托邦理想更加遥不可及的还有集权者对魔鬼山谷记忆的抹杀。“他们拿走了一切,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历史。”[17](p232)由于无法溯源历史,山谷居民陷入了自我认知的困境。这种困境也是作者对现实的真实写照:有色人种渴望的自由美好生活成为空谈,在种族主义的炙烤中陷入困境。甚至南非白人亦是如此,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他们面临着空前的身份危机:生活在南非,却不是南非土著人,而是殖民者后代,成为南非有色人种仇视的对象;逃往西方白人世界,也被当作外来者。他们进退两难,成为“夹缝人”。布林克的描述,实际上表达了对南非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共同深切关怀。
三、布林克的乌托邦空间建构
卡尔·曼海姆在其著作中提出:“如果把‘乌托邦’这个术语的含义限定为超越现实、又打破现行秩序束缚的取向,乌托邦式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思想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一个人可以把脱离现实或超越现实存在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取向——而且仍然有效地实现并维持现行事物的秩序。……只有在它试图打破现行秩序的束缚时,这种不协调的取向才成为乌托邦式的。”[22](p234-235)南非社会曾经是一张武装暴力和意识暴力相交织的网,长期以来遭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后种族隔离时代各种不安因素的影响。作为一位对南非社会有着深切关怀和历史责任感的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布林克在小说和社会活动中均表现出对南非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乌托邦理想国度的憧憬与追求。在布林克笔下,主人公逃离公共领域,即为打破现行秩序,这是实践乌托邦的必经之路。人的天性决定人是需要乌托邦想象的,相信乌托邦是比现实更为“真实”的理想社会,这种“真实”不是人的感官所能够感知到的客观存在,而是犹如地平线般不断向远方伸展,给人以无限希望和憧憬。布林克深刻挖掘着埋在南非残酷现实里的乌托邦希冀,并将其转化为作品中主人公对乌托邦空间的建构;同时在反乌托邦语境下,布林克采用逆向思维,曲折表达了其对南非社会美好愿景的期待。
(一)海边的伊甸园:亚当与“夏娃”的乌托邦空间
人类活在二元世界中,既作为自然人身处自然的世界中,又作为社会人生活在历史的世界中。在殖民主义时代的南非,这种健全与快乐,这种作为人的完整性只能在逃离公共领域之后在与世隔绝的荒野乌托邦里才能实现,这多少与库切笔下的《内陆深处》及“卡鲁农场”、施赖纳的“农场小说”、戈迪默的“七尺乡土”有异曲同工之妙。《风中一瞬》中,亚当和伊丽莎白逃离公共领域,来到荒无人烟的海边,甚至可以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般毫无拘束,白日在海里游泳捕鱼,夜晚窝在洞穴里生火做饭,相互取暖。他们在此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乌托邦空间。这也体现了布林克对摆脱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政治束缚的理想乌托邦的向往。
在荒野生活中,伊丽莎白逐渐被亚当强大的野外生存能力所折服:他懂得如何追踪猎物,如何挖洞取火,如何用动物毛皮做蓄水袋,知道哪些果子能吃哪些则不能,渴的时候用什么根茎解渴……“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教会给我”,[14](p125)伊丽莎白也希望成为一个能在野外生存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关键在于学习希望,希望高于恐惧,它使人的心胸变得开阔。伊和亚当在海边伊甸园的生活充满了人类最原始的希望与想象。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伊丽莎白对大自然与爱情的激情渐渐褪去,野外生存的艰难让她开始怀念开普敦的贵族生活。亚当出于对伊丽莎白的爱护和尊重,放弃了自由的荒野,保护其回到开普敦。纵观小说的脉络,不难发现亚当对开普敦繁华的社会生活也是极其向往的。初遇伊丽莎白,他总是打听开普敦的故事,什么都愿意听,说明在长时间与世隔绝之后,亚当对人类社会的聚居生活十分期待。亚里士多德曾说,能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的不是野兽就是神。人具有社会性,但自由与繁华不可兼得,这是亚当乌托邦理想的遗憾,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南非残酷的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抹杀。
两人逃离南非社会是对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抗争,最后的回归象征着他们建构乌托邦空间努力的失败。当两人回到开普敦,伊丽莎白重获贵族身份,而亚当却被处死。通过这一结局,布林克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理想社会必须建立在开明的政治制度基础上,这在18世纪南非种族主义盛行和黑人奴隶制尚未废除的情境下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布林克也说明了不同阶级对社会革命的坚定性是有差异的,客观来说,伊丽莎白属于南非上流社会,属于统治阶级,白人女性虽然是性别政治的牺牲品,但她们同时也是黑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所以伊丽莎白的生存境况仍远远优于亚当,这种差异的结合注定了他们乌托邦建构的失败。
(二)寻找盖瑞普:实践乌托邦
布洛赫认为,生活中充满了乌托邦的设想。菲莉达自幼辛苦劳作,遭受白人奴役,但仍然对未来存有一份希冀:“这肯定不是生活的全部,这不可能是全部。终有一天会发生什么。”[13](p281)她的期待没有落空。终于,在1834 年12 月,南非的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了解放黑奴的法令。“长期以来,是他们(白人奴隶主)决定了他们有权力说:菲莉达,你是个奴隶。但是他们没有权力说:菲莉达,现在你自由了。这句话只有我能说,而我今天就要说,今天,我是个自由的女人。”[13](p282)虽然从历史来看,南非在1834年之后并未停止对黑人的迫害和压榨,但奴隶制的废除已是南非黑人迈向自由的一大步。所以对于菲莉达而言,她有机会重新审视生活,仿佛它已经改变了轨道,开始朝着一个方向进发,这个方向的终点就是她理想的乌托邦——盖瑞普。奴隶制的废除和对基督教的摒弃为菲莉达乌托邦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从此,她不再被基督教所宣扬的“白人至上”理论所蒙骗,砍断了对白人奴隶主、对种植庄园的习惯性依赖,摆脱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困境。所以当奴隶制被废除后,她不像其他黑人同伴一样仍然依恋着赖以生存的种植庄园,而是毅然决然离开,去寻找梦想中的盖瑞普——自由而开明的乌托邦。《菲莉达》中的弗洛里斯说:“在那里(盖瑞普——笔者注),土地是开放的,一切都是自由的。”[13](p285)在寻找盖瑞普的路上,他们可以搭乘好心人的马车,拉本可以利用自己做棺木的手艺赚取路费,他们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以前她的自由只存在于弗朗斯泡沫般的虚伪承诺中,但在寻找盖瑞普的路上,菲莉达感知到的自由却是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我自己选择了自由。我相信它所以选择了它。这种自由犹如太阳、月亮和繁星。太阳升起并不是因为有人命令它,而是因为这是它的本性,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它不要升起。”[13](p299)这是属于她的自由,她成为自由本身,而这正是菲莉达一直以来所向往的。在这里,布林克借菲莉达之口,发出了内心追求民主、文明、自由的呐喊。
对菲莉达而言,这次出行的意义非比寻常。一方面,她要寻找的是梦想之地,自由平等的乌托邦——盖瑞普。另一方面,此次出行不是在白人指使下进行的,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完全出于菲莉达的意愿,这是奴隶制废除后她做的第一个自主决定。所以当她终于到达盖瑞普,沐浴在河流里的时候,终于醒悟,她此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找到盖瑞普,她所要寻觅的在路上就已获得,而她必须经历这次旅程才知道,来的地方才是归宿,只有经历了这次旅程,才知道黑人终于可以获得自由。“乌托邦本质上是对人类和谐幸福的神秘渴望,而不是未来人生活的具体蓝图。”[23](p14)所以对于菲莉达来说,能够自由活动,来去自如,感知这一自由才是此行目的,而这一目的实现也为她以后的生活加满了动力与渴望。
(三)反乌托邦里的乌托邦希冀
反乌托邦小说以逆向思维对现实社会中的集权主义及其带来的各种形式的压迫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魔鬼山谷》是布林克第三次创作转型(1991—2015)中的作品,这一时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土崩瓦解,政治境况发生巨变。[24](p55)这部小说也是布林克尝试反乌托邦创作的华丽之笔。作者采用了对比的叙事形式,也就是说没有单纯讲述另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而是将虚构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相比较,通过对比来表达主题。
南非社会曾充斥着暴力和犯罪织就的网,根据小说中犯罪记者的工作记录:“每小时有3 起谋杀案,每12 分钟1 起强奸案,每5 分钟1 起持枪抢劫案,每20分钟1起猥亵儿童案。”[17](p16)他通过这些数字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也是当时南非社会的真实写照。魔谷的原型是南非小高原的死冥界(Die Hell in the Little Karoo),[25](p71)谷里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伦理道德丧失、极端种族主义盛行、性别压迫严重、人性发生异化。到故事最后,魔谷因为气候异常,渐渐不适宜人类生存,指涉在极权统治、性别政治和种族主义的阴霾下,人们难以喘息,无法存活。
魔谷中的罪恶实际上是南非社会各种罪恶的放大,布林克的描述揭露了基督教外衣下的集权统治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彻底将南非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毒瘤暴晒在世人面前,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南非社会如不进行彻底改革或许会成为“魔谷”。布林克对各种社会弊端的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是在履行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责任,也寄托了作家改变南非社会的政治理想。
四、结语
乌托邦是一种理想维度,是一种人们所希冀和祈求但于现实世界并不显现的理想社会。对乌托邦社会的追求成为人们生活的动力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推动着人类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纵观布林克作品中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写作,可以看到作者对南非现实社会弊端的强烈批判和对美好政治愿景的追求。前者体现在反乌托邦小说中对罪恶的鞭挞和批判,后者则体现在乌托邦小说中主人公对乌托邦的追寻。所以,不管是乌托邦书写还是反乌托邦书写,实际上都寄托了作者对平等自由的美好社会的向往和乌托邦政治理想。如何才能实现乌托邦和社会重建呢?布林克认为“除非与过去的黑暗和沉默达成和解,南非社会,像人一样,无法成长和成熟”,[26](p25)唯有用想象力去抓取过去和它的沉默,才能迈出种族和解和社会重建的第一步。1994年,南非政府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旨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真相委员会听取了21000名证人的陈述,这些证人中既有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也有当年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作恶者,[27](p5)所有这些努力都在为南非的乌托邦政治理想铺垫。南非社会也越来越贴近布林克的美好畅想:“南非的未来建设在不分肤色、种族、阶级、信仰及性别的人权认知、民主、和平共处和所有人平等发展的基础上。国家统一及所有南非公民的良好行为与和平追求,需要南非人的妥协、一致和社会重建。”[28](p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