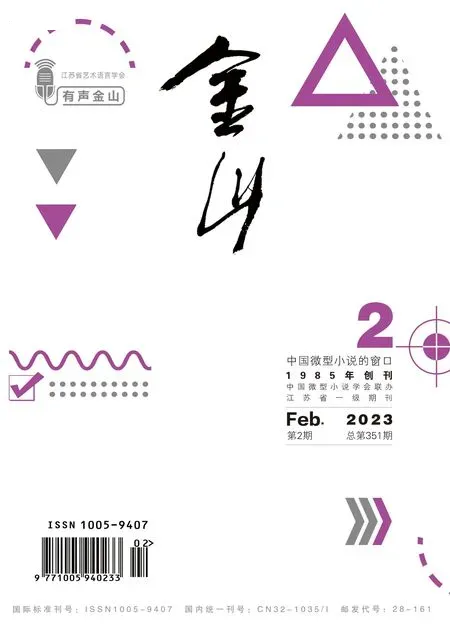东坡村的牛马驴骡
2023-03-10河北律新民
河北/律新民

诵读:江苏非鱼
独 角
坝上东坡村的兰朵哭声淘淘,泪水涟涟。她丈夫王彪被独角顶死了。
独角是头牛。它挣脱犁杖追撞郭守亮时,王彪冲上去握住了它的那只角,独角一甩头,牛角撞在王彪肚子上。
哨音尖啸而急促,嘟嘟——嘟嘟——开会啦。
生产队长马启狠吸一口烟:“独角顶死了王彪,保不准哪天再顶别人,将它杀了分肉,还是卖了分钱,大家说咋办?”
郭守亮从脸颊上移开颤抖的双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公理,必须杀独角祭王彪!”
坝上没有不下雪的冬天,一尺来深的积雪,别的牛连空水车都赶不出去,身大力不亏的独角却能往返十二里去拉水。没有独角拉回水,村里人只能融化积雪越冬,淡黄色的雪水,喝上一口,串着野蒿子的辛辣味儿。
“独角……牛没罪,它头上那角有罪。它一头撞不死王彪,是它头上的角顶死的。”兰朵的话语轰然放大了满屋的哭泣声。
马启宣布:“按兰朵的意见,锯掉有罪的那只角,明天给王彪送葬时,焚牛角祭亡灵。”
人到中年的王彪和兰朵,家中土炕从来没凉过,兰朵被蚊子蹬一脚,王彪也得心疼好几天。不知是籽种不行,还是地亩不行,就是不生娃。这无儿无女的,出殡送葬谁扛幡?村里的小字辈呼啦啦抢着扛,郭守亮握紧幡杆不撒手。
送葬队伍缓缓蠕动着。郭守亮手持魂幡仰天呼号:“大路朝天走半边……王彪大哥回来呀!回来呀!”
王彪的坟前燃起莜麦秸,熊熊火焰暖了春天的风。兰朵跪在坟头,双手将牛角缓缓地推入烈火中。焚烧牛角的腥辣味儿从火中扑出来,又随着升腾的缕缕白烟,云上了湛蓝湛蓝的天。
谁都听得见,哞……哞……哞……村里传来了牛吼声。
火烧云
东坡村的那挂胶轮马车,两匹稍子马油光水滑黑缎面,驾辕的红骝马,一朵飘动的火烧云。
车把式高连奎属鼠,绰号“老耗子”,年近五十岁,天生笑脸却爱骂人,嘴边常挂着“狗娘养的王八蛋”。你指责他骂人,他就说:“我是赶大车的,不骂人。”言外之意,被骂的都是牲畜。
一件突发的事儿,让老耗子爱骂人的习气一扳闸,刹车了。
马车满载着几百张绵羊皮驶入一路下坡的盘山道,坡路将尽的时候,马车的刹车闸线崩断,溜坡了。老耗子向前冲去,要拽住稍子马圈停马车,他一把没抓住马笼头,自己却摔倒在车道上,驾辕的火烧云掠过瞬间,叼住他的棉袄一甩头,将他甩出车道外。
老耗子瘸着腿追过山弯时,马车竟然奇迹般地停住。他扑通跪在地上,给火烧云连磕三个头。
“你说出花来,这车我也不赶了!”老耗子硬是将马鞭交给了生产队长马启。
几年后,火烧云老了,撤下来干轻活。老耗子告诉妻子,火烧云将来老死,就埋进咱家坟地。
没想到老耗子又骂人了。
“狗娘养的王八蛋,把火烧云按驴肉价儿卖了,你还算人吗?今天我不赶大车也骂牲畜。”
老耗子在队长家门口跺着脚骂,队长猫儿似的没敢出屋。
暖 驴
大年初一,插队知青安达怀揣一壶热酒,去畜棚给大黑拜年,大黑是头驴。
腊月,安达骑上大黑,冒严寒踏积雪,去平安堡邮局取父亲汇来的五元钱,再给队长捎买二斤白酒。
回程刚走几里路,铺天盖地刮起白毛风。安达从大黑背上跳下地,放长缰绳让大黑牵着走,此刻,他只能相信老驴识途。
骤降的气温,冷透了。安达扭开军用背壶盖,咕咚咕咚几口酒,一股热流蹿上身。
大黑突然停住,转身用头拱蹭安达的怀。噢,忘记给它戴棉头套了。
坝上的严寒天气里,骑驴骑马外出,都要用棉头套护住它们的脑门儿,否则,它们会被冻伤颅脑而躺倒。
安达解开白茬皮袄,将大黑的头搂进怀,暖着它。
大黑又牵着安达搏击风雪继续前行。焐暖了大黑却消耗了安达的热量,他咕咚咕咚又喝几口酒。
天哪,大黑又停住了。
安达敞开皮袄搂进大黑的头,大黑又像哺乳的孩子找到了娘。
饮酒——焐驴——前行,饮酒——焐驴——前行……不知循环了多少次,大黑牵着安达回到知青点儿。
畜棚里,安达从怀里掏出酒,咕咚咕咚饮下去,解开皮袄敞开怀,大黑扎进他怀里。
大黑鼻翼呼出的热气暖暖的。安达倾听着大黑的喘息声,还有其它牲畜吃食草料的咀嚼声。
花 舌
花舌是东坡村的黑骡子,驹子时,饲养员老温头儿发现它舌头青白斑驳,花舌。
老温头儿说,花舌牲畜爱记仇,招惹了这种牲畜,保不准哪天一顿蹶子,踢惨你。
骡子长到八个月就该调教,花舌两岁多了,笼头没戴过。它无拘无束,抢马的草,抢牛的料,掠食青青的莜麦苗。它像撒欢儿的风,在村中飘来荡去,人们老远就躲它。
队长马启终于扬言要驯服花舌。他指挥几个小伙子,拖起大绳缠住花舌的腿。马启闷足劲儿,咣的就是一膀子,将花舌撞倒在地。解开大绳,驱使花舌重新站起来,又用大绳缠绕它的腿……花舌在马启面前瑟瑟发抖。
马启给花舌备上鞍子,勒紧肚带,调好双蹬,骑上它稳稳地绕村子转了三圈儿。
突然,花舌一蹶子将队长尥下地,挣脱嚼子,一溜烟颠了。
花舌重获自由,横蹦竖蹿,还时常立于村头土丘昂首嘶鸣,它唤不出东方日出,却也有几分君临天下的惬意。
那天早晨,花舌陷进了一处废薯窖,脖子卡在窖檩上憋断了气儿,人们争相围观。
花舌的舌头从嘴角耷拉出老长,淡粉色的舌头,根本没有青白斑驳的花纹,马启瞪了老温头儿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