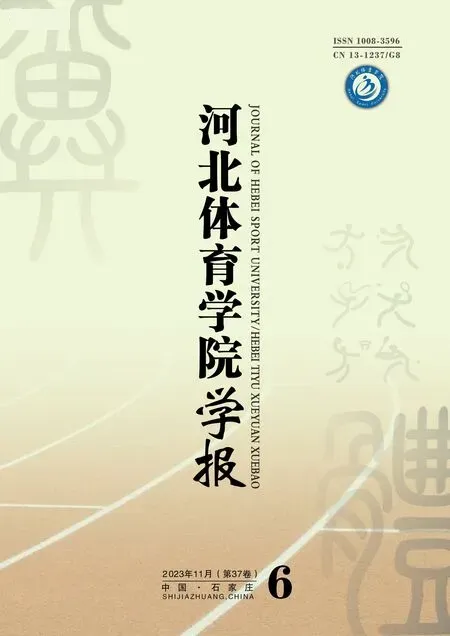足球原始
——现代社会中的动物美学
2023-03-07路云亭
路云亭
(上海体育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438)
足球是一种关于极端之爱与极端之恨的悲情叙事。从悲剧主义视野上看,足球宛如一种关于人类终极价值的预演过程。好在足球仅仅是一种游戏的形态,它旨在诠释世界的本来风貌,却意外地成为一种关于生态、物种、人类理想、信念、想象力的复合性喻体。足球是一种史前文明的再现品,其中不乏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猎食类动物的纪念性意义。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空置状态下的足球场域更像是一种关于史前狩猎行为的活体演示博物馆,举办赛事的足球场也很像一种精心构建出来的猎场,足球人则是人类狩猎意志的守卫者,因此,足球与其说是一种竞技行为,不如说是人类文化、宗教、教育、艺术的融汇体,且一直在多重境遇中扮演调和者的角色。足球出于狩猎之道,又超越世间万物,进入一种人与自然的重构空间。无以否认,足球展示出一种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本质关系。
1 足球是对人类狩猎行为的写意性模仿
将足球还原到狩猎文化的体系内便会发现,足球竞技本身更近似那种群体性狩猎场景,足球借此构建出一种大型狩猎活动在现时代的真实性、身体性与感验性遗脉。莫里斯从狩猎仪式的角度指出,“足球远不止一场比赛而已”[1]26。莫里斯显然注意到了足球的象征性意义。足球的象征意义来自一种固有的社会原型,其意义指向人类的史前狩猎行为。“每一场足球比赛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要想更清晰地认识足球运动的诸多面孔,我们若是从‘仪式性狩猎’的概念开始,将它们独立开来、逐个探察,必能有所益助。”[1]26莫里斯借用“仪式性狩猎”的概念解读足球赛事的本义,在更高的角度确立了一种对人类远古职业的敬意。Peter Swain曾记述过足球与狩猎性运动项目同时出现在英国的情况。“公园提供了秋千、足球、射箭、拳击以及其他游戏项目,这些项目也得到了一定的赞助,这清楚地表明,它们是多么强烈地受到该镇的‘辛勤的劳作者们’的喜爱。”[2]由此可以看到足球与射箭等狩猎技艺之间的特殊联系。足球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进球数量的追求和对对手进球数的压制两方面,两者皆源于史前狩猎的惯性。
足球的确有某种象征意义,但也有其极为普泛的一面,莫里斯对此做过解释。“对某些人来说,这些象征意义完全无足轻重,在他们眼中,现代足球是人类身体技巧的抽象竞赛,类似一种规模更大的棋类游戏,而关于球的部分不过是多余的‘野蛮’元素。”[1]237现代足球所谓的野蛮性更容易为东方人士所感知。“原始足球是有一点‘野蛮’的,先人喜欢这种游戏,或许多半是为了寻求一种刺激,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而文明社会的发展使原始足球脱胎换骨,分离出美式足球、橄榄球等‘蛮式’部分,而其精髓——用脚踢球——则非常珍贵地保存下来,而且赋予新的文明规则,为现代和全人类所喜爱。”[3]其实,人类社会的职业发展一直有两条路径,一条是物质性、世俗性与实用性的选项,另一条则是精神性、艺术性与心理性的选项。前者发展出一种职业链,如从远古狩猎发展到现代商业社会中的诸多职业,现代足球的竞斗早已脱离了古足球时代的混战状态,代之以不同的角色分工、阵型类别和战术套路。后者进化出一种文化链,构建出一种超越足球竞技本体的文化延伸事项。
足球仅是人类社会万千职业中的一种,足球预示着一种工作的权利,参与其中者也是劳动者。莫里斯曾引述过法国作家让·季洛杜的观点:“足球是游戏王……人类所有的伟大游戏都与球有关……在我们的生活中,球是逃离规则的最便捷的途径,这就是它最有用的特性。在这个世界上,球拥有一种尚未被完全驯服的天外之力。……足球之所以风行全球,是因为它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球的效果……除了球本身的特性,即弹性与独立性以外,球队里11个精明的头脑和11个人的想象力还赋予了它额外的动力。我们之所以禁止运动员在足球比赛中用手碰球,是因为手的入侵会使球不复成为球,球员也不再是球员。手是作弊者……球不允许任何作弊,这让它更显崇高。”[1]237足球还称得上是一种高度具象化的哲学,具有多元化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喻体性价值。Richard Giulianotti认为:“足球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和情境是在地方、国家和跨国层面上形成个人和集体对全球比赛理解的核心。”[4]正因如此,足球中的诸多细节颇值得玩味。足球是由不同球员的位置构建出来的,前锋、中卫、后卫、门将之类的场域角色很像远古狩猎时的不同类型的猎手,而阵型、套路之类的概念性元素很快就和足球的战术体系融在一起。很多经典的足球教材直接将训练核心解读为狩猎行为。“所有队员在一块固定范围的场地内活动,一名或多名队员充当‘猎手’去抓其他的人。在追捕过程中,只要被追者能和另一名队员通过拉手、拥抱等结成一组的话,他就能免受‘猎手’的抓捕,否则一旦被抓,就要充当下一个‘猎手’。”[5]狩猎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娱乐、游戏的复合性代名词,人类社会很难变更其千年不易之基本习性。
绝大多数的动物无法进行生产性劳作,其生存技能大多仅限于直接获取食物,不同层次的动物获取食物的方法差异很大,由此构成了为现代人所熟知的生物世界的食物链。作为生态学术语的食物链概念进入人文社会学科便衍生出相应的美学范式,但其中的生物伦理亦不宜被人忽略。
足球是富含生物元素的文化载体。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生物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生命的世界肯定不同。感觉与知觉是有机体生存的必要手段,也因此让世界保持稳定。”[6]狩猎是一种联通人和生物关系的最为普遍的行为,它也几乎可以决定现代人的职业类型。现代社会的职业种类繁多,分别象征着远古时代多种多样的狩猎场域。远古人捕获猎物可以给逐猎者带来食物、安全感与社会地位,而现代职业也与之类似。远古狩猎还有一种精神性、神圣性与文化性内质,但现代人的求职动机中较为凸显世俗性内涵,其所释放的是一种物质优先的理念,这也意味着现代人的狩猎观与古代人有明显的差异,而打通两者的则是足球竞技的综合体。从本质上说,足球既以狩猎为原型,也可下启现代商业社会的职业分布结构,抑或还可以构建出一种关于缠斗、抵抗、放弃、升华之类的组合性镜像。
在现代足球竞技活动的促动下,原始狩猎与现代职业之间生发出很好的共鸣点。然而,现代职业在脱离了原始狩猎的既有体系之后,在很长时间给人们带来焦虑感,因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以技术革新为前提,而技术革新一定会淘汰大量的古旧职业,进而给很多行将被淘汰的人带来巨大的心理不适感。于是,人们迫切想要设计出一种打通两者的媒介,以消弭那种焦虑。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与远古狩猎相似的文化品类,这便是以足球为代表的球类运动项目。由此可见,足球并不仅仅是一种展现参与者身体技能的运动方式,它还有超越身体技能以外的仪式性、象征性与抽象性的符号学价值。由于蕴含着远古狩猎的内在精神,足球的多维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的关注。无以否认,现代足球演进至今,已然是一种成熟的文化类型。它有自己固化的属性,且在现代社会占据很高的地位。足球一向拥有现代人向往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同样源于远古狩猎。人们在狩猎行为中很容易获得自由与解脱。相比较而言,足球属于对石器时代文明形态的戏仿。在微观的领域更是如此,足球所释放出来的自由感更像是一种场域内的体验性元素,而非绝对自由的精神符号。
足球的自由感大多来自狩猎时代逐猎者的想象,其意义指向在于直觉、感性以及与生俱来的简单的乐趣。足球的最高意义在于自由,自由并非为所欲为,恰相反,自由是一种摆脱非常态束缚的仪式化程序。相对来说,摆脱约束能力最强的人也便更容易成为足球明星。且以知名球星的个体化生活为例。只要探讨一下足球巨星们球技的生发源头,便可看到足球的自由感的内在能量及其生发原理。贝利、马拉多纳、梅西等足球巨星的技术体系中有特殊的理念因素,也有其习惯性动作程序,更有一种对原始猎场中诸多元素的个性化认知,其中包括奔跑中的变速、肢体语言中的敏捷感、触球时的微观感受、对球场空间的立体性研判以及对敌手方位的超前判断。无以否认,任何一位高水平的职业球员的踢球乐趣皆源于那种人类狩猎时代的常规情境,那里具有更多的不可知性,也意味着那里包含有更多的创造性、想象性与实验性元素。足球巨星所拥有的技术细节也因此构建出一种只能意会的迷人情境。换句话说,衡量足球本体价值的尺子仍是一种自然之道,足球尊崇的是自然哲学,其中不乏丛林法则。在此意义上看,足球大体与生物世界中的其他身体展示形态具有相似性。
2 足球是远古狩猎法则的现代性延伸
足球的仿猎内质仍有深度阐释的余地。其实,狩猎活动异常古老,它的现代性价值在于演示出一种现代人所从事的职业的原型。挪威学者Linda Marie Bye曾说:“与英国的狩猎传统不同,挪威的狩猎传统一直是一种基于收获原则的公共传统。然而,尽管这种从大自然的丰富资源中收获的基础仍然存在,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强调与狩猎有关的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娱乐、兴奋和友谊。”[7]狩猎一度是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随后才演进为一种体现原始文明的主体构件。其实,狩猎时代所缔造出来的想象力一直有一种跃出其单一性身体技艺的能量,且已然超越了足球界乃至体育界的价值范畴,成为一种泛在的核心能量。狩猎极易构建出一种超越狩猎本身的想象空间。Azhar Kola等人看到了狩猎伦理的合理性与虚伪性的并存状态。“狩猎纪念品经常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比如2015年美国牙医Walter Palmer在非洲西南部杀死狮子Cecil的反应。这种反应是以对野生动物的浪漫化且往往是拟人化的态度为前提的,与肉类工业中每年被人类屠宰的数百万只动物相比,像Cecil这样的可识别的动物获得了更高的地位。”[8]针对狮子这样的顶级猎食者的捕猎行为会受到全社会民众的抨击,因为它影响了人类对强大猎食者的图腾崇拜的基本惯性。
Roberte Hamayon曾经阐释过狩猎的原始快感。“在游戏期间炫耀的喜悦还旨在培养另一种感觉:欲望。狩猎的欲望与猎人在夜间守夜时讲述的感官故事在其梦中唤起爱的欲望平行。在这方面,俄语特别明确。对于‘狩猎’,它使用了反身动词ohotit’sia,这个词源自于固定语ohota,它同时表示狩猎、需求、欲望和快乐。根据这个词源,狩猎被解读为‘享受’,亦被解释为‘追逐人们想要的东西’,仿佛追求欲望本身就很重要,不管它是否获得满足。”[9]足球就是这样一种仿猎性演示形态,它充满了高度的演示性,并包含了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情感类型。
莫里斯试图勾勒出现代狩猎与古罗马斗兽之间的链接关系。“农业革命之后,城市扩张紧随而至。大型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安分的游牧部落没有了野外运动的空间,也再无希望享受狩猎的快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罗马人想了一个办法,它对后来足球部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他们完成了一项伟业,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竞技场,也就是罗马斗兽场,这实际上将狩猎活动带到了人们身边。”[1]20尽管狩猎文明较诸农业文明略早,但是,狩猎文明对大自然的依赖性更强,且与自然的关系也更近,其与竞技游戏的关系也更为紧密。
通常而言,牧业社会是沟通狩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中介。英国是从牧业社会直接过渡到工业社会的,因此,英国人未曾感验过农耕文明的极致形态,更无以对其产生高度的精神依赖乃至膜拜之情。正因如此,英国人在迎来工业革命之后,很快就将农耕文明彻底抛弃。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使人生发出原先未曾见过的隔膜感,工业品开始替代人类自身,于是,人类社会中的技术革命构建出一种全新的权力结构,它使得世界的多维性反复出现。Rodanthi Tzanelli曾引述Brecht的观点,认为互联网记忆“在抽象性与特殊性以及理论与经验之间摇摆”[10]。从当下的智能视频网络中即可感知,技术强化了人类文化交际的深度,却也给为数众多的人带来不适感,正因如此,智能网络时代给人类带来幸福感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人们对既往历史的纪念冲动。原始文化价值的再认知潮流即源于此。
Azhar Kola等人阐释了狩猎行为与权力的结构性关系。“Luke进一步将狩猎与掠夺性异性恋混为一谈,认为两者同时是权力、支配和致命的性行为的表达。”[8]狩猎文化的现代性意义在此得以体现。狩猎一度是事关生死存亡的极端性事件。Azhar Kola等人揭示出了狩猎过程中有关猎物死亡的核心议题。“它以动物的死亡为中心。来自我们的参与者的沉默以及我们作为研究人员的疏忽让人们感受到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显示出更广泛的猎人猎杀的权力动能。”[8]正因如此,狩猎与人道主义的矛盾一直存在,然而,人类一直都在寻找摆脱狩猎原罪感的正当理由。亨利·梭罗曾说:“我赞成捕鱼并不是因为我不人道,而是因为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么热爱捕鱼。对于虾和鱼儿,我一点也不同情怜悯,毕竟自然法则就是如此啊。”[11]这里显示的是对生物世界基本秩序的尊崇意向。
一切都在变化。整体而言,现代狩猎已经转化为一种休闲资源。“人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有关非洲狩猎或艺术的精神漫谈,他们经常坐在美丽的花园里,一边品茶一边高谈阔论,过着毫无压力的闲适生活。”[12]其实,这里又生发出一种新的悖论。狩猎的惊人之处在于人们制造出了生命终止现象,而狩猎者又可以在此现象中获得更大的生存动力,类似的现象充满了惊悚性,这便让狩猎表演成为可能,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的悲剧精神得以显现。Erik Cohen看到了狩猎悲剧性背后的静默、反思、纪念性情感。Erik Cohen高度推崇狩猎过程中的自然性的超高价值,狩猎的过程与人类远古的献祭仪式在此得以呼应。“这种争论在Kheel对‘神圣猎人’的描述中达到了顶峰,对猎手来说,‘狩猎是一种宗教或精神体验’,并成为一种‘类宗教仪式’。Holmes Rolston声称‘狩猎不是运动;这是一个基本的、强制性的追求和占有带有生态系统特性价值的圣礼。’Kheel总结道:‘依照他们的世界观,神圣猎人不会‘杀死’动物;相反,是动物‘奉献’出了它们的生命’。”[13]Erik Cohen试图解读出休闲狩猎与战利品狩猎的差异性。“最近的研究文献展示出一种趋势,应当优先考虑战利品的意义,而非追求一种深刻的、全面的体验。Gunn划分出了运动猎人和战利品猎人的差异,他们‘屠戮仅仅为了获取一种人所共知的有能力杀死了一头猎物的证明’,但‘不能声称他们是在与狡猾的对手斗智斗勇,更不能说冒个人性的风险了’。”[13]在此意义上观照,足球既带有一种史前逐猎的意味,亦具备现代性的高度抽象感。足球对狩猎有超越的作用,而非仿真的意向,足球的原始意义不仅体现在对狩猎行动的戏仿,还带有争夺战利品的实际意义。“1790年的一份记录这样写道:‘丹麦军队的首领被杀掉以后,他的头被人们嘲弄地踢来踢去;从那以后,当地就形成了在那一天举行足球赛的传统。’德比郡的阿什伯恩每年仍在举行忏悔节足球赛,……本年度特制的比赛用球也将成为进球者的战利品。”[1]237然而,究竟何为现代足球?现代足球对古代足球的超越性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简单来说,以狩猎为核心的技艺往往具有很强的审美性。不妨看看美术学界人士对足球的评议。“我们为什么要用透视看东西?西方有很深厚的文化解释能力,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方狩猎文明瞄准猎物、射杀猎物、分割猎物等社会生存活动的方式上,可以解说到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以及黄金分割上面,但是中国人从来不需要这样看。”[14]由此不难看出,狩猎时代的记忆符号不仅在足球之类的球类运动中得到了继承,还对人类社会中的美学理念产生过深刻影响。只要略加考察就会发现,当今流行的各种以速度见长的运动或表演艺术形态都与人类的狩猎记忆有关。
足球有很多超体育的感召力,高度认可足球价值的人会对足球中衍生出来的诸多可塑性元素抱有好奇心。摩托车足球以及大象足球之类就属于正统足球之外的另类实验性足球。即便退回到足球本体中也会发现一些由足球自身派生出来的分支化、小型化、微观化的足球游戏手段。人们常会看到三人制、四人制、五人制的足球,还有沙滩足球、室内足球以及作为训练手段的抢圈足球之类,这样的足球类型未必会成为主流体育项目,但是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足球的潜在生命力,亦可洞悉其与原始狩猎现象的内在链接点。
足球是一种行为文化,充满了感性化元素,其功能略等于现代艺术。较诸古典艺术,足球中轻快愉悦乃至滑稽可笑的元素恰可体现出其特点,人们很容易看到球员在比赛的间歇展示出来的高度轻快的表情,球员一旦射门成功,还会有更为欢快的庆贺动作出现。如亲吻手指、亲吻衣角、亲吻草地、滑跪、跳非洲舞、飞跃广告、翻筋斗等等,以及C罗的垂手操、姆巴佩的抱臂观、哈兰德的打坐冥想、梅西的晒球衣等相对固化的庆祝动作。弗朗西斯科的庆祝动作更为多样,其中包括脱掉上衣仰天咆哮、挥舞双拳自我沉醉、左拳紧握亲吻中指、面向观众扮出鬼脸。1998年9月的一次评选显示:最佳庆祝动作是马克·切努的双臂高高举起在空中交替划圈;排名第二的是卡雷卡在1986年世界杯上做出的动作,张开双臂,在球场上飞奔并同时摇摆;排名第三的是克林斯曼,他进球后常常高举双臂并做出战斗机一样的俯冲动作, 他的绰号“金色轰炸机”也由此而得[15]。足球的欢悦感很强,其欢悦性行为与史前生物高度一致。从表面上看,足球似乎仅需一击致命的爽利之气,而不需要多少妩媚动人的漂亮舞姿,其实不然,足球本身就是充满动感的新型舞剧,而透过现象方可看到其真实命义。其实,人们在鸟类行为中可以更好体会到人类需要的欢悦性动作形态。舞蹈是部分鸟类的专利。达尔文曾经描述过类似的情景。“圭亚那的岩鹤、极乐鸟以及其他一些鸟类,聚集一处,雄鸟在雌鸟面前轮番地展示其美丽的羽毛并表演一些奇异的动作;而雌鸟则作为旁观者站立一旁,最后选择最具吸引力的伴侣。”[16]为求偶的功利性所限定,鸟类乃至人类的舞蹈都有性炫耀的成分,这也是舞蹈这一独特的动感体系与足球高度兼容的理由。然而足球的庆祝动作内涵更丰富,英国运动心理学家马丁·佩里认为:“庆祝动作已成为运动DNA的一部分了。”[17]从仿猎性行为动机的角度看,球员射门成功后的欢乐感同样来自狩猎成功后的愉悦感。
3 仿猎球戏对现代人的生活观念的干预
心理学家在探讨学习动力的时候曾关注过狩猎快感问题。“我们通常需要两种快感的加持,才可以长久地维持学习动力,它们分别是狩猎快感(pleasures of the hunt)和享用快感(pleasures of the feast)。这两个术语出自美国精神病学家唐纳德·克莱恩(Donald Klein)的一个比喻。克莱恩说,一个原始部落里的猎人如果想磨炼好打猎这项技能,那么首先他要能感受到狩猎快感,也就是在追逐猎物时感受到的那种兴奋、渴望、刺激和力量感。狩猎快感主要由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产生。多巴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当多巴胺大量分泌时,人们会体验到追求目标的欲望。这是一种让人紧张的快乐,有了它的加持,人们才会有足够的行动力。尤其是当新手猎人刚开始学习如何追逐猎物时,狩猎快感至关重要。”[18]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中的教育源于狩猎教育,球迷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也体现在这里。球迷有球瘾,猎人也有猎瘾。终生狩猎的人一旦失去了狩猎的机会,就会变成一种向往狩猎甚至膜拜狩猎的人。基于同样的原理,球迷看不到球赛,就会变成一群失去了生存动力的人,还有可能发展成丧失社会理性的人。
笔者早年在山西农村生活,曾跟随一名非职业猎手参与过一次狩猎行动。笔者清楚地记得,村民虽然和该猎手打招呼,但都不太亲热,大多只是对其打猎之举感到好奇而已。不难看出,猎人在农耕文明体系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也无以成为主流,对一些一辈子侍弄土地的农民来说,狩猎带有不务正业的色彩。当时的中国农民对待猎人类似于现在的人对待赌徒,心存反感,敬而远之。只有两三少年很感兴趣,尾随在其身后。从中可以看出,相比枯燥乏味的农业劳动,狩猎活动所具有的游戏性、娱乐性、专注性和休闲性,很容易激发儿童少年的好奇心。笔者还曾听说过一位半职业猎手的故事,他每年冬天都要上山狩猎,大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禁猎令颁布以后,这位猎手经常对着空气做一些扣动扳机的动作,有时也拿一些假枪之类的东西摆几个空枪空放的姿势,借以满足那种狩猎时代的心理记忆。概言之,中国的农民对容易上瘾的职业保持着高度的疏离感与警惕性。从微观的角度看,中国农民心目中的成瘾性职业带有显性化的“原罪”成分,这也成为其存在合理性被否定的原因。然而狩猎有其显著的游戏性,会引发独特的快感,进而“激发追求的欲望,维持追逐目标时的行动力”[18]。从这个角度来看球迷的观球成瘾现象,不仅仅具有现实的真实性,还有更为超现实的主观能动性。
狩猎行为的成瘾性引起了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在多巴胺系统的加持下,年轻猎人们强迫性地学习危险的打猎活动,停不下来。类似的体验也会出现在吸食某些毒品(比如可卡因)的人身上。可卡因这类毒品会直接刺激大脑大量分泌多巴胺,让人产生停不下来的吸食欲望。学习追逐猎物与吸食可卡因都会让人体验到狩猎快感。既然强迫性的欲望是成瘾的关键特征,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说:那些年轻猎人们就是因为‘对打猎上瘾’才坚持学会了这种技能。所以,成瘾其实是学习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有些成瘾物激发狩猎快感,有些成瘾物激发享用快感。成瘾实际上就是对学习环路中两大快感的浓缩和模拟,是关于正常学习过程的一个‘角色扮演游戏’。”[18]心理学将那种狩猎快感与心流学习作比,进而认为人类的学习过程完全是狩猎行为的高仿行为。“进入心流后的练习往往能让人迅速成长。而在心流中体验到的那种混合着刺激与紧张的快乐,正是狩猎快感。再比如说,为什么现代竞技体育能激发出人类最大的运动潜能?那还不是因为竞技体育的获胜者能名利双收,体验到无敌的享用快感吗?”[18]不难看出,成瘾现象是人在遭遇困难后的摆脱诉求及其系列性的动能,属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可贵的品质,成瘾现象的原点在于好奇心,它属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闯关诉求。
人类进化过程要经过很多极为困难的关口,这些关口几乎与生死等值,人类如果无法闯关,轻则个体死亡,重则种族消失,正因如此,人类有一种对未知事物的忘我的探索欲望,这便是成瘾现象的本质。成瘾现象在足球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足球成瘾有很多分支类型,包括赌球成瘾、看球成瘾、踢球成瘾之类,其核心点在于探索足球的奥秘,而其初始化的源头仍在于狩猎记忆。且以看球成瘾的球迷为例。特定环境中的球迷也在扮演猎手的角色,高强度的角色扮演欲望最终冲决了防止他们成为猎手的防线,球迷最终成为一种恒定的优秀猎手角色的俘虏。无以否认,狩猎行为所演示的是一种夺取战利品的象征性故事。争夺战利品的过程无非显示出一种成功与失败、获得与失去之类的极端对应链。人们获得了胜利自不待言,而失败者也可以利用信仰来获得心理平衡,正因如此,足球中的信仰成分很高,其在足球的文化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不难看出,足球场域中的球员与球迷高度类似远古的狩猎者,他们高强度的专注力其实也是一种致幻剂,置身其中者会以为世界的中心是足球,而其余的事物几可忽略不计,甚至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其实,类似的思维惯性也源于狩猎记忆。足球竞技给胜利者带来欢愉的引信,还给失败者带来不至于彻底毁灭的安慰。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足球的致幻性、虚饰性与信仰性在任何一位关注者心目中都大体一致,那是足球高度感性化的特质所引发的人们对足球本体的崇拜。戏仿狩猎的足球可能会使生活变得更神奇,但也可能让生活不太规范。换句话说,足球是一种人类制造不均衡语境的行为,其像狩猎一样,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探险性动作程序,还是一种人类在挣脱险境后的自我解救状态,它可以将悲剧转化为喜剧,又将喜剧推高到极度欢悦的境界。
任何动物都无以拥有特定意义上的床铺、被褥、餐桌、服饰,遑论大厦、飞机、飞船、电脑。因此,对人类来说,动物性就是简约性。足球在更多的场域中都仅仅是一种简约化的生活符号,它天然地反对一切多余的物象,删削掉了诸多繁文缛节。当然,足球仍是一种高度辩证性的文化实体,它是一种简约性与繁复性的复合体。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的幸福感越来越朝着淡化甚至隔绝攻击欲的方向发展,其所体现的是一种自省的价值,而足球在其中扮演着一种启导者的角色,而非绝对的主宰者。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曾说:“确实很显然,生殖利比多的作用导致个体盲目地为种类的利益而超越自己,俄狄浦斯危机的升华作用是人屈从文化的过程的根源。……事实上任何奉献性都无法从这里生成出利他心来。”[19]高强度的张力场域可以使人精神升华,而足球是一种人设的张力场。虽然精神升华未必是一种利他主义思想,却是一种失衡后的精神自我恢复的程序,足球的精神统摄价值在此得以展示。
4 结束语
狩猎文化对人类的影响力很大。它源于获取食物的方式,又延伸于现代社会,且对当下的社会学、生物学、艺术学、体育学皆有影响,并在当下商战体系下的场域觅得新的生机。在一种多元化的学术语境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精神属性都会得到舒张,人所共知的拼搏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性本然性的术语,其原点仍在于原始狩猎。其实,常态下的人往往执行的是一种获取战利品的策略,它却意外地给人类的智能进化提供了动力。然而,人类还有一种难以安放的原始意志,且可以存活在人类自身的身体游戏领域。无以否认,狩猎行为牢固地维系着人类和动物的刚性化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无法脱离动物而独立生存。人和动物的关系几乎决定了人类的进化方向,而狩猎仅仅是人与动物关系中的一种最为简约的链接点。其实,人类的狩猎行为只是一种由历史营造出来的求生行为,其在现代社会获得了一种更新换代的存在契机,它也因此而成为人类全方位探究人与动物关系的存在物。狩猎文化乃诸多猎食类生物的要务,猎食类生物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几乎为此付出了终生的努力。对人类而言,它也足以构建出一种围绕猎食类动物而兴起的复合性学科,而足球就是处理狩猎情境中诸多复杂关系的最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