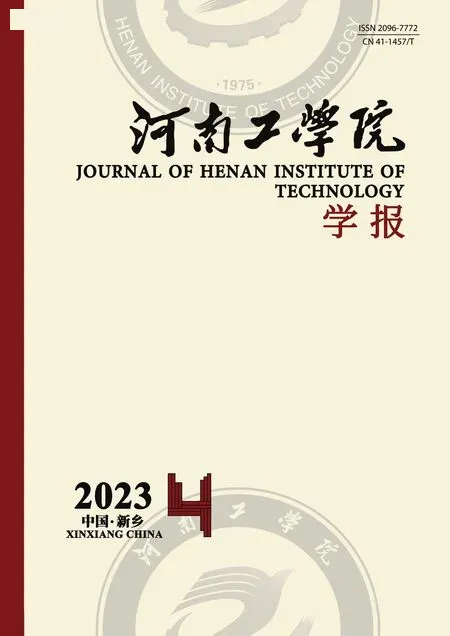论康德义务论中的善人观
2023-03-05郭鹏坤
郭鹏坤
(河南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0003)
康德认为莱布尼茨“发明”了“单子”说,在同样意义上,施尼温德(J. B. Schneewind)认为康德“发明”了“自律”这一深刻、难以理解的道德概念,“道德主要是与人们施加给自己的法有关,并且,在这样做时,他们也必然会给自己提供一种服从的动机。康德把以此方式在道德上实行自治(self-governance)的行为主体说成是自律的”[1]589。Autonomy(自主、自律)本意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由auto(self)和nomos(rule or law)两部分组成。一个城邦或国家的独立性在于拥有自治权、立法权,这个概念逐渐从政治语境延伸到作为个体的人身上从而成为伦理概念:道德上自我立法的自律者,即康德义务论中的善人。
1 人性禀赋和“非社会的社会性”
探究康德义务论中的善人观,有必要了解康德如何看待人性(human nature)和恶的根源以及善的可能性,以此为基础才能充分理解自律的伦理内涵。康德认为,从人的原初禀赋及其目的而言,人的本性有三个规定要素。第一,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具有动物性(animality)禀赋。所谓动物性禀赋就是人服从自然的、机械性的自爱,这不是理性指导下的自爱。它的目的包括自我保存、种族的繁衍以及与同类生活的自然性的社会本能。第二,人作为一种有生命且理性的存在者具有人性(humanity)禀赋。人性禀赋也是自爱性的,它是通过运用理性与他人进行比较以断定自身幸福与否,不过理性在这种禀赋中只是隶属于其他动机。第三,人作为一种有理性且同时能够负责任的存在者具有人格性(personality)禀赋。这一禀赋使人容易对道德法则产生敬重,具有将道德法则作为道德动机的素质。尽管人性禀赋和人格性禀赋都包含理性,但是二者体现的是不同的理性能力之运用,人格性禀赋的本质特点是,“无条件地、通过确认自己的准则为普遍立法这样的纯然表象来规定任性(1)“任性”的德语词为Willkür。国内学界对之译法众多,最常见的翻译有任性、任意、决断、决意、自由选择、自由抉择等。英文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一般翻译为free choice或choice。康德对Willkür和Wille两个意志概念有时混用,后来又做出区分。贝克(L. W. Beck)指出,在康德之前,这两个意志概念都有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康德在其批判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都曾使用过这两个概念,前者强调开启因果序列的自发性意志自由概念,后者强调立法的自律意志概念,这两种能力有一个同样的“意志”名称,就是自由意志,《实践理性批判》成为这两个意志概念的交汇点,在后期的著作中两个概念才被明确地区分开来,前者为任性/决断,后者为立法的意志。在做出区分之前,康德有时交替运用这两个概念,有时又在默认上述区分下运用这两个概念。在康德在世之时,他本人建议将Willkür翻译为arbitrium,以区别于voluntas。张荣教授在《“决断”还是“任意”(抑或其他)?》一文中指出,康德的Willkür概念同拉丁词arbitrium有很深的渊源,康德的这一概念的含义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关于自由意志的思考有内在关联。本文一般采用“决断”这一译法,决断更广义,自律毕竟也是决断(一贯的、必然的道德决断),决断是自发性的,但不排除是他律的。康德后来从狭义的意志概念出发指出Wille无所谓自由不自由,只有Willkür(决断)是自由的,为了尊重中文译者,在引用中文译本时保留译者的翻译。,而且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2]11。
从整体上看,康德认为人本性中的这三种禀赋都是善的,它们都不与道德法则相冲突,都促使人们遵循道德法则。但是动物性禀赋与人性禀赋和人格性禀赋有所不同,动物性禀赋与人性禀赋后天会嫁接各种恶。如同卢梭这一观点——人在自然状态下的自利和自爱都是善的,康德认为,人的动物性自爱和理性自爱在原初上也都是善的,恶并不是人本性固有的而是后天嫁接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追求自爱、自利,并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判断自己幸福与否,“即在其他人的看法中获得一种价值”[2]12,起初只是追求平等,担心他人对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继而发展出一种不正当的偏好,谋求对他人占据优势,并成为嫁接的恶。
自负、傲慢、恶意、忘恩负义等恶习都是文明人的特征,它们来自于人的社会化。只有在社会生活中个人才会有谋求对他人享有更大优势的偏好,康德称之为“非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ble sociality)[3]6,即人既有进入社会的倾向性,试图使自己社会化,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才会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人,才能使自己的禀赋得到发展;又表现为分裂社会的阻力,要求自己趋向于单独化,想要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摆布一切,在虚荣心,权力欲、贪婪的驱使下在同类之间挣得一席之地,也因此成为对方的阻力,虽相互排斥和竞争,但彼此又不能相互脱离。如果把“非社会的社会性”放在人类历史发展层面来看,康德认为它具有积极意义,人类以它为手段促进了个人的才智发展,从客观上为建立正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条件。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它是消极的。使人处于危险境地的并不是人的离群索居的粗野本性,而是来自与之有社会关系的人:
无须通过粗野本性的诱惑,那本来就应该如此称谓的激情在他心中就活跃起来了,这些激情在他的原初善的禀赋中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他的需求仅仅是很小的,他在为这些需求操心时的心态是有节制的和平静的。只有当他担心他人可能会认为他可怜,并且在这方面蔑视他时,他才很可怜(或者他自认可怜)。当他处在人们中间时,妒忌、统治欲、占有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怀有敌意的偏好,马上冲击着他那本来易于知足的本性……这就足以相互之间败坏道德禀赋,并且彼此使对方变恶了。[2]81
只要人处于社会关系中,“非社会的社会性”这种激情就无法根除,妒忌、统治欲、占有欲和与之相关的怀有对他人敌意的偏好就会冲击着人的原初为善的自然本性,就会导致人过度地看重自己,把自爱和归之于幸福名义下的自利看得比他人都重要,因而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总有趋恶的倾向而免不让了彼此陷入冲突之中。
虽然个人有不可根除的恶的倾向,但作为“类”,随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不断进步,人在道德上也是不断进步的。康德本人对这种前景抱以确信的态度(这是启蒙思想家的普遍观点):
人是这样一种东西,他虽然被恶毒败坏了,但毕竟是天赋有丰富的创造才能同时也有某种道德素质的理性生物,对于自私自利在他们之间所造成的灾难,他们随着文化的增进只会有越来越强烈的感受;而且,他们在自己面前看不到克服这灾难的任何别的手段,只除非他把(个别的)私人感觉哪怕是不情愿地服从对某种(公民社会的强制性)原则的(一切人协调的)共通感。而对这原则的服从又只是根据他们自己所订的法律,通过对这一点的意识,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高尚,感觉到自己属于一个适合于人的规定性的类,就像理性在理想中把这规定性显示给人的那样。[4]209
2 人何以成善
人以幸福的名义追求偏好和各种欲望对象并非恶。判断一个人为恶或为善要追溯其行为的准则,准则根源于决断(Willkür)。因为决断(或任性)并不为任何动机所规定,除非个人把某种行动动机纳入准则,换而言之,准则提供了人的行动理由,动机则提供了准则的质料(或者说内容),只有将动机“结合”到准则中,才会产生行动:
任性的自由具有一种极其独特的属性,它能够不为任何导致一种行动的动机所规定,除非人把这种动机采纳入自己的准则(使它成为自己愿意遵循的普遍规则);只有这样,一种动机,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动机,才能与任性的绝对自发性(即自由)共存。[2]7
一个人之所以是恶的,不在于动机的内容,而在于行动的准则,如果没有将道德法则作为至上原则限制个人准则,那么,为恶就不可能避免,“人是善的还是恶的,其区别必然不在于他纳入自己准则的动机的区别(不在于准则的这些质料),而在于主从关系(准则的形式),即他把二者中的哪一个作为另一个的条件”[2]22。一个人要成为纯粹善人,道德法则不仅是准则,而且“道德法则在理性判断中自身就是动机”[2]7。因此,康德的义务论立场是严峻的,要么意志被道德法则所规定,要么意志被其他动机的准则所规定,即:
假如法则并没有在一个与它有关行动中规定某人的任性,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与它相反的动机对此人的任性发生影响;而且由于这种情况在上述前提下只有通过此人把这一动机(因而也连同对道德法则的背离)纳入自己的准则(在这时他就是一个恶的人)才会发生。[2]7-8
这种严峻的义务论排除了中间立场。意志的脆弱、道德的不纯、本性的堕落这些主观条件都能导致恶的发生。自律意味着一个道德上的善人要做到遵守义务上的纯粹性。道德上的善人不同于其他意义上的善人。例如有人在坚守准则合乎道德法则方面是坚定的,在行为上完全能体现出道德性,但动机不一定纯粹,因此,就行为的经验特性可以称之为道德。对于这些人来说,需要坚守遵守义务的准则,改造行为方式,才能逐渐上升到道德的纯粹性。有人在遵守义务的准则方面是坚定的,但这种坚守是出于自爱目的,这种情况下,人只是“律法意义上的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需要通过转变心灵而成为一个“新人”。而对于那些在准则上败坏的人,则需要通过思维方式的转变,确立性格而成为一个接纳善的主体[2]32-33。康德指出,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从一种性格的确立开始”[2]33,与此同时,
个性(即性格——笔者注)的建立正如某种方式的新生一样,是他为自己立下某种誓言的庆典,它使这个正在发生内心转变的时刻有如一个新阶段一样使他不可忘怀。教育、示范和开导能够使对一般原则的这种坚定性和持久性显示出来,并非逐步地、而是爆发式地、仿佛在厌倦了本能的动摇状态之后突如其来地显示出来。[4]171
康德视性格为理性人的最低限度,又是个人内在价值或尊严的最高限度。具有性格意味着意志具有坚定的实践原则,这对最为普通的人都是可能的;拥有性格也意味着走向理性为自身独立地规定原则,这些原则可能有错误和缺陷,但是这本身就值得赞叹和珍视,因为恶人没有自己的性格、带着自相矛盾,为了自利不择手段,不讲原则。因此,道德修养并不是单纯地学习模范或榜样,而是从转化思维方式开始。逐步认识道德原则的至上性和义务的纯粹性,自律才是可能的。
3 人的成善途径
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指出,动物类的规定性即本性在个体中就得以体现,某类物种是什么,此物种的个体就显现出其规定性。而对于人来说,“人是什么”,只有通过人类整体世代的进步和持续的完善才显现人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只有在作为目的王国的自律个体那里才能体现出人的本性,人真正成为“人”是一个以整体形式不断上升的文明化和道德化进程。这个进程也就是人性中三种始源禀赋及其目的实现的进程,同样,也是恶的倾向被克服的进程。实现人的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就是推进人的“幸福”,克服恶的倾向就是充分发展和实现人的人格性禀赋。
推进人的幸福是利用“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一“恶”的手段来实现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对抗来唤醒人自身的力量,克服懒惰的倾向,在寻求统治欲、占有欲的追名逐利过程中发展自身的自然天赋,康德视之为“天意”的安排或自然的意图。通过这种手段,人的(外在)自由得以最大程度实现,这就迫使人们建立自由权利得以相互承认的宪政国家,并进而构建宪政国家的联合体——国际联盟。人类的这种文明化进程是实现人格性禀赋和道德化进程的必要条件(2)近些年一些学者从人类学角度、宗教哲学角度进一步阐发如何实现从经验角度的外在自由(自由决断)到内在自由(先验自由)的过渡。如劳登(R. Louden)认为,政治和法律的进步是深层道德进步的必要预设,文化和文明化是道德化所预设的准备步骤,法律、艺术、文化、宗教共同体等这些外在的进步为内在的道德进步的必要条件。尽管道德的进步是整个人类共同体的事情,但也并非与个人的道德身份不相关,道德性和道德进步也指向个体(Louden, Robert, Kant’s impure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弗莱尔森(Patrick Frierson)认为,劳登错把有益的经验当作必要条件,他转而从个体角度用如何实现道德意向的转变来说明个人如何从具有恶的倾向实现道德意向的思维转变。按照弗莱尔森的观点,个人在慎思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未来可能诱发恶的倾向的经验性影响以限制恶的倾向,从而排除善的阻力,而作为本体的意志具有与恶作斗争的意向,个人应该接受与出自本体意志品格一致的行为方式,考虑到促使个人行为与出自本体意志行为相一致的经验性因素。同时,弗莱尔森还从宗教哲学方面强调神恩对道德提升的重要影响(Frierson, Patrick, Freedom and Anthropology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劳登和弗莱尔森的观点是互为补充的,他们主要围绕康德的人类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等资源分别从社会和个体两个不同的路径阐述善人的可能性。。因此,康德也称普遍公民状态是人类一切原初禀赋得以发展的母腹。这就意味着,没有充分保护个体自由的政治共同体,理性的公共运用就会受到限制,从而阻碍道德的进步。可见,成就道德上的善人并不取决于单个人的努力,而是人与人共同联合起来成就的事业。单个道德的人并不足以对抗人作恶的倾向,反而会被它所吞噬,只有人联合起来,立志于进入一个立足于自由原则和合法强制原则的公民状态,才有可能逐渐过渡到理念上的伦理共同体——即目的王国。这样一来,道德进步首先依赖理性的社会机制,必须以外在自由和权利获得保障的政治共同体为起点,“在缺乏善良意志和只有法律动机出现的地方,借助法制手段,在公共的法律正义就可以部分地强化应该存在和应该发生的事情”[5]121,也就是说,首先通过法制强制手段规范外在行为,使合法的外在行为具有善的表象,这是人成为善人的必要条件。因此,“没有政治共同体作为基础,伦理共同体就根本不能为人们所实现”[2]82。没有伦理共同体,作为自律的道德上的善人也就没有可能性。这就是保障外在自由的权利原则和宪政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性。
康德说,“能与意志自律共存的行动,是允许的”[6]79,允许的行动除了自律行为之外,就是外在行为符合道德法则(并非出于道德法则),它的标准如下:“任何一个行动,如果它,或者按照其准则每一个人的任性的自由,都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就是正当的。”[7]28这个标准也是外在行为的权利原则,只要外在行为符合法则的要求而没有彼此冲突,个人行为就是正当的,一个人可以从其权利出发要求他人遵守法则,但不能要求他人把遵守法则作为行动的动机。权利原则必然对应权利义务(3)权利义务也称法权义务。“Recht”包括三层含义:法则/法律、权利、正义,康德运用该词时这三层含义都体现出来了,该词汉译为“法权”。英文通常翻译为“Right”,但它并没有完全体现该词全部含义,为了通俗易懂,本文采用“权利”一词。,“如此外在地行动,使你的任性的自由应用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7]28-29。权利义务是严格义务(康德也称之为狭义义务),它是能够进行外在立法以及伴随外在性的强制的义务概念。其实,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既包含权利义务,又包含德性义务。道德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尊重人的权利,不能伤害人的正当利益。权利原则是政治建构原则,一个政府或国家的合法性必须以保障和维护每个公民的权利为目的。权利原则规定正当行动的本质,也是检验行动是否正当的标准,因而权利原则必然对应着权利义务,遵从权利义务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尽管它并不要求出于义务行动。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对他人按照普遍法则的自由行动构成障碍,这也是不道德的。
只依赖于外在立法的义务行为其道德价值和义务范围是有限的。道德本质是自律性的,从内容而言,它既包含完善的义务,也包含不完善的义务;从动机而言,自律的动机是纯粹义务动机。一个人只是依据道德法则而行动,但在道德事务上没有自律,这并不非过失,只是意志软弱。只是保持行动与法则不冲突,做一个守法的人,并不具有功德;如果把守法的义务作为行动准则,这也就把权利义务转化为德性义务了。在康德那里,法和德行都包含在道德里面(4)德文Moral和 Sitten都是“道德”,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道德形而上学》用的就是Sitten。这两个词细微的区别是Moral比较抽象和广义,Sitten比较具体。这两个词的衍生词分别是Moralität(道德性)和Sittlichkeit(德性)。。道德的至上原则是抽象的自律原则,广义义务是具体的德性义务[8]69,95-96。德性义务是广义的义务,它体现了自律这一道德本质。德性义务和法权义务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于后者来说,一种外在的强制是道德上可能的,但前者仅仅依据自由的自我强制”[7]168。尊重人的权利有助于培养和发展自律,康德也称尊重人的权利是迈向道德进步的巨大步骤,道德离不开权利的支持,“政治对于道德的两重性支持分别是仁爱和尊重人的权利,仁爱如果没有权利作保障,将彻底沦为欺骗”[9]95,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为伦理共同体创造条件,“政治的目的就是要为道德创造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中,人们出于非道德的理由来遵守道德法则,而某些道德目的也会通过法律动机得到实现”[5]68。从政治共同体推进到伦理共同体,依赖人们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道德努力,目的王国这个理想就是自律个体的联合体。也只有在这个伦理共同体,人作为自律者实现了人的理性本性。
自律是一种内在自由状态,人通过驯服和驾驭自身的激情,从而实现自我控制而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因此自律是一种德性,“德性的真正力量就是平静中的心灵及其一种深思熟虑的和果断的决定,即实施德性的法则”[7]191。康德也称德性为道德的勇敢,履行广义义务有着值得称赞的功德。人这种有限的理性本性就决定了道德必须从基本的要求上升到更高的要求,从法权义务上升为广义义务。广义义务包含两类内容:第一类是自我的完善,发展自身自然禀赋和完善自身的道德禀赋,发展自然禀赋有助于个人幸福;完善自我的道德禀赋,培养行动准则趋于与道德法则一致的道德意向,在道德上完善的人才配享幸福。第二类是把他人的允许目的作为自己的目的,亦即把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至于这些人把什么当作他自己的幸福,由他们自己去做主和判断,人也有权拒绝他人所认为幸福的东西,至于人履行义务到何种程度由道德行动者自由决断。康德在论及这种义务时说到:
如果没有人会对他人的幸福有所助益,但也并不故意地对这种幸福加以剥夺,那么虽然人性还会能够存在;但如果每个人也尽其所能地努力促进他人的目的,那么前一种情况毕竟是消极地,而不是积极地,与作为自在目的本身的人性协调一致。因为作为自在目的的本身主体,其目的也必须尽可能地成为我的目的,不论哪个表象会对我发生怎样的结果。[6]66
关于这种具有仁爱维度的义务,奥尼尔(Onora O’Neill)给出了这样的支持理由,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但人是有限的,不仅理性有限,而且行动能力有限,并且行动能力还容易被削弱、损害,因此,人不可能自足自给。人作为互相之间彼此行为的接受者必须建立尊重或维持各自的行动能力,这不是消极地互相之间互为目的,而是积极地按照特定的规则来行动,互相尊重行动能力和支持这种行动能力,所有人的行动能力才能得到保障,这也会得到通过互相交往的非自足的、不完善的理性存在者的普遍赞同,目的王国就是由如此的成员构成的,在其中人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的接受者[10]178-179。其实,这个目的王国理念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伦理背景。尽管康德将自律看作自我立法,然而作为目的王国成员的人只是目的王国的成员,并非首脑,目的王国这个伦理共同体被康德称为“上帝的国度”或“不可见的教会”,作为这个伦理共同体的成员,人既是上帝的子民,又是臣民。这个理念上的伦理共同体的道德立法者是上帝而不是人,德性义务其实是上帝的“戒律”,如果不在理念上预设上帝作为道德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个伦理共同体在理念上是不可能的。对于政治共同体,如果在道德上没有将人们联合在一起的原则,会造成一种无序的伦理自然状态,即使每一个个别的人的意志是善的。在这种状态下,恶的倾向侵袭人心中的善的原则,败坏人的道德禀赋,“伦理自然状态也是对德性法则的一种公共的、相互的损害,是一种内在的无道德的状态”[2]85。尽管伦理共同体不能被强制,但人应该结束这种状态,这不是某个人的道德任务,而是人类整体道德理想和目标。目的王国必须有一个公共立法者,这个立法者的戒律是联合所有人的法则,因此必须在理念上设定上帝是这个伦理共同体的立法者,作为国王,上帝能看透人的心灵意念,以德福相配的方式保证至善的可能性。不过,这又会与善人的自律构成一定的张力,当代学术界对之有不同的诠释。
4 结语
对于康德道德哲学中人克服恶的倾向,最终实现善人的可能性,既需要个人的道德努力,更需要社会制度提供必要条件。并且,善人的自律和善人联合体的目的王国在康德那里又深深植根与西方的宗教文化。这导致康德道德哲学中道德哲学面临一定的问题。
其一,意志的自律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关于这个自律的道德主体是否真的具有道德上的立法身份,后来的诠释者有很大的争议,由此引发了当代学者对康德道德哲学的两种不同诠释——道德建构主义诠释和道德实在论诠释。建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是“六经注我”式的诠释,将康德罗尔斯化;实在论的代表伍德则是“我注六经”式的诠释,康德的立场只能被视为伍德的道德实在论视阈中的康德[11]32。建构主义者认为,自律是以某种方式选择了某类行为准则,这种选择方式使这类准则具有法则地位;与此相反,实在论者认为,自律并不是以某种方式选择道德法则,道德法则是客观实在的,这种客观性基于人作为自在目的的绝对价值属性。如果道德法则真是意志所立,那么它可能具有相对化的危险;如果道德法则具有客观实在性就排斥立法之说,这就是康德道德哲学所面临的“欧绪弗洛问题”(The Euthyphro Problem)(5)“欧绪弗洛问题”(The Euthyphro Problem)出自柏拉图的《欧绪弗洛》篇。在《欧绪弗洛》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向欧绪弗洛提出一个关于虔敬的难题:虔敬因为善而被神所钟爱,还是因为它被神所钟爱因而为善?如果问题的答案是前者,那么虔敬本身就具有客观价值,独立于神的意志;如果问题的答案是后者,那么虔敬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客观价值,它的价值依赖于神的意志。。
其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康德道德哲学中具有自律意志的善人是抽象的人,是剥离特定社会关系的人,因而善人自律的道德法则只具有空洞的形式。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501从唯物史观而言,经济关系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人“是什么”是在其所处时代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一切关系中塑造而成的。道德法则反映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它不是抽象、超然于经济关系的普遍先验观念。康德将其道德哲学中善人、及其自律的普遍适用性的道德法则和目的王国理念最后都隐含在西方宗教传统中,不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精神的哲学抽象表现和道德理想。
(责任编辑 陈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