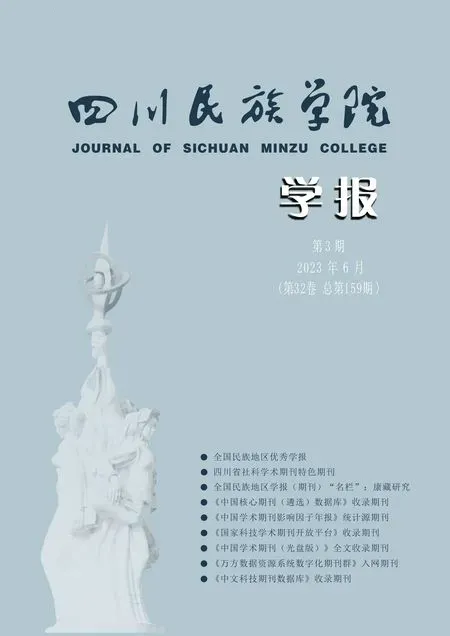名辩学与因明学中的逻辑比较
——以公孙龙《坚白论》《白马论》和因明学中的相关命题为中心
2023-03-04赛藏
赛 藏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中国古代的名辩逻辑、佛教因明学、西方逻辑学被称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它们既有人类逻辑思维共有的特性,也因各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从内容到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公孙龙是中国古代名辩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公孙龙著作丰富然多数散佚,现存《白马论》《坚白论》《指物论》《迹府》《通变论》《名实论》六篇为研究公孙龙思想的主要文本。公孙龙逻辑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但多数通过形式逻辑的相关理论对其著作进行梳理分析,未见到将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和因明学进行比较研究。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和藏传因明学虽分属不同的逻辑系统,但公孙龙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同藏传因明学的内容有契合之处,充分显示了人类逻辑思维的共性特点及中华文化内在的一致性。藏传因明学包含摄类学(Bsdus grwa)、心类学(Blo rigs)、因类学(Rtags rigs)三个部分。摄类学主要培养人的论辩思维和记忆能力,心类学立足于“现量” (Mngon sum),主要揭示人类认识产生的条件、过程、结果,而因类学基于“比量” (Rjes dpag)的内容,主要论因三相(Tshul gsum)的定义,有效的论证形式和错误论式的类型等内容。这些分支学科组成了因明学的整体要义,且为正式研习《集量论》和《释量论》等因明论典夯实了基础。本文主要将公孙龙《坚白论》《白马论》与藏传因明摄类学中的“红白品”和心类学有关“识”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
一、《坚白论》与“心类学”的比较
《坚白论》以主客两方一问一答的方式论辩了“坚白石”为相盈或相离的内容。主方(即公孙龙)主张“坚白石”相离,客方主张坚和白相盈于石。通过主客双方的问答不难发现,主客两方的论点相驳,是因为公孙龙所言之“坚白石”相离是在抽象的概念意义上的相离,而客方所持“坚白石”相盈的观点基于具体的实在物。公孙龙的“离坚白”主张虽与当时的主流思想相违而遭到抨击,但其著作所投射的丰富的逻辑内涵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
公孙龙在《坚白论》中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1]120从认识的层面而言,公孙龙指出视觉只能知道石头的颜色而不能感觉石头的坚性,所以见到白的时候不能见到石头的坚性,摸到石头的坚性时不能摸到石头的颜色,所以坚白石相互分离。公孙龙在《坚白石》中承认了感官职能的独立性,心类学中也强调感官在认识产生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心类学根据感官职能的不同,将人的认识分为眼识、鼻识、耳识、舌识、身识五类,分别代表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将认识依感官分类的目的在于显示感官对认识产生的决定性。心类学中认识产生需要具备三个内外条件,分别称作“所缘缘(Dmigs rkyen)”“不共增上缘(Bdag rkyen)”“等无间缘(De ma thag rkyen)”。“所缘缘”指所要认识的对象;“等无间缘”是认识产生的内在条件;“不共增上缘”是认识产生的物质载体即感官,也是各种认识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不共增上缘”拿视觉来说是“眼根”(Mig dbang)、听觉来说是“耳根”(Rna dbang)、嗅觉来说是“鼻根”(Sna dbang)、味觉来说是“舌根”(Lce dbang)、触觉来说是“身根”(Lus dbang)。眼、耳、鼻、舌、身对应色、声、香、味、触五类境。不依所缘境命名五识而以各识的不共增上缘来称谓,这恰恰反应了不共增上缘是区别五识的根本所在。心类学中对每一个根都有明确而详细的界定。《藏传因明学入门》中说:“眼根指处在能做非同一般的增上缘类中的内色清澈者,谓之眼根。其事相是,在眼根所依处,形成一个恰似胡麻花大小的透明色(体)。”[2]眼根只能显现认识对象的颜色和形状;同样,耳根上只显现各种声音,而不能显现颜色和触觉等,耳根识只是对各种声音的认识。
根敦珠的因明学著作《量理庄严论》中说:“缘于海螺色之眼识,对海螺触觉无量识,因不论从直接了知还是间接了知都不能缘其触觉(Dung gi kha dog’dzin pa’i mig shes chos can/ dung gi reg’jam po la tshad ma ma yin par thal/ de la dngos rtogs dang shugs rtogs tshad ma gang yang ma yin pa’i phyir/)。”[3]59-60意思是说,眼睛只能看见海螺的颜色,而不能了知海螺在触觉上的属性。这里指出了各感官职能的差异性和专有性,但没有得出类似于“坚白石”相分离的结论。金岳霖先生在《形式逻辑》中对公孙龙的“坚白论”做了这样的评价:“他的关于名与实的关系的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关于共相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论之上的。他认为共相是一种独立存在。他的‘坚白论’就是企图论证一块白石头的白色和坚硬性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4]344
公孙龙承认:“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一二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1]122从名实关系的角度看,此处,公孙龙强调了名“坚”和名“白”之间的差异性;从认识的层面讲,公孙龙指明了同一感官只能认识其对象的特定属性而不能同时兼识其他特点。所以,只有坚石和白石,没有“坚白石”。 但是,公孙龙在此立足同一认识对象而强调不同的感觉不能同时生起,没有涉猎诸感官集中认识各自认识对象时的先后次序和状态,也未涉及是否存在统摄坚和白的意识的存在。在实际较复杂的认识活动中,各种感官认识同时产生与否是直接经验无法快速辨别的,这也是古印度其他派别和佛教长期辩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公孙龙在《坚白论》中明确指出了感官功能具有差异性和局限性,但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加以系统地分析和归纳,也没有进一步探讨以根识作为对象的识的类别的存在问题。因明学对外在客观实物如何显现于感官,通过显现于感官的客观事物的表象而产生知觉,并最后做出分别和判断的过程有详细说明。
《坚白论》中说:“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1]124对此,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解释说:“坚、白二者作为共相,是不定所坚的坚,不定所白的白。坚、白作为共相表现在一切坚物、一切白物之中。”[6]108此处公孙龙承认了事物具有个性和共性的属性。对于如何认识“白”,公孙龙在《坚白论》中说:“且犹白以目(见),(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1]126公孙龙不仅指明了认识产生的内外条件,还表明了知觉与抽象思维的区别。有些学者将其解释为“他所说的‘神见’就是指人要用具有能动反映外部世界之功能的大脑去对从实践中所取得的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以便取得对外部世界的正确认识。这实际上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思想之雏形”[7],将“神”理解为抽象的思维活动。故此,公孙龙承认,认识有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不能认识事物的一般性,只有抽象的思维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此观点与因明学中的“分别识”和“无分别识”的概念相似。因明学认为,“现量”属于“无分别识”,“比量”属于“分别识” ;现量相当于认识的初级阶段,没有形成概念和判断,对认识对象只有知觉上的认识,比量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已形成概念和判断。克珠杰在《因明七论除意暗庄严疏》中说:“声、瓶等具有个相和共相两面,缘自之现量只显现个相,不显现共相。缘自之分别识上只显现共相,不能显现个相(Sgra bum sogs don rnams la yang rang gi thun mong ma yin pa’i rang bzhin dang/ thun mong gi rang bzhin gnyis gnyis yod la/ rang’dzin mngon sum la ni rang gi thun mong ma yin pa’i rnams pa’char gyi/ thun mong gi rnam pa’char mi srid la/ rang’dzin rtog pa la ni rang gi thun mong gi rnam pa’char gyi/ thun mong ma yin pa’i rnam pa’char mi srid/)。”[8]这里明确指出了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个性,只有理性和抽象的思维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共性。
公孙龙在《坚白论》的结尾处指出“力与智果,不若,因是”[1]126。意思是说,知觉和抽象的思维认识相比较,重要的是思维的认识。在因明学中,肯定现量对比量的作用,承认一切抽象思维归根结底基于现量的认识,没有现量的认识,抽象的比量认识无从谈起。法称在《正理滴论》中说:“正确知识有二,即现量和比量(Yang dag pa’i shes pa ni rnam pa gnyis te/ mngon sum dang rjes su dpag pa’o/)。”[9]所以,在因明学中现量和比量都是正确认识,对两者孰轻孰重没有作太多比较,只是指明了在认识客观事物、辨明是非曲直时二者的作用缺一不可。 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是战国名实散乱时期的产物,其内容有极强的社会性。分析公孙龙《坚白论》文末的“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1]126,可管窥公孙龙写《坚白论》的意图和目的,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古代逻辑与因明学的差异。
二、公孙龙《白马论》与“摄类学”的比较
《白马论》是公孙龙诸著作中较有争议的一篇,许多人借公孙龙“白马非马”的主张对其冠以“诡辩论者”的称号。然而随着对公孙龙逻辑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对公孙龙“白马非马”的曲解逐渐变小。“白马非马”是《白马论》全篇的核心内容,“白马非马”单从字面理解有违常识,通过《白马论》中主方的解释,可知“白马非马”是言之有理、合乎逻辑的。
《白马论》中主方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不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1]103这里说如果要一匹马,黄马和黑马皆可,但如果要一匹白马,则黄马和黑马不符合。此处公孙龙所言“白马非马”之“马”为抽象的马的属概念,而“白马”指马的种概念,所以“白马”和“马”是概念相异的两个词项。“白马”寓于“马”,但“白马”不包括所有马类,所以称“白马非马”,也可以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反对“马”的概念和“白马”的概念的外延关系为同一关系。金岳霖先生在《形式逻辑》中说:“从现代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白马’和‘马’作为两个类确乎不是同一的。因为白马类包含在马类之中,而马类却不包含在白马之中。在这一种意义上说白马类与马类不是同一的,这是正确的。”[4]346所以,公孙龙从外延关系的层面论证“白马非马”的命题是合理的,可窥知不同概念所指称对象的差异及区别种属概念的重要性,体现了概念对人的行为的指导意义。
公孙龙在《白马论》中说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1]102又说:“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1]105可知,公孙龙主张的“马”是从形态方面指称其内涵,而“白”是从颜色上确定其内涵。故“白马”是“白”概念和“马”概念的结合,所以“白马”是区别于单从形态方面指认的“马”的概念。公孙龙继续论证说:“以有马为异于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1]105此处公孙龙从“马非白马”的前提,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
公孙龙在《白马论》中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非马也。故曰:白马非马。”[1]105对此,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这一点似乎强调,‘马’这个共相与‘白马’这个共相的不同。马的共相,是一切马的本质属性。它不包含颜色,仅只是‘马作为马’。这样的‘马’的共性与‘白马’的共性不同。也就是说,马作为马与白马作为白马不同。所以白马非马。”[6]106此处,公孙龙首先区别“白马”和“马”,而后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 另外,公孙龙从颜色方面强调了有颜色的“白马”与没有颜色的“马”是不同的,从而得出“白马非马”。
根敦珠的《量理庄严》中说:“若云,持海螺为黄色的眼识对海螺的颜色是错乱识,但对海螺的形状是无欺智。以上的有法,对海螺的形状不是无欺智,因为对此既非直接了知亦非间接了知,若言第一因不成,于彼显现白海螺之白色和海螺的颜色是成住质一 ……(Kha cig na re/ dung ser ’dzin gyi dbang shes de dung gi kha dog la ’khrul yang dbyibs la ma ’khrul ba’i tshad ma yin no zhe na/_de chos can/ dung gi dbyibs la tshad ma ma yin par thal/ de la dngos rtogs tshad ma yang ma yin/ shugs rtogs tshad ma yang ma yin pa’i phyir/ rtags dang po ma grub na/ khyod la dung dkar bo snang bar thal/ dung gi dkar bo dang dung gi dbyibs gnyis grub bde rdzas gcig yin)。”[3]51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眼识而言,“白海螺”是“形”和“色”的同一,是形、色不可分离的具象。由于眼疾等原因见白海螺颜色为黄色的眼识,对于白海螺的形和色都是错乱识,因为具体事物白海螺的“白”和“形”是不可能被眼识分别认识。所以,缘海螺为黄色的眼识对“海螺”的“色”和“形”都是错乱识,因为“海螺”的“形”和“色”同生、同存、同灭,不能把“形”和“色”割裂开来认识。此处,藏传因明学从侧面论证了“白马”是形和色的同一,且形、色不能割裂开来认识。在因明学中眼识所能认识的是具体事物的“形”和“色”。所以,根敦珠承认了眼识只能认识具体事物“形”和“色”结合的方面,侧面承认了“白马”是形和色同一,认为在“白马”这一实体上,不能分别指出“白”是哪个、“马”是哪个。 由此可看出公孙龙的主张和藏传因明学的根本区别。从公孙龙论证“白马非马”的几个步骤中不难发现,公孙龙强调的是内涵和外延相异的“名”之间的区别,而忽视了一般的“名”与个别的“实”之间的联系。
藏传因明摄类学中没有直接出现“白马非马”命题的原因是:第一,摄类学中有专门的章节探讨种属概念的区别,所以,不必纠结“马”概念和“白马”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差异;第二,摄类学中有专门的术语可暗示两个词项之间在外延上的差异,如“Rta rta dkar po yin pa’i ma khyab/(马不定是白马)”这句话中的“Ma khyab (不定)”已显示出了两个词项外延上的大小;第三,藏文中,“白马非马”容易引起歧义。
在藏传摄类学第一品“红、白品”中,出现“白马是白马,但白马非白”的主张,摄类学“白马是白马”的命题强调了主项和谓项的同一关系,而公孙龙“白马非马”的主张强调了主、谓项外延和内涵的差异,但不否认主项和谓项的种属关系。《摄类学》中说:“白马是任一根本四色,白色故,若不成,言白马是白色,汝为白马故,不定,白马非白,非颜色故(Rta dkar po chos can/ rtsa b’i kha dog bzhi po gang rung yin par thal/ dkar po yin pa’i phyir/ ma grub na/ rta dkar po chos can/ dkar po yin par thal/ khyod rta dkar po yin pa’i phyir zer na/ ma khyab/ rtsa bar’dod na/ rta dkar po chos can/ dkar po ma yin par thal/ kha dog ma yin pa’i phyir/)。”[10]按照字面理解“白马非白”是令人费解的,但此处的“白马”是具有白颜色的马,“白”指称抽象和共相的白的概念,所以“白马非白”不是说白马不是白颜色的,而是指白马不属于白色的范畴。公孙龙在《白马论》中向客方解释“白马”和“马”两种概念的内涵时说:“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1]107公孙龙明确承认白马是被白颜色限定了的马,被白色限定了的白马不是白色,承许了“白马非白”的命题。公孙龙和藏传摄类学共同承许这样的命题的原因是:第一,“白马非白”的命题符合常识;第二,“白马”和“白”不仅内涵不一致,且“白马”和“白”之间不构成种属关系。所以,“白马非白”的命题两者都易于达成共识。
公孙龙《白马论》通篇虽未明确指明其“正名实而化天下”的意图,但通过《白马论》中强调的不同概念所指称的内涵和外延的差异可知其暗含“正名”的思想。
三、结语
在因明学中,“现量”和“比量”被称为正确认识,现量是对认识对象的感性认识,比量是通过“因三相”所规定的程式获得对认识对象的理性认识。公孙龙的《白马论》和《坚白论》强调认识对象及其名称之间内涵和外延的一致性,对不同层次的认识的界定、认识对象的分类及其标准是含糊的。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现实性和实践性的风格。因明学对于知识论和逻辑本身的探究细致入微,然而缺乏将系统的理论用于实际生活。故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两种逻辑体系各有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如何避免使其成为一种绝学,如何充分发掘因明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析的一大问题。笔者认为,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所具有的鲜明的社会意义,对于富有思辨性的藏传因明学从经院趋向社会化和大众化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有助于因明学在新形势下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通过名辩逻辑和因明逻辑部分内容的比较研究,一方面体现了汉藏文化在逻辑层面的相似性,从而管窥中华文化内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中华文化的羽翼之下共存的名辩和因明两个逻辑体系能够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为甄别完善中华文化的逻辑内容发挥重要的价值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