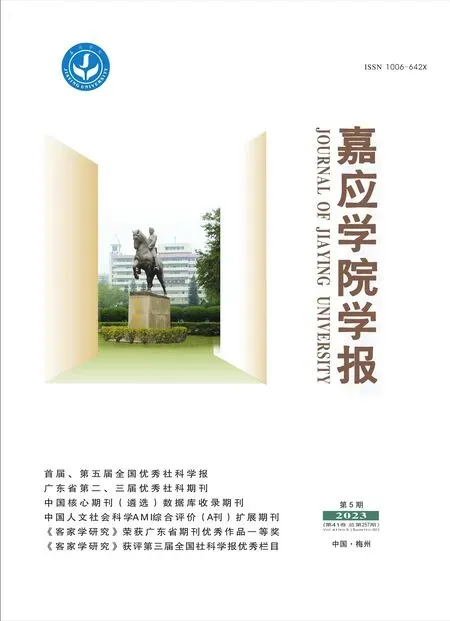谢清高与《海录》蕴涵的梅州历史
2023-02-20魏明枢
魏明枢
(嘉应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谢清高生于乾隆朝,口述《海录》在嘉庆朝,名闻于道光朝。他不是海外移民,但他率先走出国门,周游世界,最后定居澳门,还留下了深刻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海录》。《海录》面世以来便受到了政学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且一再重版、校订。谢清高及其《海录》蕴含着当时梅州与中国和世界之历史关联,具有特定时代的客家属性。
一、充满艰辛的人生奇缘
谢清高大约出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的嘉应州金盘堡(今梅州市梅县丙村,而非今城东一带金盘桥),他在大山里的“底层”社会成长,却在大海的波涛中成就其“高层”影响,其简短而艰辛的一生充满了奇缘、奇遇。
(一)海上奇缘
著名学者冯承钧勾勒谢清高生平事迹:乾隆四十七年(1782)开始航海,乾隆六十年(1795)结束航海,嘉庆元年(1796)目盲,道光元年(1821)去世,享年57 岁。新研究则认定:1787 年,谢清高定居澳门,在海外游历了4 年而非14 年,1793年之后双目失明,在澳门以经商自活,而非做翻译;至1821 年去世,在澳居住了34 年,而非26 年。[1]37
谢清高可被视为一位“不成功”的“从事民间海外贸易的普通客家商人”,也可视作一名海外移民。他年纪不大便无奈出洋(其目的地应当是“过番”而非论者所谓的“海南岛”,史料说是“出海南”,并非海南岛,可理解为海之南,即南洋可能更加合适),却又在大海上遇风暴船覆,为葡萄牙人救起,然后在其船上做帮手而随船游历世界各国。即如安京所说:“谢清高的一生是十分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但谢清高的一生又是十分独特的,富有传奇色彩。”[2]50
梅州贫民出洋谋生本就已经有点出格了,却又成为东来的西方人的海员,周游世界就更不易了,论者甚至称其为“中国海商”。晚年,他定居澳门,还与葡萄牙人打官司,甚至在澳门以“通译”谋生[1]7。谢清高的人生确实有点复杂,也有点不可思议。
至此为止,谢清高的一生也只能说是一段奇缘而已。可这奇缘却有着内在的时代内涵:其出洋谋生意味着当时程乡与南洋关联紧密;为西方人船只所救则又有着大航海与西人东来的时代背景。他还很细心,以其惊人的记忆及语言能力,记录了海外经历和沿途见闻,形成了记载海外见闻的《海录》。
(二)心有世界
《海录》所记录之人和事是如此之多而且新奇。据推断,谢清高航海时作了航海简志,从而成为记录者的底本:
一个比较合理的推定就是谢清高原本有一个日记或笔记本类的底本,底本的名称即《海录》。谢清高口授的内容是对这个底本的补充、说明。否则我们很难想象,谢清高能仅凭脑子就记住近百个国名、地名(这仅限于总目中的,不包括每一国中的区划名或地名)、方位、航程、风俗、特产,甚至外国译名。杨炳南在澳门看到了谢清高的底本,而吴兰修是在家乡看到了谢清高的底本。[3]4
谢清高之族弟谢云龙重刻《海录》时强调:“族兄清高,奇男子也。读书不成,弃而浮海。”[3]332当代校释者则猜测说:“谢清高幼年应读过一点书,识—些字,这使他能够有见识,有兴趣,有能力记述海外见闻。”[3]绪论1亦有说:“谢清高的航海时期应在乾隆四十七(1782)至乾隆六十年(l795)之间,至《海录》中所记乾隆以后之事,盖得诸传闻。”[4]102
乾隆末年至嘉庆十三年(1808)间,谢清高卷进了一场与定居澳门葡人的借款纠纷与官司。论者据此官司纠纷档案认为,于31 岁时,即乾隆六十年(1795),谢清高双目失明,不能再出海,在澳门似乎颇有名气,被称为“盲清”。而且自1782 年获救后:
他并非十余年中一直在海外漂泊,而是自初次,或最初二、三次出海归来后,便开始在澳门租居葡人房屋。在他漂洋过海的十余年间,一直支付着租银,每当出海归来,便居住于桔仔围。[5]160-161
或者说,谢清高根本不识字。《海录》记录者杨炳南说:“余乡有谢清高者,少敏异……所至辄习其言语,记其岛屿……流寓澳门,为通译以自给。”[3]329强调“少敏异”却未说其读书之事,其中之“习”“记”“通译”等字眼则明确其是读书识字者。地理学家李兆洛则明确说:“清高不知书。同乎古者,不能征也;异乎古者,不能辨也。”[6]以史料征引而认定“不知书”,其要求显然有点高。冯承钧校注《海录》亦谓:
清高一贾人耳,必不识文字。特往来海上十有四年,耳闻目见者广,故其所言虽可据,亦不尽可据。书中译名多从嘉应音读,自未可以正音绳之。[3]336
当代学者依然猜测,《海录》所记的很多地方及人和事,都是道听途说。比如,论者认为:“谢清高并未到过西婆罗洲,他的记录或许还是来自海客水手们的口耳相传。”[7]
事实上,谢清高与澳葡西洋理事官唩嚟哆打交道时要外请通事,且不能书写葡文状纸,不能单独处理此次与葡商的债务纠纷,可见其葡语程度并不高,所谓“以通译自给”[3]329和“为人通译”[3]332,当指他有时沟通华葡两族的民间交往。[5]165他贷出毕生积蓄却本利无收,甚至无力支付请人书写葡文状纸所需的十枚银元,“不复能操舟,业贾自活”,只能租居葡商“桔仔围”铺屋用以“摆卖杂货生理”为生。[5]158
(三)口述传奇
《海录》无论是心记还是手写,谢清高作为其口述者则是非常明确的。贫民过番、西船水手、口述《海录》,三者的结合显得如此巧合而充满缘分,梅州、海南、澳门与世界在此交集,所有这些无不内涵着强烈的时代特色:命运使他成为清代最早放眼世界、介绍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这是谢清高始料不及的。[2]50
学识和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谢清高,阴差阳错地青史留名,本来只是一名“好奇的旅游者”[1]39、“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8]40,“却因为偶然的机遇,走遍世界,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8]40被后世誉为“周游世界的第一位中国海员”[9]、“清代最早放眼看世界的人之一”[1]39。“谢清高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又是中西交通史和中葡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名垂不朽的人物。”[3]3论者强调说:“谢清高走向世界,实属偶然。”[10]4《海录》似乎也是杨炳南或吴兰修之偶遇记录。“失明水手讲述看世界的传奇故事”,其路径并非完全无章可循,回到历史的现场,或许还是可以寻找许多的回答。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其传奇还将不断地被翻阅和警示。
二、士商合作写传奇
《海录》自然不能简单视为谢清高的著述,而是谢清高及其同乡杨炳南或吴兰修之共同著述,他只是口述者,另外还有记录者,记录者有其加工和整理的过程。谢清高可被视作水手、海员,甚或是商人;杨炳南和吴兰修则是典型的读书人,所谓“士”。《海录》可谓是士人与水手的合著。
(一)士人参与
《海录》的记录者是谁?这已经有许多的争论。饶宗颐[11]、冯承钧及当代学者周桓[4]102和安京[1]等人都作过很深入的探索。杨炳南、吴兰修、李兆洛都被加入到记录者的争论行列。李兆洛(1769—1841),字申普,江苏阳湖人,嘉庆二十五年(1520),“游广州识吴广文石华,言其乡有谢清高者……”[1]38但其并未留存《海录》文本。
《海录》之后世流行本,“杨炳南编著本为最早的刊本。刊行时间大约在1820 年或稍晚,是清代刊本中的全本,其余刊本大多对杨炳南编著本进行了删节、改写、改编。”[3]绪论10而且,“原书虽不分卷,但颇具条理,……此书所记以谢清高耳闻目见者居多,故为十八世纪后期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书。”[4]102
吴兰修与杨炳南事迹均载于《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当然,吴兰修名气要比杨炳南更大更早,还载于其他几种传记中。嘉庆二十五年(1820),杨炳南到澳门“遇谢清高以及笔受《海录》时,他还不过是诸生之一”。[4]102
安京等学者们关于《海录》版本的见解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但显然都只是建立于“推断”,便必然难于成为最后定论。故亦有论者论证认为:
安京的推断,忽略了杨炳南、吴兰修等客家籍人士的交往关系和时代背景,特别是时空观念和事件发生时身份的差异。正是这些背景决定了吴兰修送呈李兆洛修订的稿本正是辗转经手的杨炳南笔录稿本的可能性最大。
一是《海录》并不存在两个记录人,李兆洛看到的吴兰修所送书稿实际上与杨炳南整理本同源。二是林则徐所云《海录》出版的时间1820 年也不太可能,实际出版时间当延后数年。①刘奕宏《世界地理著作〈海录〉:有两个记录人杨炳南与吴兰修?不可能!》,来自“谈梅客”公众号,2023-04-05。
无论其撰写过程如何,亦无论其记录者是杨炳南还是吴兰修,他们都是谢清高的同乡,他们既有感于其海上奇遇,亦同情其坎坷境遇,“都是举人出身,在政治上或学术上都有相当成就,记录、刊刻谢清高的海外见闻并没有功利主义的目的”,[1]38其举人身份及著作都能够展示其学界地位。《海录》是高水平的梅州士人参与的成果,这是确定无疑的。
(二)源于实践
士人参与,乃社会文明得以文字相传的根本条件,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文明的初始形态值得高度重视。《海录》之成书,乃源自梅州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的社会实践。每个人的生活及其生产实践皆属于历史范畴,是否被历史所认知则要看其是否身处历史长河之主流。
世界历史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杰出历史人物都是先进阶级的代表,其活动亦是走在时代之前列,其目光更是能够超前于时代。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人总是特殊个体,其所参与或创造之社会实践,能够与时代发生共振,然后会成为历史人物。历史发展有其共同的天时,有其特殊的地利,其关键则在于人和。所谓人和,既内蕴着个人进取的努力,更有其所处社会和时代之价值导向。
谢清高是位身处于历史长河主流中的梅州普通民众。梅州社会的特殊性让其走出大山而走向大海,其活动与社会关系从而契合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方向。他虽非熟练掌握葡萄牙语,但侨寓澳门,年轻而游历各国,亦能用心于语言及其环境,与东来欧洲人特别是葡萄牙人有较多往来,便具备了必要的语言和文化能力。故论者强调:
他懂葡语,与居澳葡人往来密切……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难有人对西方的了解出于其右,这正是《海录》一书的价值所在。[5]165
《海录》乃由谢清高口述,由杨炳南“加工、整理、补充”,乃其二人“合作完成”,实质上便是初级实践者与梅州士人之合璧。而“认识这一点,对研究(海录)是十分重要的”。[3]绪论1杨炳南“序”说:
与倾谈西南洋事甚悉。向来志外国者,得之传闻,证于谢君所见,或合或不合。盖海外荒远,无可征验,而复佐以文人藻缋,宜其华而尟实矣。谢君言甚朴拙,属余录之,以为平生阅历得藉以传,死且不朽。余感其意,遂条记之,名曰《海录》。所述国名,悉操西洋土音,或有音无字,止取近似者名之,不复强附载籍,以失其真云。[3]329
作为初级或不得志的士人,罗芳伯走向世界,成为海外移民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员,其影响非同凡响。谢清高则长期生活于澳门,生活于社会底层,其文化水平显然不高,虽强烈期望“以为平生阅历得藉以传,死且不朽”,却只能等待他人“录之”。同乡士人之帮忙传世,其人生之愿景得以圆满。
(三)梅州出产
杨炳南弥补了普通民众(谢清高)的知识不足,有意识地将民众的生产实践加以总结与提升,海员的眼界沉淀在士人的笔下,海员和士人同样展示出对海外世界的浓厚兴趣,这就有点巧,却又是那么具有必然性。论者强调:
此处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研究的题目,即谢清高的《海录》在多大程度上是作为海员的他个人的东西,作为笔受者,杨炳南的文化积淀对这本小册子到底有多少影响呢?[12]69
《海录》不能简单地被视作历经磨难而终生艰辛的普通民众的著作,还展示了梅州士人的那种时代敏感,他们都来自嘉应州,是那个时代梅州的共同代表。《海录》是乾嘉间梅州人走出围龙而走向中国和世界的重要体现,展现了近代梅州的世界眼光和胸襟视野。这部私人游记很快被士人认可,很快又被中国最高层所接受和夸赞,为政学两界迅速接受,可谓为时代所认可而青史留名,蕴涵着深刻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
《海录》成为梅州客家对于中国的独特贡献。作为一个实至名归的侨领,罗芳伯以其重大的功绩撰写了华侨海外经商和创业史;作为一个生活艰难的小商人,谢清高则将其苦难经历转化为适应时代的世界眼光,进而闪耀历史舞台,以其独特方式深刻影响海禁大开后的晚清中国历史。
谢清高与其《海录》看似仅是一个个案,其中所反映的却是梅州客家人移民海外经商的历史和文化,反映了客家人重视文教,又重视海外经商谋生的社会风尚,这是梅州侨乡社会正在形成的历史现象与实在。
三、超越国界的全球视野
《海录》成书之后即备受称誉,被多次刊刻、辑录、改写、注释,突出显示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海录》的成就首先在于其作为游记及其地理性视角,开阔了时人的世界视野。
(一)不仅仅是游记
2016 年,《海录》被当作中国经典游记重新出版,列入“世界著名游记丛书第2 辑”,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谢清高当年就是以旅游者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并无特别的政治目的。他看到了英、法、荷、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的殖民地及其对殖民地的统治情况,虽然从军营外亦知道这里有殖民军队,但整本书所记主要是各地的民情风俗、物产和一些特别的印象,所记皆为商品和民生。因此,《海录》被认定是东方的《马可波罗游记》。
《海录》虽不是第一部近代欧洲游记,却是产生实际影响的第一部近代游记。论《海录》者常不忘其开启近代中国人看世界的历史影响及其地位。事实上,在开启中国人与欧洲以及世界近代历史的开放和交流史的意义上看,其历史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从杨炳南、吴石华等同乡认识到其重要性开始,然后由林则徐开启其国家和民族层次上的重要性认识,到后世学者们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史的视角和视野去评述,一脉相承,层层递进。
旅游首先是需要有条件去旅游,打开旅游的模式。谢清高出生于嘉应州的大山里,这里的梅江连接着南海,但他却是生活在珠三角的澳门,他却是出海去做生意,后来更是作为水手驾船去周游世界,去帮助西欧商人做海外贸易生意,这当然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偶然的事情,从大山中要知道海外世界,然后才有可能走向世界。
游记本身往往是个人亲身经历,所见所闻都是个人观感。旅游之后必然会有印象和看法,但能够形成怎样的印象,比如说,印象的深与浅,所关注的对象是否具有时代内涵,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精神和文化上的能力,形成游记就更不是件容易的事。
《海录》不仅是谢清高个人的撰录,他虽然能够在澳门做点翻译工作,其文化基础和外语水平其实并不高。《海录》记录者杨炳南和吴石华等,皆其老乡,又能够认识到其重要意义,两者的“偶然”结合,却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一群人共同关注的结果。下层民众因其日常生活和一日三餐,自然而然地介入历史发展中,高层人物的关注则往往是历史现象已经开始凸显,记录则加强了认识,让现象更加清晰。
(二)世界地理著作
谢清高是鸦片战争前“走得最远、最广又留下著作的第一人”,甚至被誉为在林则徐之前“开眼看世界”者。[10]4《海录》记述了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是“我国近世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最早著作”[13],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最早讲述西方世界的一部著作”[14]内容简介。康熙年间,樊守义(1682—1735)游西方12 年,撰写了《身见录》,但直到1937 年才被发现。中国当时主要面对俄罗斯和蒙古这些陆地边疆,《身见录》所记录之欧洲,显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关注。事实上,康熙有传教士们当顾问而别具世界知识,也没有闭关锁国,台湾之海洋地位和世界性影响却要经过启迪才受到充分的重视。
《海录》记述了一名贫民亲身经历及其所观察的海外世界,可谓海外游记、地理著作、商贸考察报告,等等。《海录》之价值则从其记录开始,不仅口述者自己,记录者及其相关的士人都已经高度重视之,都已经感受到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意识地适应和顺应时代发展。吕调阳在《海录》序言中认为:“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大西洋,自谢清高始。”也就是说,谢清高是最早关注欧美各国的中国人,《海录》则是中国最早记录欧美各国的著作。《海录》深刻影响了以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畲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由此体现其于世界地理知识的初始记录意义。
乾隆中后期,大航海而来的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亚太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必须直接面对的最大威胁。虎门硝烟和鸦片战争则成为激活《海录》的外在力量,使其受到林则徐、道光帝等高层政治人物的瞩目。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奏稿推介说:“《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在粤刊行,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15]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徐继畲著《瀛环志略》,皆以《海录》为重要资料,《瀛环志略》等近代名著皆大量引用《海录》。论者认为:《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都参考过《海录》,《海国图志》“几乎将《海录》内容全部囊括其中,并加以注释……《海录》主要是通过《海国图志》等书的流传产生影响的。”[16]117
《海录》成书后,直到道光壬寅年(1842)才刊刻,同治庚午年(1870)和光绪辛巳年(1881)重版,其时代性的实用价值被不断激发。现当代学者则给予注释和解读,且多次出版,其历史研究和学术经典的地位受到了高度肯定。
四、超越时代的历史经典
当代人甚至称誉说,“文化水平不高”的谢清高,“为近代中国留下一本绝世奇书”。[14]内容简介之所以“奇”,在于简单的仅二万多字的《海录》竟然成为历史经典。
(一)引导时代眼光
从根本上看,《海录》只是一部简介个人见闻的私人游记,其内容则包含了大量工业文明的知识。谢清高亲身深入近代欧洲,以新鲜事物而介绍了源生于欧洲的工业文明,实际上成为最早传播欧洲工业文明信息的中国人。
《海录》介绍了葡萄牙、英国、瑞典及美国等国家的地理和民风民俗,甚至还介绍其国家民性文化和政治制度,这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国人的地理视野,而且扩展了国人的时代文明理念。最早通过亲身经历把美国介绍给国人应是谢清高,[12]46他介绍美国(咩喱干国)及其轮船:
疆域稍狭,原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外俱用轮轴,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自行驶,其制巧妙,莫可得窥。小西洋诸国,亦多效之矣。自小西洋至竿里干,统谓之大西洋,多尚奇技淫巧,以海舶贸易为生。自王至于庶人,无二妻者。山多奇禽怪兽,莫知其名。[3]264
美国及大西洋两岸“多尚奇技淫巧”,又因其“以海舶贸易为生”,蒸汽轮船也成为“奇技淫巧”,这几乎成为中国人认识西方世界的一种固定眼光。《海录》描述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
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达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17]
《海录》描述先进的伦敦自来水供水系统:
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须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3]250
《海录》已经接触了西方近代法律,引介了一批近代法律新词,[16]116成为20 世纪从日本大量引入现代法学词汇之最初源头。
《海录》是一名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对近代欧美社会的最初感受,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同时受时代的严重局限,其褒贬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痕迹,[12]69常以夏释夷,不认同西方风俗,亦难免误解,比如美国成为“原英吉利所分封”。所有这些都使后人颇感遗憾,或者纠正之[18],或者感叹之[19]。然而,谢清高却已经明确感受到了,源于西欧的工业文明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世界。
(二)语言译介成就
走出梅州,越过大海,来到陌生的国度里,感受异国情调,自然还是先听其语言。罗芳伯便在其诗中渗入了音译的婆罗洲词语,已经能够较好地使用外国语言入诗。罗芳伯《游金山赋》说:
至于名物称呼各异,唐番应答攸殊。沙寮依然茅屋,巴历原是金湖。……由郎荡漾于怀中,乍分还合;刮子婆娑于水底,欲去仍留。
“沙寮”就是茅屋;“巴历”就是金湖;“由郎”则是旋转之以甩出沙子而留下金粒的淘金用具,马来语dulang。这些西婆罗洲词汇和文化显得如此趣味。
走出国门,回来介绍异国风情,这必然要涉及语言翻译。谢清高随外国商船游历海外各国,又用一个旅游者的眼光看待世界,关注当地的环境、方位、物产、建筑、服饰、礼仪、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等。他博闻强记,还有较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或多或少听懂各地方言。
《海录》介绍了英、美等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涉及到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宗教和风土人情等专有名词,借助自己的语言优势,“谢清高在处理专有名词及各种不同题材文本时采用了音译、穿插评论性文本、归化与异化等译介策略。”[20]介绍外国自然少不了外国语言,其译介难免有错,总体上却相当值得称道。其特点则是颇有客家和葡萄牙口音特色,以译者之口音作记录和介绍,在语言翻译之初始阶段,这实在是必然而必要的。冯承钧《海录·序》称:
往来海上十余年,自不免娴悉各地语言。……然译音颇多舛讹,似多凭诸耳食。……书中译名多从嘉应音读,自未可以正音绳之。原名或本各地方语名,然亦多采葡萄牙语名。[3]335-336
晚清时期,黄遵宪诗歌亦大量借用外国语言,还引起其关于语言和文字的思考。从民间文人和普通民众的外国语言关注,逐渐引起士大夫官员、甚至是外交专业人士的关注,这是梅州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