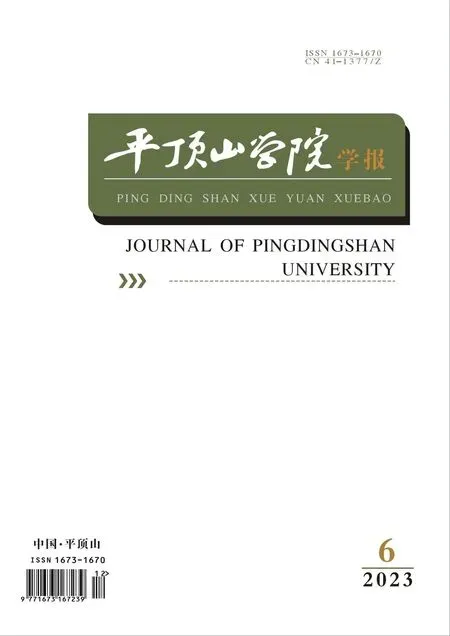冯友兰仁学中的共情思想研究
2023-02-20贾丹丹
贾丹丹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冯友兰(1895—1990)是现代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新理学以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为立场,吸收借鉴西方哲学的理性观,为传承中国儒学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尤其是他对传统儒学中仁爱思想的深刻理解和阐发,推动了性情论研究,对现代新儒学、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等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学者们对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已展开了比较丰富的研究,他的人生境界说、觉解说更是深受关注,然而,学界在谈论冯友兰仁学时,却往往忽略了其思想中人性假设与伦理界定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冯友兰说,仁“不是泛指任何一种精神境界,而是确指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1]。他还说:“真正风流底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2]314“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底同情。”[2]315这里冯友兰所说的“仁”作为一种境界,以及“我”之于万物的“同情”,与西方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中的“共情”(empathy,又译作“同感”“移情”“移就”)在认识论意义上有着诸多的学理相通之处。因此,本文拟以西方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相关知识为理论基础,以冯友兰仁学中的性情论为研究对象,从情感性(“同情”)、利他性(“无我之情”)和责任性(“圣人”)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旨在从认识论角度深入探讨冯友兰仁学中的共情思想,进而揭示出它的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同情”:共情的道德表征
根据上述冯友兰境界说中关于“仁”的表述,人唯有真正处于天地境界时,才会拥有一种关爱世间一切的深情。这里的“深情”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天地境界的人的“玄心”赋予其自身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即一种无我的情;第二,天地境界的人的“情”,始终都可以与世间万物处于一种共鸣状态。这里的“无我”和“共鸣”被视为仁者的两个属性,即唯有放下“我”的执念、真切感受世间一切的“他性”存在,才会拥有这种理想人格。很显然,这是冯友兰对人性假设和伦理定位的最高界定,或者说,冯友兰的仁学是把道德构建植根于情感,他提出的“仁”作为“深厚的同情”,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我”与他者的“共情”。
首先,从词源学上看,“共情”的德语“Einfuhlung”指“感觉进去”,即一种从此到彼的动态投射过程。换言之,从此(我)到彼(他者)的过程中,我们作为“我”在与他者交往时,以一种共享感觉的方式达到情感上的共识。对于冯友兰的仁学来说,天地境界的人觉解到了一种“深情”,不过它不是主体性的,而是被赋予一种“无我的”非主体性的情感。如冯友兰所说,新道家有许多人主情,“倒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3]。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的天地境界是一种情感境界,也就是说,儒家所说的“仁”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与世间万物的相恰切的情感,它不再区分“我”与“非我”,因为“我”已经消失;它也不再区分内外,因为一切都处于一个共鸣般的同频状态。简言之,冯友兰的“同情”论是一种前主体性的、理想性的人性假设。
其次,从儒学的发展史来看,冯友兰仁学中的“同情”论同样可以在王阳明“万物一体”的伦理观中找到类似的表述。例如,王阳明曰:“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4]但是,二者在认识论意义上的逻辑起点设定方面略有不同。王阳明万物一体观中的“情”属于一种环境美德伦理,“他的伦理学所关注的对象超出人类而涵盖天地万物”[5]。然而冯友兰对万物的界定始于他对人性的假设,即世间一切存在始于无我,因为有了无我之情的存在,仁才得以成为现实。这里蕴含着儒学的积极入世态度,“我”是被预设在了所有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中了。例如,冯友兰在论及境界说时,曾辨析了“有我之情”和“无我之情”:前者指的是“我”作为认知主体对一切存在的理解都始于“我”的理解和判断,后者也仍然是以“我”作为认知主体,但“我”的理解并不是判断理据,“我”之“情”不能介入我的判断,因此才会真正形成一种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的真实观照,即虽有情而情非“我”有的这种非主体性情感。简言之,“有情无我”,就是不要将情感与自我联系起来,它不属于某个特定的认知主体的主观感知。
再次,从情感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来看,冯友兰是把“情”作为仁学构建的始端,实际上是把情感视为社会道德构建的基础。例如,他对人的伦理行为的反思,同样也是依据“我”与情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应该如何办。此所谓应该,并不是从道德方面说,而是从所谓人情方面说。”[6]364或者说,我们所“应该”有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应该围绕“情”来展开,一切都“应该”是基于人的情来制定,而不“是”出自某种客观的行为规范。对于冯友兰来说,这里的伦理域转换不只是对儒学之礼的反思,更为理解西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提供了参考,即“情”是我们构建社会伦理的基础。
总之,冯友兰境界说中关于人性论的表述肯定了“无我之情”之于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实际上是摒弃各种生物性情感,以存在论而非道德性质的“情”对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进行还原,使其从客观化的、机械的行为规范转化为情感性的、人性化的行为准则,从而倡导了一种非工具性的伦理生活。
二、“无我之情”:共情的利他动机
根据冯友兰的境界说,处于天地境界的人应以其“无我之情”关爱世间的一切存在,那么,这种人性假设的动机是什么呢?冯友兰在《新世训》中曾这样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即在其是理性底,所以他能有文化,有了文化,人的生活才不只是天然界中底事实。”[6]352“文化出于人的理性的活动。”[6]352这里的“事实”之于人的生活(存在),显然在认识论意义上是一种事实判断,而拥有了“理性”“文化”的人,他的生活(存在)才会被赋予价值。简言之,人的存在也拥有一种从“是”到“应该”这样的伦理域切换,有助于这个切换完成的重要因素是“理性”,或者说,“理性”是人存在的根本,以及其伦理性存在的认识论价值。那么,“理性”(1)或者以某种生成语境来说,即“文化”。作为人实现(伦理性)存在的动机,为何如此重要?又如何表现呢?
首先,理性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标准。恰如冯友兰认为的,“所谓理性有二义:就其一义说,是理性底者是道德底,就其另一义说,是理性底者是理智底。西洋伦理学家所说与欲望相对的理性,及宋明道学家所谓理欲冲突的理,均是道德底理性。西洋普通所说与情感相对底理性,及道家所谓以理化情的理,均是理智底理性”[6]351。这里,冯友兰把“理性”解释为同义词“道德”/“理智”的不同表述,前者的“理性”是能指,是形而上的、类似于“道”的存在;而后者是所指,“道德”和“理智”是其在现实语境中的具体表现。亦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性的,让人之为人成为常态,而“理智”是价值性的,让人之为某种特殊存在成为现实。这一点可以从冯友兰关于西方的“理”和中国的“理”的简述中看得出来,二者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智行为,是与情感行为相对的。或者说,拥有理性的人,才能发现如何与“他者”(生命体)和“他性”(非生命体)共享存在,并形成一种特定时期的文明,表现为特定的文化。
其次,“觉解”是让人的道德境界敞亮的伦理进路。根据冯友兰的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四个层次的人都以不同程度的觉解展示出了其伦理行为和价值,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利他性”。
第一层次中,自然境界的人处于零性状态,彼此之间是一种生物性的行为,不存在利他关系。冯友兰就曾提出,自然境界的人的行为是以“顺才”“顺习”为特质[6]498,他们自然天成,一切都顺其自然。“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自发底合乎道德底行为。这种行为,就其本身说,是自然的产物。”[6]520可以看出,处于自然境界的人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行为,或者说,人对行为的道德意义没有了解,只是顺着个人习惯或社会习俗做了合乎道德的行为。这类行为尽管合乎道德规范,但是它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因为只有道德行为才有道德价值,而“道德行为的道德价值,则即在其行为本身。其行为本身若不是为道德而行底行为,则其行为只可以是合乎道德底,而不能是道德底”[6]521-522。因此可以说,冯友兰将第一层次的人性设定为一种“非道德性的”“生物性的”伦理准则,处于这个境界的人的伦理判断以其自身的自然天性进行类比,“虽不必积极地合乎道德底规律,但亦消极地不违反道德底规律”[6]341。
第二层次中,功利境界的人处于单向度状态,彼此之间是一种自利的行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利他关系。根据冯友兰的观点,“在功利境界中底人,有合乎道德底行为,是将其作为求其自己的利的方法。但以为道德行为不过是如此,则即是对于道德,未有完全底了解。而照此种说法,以做道德底事者,其行为只是合乎道德底行为,而不是道德行为”[6]536。处于功利境界的人即使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程度的觉解,却仅限于这些行为对自己的价值,这只是一种“为利”[6]499的行为,因此,处于这个层次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会有合乎道德者,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他因素,他们的行为只是一种“自爱”。
第三层次中,道德境界的人处于双向度状态,彼此之间是“行义”[6]499的,存在利他关系。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对于道德价值已经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觉解,不仅可以做出客观上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还可以真正理解其行为的社会意义,自觉做出这样的行为。或者说,这个层次的人的行为动机是“行义”,如冯友兰所说,“行义者,其行为遵照‘应该’以行,而不顾其行为所可能引起底对于其自己的利害”[6]546。这个层次的人之所以能够“行其义”,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的关系有所觉解,即觉解到人性蕴含在社会之中,以及在社会之中人性才能得以实现。
根据冯友兰的观点,这里的“义”是一种伦理判断的标准。因为如冯友兰所说,“求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6]499,而且,“尽伦尽职的行为,是道德底行为。凡道德底行为,都必与尽伦与尽职有关”[6]546。从这个角度看,冯友兰关于第三层次的人性假设是利他的,在他看来,“人不但须在社会中,始能存在,并且须在社会中,始得完全。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分。……社会的制度及其间底道德底政治底规律,并不是压迫个人底。这些都是人所以为人之理中,应有之义”[6]500,处于这个境界的人的行为具有道德性。
第四层次中,天地境界的人也处于单向度的状态,即“大无我”[6]505,彼此之间是一种无我的利他关系。在冯友兰看来,天地境界的人的行为既不为自己求利,也不为自己行义,一切都是为了“事天”。根据冯友兰的观点,“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人能从宇宙的观点看,则其对于任何事物底改善,对于任何事物底救济,都是对于宇宙底尽职。对于任何事物底了解,都是对宇宙底了解。从此观点看,此各种的行为,都是事天底行为”[6]566。处于这个层次的人愿意为“事天”而行动,是因为他觉解到自己的存在是社会性的,因此,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基于一种整体认识论意义上的,超越了狭义上的道德,直达形而上的“道”。
对比冯友兰境界说中的四个层次可以看出,他关于人性假设的基点是利他性,即按照人对世间一切存在的觉解程度的高低来区分。这里的觉解能力并不仅仅在于对某个事物的事实性认知,而在于他对世间一切存在的情感性接受。境界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主导思想肯定了境界层次的提升与觉解程度之间的正相位对比及其与主观情感接受的反相位对比,尤其是冯友兰“无我之情”推崇“利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强调共情在道德知识方面所起到的一种认知的或者认识论的作用,主张人性中的“情”不只是一种情感形式,更是一种对于他者认知的进路,这是通向深入了解情感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识论方向。
三、“圣人”:共情的本性
在论及情的利他性时,冯友兰始终都把人的境界作为考量的一个标准。相比于天地境界的道德之高远,他又时常把人的生活世界作为另一个考量标准。在他看来,对于道德规律来说,“一个社会内底人的生活方法,一部分可以随其社会所行底道德规律之变而变。一种社会内底人的生活方法与别种社会内底人的,可以不尽相同”[6]340。这里冯友兰把“道德”“社会”与人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了一起,主张处在不同社会的人的生活方法不尽相同。如此看来,人的社会性就成了道德形成的关键。道德与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如同我们对“道”的认识,“道”可以是形而上的、神秘的“不可道”,但是,它却可以具体化为生活中的“道理”。冯友兰在《新世训》中曾这样评价宋明道学家:他们是“哲学家”,但是他们所讲的内容大部分不是哲学,而是“为学之方”[6]340。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有些方面,“为学之方”就是“生活方法”[6]340,且“能完全照着生活方法生活下去底人”就是圣人[6]342。
根据冯友兰的观点,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是“理性”,但理性的人却必须是拥有生活世界的人。“无论就理性底的哪一义说,人都是理性底,而不完全是理性底。但完全地是理性底却是人的最高底标准,所以人必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6]353冯友兰还进而指出,“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就是做人[6]353,或者说,做人的目标是成为“人之至者”也即圣人[6]350。这样,冯友兰就把“圣人”和生活关联在一起,为人之为人的社会性做了责任性规定。
首先,人作为认知主体,应该自主提高觉解,这也正是冯友兰所肯定的人之为人的责任。他在界定“觉解”这个概念时这样写道,“人做某事,了解某事是怎样一回事,此是了解,此是解;他于做某事时,自觉其是做某事,此是自觉,此是觉”[6]471-472。冯友兰对于境界说的层次区分始终是以“觉解”为认识论基础,其价值在于让我们知道对世间万物程度不一的觉解决定了我们距离理性的远近,而如何做一位生活世界中的“圣人”本身就蕴含了一种责任观、一种“我”之于他者的共情伦理。例如,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冯友兰认为,“真能行忠恕者,即真能实行仁,若推其成就至极,虽圣人亦不能过。所以忠恕之道,是一个彻上彻下底‘道’”[6]362-363。这里的“恕”即一种共情,且是中国儒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具有的理论自觉,强调尊重彼此之间的不同。换言之,要以宽容(恕)之道对待他者的行为,进而做出真正合理的、合法的伦理判断。
从这个角度看,冯友兰把觉解视为人(认知主体)在道德观生成方面的基础性概念,处于不同境界的人会根据觉解程度产生不同的情感认知,而特定情境中人所体验到的特定情感本身就已经体现了其所在层次的内在道德价值。冯友兰倡导的“圣人”作为一种“完全”或“近乎完全”意义上的人[6]350是一种理想的人性假设,这显然是在推崇该层次的情感及其内在的道德价值,寻求并构建一种道德力量,让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彼此相互产生一种情感上、认知上的共享。
其次,重新界定“性”和“情”是冯友兰新理学在伦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他对宋明理学性情论的改造强调了人之于社会的责任。根据冯友兰的观点,事物依照某理而有某性,而性就是“理”在事物中的实现者:“有山则有山之理。有水则有水之理。有某种事物,则有某种事物之理。”[2]128冯友兰不仅坚持、肯定了程朱理学“性即理”的主张,而且把原本属于人的“情”抽象化为实际事物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恰如冯友兰所说,“从性所发之事,程朱名之为情;情即性之已发。……照朱子的讲法,仁是性,是未发,恻隐是情,是已发。未发之性不可见,但可于已发之情见之”[6]97,“情”就是“性”在现实中的表现,我们通过认知所能习得的关于性情的道理将要决定我们的行为动机。
在冯友兰看来,性分三品,中品为“一事物之气质之性能达到其类事物之气质之性于一时普通所能达到合乎其义理之性之程度时”,而其超过此程度者是上品、不及此程度者是下品,且“上品是善底,下品是恶底,中品是不善不恶底”[6]87。换言之,“情”的善恶在本质上是取决于“性”的,合乎义理是一种责任,人的行为在动机上表现为下品则是与社会公德相冲突。因此,人的社会责任取决于其品性中共情程度的高低,以及由此导致的其行为中道德动机的高下之分,而“圣人”表现出的“无我之情”充分展示了其品性中的亲社会性。
从认识论角度看,冯友兰仁学中关于“圣人”的责任论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美德论的观点,即作为拥有美德的人,“圣人”是一种理想的人性假设,共情作为一种优良品质存在于情感和理性同时处于良好状态的“圣人”身上。同时,它也延续、拓展了亚氏美德论,把美德与实践智慧相关联,让“圣人”在现实社会中具象化,让“圣人”的行为在具体的语境中表现为一种合理、合法的正确行为。冯友兰对“性即理”的理解显然深受西方新实在论的影响,或者说,他在改造儒学思想时,重新思考了人对外在世界的认知问题。冯友兰一方面驳斥了关于“理”或“道”的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另一方面也反思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立场,进而通过境界说来倡导自己的情理学说,即一种以对事物的觉解为认知理性的途径、以仁爱之情为人性理想的伦理境界。他不仅描绘出了一幅人性道德成长图,让我们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分析更有逻辑性,还辅以“圣人”世俗化的过程,让“道成肉身”的过程更加具象。
四、结语
在冯友兰仁学中,“同情”作为共情的道德表征,展示出来的是他对世间一切存在的情感性接受,而这一切的实现依赖“无我之情”,因为后者去掉了“我”的执念,在觉解程度上完成了“我”与“他者”的认识共享。“圣人”作为冯友兰“道成肉身”的伦理学运用,则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借鉴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中的共情论来分析冯友兰仁学中的情感伦理,且其情感性、功能性、亲社会性与冯友兰仁学中的“同情”“无我之情”“圣人”等与情感伦理相关的表述在认识逻辑上确实存在重要的隐性关联,但它们的不同之处也很突出。例如,冯友兰以存在论而非道德性质的“同情”对现实社会中的传统道德进行还原,这一点远比西方早期情感主义伦理学家休谟的同情论在哲学认识论意义上要高远得多。
总之,冯友兰仁学中的共情思想被赋予了一种非对象化、非主体性的存在方式,实际上这是较早的一种理论自觉,对于研究当前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它也为当前反思工具理性主导的伦理现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对如何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以及人所“应该”秉持的伦理生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