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洛托夫斯基与后戏剧
——兼论欧美戏剧学向表演研究的范式转移
2023-02-20张佳棻
张佳棻
一、 戏剧学的范式转移与工具性定义
当既有的理论无法表述或囊括新的实践时,学科的范式转移便应运而生。
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剧坛,波兰戏剧导演耶日·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 1933—1999,以下简称“格氏”)的“后戏剧”实验便携带着这种转换范式的强大能量。他在1970年宣布“离开剧场”,自此远离剧场建筑、观演关系与商业机制,但他并未完全离开戏剧,而是以戏剧作为福柯式的“自我技术”(1)“自我技术”是“那些能让个人对自己的肉体、灵魂、思想、行为施加某些影响的技巧,人们运用这些技巧旨在改变、改造自己,或者说旨在能于某种完美、幸福、纯洁、超自然权力等状态下行事”。参见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90页。,突破了传统戏剧的教育/娱乐建构,拓展了戏剧的哲学与实践意涵。格氏这股强劲的势能,让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在1967年与他相遇之后,从学者转入先锋戏剧导演的行列(2)谢克纳在1967年邀请格氏到纽约大学开设为期四周的演员工作坊。他早上参加工作坊,晚上便在草创的“表演剧团”(The Performance Group,TPG)进行实践,用格氏的表演训练创造出他在美国先锋剧界的代表作《酒神在1969》(Dionysus in 69’)。并促成“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3)本文将“Performance Studies”直译为“表演研究”,作为这个新学科的指称。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的译名“人类表演学”可以视为“表演研究”旅行到中国并且发展出中国民族特色的分支。See 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Studies:An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New York:Routledge, 2020), 30.这一新学科的诞生。而另一方面,格氏本人则转向一种实践性的学术探索。
在1999年,雷曼出版《后戏剧剧场》(PostdramaticTheatre)。他在书中并不讳言“后戏剧剧场”一词出自谢克纳(4)Hans-Thies Lehmann, Postdramatic Theatre (New York:Routledge, 2006), 26.,只不过谢克纳以之指称范围较小的“发生”表演(happenings)(5)“发生”(或译“偶发”)艺术是纽约罗格斯大学艺术史教授与即兴艺术家艾伦·卡普罗(Allan Kaprow)在1959年发展出来的一种表演形式,其代表作是《分成六部的十八个偶发》(18 Happenings in 6 Parts),具有多元焦点、同时性、偶然、拼贴、非叙事性等后现代特征。See Michael Kirby,Happenings:An Illustrated Anthology (New York:E. P. Dutton & Co., Inc., 1965).,而不是要建构一种新的戏剧史观。谢克纳坚持以“表演”涵盖1970年代以降的戏剧/类戏剧实践,因其认为“‘表演’比戏剧或任何一种表演艺术都还要广大”(6)引文出自笔者与谢克纳的电子邮件(2022年5月3日)。谢克纳补充道:“在1966年TDR第10卷第4期(第46页)以及《表演理论》(罗德里奇[Routledge]版)的‘方法’一节,我写道:‘很显然,发生这种后戏剧剧场无法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来讨论。’所以这个词汇在那里已经有半个世纪。不过这句话没有收在2003年版的‘方法’里头。”(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特别是许多跨界/出界的作品,像是雷曼书里提及的观念艺术或行为艺术,即便具有戏剧表演的特质,也不再适用“戏剧”这一表述。在雷曼的书里,他并未深究格氏与谢克纳的联系,但格洛托夫斯基、谢克纳与表演研究都是他“后戏剧”网络的重要环节。雷曼“后戏剧”偏于实践的归纳与史观的创新,谢克纳“表演研究”则聚焦于学科的改良与艺术实践的社会政治意义。
在《戏剧、脚本、剧场与表演》(Drama,Script,TheatreandPerformance)一文中,谢克纳试图从语汇拆解传统戏剧的建构:他认为“Drama”的中心是戏剧文本/文学,“Theatre”的内核是演员的表演,“Performance”则偏重复合的观演关系。(7)Richard Schechner, “Drama, Script,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TDR 17, no. 3 (1973):5-36.雷曼《后戏剧剧场》对“Drama”与“Theatre”大致沿用这样的区分,前者指戏剧文本/文学,后者指剧场的物质性/技术性元素;李亦男教授将之译为“戏剧”与“剧场”。
本文无意在语汇与翻译上打转,但表述的混乱无疑是范式转换期的重要特征。格洛托夫斯基作为超越既定结构的代表性人物,其工作在语汇上无可避免地体现了相当程度的表述困境。他的工作不再属于传统戏剧,然而还是必须以既有戏剧词汇(加上缀词或形容词)来进行自我表述。例如,他以“post-theatrical”一词指称自己离开剧场之后的工作,或以“para-theatre”来描述他的新工作相对于传统戏剧某种“伴随/边缘/之外/异常”(para-)的关系。
为了讨论的便利,本文对于“Drama”与“Theatre”两个词汇将沿用“戏剧”与“剧场”之译名,其工具性定义如下:以“戏剧”指称传统上的戏剧学科范畴或戏剧文本,以“剧场”(场地/场域)指称技术与实践层面。此外,以“后戏剧”指称雷曼式的戏剧史分期,以格氏自铸的“后剧场”一词称呼他的实践工作。若是抵触既有翻译(如“Poor Theatre”一般译为“质朴戏剧”),但为了叙事的统一,笔者不得不在本文(除了《迈向质朴戏剧》书名)将之译为“质朴剧场”(因其重心不在文本,而在表演与观演关系之实践层面)——尚祈前辈与贤者包容与见谅。
二、 后戏剧同盟:格洛托夫斯基与谢克纳
国内对于格氏的了解大多以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发行的《迈向质朴戏剧》(8)书名沿用既有译名,以下不另做说明。为基础。然而格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质朴剧场”十年的导演实践(1959—1969),更在于他“离开剧场”之后三十年游走于欧亚美非的“后剧场”探索活动(1969—1999)及其引发的种种戏剧观念变革。
谢克纳是美国最早关注格氏的戏剧学者。他从1960年起就在自己主编的《杜兰戏剧评论》(TulaneDramaReview)(9)谢克纳1967年离开杜兰大学到纽约大学任教后继续执编,遂将《杜兰戏剧评论》更名为《戏剧评论》(The Drama Review),以下简称“TDR”。选入介绍格氏质朴剧场的文章(10)See Jerzy Grotowski and Richard Schechner, “Doctor Faustus in Poland,” TDR 8, no. 4 (1964):120-133. Eugenio Barba, “Theatre Laboratory 13 Rzedow,”TDR 9, no. 3 (1965):153-165. Ludwik Flaszen and Eugenio Barba, “A Theatre of Magic and Sacrilege,” TDR 9, no. 3 (1965):166-189. Jerzy Grotowski, “Towards a Poor Theatre,” TDR 11, no.3 (1967):60-65.,并在1967年邀请格氏到纽约举办演出、讲座与演员工作坊;两人的对话就收录于尤金尼奥·巴尔巴(Eugenio Barba)编辑、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作序的《迈向质朴戏剧》。(11)格氏与谢克纳(译者将“Schechner”译为“史施诺尔”)的访谈收录在“同美国人的交往”一节。参见:[波兰] 格洛托夫斯基:《迈向质朴戏剧》,魏时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185—196页。谢克纳最著名的导演作品,美国先锋戏剧代表作《酒神在1969》(Dionysusin69’),便是以格氏质朴剧场训练创造出来的作品。
当格氏在1970年宣布“离开剧场”时,谢克纳仍持续关注格氏的动向。纽约大学的戏剧学研究所在1981年整合出“表演研究”这一新的学科,除了受到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和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2)谢克纳认为社会及文化人类学对于构筑他的表演理论非常有益,因为人类学家以一种“戏剧性的观点”看待人类的行为。See 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Theory (New York:Routledge, 2003), ix-x.的影响,亦与格氏后期的探索活动脱不了关系——戏剧从美学范畴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方法”(methodology);“世界一舞台”不再是一种隐喻,而是人类面向“表演世代”(13)安迪·霍沃尔(Andy Warhol)曾说“人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特别是在智能手机与社群媒体出现之后,人人都成了屏幕前的表演者。的基本存在模式。(参见图1)

图1 格洛托夫斯基(左)与谢克纳(右)在纽约大学,1982年(摄影:钟明德)
谢克纳对格氏的悼词亦体现出其关系的情感动力:“虽然我们年龄相仿,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他的儿子。当我得知他的死讯,我哭了。”(14)Richard Schechner and Lisa Wolford, The Grotowski Sourcebook (New York:Routledge, 1997):xxviii.“格洛托夫斯基研究”是谢克纳在纽约大学表演研究所的一个特别教学与出版项目;他汇编的《格洛托夫斯基资料集》(TheGrotowskiSourcebook)(15)Richard Schechner, The Grotowski Sourcebook (New York:Routledge, 1997).奠定了格氏研究的基础。
谢克纳的几位中国弟子也承续了格氏的后戏剧脉络。在1980年代晚期,谢克纳通过孙惠柱、曹路生与上海戏剧学院建立友谊,《戏剧艺术》开始刊载关于美国先锋戏剧以及与格氏后剧场活动有关的文章。(16)理查·谢克纳:《先锋派的没落与衰亡》,曹路生译,《戏剧艺术》,1991年第1期。 理查·谢克纳:《东西方与巴尔巴的戏剧人类学》,周宪译,《戏剧艺术》,1998年第5期。[波兰] 耶日·格洛托夫斯基:《表演者》,曹路生译,《戏剧艺术》,2002年第2期。 丽沙·沃尔夫德、托马斯·理查兹:《表演的刀锋——托马斯·理查兹访谈录(节选)》,吴靖青译,《戏剧艺术》,2002年第2期。其后,上海戏剧学院于2005年成立“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研究中心”。在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格洛托夫斯基年”(17)2009年是格氏逝世10周年,波兰剧场实验室成立50周年及其解散25周年的纪念年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年定为“格洛托夫斯基年”(The Grotowski Year),由波兰的格洛托夫斯基中心(The Grotowski Institute)担任主办方,在波兰、英国、法国、美国等地发起纪念论坛、研讨会与表演活动。纪念活动,两年后,也就是2011年,上海戏剧学院便邀请“格洛托夫斯基与理查兹工作中心”(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 and Thomas Richards)到上海开设讲座与工作坊,2012年又举办以格氏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都可以视为同一个学术传播脉络的系列事件。在中国台湾方面,则有钟明德(前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院长)在2001年出版《神圣的艺术》,这是中文学界第一本介绍格氏生平工作的著作。(18)钟明德:《神圣的艺术:葛罗托斯基的创作方法研究》,台北:扬智出版社,2001年。“葛罗托斯基”即“格洛托夫斯基”。
虽然关于格氏“后剧场”的讨论在国内尚未完全展开,雷曼的“后戏剧”理论仍有争议,但其观念已经透过谢克纳的表演研究(或中国化的人类表演学)进入我国。下面,本文将从格氏的双重身份——导演与学者——重新探索格氏质朴剧场及后剧场活动对于今日戏剧实践与学科创新可能的价值。
三、 格洛托夫斯基导演:表演作为自我的解剖与存在的敞开
“质朴剧场”(1959—1969)是格洛托夫斯基对20世纪60年代欧美戏剧生存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法。在影视新媒介的进逼下,以剧场舞台为主要演出空间的戏剧如何求生?格氏认为舞台剧无法在制造幻觉的技术上或经费上和影视产业一较高下,遂将注意力聚焦于戏剧的在场性,针对演员与观众的关系进行实验。由于观众是难以控制的变因,他便把心血投入演员训练。
格氏认为演员“必须把角色当成手术刀,用它来解剖自己……去研究隐藏在我们日常面具背后的东西——我们人格的内核——如此才能以之作为牺牲、把它暴露出来”。(19)Jerzy Grotowski, Towards a Poor Theatre (New York:Routledge, 2002), 37.透过演员的自我穿透与自我揭露,格氏意图创造这样一种观演关系:“如果演员……经由逾越、亵渎与骇人的叛逆,卸下日常生活面具,揭露了自己,或许观者也会进入类似的自我穿透过程……观者会知道,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这是一种共同行动的邀请,即便经常会引发反感或愤怒,因为我们平日的努力就在于隐藏关于自我的真相,不只对世界隐藏,也对自己隐藏……但在这里我们获得邀请,暂时停下脚步并仔细瞧瞧[自己]。”(20)Jerzy Grotowski, Towards a Poor Theatre (New York:Routledge, 2002), 34-37.为达此目标,他除了采取极度考验体能与反惯习(anti-habitus)的演员训练(如禁止言谈与深夜工作),用以消除演员有机体的形体与心理阻碍,亦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氏”)晚年新发现的“形体动作方法”(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进行改良。(21)近年来亦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如陈世雄:《“形体动作方法”的多种解读》,《戏剧艺术》,2019年第5期;吴靖青:《斯坦尼与格洛托夫斯基——两种表演训练相融与互补的可能性》,《戏剧艺术》,2009年第5期。
斯氏的形体动作方法可以说是“体系”的一次“范式转移”——演员表现真实情感的方法从“由内向外”的“情绪记忆”(从内在记忆召唤过往情感经验)变成“由外向内”的“形体动作方法”(以外在身体动作刺激当下的情感反应)。斯氏发现情绪记忆的缺陷在于企图以意志操控情感,然而情感根植于潜意识或无意识,演员无法透过理性的努力“再现”过往的情感;即便从内在“作”出情感,这种情感很可能是对记忆的想象或扭曲。此外,演员也可能在回忆中触及过往创伤而导致歇斯底里或疯狂。(22)Stephen Wangh, An Acrobat of the Heart (New York:Vintage, 2000), 303-306.
因此,斯氏开始研究“心理—形体过程”(psycho-physical process),其假设是:所有形体动作都是特定心理状态的流露。因此,演员的任务不再是寻找情感,而是寻找适合人物设定与规定情境的形体动作,借此引发相应的情感之流。(23)Sonia Moor, “The 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s,” TDR 9 no. 4 (1965), 91-94.这么做的好处是:演员不会因为无法控制情感而使演出乱了套,无论如何,都可以在规划好的行动中完成表演任务。至于要如何在排练中规划才能够引发特定情感的外在行动,那是斯氏尚未有机会深究的领域。(24)近代身心学(somatics)及其延伸的各种技术,如亚历山大技巧(Alexander Technique)、费登奎斯方法(Feldenkrais Method)或罗夫结构整合治疗(Rolfing Structural Integration),都证明了斯氏晚年的假设。这些方法也成为现代西方演员或舞者经常使用的辅助训练。
格氏继承了斯氏遗绪。为了协助演员显露其存有的核心,他对演员展开了严格的身体训练——一边去除演员身心因为种种社会制约产生的防卫机制和表达障碍,一边研究“心理—形体过程”的运作机制。格氏1967年在纽约大学传授质朴剧场训练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对于头倒立或翻滚这一类高强度的体能操作感到不解,认为它们与演技毫不相干。然而,这些看似纯粹的身体训练事实上以演员的情感/心理状态为标靶,目的在于以外在的形体挑战激发演员内在的情绪反应,使演员有机会在当下直面自身的感受(而非想象与再现)。例如,头倒立经常会激发演员对于颈部扭伤或死亡的恐惧,此时演员的任务就在于全然地体验这些情感,同时观察特定身体姿态与情感的联系,学习透过有意识/可控的手段(形体动作)来引导无意识/不可控的心理状态(内驱力/情感)。每个演员都必须研究自己独特的“动作—情感”反应机制,使之成为舞台表演的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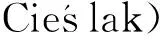
格氏的训练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表演。演员的身心处于某种既合一又离解的状态:一方面,演员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translucent),内在脉动直接显现为外在行动;另一方面,演员的话语与身体/情感又有着某种显而易见的间隙。采斯拉克嘴上读的是王子的台词,身体却展现了与其初次性体验有关的形体动作和情感之流。他个人的情感触动了观众,观众却“误以为”自己是因为王子的苦难而感动。文本与角色成了采斯拉克的保护伞,让他能够放心地展现内在的秘密情感,而不至于成为在陌生人面前毫不遮掩的暴露狂,或担心过于个人的体验遭受观众的批判。观众之所以能够安心接受表演者赤裸裸的表白,则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在观剧,而演员只是在“扮演角色”。
格氏追求剧场中真实的“相遇”(encounter),但是又极其聪明地利用了剧场的框架对真实的情感进行必要的伪装,在一种微妙的矛盾之中,同时卸下了表演者与观众的心防。斯氏则称之为“交流/交融”(communion),“就像一条地下河,在话语下面和沉默中不断地流淌,在主体与对象之间成为一种看不见的联系”。(28)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自我修养》,刘杰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2页。
这种以个人生命体验为素材的表演带着极为强大的真实感,或是“灵光”(aura)。王子的痛苦与演员过往经验中爱欲的狂喜恰巧形成一种难以言说的矛盾,为这一出戏创造出复杂的情感深度。当时在格氏门下学习的巴尔巴在观剧之后这么说:“有些幸福的片刻强烈到叫人害怕。我整个人叫《忠贞的王子》(《忠诚的王子》)给震昏了,却不害怕。没有任何演出曾给过我如此大的冲击,我飞了起来,再落地已经不是同一个人……我看着奇斯拉克(采斯拉克)演出主角,像是在针尖上跳舞的天使和雄狮。这个异象在我的灵魂烙上了一道刻痕。在今天,我做导演的梦想就是我的每个演员都可以抓住他的观众,就像理查·奇斯拉克抓住了我一般。”(29)此处沿用钟明德译文。See Eugenio Barba,Land of Ashes and Diamonds:My Apprenticeship in Poland (Aberystwyth:Black Mountain Press, 1999), 92.这是本雅明的“灵光”(30)瓦尔特·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格氏的作品由于导演手法与演员的内在过程难以复制,因此带给观众一种不可言喻的震撼。这也是斯氏在《演员自我修养》提到的“光芒”,“这种我们用来与他人进行交流但是肉眼却看不见的潜流,我们给它取什么名称呢?总有一天这个现象将会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我们暂且就用光芒来称呼它们吧”。(31)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自我修养》,第190页。
在这种情况下,戏剧文本成了一种容器,用来装载导演与演员各自的(艺术)生命之光,而不再寻求阐释或表现(不在场的)剧作家的意图。以谢克纳《酒神在1969》为例,其所根据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信徒》(TheBacchae)不是目的,而是表达年轻世代存在状态的一种手段。不过,格氏更加看重文本的功能,注重演员内在生命与戏剧文本的并行。在美国的先锋戏剧里头,不加修饰地以个人经历为主要叙事的做法,经常会令演出和表演者陷入一种自我沉溺的境地。
在波兰剧场实验室最后一个作品《启示录变相》(ApocalypsiscumFiguris)为期近三年的创作过程中(32)1965年12月进入排练,1969年2月才公开演出。,格氏发现新的可能性与实验方向,让他决定走出剧场。美国戏剧评论家艾瑞克·本特利(Eric Bentley)在观戏之后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戏演到一半,我接收到某种非常明确的启示(illumination)。信息降临——不知从何而来,人们常常这么说——与我的个人生活、我的自我有关。为了让它保持纯粹,我不能公开说明它的内容。但我想,这个信息之所以降临,与剧场的公开性不无关系。我得说,在我过去的观剧经验里头,这种事从未发生过……”(33)Eric Bentley, “Dear Grotowski:An Open Letter,” in Richard Schechner and Lisa Wolford, The Grotowski Sourcebook (New York:Routledge, 1997), 167.波兰剧评者古美嘉(Jennifer Kumeiga)也有类似的陈述:“他(格氏)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短暂地触及自己的内心深处……如果我们成功了,透过直面自我的震撼而进入某种深度,我们从此就改头换面了。这个过程与情感的释放无关;而是一种觉醒或重生,以结果来看可能会是非常痛苦的。”(34)Jennifer Kumeiga. The Theatre of Grotowski (London:Methuen, 1985), 97.
或许就是这样的“非典型评论”让部分论者把格氏和提出“残酷剧场”(Theatre of Cruelty,又译“残酷戏剧”)的阿尔托(Antonin Artaud)相提并论。阿尔托写道:“戏剧……其结果不是死亡,就是痊愈……它逼使人正视真正的自我,撕下面具;揭发谎言、怯懦、卑鄙、虚伪。它让群众……以高超的、英雄式的姿态面对命运。没有戏剧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35)翁托南·阿铎:《剧场及其复象》,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第30页。“翁托南·阿铎”即“安托南·阿尔托”。这些评论都指向了戏剧在教育与娱乐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作为一种同时承载疾病与净化、死亡与重生的“近阈限”(liminoid)(36)“近阈限”(或“类中介”)是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用来指称和古代仪式“中介”(liminality)现象具有可类比性的现代活动,如剧场或运动场。“中介”的特征是既有结构的反转,二元对立、阶级分别或社会冲突暂时消解进入交融(communitas)的状态,在仪式结束后又复归于新的秩序与结构。See Victor Turner, “Liminal to Liminoid, in Play, Flow, and Ritual:An Essay in Comparative Symbology,”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60, no. 3 (1974):53-92.场域。
四、 格洛托夫斯基教授:后戏剧的转向与人的行动研究
格氏在1970年发表了他的“后剧场”宣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剧场时代(post-theatrical epoch),之后不会再有什么新的戏剧潮流,而是某种将要取而代之的东西……我觉得《启示录变相》是我研究的新阶段,我们已经跨越了某种边界。”(37)Osiński, Zbigniew, Grotowski and His Laboratory (New York:PAJ Publication, 1986), 120.格氏的后剧场探索可以再分为四个阶段:类剧场(Paratheatre, 1969—1976)、溯源剧场(Theatre of Sources, 1976—1983)、客观戏剧(Objective Drama, 1983—1986)以及艺乘(Art as Vehicle, 1986—1999)。(38)格氏工作分期之译名沿用钟明德的译法。参见钟明德:《神圣的艺术:葛罗托斯基的创作方法研究》。后剧场的每个分期就像独立的科研或教学项目,由于格氏在欧美剧坛的声望,他经常能够独立获取所需的科研经费并且打造适当的科研团队(主要参与者是他过去的演员;其次是他的戏剧同盟,像是布鲁克与巴尔巴;最后是各领域的学术专家,如谢克纳)。这使得他的出走不完全是对于剧场的离弃,而是一种辩证的否定。
“类剧场”的意思是“与剧场并行”或“在剧场的边界上”,其问题意识在于,人类的自我穿透/揭露和关系的交融能否脱离剧场的建构(文本与角色)而存在?在这个时期,格氏抛弃了戏剧的美学脉络,除去了舞台、剧本、演员、观众,只剩下主题性的活动(近似大型的游戏)与它的参与者,例如“守夜”(Vigil)或“蜂巢”(Beehive)(39)类剧场活动像是大型的戏剧或团体心理游戏,以“守夜”为例,参与者进入一处择定的“空的空间”,首先进入全然安静/没有动作的状态,接着会有“向导”开始动作,其他的参与者自行决定跟随/不跟随,随时可以离开,在夜晚的寂静之中让自身的行动与人与人的交流自然而然地发生,探索行动与沟通的本质。,以行动为手段,探索人类个体性与群体性的本质。
类剧场最重要的活动是1975年夏天在弗罗茨瓦夫“国际戏剧研究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esearch of the Theatre of Nations)举办的各种戏剧课程、论坛、工作坊、表演与类剧场活动。西方剧界知名人士,布鲁克、柴金(Joseph Chaikin,美国导演)、巴尔巴、巴霍(Jean-Loius Barrault,法国导演兼演员,又译“巴劳特”)、格雷戈里(Andre Gregory,美国导演兼作家),以及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参与者达到4 500人。(40)James Slowiak and Jairo Cuesta, Jerzy Grotowski (New York:Routledge, 2007), 22-23.这是戏剧学朝着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与跨文化研究(行动与情感能否跨越语言与文化隔阂促成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的一次尝试。类剧场活动对于当时许多参与者而言是一种解放天性、改变生命的体验,不过由于它的游戏特质,加上结构松散,也招致不少批评。此外,格氏希望在大自然中举办的类剧场活动能够解除社会规训,恢复人类天性中的创造本能,但是没多久郊外的类剧场活动又落入另一种社会关系的俗套。(41)Jerzy Grotowski, “From the Theatre Company to Art as Vehicle,” in Thomas Richards, At Work with Grotowski on Physical Actions (New York:Routledge, 1995), 120.到了1970年代末期,格氏对类剧场活动的兴趣逐渐减少,焦点从群众转回个体,开始更加关注行动的文化根源与身体技术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溯源剧场”中,格氏的问题意识进一步向人类学靠拢:论及身体行动与人类存有的关系,各文化的传统仪式或身体技术对表演者或观看者有何作用?格氏带领自己的表演技术团队在欧亚美非四大洲进行了一系列“溯源技术”(technique of sources)的田野调查,希望能够亲见古老文化的“表演途径”(performative approach),并且与这些传统的继承者进行直接的接触与学习。他在海地与尼日利亚探索了巫毒仪式与歌舞;在墨西哥与印第安原住民惠尔乔人(Huicholes)探索人类行动与自然/仪式空间的关系;在印度探访西孟加拉吟游诗人包尔人(Bauls)的歌舞。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这些传统的特殊形式(他不再导戏,因此没有“挪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要透过各个文化的传统来进行“比较仪式研究”,看看这些千差万别的身体技术是否有某种共同的形式/结构逻辑或效用。格氏也曾阅读与道家身体传统有关的书籍(42)Richard Schechner and Lisa Wolford,The Grotowski Sourcebook (New York:Routledge, 1997), 253.,可惜当时没有机会到我国进行调研。溯源戏剧在1981年年底因为波兰进入军管时期而中断,为了继续研究工作,格氏接受了美国的工作邀请。
在1982年,格氏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戏剧系的讲座教授,随后接受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Irvine)戏剧系主任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的邀请,在美国西岸开设了为期三年的“客观戏剧”计划。(43)谢克纳希望格氏留在纽约大学,但是因为格氏希望能在较偏远的自然环境进行训练课程,而纽约大学校方不同意让学生离开市区、到纽约上州上课(心理剧创办人雅各布·莫雷诺位于纽约比肯的工作与教学中心),因此作罢。See Kermit Dunkelberg, “Grotowski and North American Theatre:Translation, Transmission, Dissemin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PhD diss., 2008):148-149.客观戏剧仍旧以各文化的身体传统为主要研究课题,但由于地理位置之便(加州汇聚了来自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表演者),客观戏剧更加关注特定身体技术对跨文化表演者身心的客观影响,希望能够从中抽绎仪式行动与身心转化的基本原则。以语言学作为比喻,格氏希望找到身体行动的“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44)“生成语法”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指向一套数量有限却能衍生无限语句的普遍语法规则。
作为课题主持人,格氏邀请了许多海外专家来传授个别的技术,像是海地的蛇神歌舞、伊斯兰的苏菲旋转或是日本的剑道。这些专家先把技术传授给格氏的四个技术助理——来自哥伦比亚的桂士达(Jairo Cuesta)、韩国的张斗尹(Du Yee Chang)、巴厘岛的兰爪(I Wayan Lendra)以及中国台湾的陈伟诚。接着再由这四位助理指导学生进行实践,以“身体录入”的方式,对这些技术的客观作用进行评估。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高校和主要赞助单位(加州大学董事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要求中期考核与结项成果,这是格氏后剧场时期最接近“戏剧”的一个阶段。他与学员发展出了“神秘剧”(mystery play)——根据个人记忆中最早的一首儿歌发展的表演片段;歌曲成为主要的表演文本,表演者不扮演角色,而是透过个人记忆与相应的情感与动作之流来搭建“个人仪式”。这个时期的表演者成了自我解构的主体。
由于格氏不喜美国的工作方式,加上在美期间诊断出癌症,他在1986年接受友人赞助回到欧洲,在意大利的蓬泰代拉展开最后一个阶段的“艺乘”(45)格氏在《从剧场到艺乘》一文中提及“Art as Vehicle”是彼得·布鲁克对其工作的命名。See Jerzy Grotowski, in Thomas Richards, At Work with Grotowski on Physical Actions (New York:Routledge, 1995), 119.布鲁克在《迈向质朴戏剧》的序言中说:“对格洛托夫斯基来说,表演技艺是一种乘具。”See Peter Brook, in Jerzy Grotowski,Towards a Poor Theatre (New York:Routledge, 2006), 12.工作——以艺术作为一种“乘具”(梵语yna)(46)布鲁克的“vehicle”来自梵语yna一词,指的是佛教的各种修行路径,如大乘(mahayana)或小乘(hinayana)。。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从科研变成了传承,把他过去积累的表演知识传授给托马斯·理查兹(Thomas Richards),其成果就是“行动”(Action)——一种由吟唱与身体行动构成的特殊表演。它不再具备传统戏剧的形貌,因此很难用戏剧的标准对它进行阐释或批判;它不以观众为导向,而是以表演作为锻炼身心的自我技术,但偶尔也接受观众的存在。为了生存所需,“工作中心”过去十年来带着“行动”作品在世界巡游。在2022年1月,理查兹发出了结束宣言,终结了格氏加诸其身的光环以及重担。
五、 面向表演世代:戏剧作为一种方法
格氏后剧场工作的跨界性与实验性极强,很难以既有的戏剧范式对其进行评价,因为它“既非戏剧,也非非戏剧”,其所体现的毋宁是某种“新先锋派”(neo avant-garde)的艺术特征——它不再是对既有风格(现代派戏剧)的创新,而是对资产阶级艺术体制的反叛。(47)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格氏的先锋性格在质朴剧场时期就可以见到端倪,因为质朴剧场的美学成就并不仰赖剧本/语言,而是来自“不可复制”的“具身相遇”(导演与演员,演员与观众)所创造出来的艺术灵光;到了后剧场时期,他连“作品”都没有了——“艺术是不道德的”,“有结果(作品)的人就是对的”(48)“你不该考虑结果,但是,同时,最终你无法忽视结果,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以这种方式来说,艺术是不道德的。有结果(作品)的人就是对的,事情就是这么在运作。” See Jerzy Grotowski, Towards a Poor Theatre (New York:Routledge, 2002), 245.是他对艺术体制的揶揄。
在《从剧场到艺乘》(49)Jerzy Grotowski, “From the Theatre Company to Art as Vehicle,” in Thomas Richards, At Work with Grotowski on Physical Actions (New York:Routledge, 1995), 122-123.一文中,格氏总结自己的生平工作,认为自己的探索从“展演艺术/艺术作为一种展演”(art as presentation)一路向“艺乘/艺术作为一种载具”(art as vehicle)进发,这与谢克纳从戏剧研究走向表演研究的路径是类似的。谢克纳敏锐地捕捉到戏剧实践风向的转变,在既有的范式无法描述新的戏剧现象时,他勇敢、坚定地开创了表演研究的新范式;范式改变,又造成新的戏剧与表演实践——布鲁克的“跨文化剧场”(intercultural theatre)争议或巴尔巴的“剧场人类学”(theatre anthropology)便是在这个范式转换期产生的新现象。
谢克纳与格氏各自以“戏剧”作为一种方法:谢克纳的表演研究着眼于社会脉络与整体结构(社会文本),格氏毕生的工作则是聚焦于主体性(自我角色)的建构与解构(表演者)。他们拓展了戏剧学的范畴,赋予戏剧学新的哲学/人类学向度与社会研究的高度。在影视产业进逼的年代,格氏寻求演员与观众之间本真的敞开与交融。在今日的智能手机/多媒介时代,自我的建构与解构因为数字化而失去身体的形状与潜流,人与人的“相遇”似乎变得更加困难了。然而,表演研究让戏剧成为一种认识的透镜与生存之道,帮助我们在这个表演世代的真实与虚伪之间、在演与不演之间自由穿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