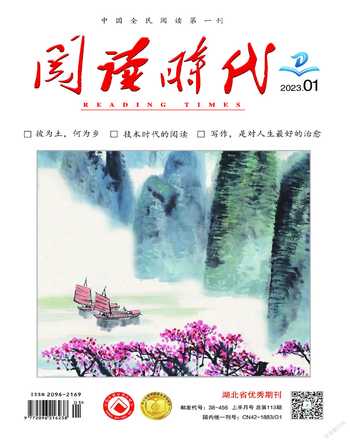彼为土,何为乡
2023-02-18刘醒龙
刘醒龙
我一直不敢在自己的写作中,对父老乡亲有半点伤害。在他们面前,我没有半点文化上的优越感。每当面对那些被风霜水土、杂草粪肥过度侵蚀的容颜时,内心深处总感觉自己占了他们的便宜。所以在写作时,能与笔下的那些人物平等相处,是我想象中的归宿与解脱。我一直不太相信在从事写作的这一群人中,有谁比乡村里的老农民更懂得生活和命运。他们是天生的社会学家、天造的历史学家、天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在乡村里,家家户户的老水牛都是大英雄,屋前屋后的老母猪全是大美人。这话没有丝毫调侃,我是百分之百地认同这些话。老水牛那毕生不改其志的劲头,比时下许多时髦学问家强。老水牛那只管耕耘不计收获的“牛格”,比那些只想收获不事耕耘的花花公子们的“人格”要强。比起那些人,得到好处越多,越爱在办公楼里骂阵,在现实生活中越是狂捞好处,越在各种场合上用“正义”的声音骂街,那老母猪心甘情愿地用一己之力,换得一户农家过上一段安逸日子,当然够得上“美人”级别。
上面这段话,是1995年秋天在一篇题名为《听笛》的文章中写下的。那时,自己还算年轻,定居武汉的时间不到两年,将这种貌似对乡村的偏袒诉诸文字,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城市化——暖气空调的无所不在,使得乡村里最为敏感的季节与气候,在个人身上显得麻木不仁;公共环境不断改善,空气污染指数的大幅度下降,同样大幅度降低了对负氧离子富聚的乡村的羡慕;自来水口感的优良,让碧水流泉仅仅作为乡村风景而存世。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日常生活中看上去早已与乡村绝缘了,重温当年的言说,赫然发现,自己的心境还是如此,丝毫也看不出今天的这个自我与当初的那个自我发生了哪些改变。不仅找不到变化,甚至还有油然而生的莫大庆幸:当初自己说的、想的和写的,没有太出格,没有走偏锋,重新读来,后来才不至于面红耳赤,自惭于世。
一直以来,乡村都是既浩大强劲又繁杂无常的存在。
《听笛》所写是对当时文学环境的有感而发。这些文字,并非刻意思考,也没有恨别鸟惊心那样的特殊思想,无非是凭着感时花溅泪的直觉有感而发。经历过风霜雨露,走通了断壁悬崖,回头来看,庞然大物的乡村,不是赵钱孙李以为其会向左便一定向左,也不是周吴郑王认定其会往右就必然往右。乡村太大了,大到地球上由人类组成的最厉害的社会,也无法把握其前行方向与节奏。乡村的太大,宛若地壳中的那些板块,比如台湾岛说起来是在向着祖国大陆漂移,每年只有几厘米的速度却是神不知鬼不觉。

文學中的乡村,属于鲁迅的是那个活着五行缺水的少年的鲁镇,属于福克纳的是小如一张邮票大小的小县,属于阿斯塔菲耶夫的是那看上去偌大的西伯利亚,实际上归结于叶尼塞河边的一滴水珠。
活在乡土文学中的乡村,科学地说,所表述的不是乡,也不是土,而是乡与土所代表如同大陆板块的那些,用世人难以知觉的方式缓慢且不可逆转的漂移。是乡与土的无限接近,又有着惊心动魄的沟壑,使其永远也无法彼此抵达。这种动态的态势,或许正是成就乡土文学经久活力的巨大能量。
现实中的乡村,大就大在一个土字,大在土地的生生不息,大在土地的无边无际,大在土地的宠辱不惊,大在土地的不废江河。反过来,现实中的乡村,小则小在体现社会认知的那个乡字,诸如乡里乡气,乡巴佬,乡下人,乡试,同乡,老乡和下乡,甚至人人都会说的乡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局限与落寞的代词。
在文学的事实面前,说一部作品有些乡气,或者说过于乡气,那种判断是不会有问题的,肯定是基于艺术要素的感觉不怎么地。鲁迅、福克纳和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中,乡村无所不在,感觉里却是洋气得无边无际,同样是相对乡气而言的了不起的认可。
有些话是必须说清楚的,不能模棱两可,东也有理,西也有理。所以,必须要强调得庄重一些:一切所谓的乡气,不过是一种脸谱,是一种品相,与乡土无关。然而,文学与现实中的普遍状况却是,乡气所指,乡土也在其范围之内。
乡土这个词,看上去只说一件事,本质上包含着乡和土两种概念。乡土里的乡是细小的感性,乡土里的土有着无限大的场域,乡土的意义是用细小的感性之乡,拥抱无限的场域之土。好比每一个人都要做的,用拳拳之心去接纳广大世界。做到这一点,需要用我们对告老还乡的乡,客死他乡的乡,乡音难改的乡,入乡随俗的乡,乡下脑壳的乡,上山下乡的乡,乡镇企业的乡,鱼米之乡的乡,还有近乡情更怯之乡,青春作伴好还乡之乡的天生敬畏,由衷尊重。在这些常见的表述中,哪怕是乡镇企业和鱼米之乡,有关乡的感性,都不是真正的情怀。
入文学越深,回望越远,越能发现文学的来龙去脉。2021年秋天,团风县老家的乡亲们,放下传承了很久的地名与村名不用,用全是赞成票的一致决定,将《凤凰琴》小说的篇名改做村名。听到消息自己非但没有欣喜,反而惊出一头冷汗,稍后才暗自宽心。这些年来,在写作中从没有过对乡村轻蔑的无礼,更没有绝望的无情。在社会改革需要普通民众分享艰难的最困难也是最困惑的时节,还记得田野上的老黄牛,不管这世上无情无义到何种程度,老黄牛们的口碑都不会有丁点损伤。回到那些曾在《听笛》中说过的话,那时候硬着头皮说,不敢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从事写作的这一群人中,有谁比乡村里的老农民更懂得生活和命运,而称他们是天生的社会学家、天造的历史学家、天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那么改村名这件事,足以证明,或许他们并没有读过小说《凤凰琴》,但在骨子里,他们就是活生生的“凤凰琴”。天下的乡村,无一不是活在牛背上,老黄牛是乡村的精灵,更是乡村的审美的开源与结论。面对凤凰琴村的乡亲,再好的小说也没什么可以嘚瑟。从乡村中生长起来的文学,转过身来又以乡村的方式被乡村慷慨接纳,这样的乡,这样的土,聚到一起可谓是相互抵达的实实在在的乡土。
明朝人李渔曾说,凡学文者,非为学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既明,则文字又属敲门之砖,可以废而不用矣。天下技艺无穷,其源头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学技,与不明理之人学技,其难易判若天渊。然不读书不识字,何由明理?故学技必先学文。予尝谓土木匠工,但有能识字记帐(李渔原文如此,不可改为账)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与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功倍之益。粗技如此,精者可知。
小说《凤凰琴》和村庄凤凰琴的关系,也是乡与土的关系。在乡土中,乡的所指,可以看作李渔所说学文时先要学会的读书识字,到了土的层面,关键是李渔所说的明理,在土的面前,不明理是不行的,没有半点矫情的土,是不以个人好恶为标识的历史、当下与未来,此理既明,那些免不了带有假设与推论的众说纷纭的乡,虽然不能真的当成敲门之砖废而不用,但一定要小心发挥,才不至于成为学技不精的拙匠。
在乡土中,乡的出场总是带着主观色彩,土则不同,不管有没有乡,土一直在场,因为土是有山有水,有草有木,有骄阳如火,有寒风如刀,有耕种与收获,有日日夜夜永不停歇的死死生生。这样的乡土之土,是我们的母亲大地。
其实,文学意义的乡土,乡与土是不可分割的。只是有鉴于某些入了过分自我的乡,随了过分自我之俗,才生生地拆开来说。就像小区里半生不熟的人在说,如果感情太丰富不找个地方安放就会泛滥成灾,那就养只狗吧!有些事,有些人,包括这里说的乡土,就是常被说成是这样的。没有谁能够将天下山水全部用钢筋混凝土进行改造,所以乡村的未来是天定的事。属于文学的乡土,也会拥有属于乡土自身的莫大生态。文学要做的,也是能做的,无非是用人人都会有所不同的性情之乡,尽可能地融入浩然之土。
(源自《小说评论》,陈蕊荐稿)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