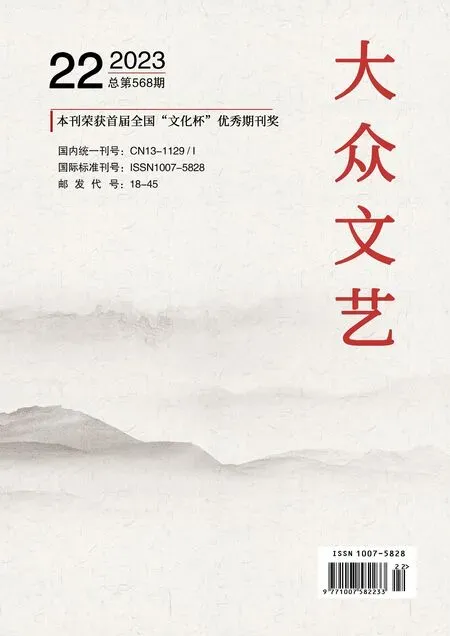失语与漂泊:王小帅电影中的人物形象*
2023-02-16裴和平
裴和平
(晋中学院中文系,山西晋中 030619)
王小帅电影作品中人物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失语与漂泊,无论是生活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还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抑或是曾经的三线建设者,在作品中都是一群没难以正常交流,处于漂泊状态的形象。王小帅的电影为何总是关注这样的群体,他们又是为何会成为失语者和漂泊者?
一、时代的失语者
本文所指失语并非指生理上失去语言能力,而是指人无法表达自己,无法与人交流的存在状态。第六代电影中的人物处于失语状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王小帅的电影中,语言之少,对白之简练尤为甚,人物要么沉默不语,要么是无法沟通,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堵在中间,把人与人都隔绝起来。具体来看,王小帅电影中人物的失语状态有三种类型:情感型失语、环境型失语以及角色性失语。
(一)情感型失语
情感型失语是指导致人物失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情感沟通。《冬春的日子》给人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丈夫小东忧心事业,陷入焦虑不安的状态;妻子小春渴望真爱,厌倦了迷失自我的生活,他们俩始终处于一种无法交流的状态,最终,一个去国离乡,一个精神分裂。《极度寒冷》中的齐雷沉浸在行为艺术的世界里,与周围人处于隔绝状态,宁可选择“死”也不与人他沟通。正如他最后一次死亡实验——“冰葬”,“冰象征着冷漠的后工业都市,齐雷的行为是否可以解释为:以自己的体温来融化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的坚冰,最后却被这种冷漠葬送?”[1]片尾,假死的齐雷无法忍受“死后”的孤独,竟然真的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左右》同样关注家庭题材,由一个得白血病的孩子引发了两个家庭之间的现实矛盾,主人公枚竹与前夫肖路,与现任丈夫老谢,肖路与现任妻子董帆,四人之间都产生了情感冲突,导演却采用了内向化的处理手法,将矛盾压抑在内心,人物对白及其简略。影片中的每一个人都对生活充满着无奈,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他们既无力奋起反抗,又不愿随波逐流,只能选择沉默和叹息。
(二)环境型失语
环境型失语是指导致人物失语的原因来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扁担·姑娘》中的东子是一个从乡下来的打工者,他与武汉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他不属于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不属于他。影片中的画外音可以看作是东子在自言自语,在这座城市没有人跟他交流,唯一的朋友高平总是跟城里人来往,他们间的交流经常处于不畅的状态。《十七岁的单车》中的连贵是一个来自底层的进京务工人员,唯一的朋友就是小卖部的老乡,除此之外,他跟其他人没有共同语言,即使是在跟老板、客户交往的过程中,他总是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每当与环境发生冲突,只能采取激烈的行为来保护自己,例如,他跟北京青年小坚之间的冲突,看似因为一辆自行车,实则源自不同阶层之间的无法沟通。《二弟》以犯罪片的叙事框架讲述了一个有关偷渡的故事,被遣返的二弟面对别人的各种询问、好奇、试探他始终沉默不言,拒绝跟所有人交流,因为他失去了曾经的“乐园”。在不平等的全球化的秩序中,偷渡者们置身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全球化和经济蓬勃发展的宏大前景忽略和淹没了个人的感觉和选择,”徘徊于一个尴尬的中间地带:“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习俗、道德规范和法律的不同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2]面对偷渡的失败,亲友的质疑,权力的训诫,还有异国法律对于血肉亲情的残忍隔离,他只有沉默,以沉默对抗一切,如同一堆烂泥瘫软无力,看上去了无生趣,其实他正沉浸在不可言说的不安与绝望之中。
(三)角色型失语
角色型失语是指由人物所扮演的角色造成的失语。在传统的父权社会,子女在家长面前没有话语权,家长在权力面前也没有话语权。《青红》中的女儿面对来自父权的压迫,只能选择沉默以对,而父亲在强大的历史意志面前,何尝不是一个无法发声的沉默者。《日照重庆》中老林在调查儿子的死因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倾听的状态,作为一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父亲,他在前妻和亲友面前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如果说青红父女的失语是由于历史意志的介入,那么老林父子间的失语则是时代精神的使然。《闯入者》中的老邓是一个横跨历史和现实的角色,现实中的老邓是一个上有老母,下有儿孙的独居老人,过去的老邓曾是一名三线建设者,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现实与历史的穿行中,既要面对历史遗留的良心账,还要处理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倍感孤独的老邓只能对着死去的老伴的照片自言自语。
为什么王小帅电影中的人物总是处于难以沟通的状态?只能从时代的宏观视角和作者的微观角度来解释。第六代导演步入影坛正值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时期,伴随着都市化和市场化浪潮而产生的群体性流动,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不断打破重组,人际关系也脱离原来的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转变为原子化的社会关系和陌生化的伦理关系。第六代导演用摄影机记录了时代巨变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他们无所依萍,内心惶惑,渴望沟通,却又无法沟通,失语成了常态。
其次,从创作者主观意图的角度来看,王小帅之所以把人物设置成失语状态乃有意为之。王小帅不止一次说过,他就是一个性格阴郁,不喜言谈的人,或许正是这种性格影响了他的电影创作,正所谓“影如其人”。作为一个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电影影响的文艺片导演,王小帅的电影与主流电影刻意保持距离,呈现的是一派非主流的现实图景,他不希望观众被卷入到故事之中,而是能够保持疏远,冷观静察,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非专注于表面矛盾。因此,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上,王小帅倾向于让人物尽可能少说话,通过身体和细节表达情绪感受,而非台词对白。
二、都市的漂泊者
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奇说过,人是历史的人质,一语道破人间真相。人们总是渴望诗意地栖居,可现实从来不给予机会,漂泊成了现代人的宿命,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会同情那些车轮下哀鸣的小草。
(一)从乡土到都市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化格局开始松动,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世代生活的土地,参与到这场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扁担·姑娘》中的高平和阮红带着“作城里人”的热切愿望从乡村来到武汉。《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快递员连贵、小卖部老板,还有那个别墅里的保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游离在都市边缘,却从未被其接纳的生存状态。现代化的都市图景对落后地区的人群产生了强大的吸引,成为后者的欲望对象,如同《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小卖店老板对别墅女子的窥视,《扁担·娘娘》里的东子对歌女阮红的欲望,这种艳羡来自底层社会对现代性的向往,可最终却欲而不得,连生存的尊严都被剥夺。
像东子和连贵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只能依靠体力谋生,带着对都市生活的潜意识欲望,相信靠诚实劳动可以换来美好生活,最初的日子充满快乐和兴奋。扁担东子每次放工回来都是吹着口哨,动作轻快,奔跑跳跃,快递员阿贵每完成每一次任务,脸上也会渐渐浮现出自信而满足的笑容。然而,都市对外来者的吸附和排异从来都是同时存在的,命运的反转随时可能发生,当这些企图忘却自己身份的人想要以一种非常手段跨越社会的无形等级,进入都市的核心领域时,一道无形的阻力迅速将他们反弹出去。《扁担·姑娘》里的高平就是一个反面典型,他不和同乡来往,跟城里人做生意,甚至染指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最终落得惨死的结果。《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小保姆,偷衣假扮,把自己想象成别墅的主人,逃不掉被驱赶的下场。一向安分守己的连贵也难逃厄运,不幸涉入都市生活错综复杂轨道,与一位都市青年的命运发生了碰撞。对连贵来说,山地自行车是他在都市里赖以谋生的物质工具,也是达成他立足北京这一物质欲望的基本保障;对小坚而言,则象征了青春期的爱欲冲动,是满足个人虚荣心的炫耀品。像连贵、东子和高平这些底层人物,他们的遭遇象征着底层社会与现代都市之间的抵牾和隔绝,尽管他们是如此的热切和执着,向往的“天堂”似乎总是遥不可及。
如果说《扁担·姑娘》和《十七岁的单车》表现电视乡村对都市的企羡与碰撞的话,那么《二弟》则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倾倒与沦陷,两者看似不同,实则殊途同归。《二弟》同样讲述一个“漂流者”的故事(影片的英文名字drifter就是漂流者的意思)。该片将摄影机对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另类边缘人群——偷渡客,他们锲而不舍的偷渡行为背后暗藏着涌动不息的底层欲望。影片并没有向观众明示二弟及村民偷渡的原因,但其中多处细节似乎藏有答案:收音机里中国加入WTO的新闻,电视机播放的国际品牌广告,美国的法律进入到中国小镇,无不暗示着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扑面而来,席卷中国。大洋彼岸的美国对于偷渡者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巨大“引力场”,他们对美国生活的幻想和对美国身份迷恋,凸显出全球化造成的地区差异与人性失衡,将落后地区的人们推向了另一条的不归路。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每个人都如同一粒小石子,随波漂流,俯仰碰撞,直至海与天的尽头。
(二)从故乡到他乡
如果说像东子、阿贵、二弟等人还算是主动离开家乡,自己选择漂泊的话,那么在王小帅的另一些电影作品中,主人公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选择了漂泊。2005年之后,王小帅的连续创作了“三线三部曲”——《青红》《我11》和《闯入者》,这些作品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家战略工程——“三线”建设为题材或背景,展现了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个人命运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冲突。作为三线建设者的后代,王小帅在他的自传《薄薄的故乡》中回忆到,当时被选中支援“三线”的工人,“一个都不能落下,必须都去”,[3]甚至连家属也得跟着一起去,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产业大转移和人口大迁徙。
正如影片所看到的,这些来自大城市的移民对当地很难产生认同,《青红》(《青红》的英文名就是Shanghai Dream)中的一家来自上海,以上海人的身份为荣,使用上海话进行交谈,保留上海的生活方式,甚至反对跟当地人谈恋爱。《我11》中王憨一家也是来自上海,总是不自觉地跟当地人拉开距离。然而,现实总是很残酷,王小帅自传中曾提到,刚开始大家每年春节还回上海,到了后来感觉自己离上海越来越远,仿佛被上海抛弃了。黯然退去的激情,无法兑现的许诺,难以融入的环境,都成为三线人逾越不了的心结。在城乡二元格局之下,城市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一旦放弃就很难找回,户籍制度、档案制度如同一道道锁链,把他们牢牢地困在贵州的那条山沟里。如果不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巨变,这些三线建设者都会终老于此,后代也许会重复同样的生活。正如影评人程青松所言:“他们像一些囚徒,时代的囚徒,被流放到那个地方。在那里做疯狂的挣扎。令他们疯狂的这个错误似乎是他们自己犯下的,他们是自己从上海到贵州的。”[4]
对于这些身在异乡的漂泊者而言,上海人或者北京人是一种能够体现价值和归属的身份认同,他们不想失去,更不希望儿女失去。正如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青红的父亲、王憨的爸爸,还有其他许多像他们一样来自北京、沈阳、上海等大城市的家庭,他们对当年的选择悔之莫及。谁曾想到历史的铁幕也有被撕开的时候,这些被遗忘在大山里人骤然看到离开的希望,拼命想要抓住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青红爸为了回上海毁了女儿的幸福,《闯入者》中的老邓为了拿到回北京的指标,暗中构陷自己的竞争对手。
如果说,在《扁担姑娘》中的农民工和《二弟》的偷渡者是主动地卷入了现代化进程,那么,这些三线建设者们则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历史和政治的漩涡之中。“当这些浮萍一样的移民家庭被时代的潮水抛掷到荒芜的岸上时,他们疼痛地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完全被历史所改写”。[5]在强大的历史意志和政治话语面前,任何个体都无法抗拒施加于自身的宰治性力量,唯有无尽的哀哼与低声的细语。
三、小结
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艺术创作的中心永远是人,始终围绕人的存在而展开活动,艺术家要关切人,艺术作品塑造人,艺术欣赏要满足人。如果离开人这个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艺术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沦为游戏和空谈。王小帅导演将摄影对准了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群,记录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真实处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幅幅充满着生活质感的现实图景,为中国电影做出了一代人所应有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