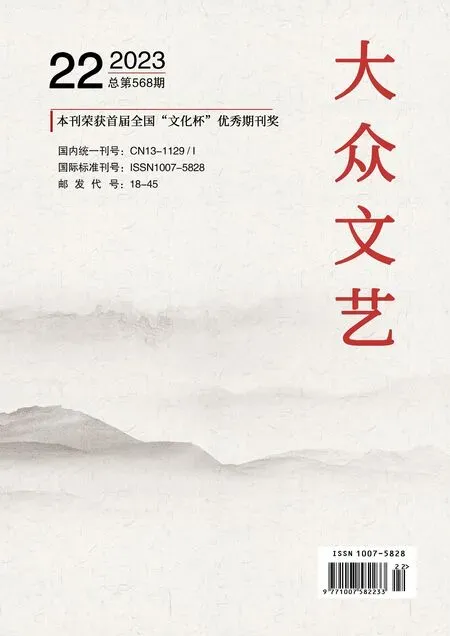山西民间信仰区域特点初探
2023-02-16马雪纯
马雪纯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晋中 030619)
人类从诞生之初就要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生存环境对生存者有着天然的、绝大的制约作用。民间信仰的起源往往出于人类最朴素的需求,而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一定区域内人类无法解决的自然问题,往往假托于神,促成了各种民间信仰的诞生。不同的地域发展而来的形色各异的民间信仰成为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都极为关注的话题,社会史视角中大量运用施坚雅、杜赞奇、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对民间信仰进行研究,对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解读也纷纷出现。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①[1],民间信仰与地理学息息相关,它的地理学视角当然也不可或缺,张伟然、蓝勇、张晓虹等人已经开始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进行研究,日、美学者对此也有深入探讨。民间信仰的变迁和地理分布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一定区域内气候、地形、物种、植被及地方文化等地理要素,有助于了解历史时期该分布区域内的人地关系。通过对民间信仰的追本溯源,可以反推出历史时期人类曾经面对过的、无法解决的自然问题,从而对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有更全面更具体的认识。
山西向来被称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存在着大量、多种类的民间信仰,明清山西地方志中所载祠庙结合留存现状及发展历程,反映出山西民间信仰所呈现的独特区域特征,其表里山河的地貌特征与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对山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形成与传播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古圣先王信仰长期留存
山西作为最早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古都林立,作为早期中国的中心地带,山西留存了许多古老的帝王崇拜,或因封地、墓地,或因事迹流传。《汉书·地理志》对河东民风的描述“其民有先王遗教”②。[2]厚重的文化积累之下,先民们形成了对造福百姓的君王、士大夫、地方官吏以及杰出人物的敬畏和信仰,封闭的地理单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传统信仰的保存提供了条件,此类信仰也只有在山西才有条件产生和存在,对古圣先王的人物崇拜在山西占比极大,成了山西区域性的文化特征。
上党地区地处高处“居太行山之巅,与天为党也”③[3],是古史传说记载的集中地,其密度之集中、内容之详备遍及上党各山各村落。例如《泽州府志》载,“炎帝尝百草至羊头山得秬黍”,《长治县志》《山西通志》对羊头山和炎帝也均有记载,在传说区域也相应地出现了伏羲、女娲、炎黄等的信仰崇拜,炎帝信仰在晋东南地区广为流传,当地的神农城、神农井、五谷庙等遗迹与众多传说一同构成了庞大的炎帝传说信仰圈。神农和黄帝除了是古帝王之外,还有其对于医药的贡献也是受到后人崇拜的原因。
相传“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平阳、蒲阪、安邑的具体位置学界仍有探讨,但都位于山西已基本没有争议,是以尧、舜、禹在山西皆有祠庙且数量较多。其后较为多见的还有汤王庙,“商汤祈雨桑林”的传说,阳城作为传说中的祈雨之地,也成了汤王信仰的中心,并在晋东南一代广泛流传,留下了众多的庙宇和碑刻。而作为晋国故地,晋文公庙也多处存在。后代君王,常以山西为龙兴之地,汉文帝、唐太宗,在太原、霍州等地存有祠祀,北魏孝文帝也在晋中区域多地建有祠庙。
除贤明君王外,忠义臣子列为祠祀的数量也相当之多,从比干、箕子到伯夷、叔齐,贤良忠臣多有所祀。在山西,春秋时期的晋国所祀忠臣有二十位左右之多,有辅佐晋文公的狐氏父子、介子推、先轸,有藏山护孤的赵盾、程婴、公孙杵臼,还有侠士灵辄、提弥明、豫让,大夫尹铎、荀息、窦鸣犊等等。此后历代名臣如汉张良、樊哙、曹参、霍光,唐狄仁杰、魏征、尉迟敬德,还有一些与民有功的当代地方官。这些贤臣良将后代多有加封,一直列于国家正祀之中,地方官员也多有维护。相对而言此类信仰在一定区域内出现,与人物本身有一定关系,传播相对困难。
古圣先王信仰的长期留存也和山西一直处于京畿之地有关,离统治中心较近,民间信仰受官方意识影响较大,④[4]教化民众的功能比较突出,通过对此类信仰的宣传与维护,宣扬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规范民众行为。儒家精神看似并未大肆在民间传播立祠,但对于古圣先王的祖先崇拜和忠义倡导却深深根植在民间信仰的血脉中。
二、民间信仰区域化
山西的地理位置优越,是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明的交界带,地形复杂,山地居多,东有太行山为天然屏障,西、南以黄河为界,《左传》讲山西的地形是“表里山河”表有大河,里有高山,山河天险,赋予了山西深山藏古刹的优越条件。这种自然环境必然对地方的民间信仰产生诸多影响。除土地庙、城隍庙、文庙、关帝庙、龙王庙、八蜡庙、娘娘庙等全国普遍性存在的信仰外,山西境内还长期保留了大量区域性极强的民间信仰,其形成与发展与当地的环境、历史、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地方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山西的高山河流划分出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山西的晋北、晋中、晋南地区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与方言,反应在民间信仰上就是不同的区域信奉不同的主神,虽然随着交通逐渐发展、商业往来愈发频繁以及国家权力的推行,一些地域性的信仰会逐渐向外传播,影响力日渐扩大,但其发源地依然是主要的信仰区域。如纪念介子推的介庙最早只在山西有,后来逐渐发展至全国,甚至于海外都有其踪迹。
晋南地区普遍存在崔府君信仰,尤其是晋东南的泽潞地区。关于崔府君的身份说法颇多,广为流传的是两宋时期“泥马渡康王”⑤的故事[5],因其护佑国家的功绩还屡次得到了官府赐额册封。一直到明清时期,崔府君形象逐渐丰满,其出身及亲属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故事流传。明初以后,崔府君信仰的地位越发重要,开始与地方社会相结合,成为地方保护神,以国家正祀的身份存在。崔府君信仰的分布范围以泽潞地区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扩散,清代以来很多地区都开始出现崔府君的祠庙。加之泽潞地区商业活动的繁荣,走南闯北的泽潞商人把崔府君信仰带到了山西各地,扩大了崔府君信仰的影响力。
晋中地区存在较多的区域性信仰应该是狐突信仰。狐突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其子狐偃、狐毛在晋文公门下,父子三人以忠义著称,在晋文公执政之路上立下极大功劳,历代统治者及民众感其忠义,因而立祀。据传狐突死后葬于马鞍山,当地人称狐突为狐爷、狐神,从忠义代表一步步变为水神,最后成为当地百姓无所不能的保护神,并逐渐以马鞍山为中心形成了狐突信仰圈,相关的庙会、传说、祭祀仪式也越来越丰富。
晋北地区佛教氛围厚重,民间信仰相对单一,较为特殊的是一类武将信仰。晋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边疆地带,甚至为外族所占,“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⑥[1],到了明代推行卫所制度,移民屯兵、修城筑堡,使得晋北地区一直以来尚武之风较为浓厚,。历代以来更是不乏骁勇善战的守将与地方官,随之而生的就是为纪念这些武将而产生的祠祀。如鄂国公信仰,祀的是唐代将军尉迟敬德,分布在朔州、马邑、保德等北部边镇,还有苏武庙、赵武灵王庙、李将军庙等等。此类信仰的产生与分布应该与晋北边区位置和战争频发有极大关系。
除大的区域范围外,还有一系列与自然地理条件相关的区域所产生的民间信仰,比如汾河流域,石楼、静乐、宁武、阳曲、太原、临汾、曲沃等地的汾水神信仰,即台骀信仰。还有长治地区的三嵕庙,因其山势挺拔、祈雨灵验,在当地香火不衰,被百姓信任崇拜。由此可见,受地理环境与区域限制,民间信仰的地域性鲜明,各地出现了类型不同、各式各样的信仰。
三、神灵职能趋同化
纵然山西各地信仰各具特色,但身处同一大区域之中,各地的民间信仰又有非常多相似之处,尤其体现在信仰的职能上,有着逐渐趋同化的特点。由于山西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使得民众的求雨需求长期存在,除常见的龙王庙外,许多有过求雨经历的古帝王和原本以忠孝仁义立祀的人物都逐渐转换为祈雨的雨神,再变为地方保护神。这种功能上的转变与地理环境、时代发展都息息相关。
地理环境包括了许多因素,如气候、地形、植被、土壤等等,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气候对民众生产、生活影响最大。山西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南北部的气候与昼夜温差差异较大,晋北相对寒冷,晋南相对炎热。全省年降水量仅400~650毫米,降水受地形和季节的影响颇大,冬季干旱,夏季多雨;其中又山区较多,盆地较少,盆地是人群聚居的密集地带,少且不稳定的降水量给人民进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于是祈雨就变为当地百姓与地方官的一项重要活动。水资源也成了社会权力分配的一项重要指标,山西有关“分水”的民间传说及史料记载也数量极多,祠庙也常作为“分水”的场所或见证者出现在碑记中。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干旱少雨的现实导致山西各地遍布专司祈雨的龙神庙和各式各样的司雨神,山西地区的龙神庙数量相当庞大,另一方面反映出山西的祈雨需求也是相当之多的。
窦大夫祠是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窦犨的祠堂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上兰村,《山西通志》载“窦大夫祠在府城西北四十里烈士峪口祀赵简子臣窦犨元至元三年建国朝洪武三年改称晋大夫窦鸣犊之神有司岁以四月五日祭”。⑦[6]据说此地古称狼孟,窦犨的封地在此,后来也成了百姓及地方官祈雨的场所。关于祠庙的存在,最早的记载出自唐代李频的一首游烈石诗,但诗中只是讲“窦犨遗像在林峦”,并不能显示出其水神职能。《阳曲县志》记载“庙临汾流而靠诸泉,宋元丰八年六月,汾水涨溢,遂易今庙,有金县令史纯碑记。”⑧[7]说明了其所处位置与汾水临近。金大定年间县令史纯的《英济侯祷雨感应碑记》说,“汾水之滨,有祠曰英济,俗呼为烈石神。考之图籍,乃春秋时赵简子臣窦犨,……英灵能兴云雨,里人立祠祀焉,旧无碑记可考”。⑨[7]由上可以看出至少从北宋开始,窦犨的职能就已成为水神。赵世瑜⑩[8]对于窦大夫从贤臣到水神的功能转换做了完整的论述,然而这种情况在山西乃至全国都并不罕见。山西地区的汤王庙、狐突庙、鄂国公庙、台骀庙、窦大夫祠、三嵕庙等等祠庙,无论最初供奉的是君王、大夫、还是山神、水神,但都在历史过程中开始承担祈雨职能,凡呈现出求雨灵验的“神通”,其余各种愿望和需求也会接踵而来,直至成为神通广大的地方神,所在祠庙最后都成了祈雨的场所。“民间信仰成三教合一的特色,那么反应在神祇功能上,各路神就成了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各种神祇的神通就不再为他身前的职业所限,而成了能够应付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类型的信仰者及各式各样愿望和要求。(11)”[9]
四、与宗教文化的融合
佛道文化逐渐传入山西后,就与本土的民间信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许多祠庙开始供奉多种或多教的神祇,这些庙宇的日常维护者也变成了僧人或道士,宗教文化对民间信仰进行了神灵和祭祀仪式的改造,以及对庙宇空间及资源的再分配,使得民间信仰呈现出新的格局和面貌。在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的融合过程中,也许开始是为了使当地百姓更容易接受新传入的宗教文化,但后来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反而是祠庙中宗教的存在使得民间信仰得以长期留存。
佛道二教文化的传入,对山西的信仰空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空前繁荣,当时战争频发,社会环境动荡,政权频繁交替,而山西在这一时期作为政府的政治重地和战略要地,处于胡汉交界之地,既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交流中心,对于佛教在山西有了充足的发展条件。据载“魏都平城时期,为亚洲盛国,西域诸国,相继来朝,从事朝贡贸易,僧徒亦乐东来弘法”。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僧人都曾在这一时期在山西进行活动,《山西通志》中记载过佛图澄曾驻锡于中条白石寺。《晋书》中也记载了佛图澄与后赵石勒的相识,在佛图澄的影响下,石勒大兴佛教并遍修寺塔,后赵当时的范围就包括今天的山西地区。还有佛图澄的徒弟释道安“在并州听大阳竺法济、支昙《阴持入经》”“后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公元351年,释道安隐居雁门封龙山,建寺传教。云冈石窟的修建,五台山道场的初步形成都发生在这一阶段,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山西的佛教已经十分兴盛,也为后来三武一宗灭佛埋下了伏笔。但佛教在山西的发展却未曾禁断,北魏孝文帝,隋朝炀帝、清朝康雍乾三地都曾驾幸五台山,历朝帝后下诏、遣使朝拜、修庙建宇从未间断。元代山西处于腹里之地,其境内山河广布,适合隐居修行,历来是方外圣地,全真道兴起之初就将山西芮城人吕洞宾尊为五祖之一,甚至认为“全真之教盖发源于此”,山西境内的吕祖祠、纯阳宫等建筑颇多,在晋中、晋南、晋北均有全真教派建筑,且常处于市中心的文教区域,与府城相近,例如太原和大同的纯阳宫都是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全真教在山西的发展繁荣,官方的支持度也相当高,为全真教及整个道教向山西境内发展提供了信仰基础。同时,道教利用统治者的力量,影响力迅速扩大,其教义又适应民众祈福避灾的信仰需求,信众人数和道观数量大为增加,在山西还开凿了多处道教石窟,使山西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区域之一。
宋元时期山西宗教呈现南佛北道的格局,佛道二教与当地民间信仰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尤其是道教对民间神祇的吸纳和融合相当普遍。以晋东南的二仙信仰为例,兴起时间在唐末左右,二仙所供奉的是晋代乐氏二姐妹。相传乐氏姐妹的生母早故,遭受继母虐待仰天痛哭,其哭声传至天神,降下黄龙,两姐妹乘龙升天,遂成仙女。二人在成仙后关心民间疾苦,有求必应,晋东南一带极为崇信,遂建庙祀之。至宋元时期,二仙与道教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宋徽宗曾封二仙为真人,真宗时期二仙再度被推崇并赋予道教形象,二仙的身份在官府认证为道教女仙。二仙通过其道教身份,获得正祀地位,道教又通过吸纳二仙获得更广大的信众。尽管道教对二仙信仰的改造始终不彻底,道士以及道教信徒还是通过重塑二仙形象、赐封道教名号、推行道教仪式等手段影响着二仙信仰。(12)[10]
也有许多民间信仰经历千年,本来已经香火寥落,庙宇残破,由于与宗教的融合才得以继续留存。上文提到的窦大夫祠在晚明时已十分破败,据明万历年间的《保宁寺养赡地亩碑记》说,一般寺庙都是“废者莫举,举者易圮,若烈石古庙是已,然特高僧世鲜故至此”,由此可知此时的英济侯庙破败不堪。这时有个叫邢海静的僧人募捐,“于烈石左建一寺,为古庙翼”。晋王府的宗人朱慎錭不仅给寺命名,而且用15两8钱银买了16亩地,“施为烈石庙保宁寺焚修之资”,意在以佛寺养窦大夫祠。(13)[8]在窦大夫祠原址的基础上又修建了保宁寺,保宁寺住持也就是窦大夫祠的管理者。窦大夫祠因保宁寺的建立而得以留存兴盛,也说明了佛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信仰的留存。
此种现象也并非个例,阳高县罗文皂镇许家园村的青云寺,当地又叫作胡老爷庙,庙内主殿供奉的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狐突,据当地百姓所言,原来是一座纯粹的道观,现今已成为一座佛寺,寺内有住持及僧人,同时供奉有佛、道及狐突三类神灵。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在发展过程中共生共存,相互吸纳融合,在当地乡村社会中共同扮演了神圣的角色。
从现存的寺庙景观的状况来看,山西许多建筑都呈现出不同朝代的建筑和不同的信仰叠加在同一空间内的情况,通过对寺庙进行时空剖面分析,可以看出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不同信仰与地方社会互动角力的过程。
五、结语
三晋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信仰,信仰的发展又孕育了这块黄土地上的人们对自然和祖先的敬畏之情、敬仰之意,以及对道德、良知的尊重和推崇。山西民间信仰的出现时间极早,留存时间极长,经历朝代更迭以及民国以来近代化的冲击,总体变化一直相对较小。民间信仰所体现出的强烈的地域特征是地方社会与民风民俗的代表,也是地理环境影响下百姓诉求的体现。《汉书·地理志》讲到“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4)[1]所谓“水土之风气”,正是自然地理环境带来的具有区域性质的民风特点,而“随君上之情欲”,《汉书·地理志》中将一地风俗的形成归咎于古帝王德行与治民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探究山西大量古帝王祠祀留存与其地风俗的重要因素。我国民间信仰的显著特点就是极具功利性,但凡所求灵应、能庇佑一方的神祇,民众都会通过建庙立祠、修筑金身等方式进行回馈,而地方官员为更好地管理民政也会对地方神祇进行祭拜、组织修缮,国家也会对这些信仰人物进行封赐。除了社会方面外,信仰的地理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封闭在各个区域的信仰留存,独特的历史地位又产生了独属山西的民间信仰,其干旱少雨的气候,又造成了神灵职能的转换。在多个层级与地理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古老信仰得以留存至今,并形成区域性的特征差异,对于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及山西区域文化提供了极好的资料。
注释:
①李洪峰.历史学读书笔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05):287.
②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二十八下,一六四八页.
③李会智.山西元以前木构建筑分布及区域特征[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01):1.
④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56.
⑤郜俊斌.宋以降崔府君信仰的塑造、传播与本土化:以山西为中心[D].广西师范大学,2012:8.
⑥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二十八下,一六五六页.
⑦康熙《山西通志》卷9,“祠祀”,第7页上.
⑧道光《阳曲县志》卷8.“礼书”,第29页上.
⑨史纯:《英济侯祷雨感应碑记》,载道光《阳曲县志》卷15,“文征上”,第41页下-42页上.
⑩赵世瑜.从贤人到水神:晋南与太原的区域演变与长程历史[J].社会科学,2011(2):3.
(11)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M].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198.
(12)易素梅.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J].学术研究,2011(7):3.
(13)赵世瑜.从贤人到水神:晋南与太原的区域演变与长程历史[J].社会科学,2011(2).
(14)班固.汉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二十八下,一六四〇页.